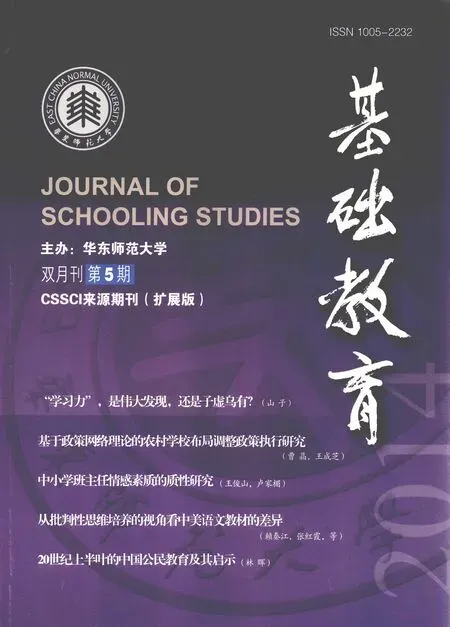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公民教育及其启示
林晖
(1.复旦大学 教育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公民教育及其启示
林晖1,2
(1.复旦大学 教育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2.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中国的公民教育发轫于清末民初。无论是公民教育理念的引入,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还是公民教育的实践探索,都受到那个时代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和启蒙维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诉求也从总体上强化了公民教育的政治性维度,而公民教育本应具有的文化维度、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则相对弱化。面对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的时代状况,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及遭遇到的困境的反思,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探索中国式公民教育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公民教育思想; 公民教育实践;政治维度;国族意识
对于个体价值的确认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文明精神特质的某种价值核心。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基本身份是公民。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确立,现代公民教育成为联结个体、群体、民族与国家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现代公民教育本身的发展演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发端于清末民初,肇始于中华文明新旧嬗变的历史性关口;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和革故鼎新的社会运动构成了中国早期公民教育的基本社会历史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之后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一个多世纪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公民教育经历了一个由兴到盛,由盛到衰的过程。今天,已经卷入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和大规模转型的阶段,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当下中国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不断迫使我们返回到教育这一培植社会文化的自然土壤上来思考下面这些问题:如何安顿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鼓励个体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又不至丧失社会文化认同感;如何在构建社会文化认同的同时,以积极的态度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和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责任;如何将传承文化传统与推进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落实在每个个体身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公民教育将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现代中国公民教育所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和反思,特别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公民教育所走过的特有发展路径的考察,将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公民教育,为我们推动中国公民教育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公民教育思想的发轫
在中国,“公民”一词古已有之。但“公”的传统,主要是指相对于“私”而言的“公”。比如《韩非子·五蠹》中所说的“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1]这里所说的“公民”是指为公之民,其含义显然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更有别于现代个体意义上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模式是以儒家伦理为价值核心,围绕科举制展开的养士教育,并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在西方历史上的诞生,与中世纪后期以来的城市自治、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扩张、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宪政体制的确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始于清末民初,但是这种传播的动机却完全不同于其发源地。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图强意识,构成了中国早期公民意识、公民理念以及公民教育的引入和传播的历史背景。“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2]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科技、制度和文化的引入,大体上是沿着先注重实用技艺,而后逐步注意科技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再关注到制度背后的相关文化学术根基这样的次序进行的,可以说大致经过了“言技”“言政”和“言学”的发展阶段。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被引入到中国并逐步传播开来的。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中国的许多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看到,要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除了围绕政体的改良、革命等一系列举措之外,还必须从教育民众这一根本处着手。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公共意识和国家意识,培养新民,成为了那一时期新教育思想的主旨。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提出了三育救国论: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并且将“新民德”置于核心的位置。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在伦理道德领域引入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主张,替代中国传统宗法,进而培养具备独立人格、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的新国民。1902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公民自治篇》指出:“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哉。”[3]
1902年至1906年期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也将培养新民作为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培养和塑造新民的最终目的是要重塑民族、重塑国家。梁启超认为,良好的国家社会是由具备了良好私德和良好公德的个体国民所组成的,就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各国之林而言,更为缺乏的是公德而非私德,而公德正是凝聚国家与社会的基础。因此,在新民的塑造中,梁启超尤其强调公德的一面。当然,梁启超的所谓“新民”,其义除了公德之外,还包含权利、义务、进取心、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要素。而对于所谓的“新”,他特别强调,除了是指从西方文化中吸收中国所不具备的积极因素之外,也指提取原本就蕴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4]3。可惜的是,在现实历史环境的催迫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救亡强国意识的导向之下,中国公民教育之后数十年的发展,却并未如梁启超所构想的那样做到兼取中西古今。
在民国早期公民教育的发展中,不少杰出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的“五育并举”和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的教育主张。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随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所谓五育,指的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强调,公民道德教育应该成为五育的核心:“五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教育,则必以道德为根本。”[5]而公民道德,则是建立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之上的。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公民道德的教育是民族自强和国家进步的根本。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在乡村推广平民教育期间,针对民众“愚、穷、弱、私”的现状提出了“四大教育”的思想。四大教育,指的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于培养知识力以克服“愚”,生计教育在于培养生产力以摆脱“穷”,卫生教育在于培养健康力以解决“弱”,而公民教育则在于培养团结力以克服“私”。在晏阳初看来,一方面,公民教育是指四大教育之一,包括了公民常识教育、农村自治研究和国族精神培养;另一方面,公民教育又是指广义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不单单指普通所谓公民科和公民训练说,也是什么生计教育、科学教育、卫生教育,都应该包括在内”[6]。当然,通过这种公民教育而培养新民的目的,仍然是指向了强化其心目中的共和政治,以期救亡图强。
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公民教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还包括一些国外的教育家的相关理论。比如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的公民教育思想[7]和杜威(Dewey)的公民教育理论[8]。总体而言,现代公民教育思想在清末民初的引入、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中国公民教育实践的开展。而这种公民教育实践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前者的不足和欠缺。
二、公民教育实践的演进
1905年,清廷颁布诏令废除了在中国施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在此前后,各地出现了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自1907年至1909年短短2年间,主要由地方绅士和进步知识分子所兴办的学堂数量从3万多所增至5万多所[9];自1902年至1907年,在校学生人数从6千余人猛增至近160万人[10]。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都构成了现代公民教育在中国实施和推进的重要前提。
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的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大致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方面存在着以政府教育政策为主导和以学校教育为实施主体的公民教育;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由部分教育改革的实践者所倡导和由社会教育为特色的公民教育。可以说,在对于中国公民教育的推进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廷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11],规定在蒙学、小学堂和中学堂开设修身和读经二科,其中以修身科为第一科,立足“中体西用”,主张将传统的忠孝伦常与适应时代的经世致用的知识以及救亡图存的理念相结合。正是借助了修身科,清末民初的公民教育才逐步正式地进入了课堂。
中华民国成立后,修身科被保留了下来,但更加强调了培养国家观念和义务观念,比如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倡导“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12]。1916年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则具体规定了要在修身科中讲授公民须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仅凭修身科已无法满足对于越来越多的公民教育内容的要求。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决议,建议编写公民课本。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了《改中小学修身科为公民科》决议案。1923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取消中小学的修身课,归并入公民科。《新学制小学学制纲要草案》对此作了说明:“修身科注重个人修养;公民科则重在研究社会环境状况。”[13]公民科取代修身科,既标志着公民科作为独立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确立,也标志着学校正规公民教育的确立和开展。
1924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织,在全国范围发起了公民教育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公民教育运动的宣言及计划》中提出,每个公民个体未能尽到社会、民族和国家责任,是造成当下国家和民族危局的根源之一,公民教育运动的宗旨就在于培养公民观念,普及公民知识;并由此提出了提倡爱国心、促醒公民责任、养成公民人格、研究国家组织及法律、讨论重大问题等五项内容。[14]江苏省教育会则提出了发展自制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履行法定义务和培养国际同情等八项规定。从1924年到1928年,这一全国性公民教育运动连续举行了五届,形式包括组织公民宣讲队、公民研究团、公民训练会、公民学校、展览会,无论规模和影响都前所未有,形成了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一个高峰。
此外,20世纪20至30年代,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实践也走上了一条探索本土化模式的道路,并且走出了学校,走向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特别是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先后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在这些探索中,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最具代表性。[15]从1926年到1937年,在晏阳初的推动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从城市拓展到了乡村,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始了平民教育实验。这一教育实验除了进行国族精神和公民知识的教育之外,尤其强调通过乡村自治来实践公民教育。在晏阳初看来,中国有着悠久的乡村自治传统,平民教育的工作是要结合这一自治传统,并通过扫盲、普及公民常识和培养国族精神等措施,将基层民众培养成对于社会和国家有高度认同感、能够自觉承担公民义务的人。30年代初,梁漱溟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办乡村学校进行教育实验。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化根基的衰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改造文化以实现民族自救。中国本就是一个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国家,目下的乡村还多少保留着传统伦理的风气,因此要实施文化改造和教育以培育新公民和实现民族自救,就应该从乡村着手。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阶段。受此影响,与民国前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公民教育更加受政府主导和制约,更加突出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更加突出了公民训练中的战时教育内容。比如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青年训练大纲》、1940年颁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以及1944年制定的《国民学校法》,等等。事实上,由知识精英所倡导的以公民教育为基础构建地方自治的理想政治的主张,与国民政府所强调的通过国民教育强化地方管控和政治统一性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互抵触的。长期的全国性战争和战争动员的客观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国民政府以战时教育主导公民教育的立场。中国的公民教育从民国初年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了40年代末已归为一片沉寂。
三、历史局限及其启示
在中华文明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救亡图存、启蒙维新的时代精神以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背景,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公民教育走的是一条借鉴西方、探索本土化、学校与社会共同发展、突出强化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的公民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上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就历史局限性的角度而言,中国公民教育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遭遇到了种种难题,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某种历史困境。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历史性困境,是因为这种困境本身是内在的,是由这个特定时代的基本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动力所导致的;换言之,救亡图存和启蒙维新既构成了特定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促成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构成了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樊篱,限制了中国公民教育进一步走向成熟。
成熟的公民教育应该包含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等多重维度,由此而培养成就的公民才可能是成熟的现代公民。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则在较大程度上偏重于突出政治主题,而在文化主题、社会主题和历史主题等方面显得较弱。
首先,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在整体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偏重于强调这种教育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功用,而对于公民教育本应包摄的文化意涵和文化价值却并未能深入发掘,甚至常常在具体的教育纲领或教育实践中使得这些文化意涵和价值过多地依附于其政治意涵以及政治功用。比如公民教育中涉及普及知识、规范语言、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多数也是以强化国族意识和巩固共和政体等理念为目标和主导。
其次,即便是在强调公民教育的政治维度的时候,也主要是以强调政治维度中的国族认同和政体认同为主;相反,对于公民个体的自我认同始终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究和教育实践。这便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偏于强调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而对于公民个体权利却缺乏深入的探究和有力的确认。
再次,革故鼎新的启蒙意识和求新求变的时代精神,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在积极引入西方公民教育理论,积极借鉴西方公民教育经验和积极推广西方公民教育模式的同时,却对于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萃取有益要素有所忽视。尽管也存在着不少公民教育本土化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并未能在深入历史和继承传统的维度上更进一步。按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说法,多趋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而罕有“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4]7
最后,拯救民族危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更倾向于将公民教育看作是达成上述政治目标的工具与利器。在这种对于公民教育的过于工具化和狭隘化的理解之下,对于“新民”的培养目标也过于强调其中的国家主题和政治认同主题,“公民—国家”模式便是这种构想下所能展望的理想模式。而这种“公民—国家”的模式,实质上仍旧偏于突出其中的政治性维度,弱化了公民教育本应具有的社会性维度、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
1949年之后,中国的公民教育再次经历起伏。1982年,我国宪法修改草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中学德育大纲》;2001年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则强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尽管这些举措标志着公民教育理念在当代中国逐步得到明确和强调,但在具体实施的学校教育中仍然普遍存在简单地以德育代替公民教育的现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体系尚待完备。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政治互动、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环境、食品以及安全等问题的突显,使得全球性公共空间领域不断扩展。传统的公民身份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遭受了重大挑战。局限于民族国家或单一文明认同的公民理念,不得不面对日益多元化和流动化的世界。多元化和超国家层次的公民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传统公民教育的危机、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迫近以及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这些都构成了对于当前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挑战,同时也构成了推动当前中国公民教育建设的有利契机。中国式公民教育的发展将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一个确切并实在的落脚点。这样一种公民教育,并非仅仅是提供一套培养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主体的知识体系,还包括这种参与活动的培养本身。如此,公民教育才能真正化知识为德性,培养公民个体意识、塑造公民集体认同、建立公民普遍价值观。换言之,这种公民教育,应立足于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尊重文明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并且最终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性目标。
[1]陈奇猷.韩非子(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04-1120.
[2]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8.
[3]康有为.公民自治篇[N].新民丛报,1902-04-08(05).
[4]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3.
[6]晏阳初全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83.
[7]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8]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9]檀传宝,等.公民教育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3-124
[1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93-369.
[1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32-551.
[1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94.
[13]新学制小学学制纲要草案[J].教育杂志,1923(15): 38.
[14]黄文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运动(1923-1930)[J]甘肃社会科学,2010(06): 157.
[15]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0-176.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thCentury
LIN Hui1,2
(1. Institute of Philisophy of Educ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2.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China began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The keen consciousness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the subju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s in that era deeply influenc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dea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urgent appeal for building modern nation-state had strengthene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general,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social dimension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were relatively weakened. In the face of the coexist condition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dilemma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to a certain extent, will provid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explore Chinese citizenship education model.
though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political dimens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G40-021.9
A
10.3969/j.issn.1005-2232.2014.05.013
(责任编辑:张国霖,朱振环)
(责任校对:姚琳,朱振环)
2014-08-2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事实与价值”(B10004);复旦大学“985三期”项目“启蒙时代政治现代性的多元审视”(2011RWXKZD015)。
林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教育哲学研究中心主任。E-mail:huilin@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