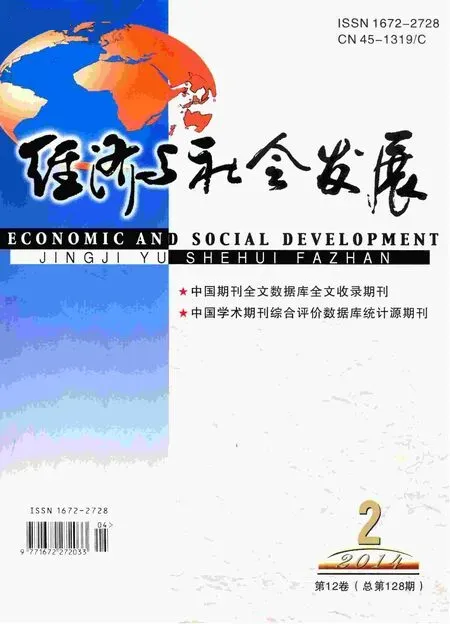苏轼出川前的道家因缘初探
司 聃
苏轼是北宋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等身,博采众家思想之长,形成了自己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哲学思想体系。学界普遍认为,苏轼作为一个儒家传统的士大夫,佛道二家思想共同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因苏轼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禅佛酬赠诗,且终身与参寥法师道潜、了元法师佛印、芝上人昙秀等几位高僧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故学界对苏轼的佛教因缘和禅佛诗文的研究颇多。相较之下,关于苏轼与道教的研究略显冷清,且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苏轼文艺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等方面,较少谈及苏轼早年的道家因缘问题。
苏轼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至嘉祐元年(1056年)进京赶考首次出川,居眉州长达十九载;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但母亲程夫人于当年四月亡故,故回眉州丁忧,嘉祐四年(1059年)再赴汴京。累计起来,苏轼在故乡眉州的时间共计二十二年之久,其出川前所受的教化与际遇对他之后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了解苏轼出川前的道家因缘,有助于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研究。
一、地域因缘
苏轼终身都与道教保持一种亲近感,这和故乡眉州的宗教气氛不无关系。眉州位于蜀地西南,相比中原,蜀地有其特殊的文化。蜀地多山水,巫风很盛,传古蜀王皆得道成仙:《蜀志》云:“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蜀人思之,为立祠,今庙祀之于湔。 ”[1](P2)又《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从,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2](P123)蚕丛及鱼凫都是蜀国先王,据文中所载,鱼凫于湔山打猎时得道成仙,而三代蜀王都长命不死,追随者亦成仙,可见蜀人对长生不死神仙术的向往。
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无疑与蜀地的神仙文化相契合。也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道教社团五斗米道便创立于蜀地,汉顺帝时(约130年)沛人张陵入蜀修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具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3](P190)。 蜀人纯厚可教化、蜀地多山川,是张道陵选择入蜀修道的两个原因,蜀人“易可教化”是因为此地本就有求仙传统,既然有上古时期三代蜀王的追随者都成仙的例子,蜀地之人自然更容易对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产生信赖;“具多名山”则表明蜀地有仙境,大凡修道,必然要选择清静幽僻之地,多山川的蜀地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人文环境上来说,都是修道的不二选择。后张道陵在鹤鸣山著道书24篇,汉安元年(142年)正式传道。
唐朝时道教为国教,蜀地亦为传道重镇。当时共28家奉旨注疏《道德经》,而蜀地便有6家,同时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晚唐五代,前蜀二主王建、王衍崇道已入痴迷境,赐号道士杜光庭“传真天师”,举止做道人打扮,“帝谒永陵,自为夹巾,或裹尖巾,其状如锥”、“妃嫔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皇帝妃嫔尚如此,自然“民庶皆效之”[4](P737)。可见蜀地修道求仙之风的盛行。故乡厚重的求仙修道氛围无疑影响了苏轼,苏轼一生都渴慕着能够得道成仙、长生不死,诗文中也多有“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之类的句子,晚年被贬琼海时,仍旧幻想“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二、时代因缘
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7年),时仁宗皇帝亲政。虽“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5](P745),但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则更受尊崇礼遇。
北宋崇道之风颇盛,细归纳有两点原因:一是沿袭前朝的传统,唐朝立道教为国教,将道教视为“本朝家教”,或云“皇族宗教”,对其扶植不遗余力。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统治者也对道教推崇备至,包括前朝的周世宗。周世宗虽大肆废佛,但却崇奉道教、优待道士。北宋接后周而建,自然也受到前朝的种种影响。二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为求江山基业千秋万代,往往要依托某宗教圣贤,以期将自己家族神化,巩固皇权。如唐王朝的统治者姓李,便声称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因此,立道教为国教,旨在显示出自己皇权的神圣性。北宋崇道亦是出于这种目的,宋真宗以《易传》中“以神道设教”为理论依据,设计出“天书降”事件,言梦中见神人告诉自己“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并将此事定义为“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6](P1069)。
为答谢天帝的频降天书之举,宋真宗大建道观,其中玉清昭应宫的耗资与规模均在宋朝首屈一指,此外,真宗下令各地建造天庆观,以感恩天帝降书。苏轼幼年随道士张易简就读于道观天庆观,倅杭时期也曾去杭州天庆观饮茶赋诗,此二观皆名天庆观,明显带有真宗朝的色彩。
真宗朝对道教的推崇,一时无二,掀起了北宋第一波崇道之风潮。真宗大建道观,普度道士,组织整理道教典籍,编撰道教神迹,使道教作为一种经由官方认定的国教在全国推广普及开来。宋真宗推行道教并非是出于纯粹的信仰,只不过是借着种种神迹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使民间崇道之风弥漫,道教地位凸显于儒释道三教之中。
宋仁宗即位后认识到真宗朝的崇道之风甚笃,使儒释道三教相互之间无法平衡制约,于是调整了政策,从减少道场数量、减少醮祭数量与规模、降低宫观诸种规模等方面着手,为前朝的崇道降温。但与此同时,他依然将道教尊为国教,建造西太一宫与西京会圣宫等宫观,且与龙虎山、云台山道士有所往来。
可以说,苏轼少年时便处在一个有很深崇道氛围的年代,宋朝时蜀地也是崇道重镇,时人曾有“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6](P1581)的论断,可见即使在举国崇道的北宋,蜀地人依旧称得上有崇道根基。
三、出生因缘
苏轼出生即与道家有着不解之缘,苏洵曾为求子而拜张仙:
洵自少豪放,尝于天圣庚午(1030年)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乃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7](P416)。
张仙是眉州人,《眉山县志》中有注:“张仙,指唐眉山人张远霄,曾师事陆修静,后居邛崃崇真观,观中有石刻像,相传有求嗣者,祷之则应。”在后世的传说中,张仙又称送子张仙,属道教神仙谱系中能赐人子嗣的男性神衹。求子的这段经历虽看似带有神话色彩,却是真实事件,苏洵与程夫人婚后久无子嗣,因而虔心求仙,后生了苏轼、苏辙两位大才子,从苏洵的字里行间中便可看出慰藉与欣喜之情。苏洵既然会将这段神奇经历写在文中,必然也曾当面告知过苏轼,一个人知道自己出生时的神迹之后,便很难不存留一定的心理暗示与自我暗示。
四、读书因缘
苏轼在《上韩魏公梅直讲书》中自述“自七八岁知读书”,与弟弟苏辙“皆师先君”,即跟随苏洵读书学习。另《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其真正入校读书的年龄为八岁,启蒙教师为眉山道士张易简。从庆历三年(1043年)到庆历五年(1045年),苏轼都跟随张道士读书。
张易简所居道观名为天庆观,上文所言真宗为感天帝降书,举国兴建天庆观,同时,亦将一批已有道观改名天庆观,眉山的天庆观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张易简是苏轼的启蒙老师,而当时的学堂便设在天庆观。50余年后的绍圣五年(1098年),苏轼谪居岭南,时广州城西有一道观原名玄妙观,真宗大中祥符间亦改名天庆观,观内有堂名众妙堂,苏轼游广州天庆观,忆起幼年时在眉州天庆观读书的事情,作《众妙堂记》一文: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
此文是苏轼晚年所作,具体创作时间应为绍圣五年三月十五日,其时年六十一岁①此文落款有两个版本,一为“绍圣六年三月十五日”,一为“戊寅三月十五日”。绍圣为北宋哲宗的年号,此年号只使用了五年(公元1094-1098年),故采信后者。。虽已是逾耳顺之年的老人,却依然难忘幼年时传道授业的恩师张道士,在梦里重回当年的天庆观北极院,虽然此时自己已成了“老先生”,而昔日的老师张道士还“如平昔”,与他坐而论道,讨论种种哲理问题。可见当年三载读书生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张道人亦是让他几十年不见仍记忆犹新。
张易简既是道士,教授童子时便免不了以道家思想相授。《众庙堂记》所描述的梦境中,当年龆龀孩童已成老先生,与昔日的启蒙老师共同探讨艺术与技巧的关系。二人的问答中带有明显的道家哲学色彩,先用《老子》语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8](P53)做楔子,各自阐发对“玄”、“妙”的解读,进而引发出对“技与道”的探讨,而文章结尾从梦境转入现实,原来此天庆观非彼天庆观,是广州崇道大师何道士“学道至于妙者,自命其堂为众妙堂”。从梦境到现实,从幼童到老叟,皆与道教息息相关。
不光启蒙老师张易简是道士,和苏轼同在天庆观学习生活三载的同窗陈太初后来也成了道士。苏轼后在《道士张易简》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陈太初尸解的奇幻过程:
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予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有得道者曰陈太初。”问其详,则吾与同学者也。前年,惟忠又见予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使卒异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异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干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此文作于苏轼黄州任上。当年陈太初与苏轼都拜张易简为师,几百弟子中,也唯独陈太初与苏轼被老师交口称赞,“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可见陈太初亦是天资聪慧,苏轼几十年后回忆,仍旧有惺惺相惜之情。后苏轼出川参加科举,继而仕宦,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眉山道士陆惟忠来探,告陈太初道成尸解之事。道教认为得道之人可以舍弃肉体而登往仙界,或不留肉体而升天。陈太初之所以日后可成得道之人,大概与眉山崇道气氛有所关联,或也受授业恩师张易简影响。苏轼在文中记录了陈太初尸解,用精准简练的文字营造出陈太初聪颖豁达、与世无争的形象,使读者观其文就可感受到太初仙气萦绕,而从苏轼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他对昔日同窗得道归仙的艳羡与崇拜。
苏轼对得道之人尊崇已非成年后经验积淀的自然选择,而是幼时便已有之。《眉州属志》记载:“矮道士李伯祥,州人,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东坡尚幼,一见叹曰:‘此郎君,贵人也’。”[9](P178)此事亦见苏轼《题李伯祥诗》:“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一偶出奇语的老道见幼年苏轼便赞叹此郎君为贵人,不仅说明苏轼天资聪慧,更显示出了苏轼与道人之间的亲近之感。
五、天性近道
一个人成年后的倾向,往往在其年幼时便有所流露,此之所谓天性。苏轼第二次外任杭州时,作《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一诗,中有“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一句,后悔自己没有顺从少年时的心愿去甘贫守道,而是出川求仕,从此被限于一格局狭小之境地。从现有史料来看,章传道其人已不可考,仅仅知道其为“闽人”,但从他的名字和与苏轼的唱和诗推测,章传道即使不是个道士,也一定是个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苏轼在守杭期间与章传道屡屡相会,此诗即是与其的酬唱诗,诗文甚长,可见苏轼少年时怀有修道之心,在诗中向章传道一吐胸臆。此外,苏轼元祐时期所作《跋李伯时卜居图》也可辅证:
定国求余为写杜子美《寄赞上人诗》,且令李伯时图其事,盖有归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
所谓丘壑,历来解释不同,此处可做隐逸理解,类似南朝谢灵运《斋中读书》中“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10](P1186)之意。苏轼言自己少年便想隐逸山水田园,应该是对元祐时期的党争纷扰厌恶透顶,恨不能遂少年心愿隐逸。李伯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与苏轼素来交好;王定国更是苏轼挚友,曾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此诗虽为题画诗,实是赠两位挚友,所言自然是真实心声。
晚年苏轼谪居琼海,曾在《与刘宜翁使君书》谈到少时的心愿:“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追”,此文是苏轼被贬惠州时所作。刘宜翁是苏轼尊崇的道士,颇懂养生之术,苏轼对其尊崇有加,在诗中盛情邀请其来游玩,最后竟然以“则小人当奉杖履以从矣”结尾。虽是谦辞,但谦卑的程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谦辞,想苏轼一介文豪,天下无人不识,居然屈尊到如此地步,可见刘宜翁在苏轼心中的重要地位。所谓龆龀,指垂髫换齿之时,也指代儿童或年幼时期。苏轼说自己幼年即崇道并非刻意讨好刘宜翁,在其它诗文中也有过类似追述,如《与王庠书》:“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此书亦是其贬谪岭南时所写,王庠是苏轼的同乡兼晚辈,娶苏轼侄女为妻,苏轼称其为 “姻亲”,在给黄庭坚的信中称“有侄婿王郎”。苏轼在给姻亲小辈的信中回忆往事,所说的自然是肺腑之言,可见“龆龀好道”之说不虚。
由此可知,苏轼在杭州任内、元祐年间、岭海时期都写过关于年少时欲隐居山林学道内容的诗句,苏轼在海南时,于垂老之年称自己 “龆龀好道”,便是对自己少年时思想倾向的一个总结,他幼年在道观读书、启蒙恩师即是道人、同窗陈太初成年后也得道成仙,苏轼长期在眉州这种充满道教氛围的环境下生活,对道教有种亲近之感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这也便不难了解为何苏轼对修道求仙的热爱终极一生,视道家为其精神上的桃花源了。
[1]王文才,王炎.蜀志类钞[M].成都:巴蜀书社,2010.
[2](宋)李昉.太平御览:第八册卷八百八十八[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晋)葛洪.神仙传校释·张道陵[M].胡守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后主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宋)苏洵.嘉祐集笺注:卷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老子.老子注释及评介[M].陈鼓应,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9]中国方志集成·四川府志辑:第39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