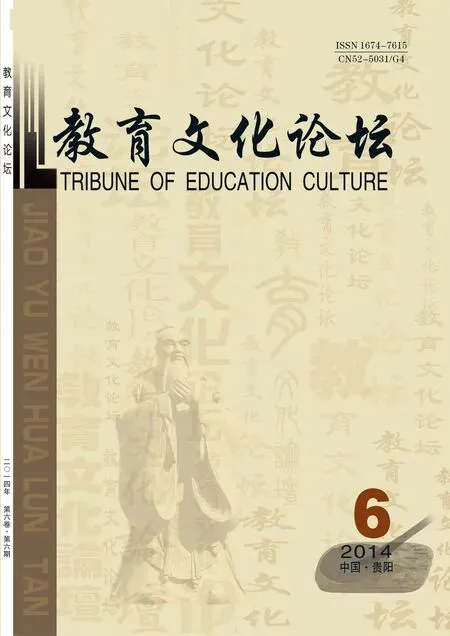村庄里走出去的文化人
——谨以此文纪念本刊最尊敬的已故学术顾问刁培萼教授
刁维国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苏中里下河“刁舍村”刁姓家族的来源
苏中里下河*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总面积13500余平方公里,属江苏省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平原介于这两条河道之间,故称里下河平原即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区主要有东台、兴化、高邮、大丰、江都、泰州、盐城、淮安、建湖、宝应、阜宁等城市。刁舍村的“刁氏宗支第一代耀先公行列三房(即弟兄排行老三),约公元1780年左右(清代乾隆年间),距今约200多年前,因灾变[變]从苏州阊门迁移于今泰州姜堰以北居住。其时地广人稀,插草为标,因而定地名曰刁家舍。”*刁焕国等.刁氏族谱及刁氏宗支图表[B].家族档案.刁焕国口述;刁庆辉,刁庆玺等记录、整理并制作图表。“其大房(刁耀)同时迁居今通扬运河姜堰段北岸刁家桥和刁家岱附近;二房(刁耀 )定居于河横村(今沈高镇河横村)。”*耀先公的两个哥哥即老大和老二的名讳失考.记录于本村《刁氏族谱》《刁氏宗支图表》前言部分的这段文字,为我们弄清“刁家舍”刁姓家族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刁家舍”的村名一直延用到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期间农村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人民公社时期,将原来的“刁家舍”改名为“五一大队”。村名一直延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记得“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的个人履历表中填写的村名还是“五一大队”。但就在我尚在南师读本科期间,原来“五一”大队的村名已经改为“刁舍村”。“刁舍村”的村名延用到上个世纪末。跨世纪期间,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精简农村基层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取消“刁舍村”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立建制,因此“刁舍村”的留守村民划归村西边的“夹河村”管辖。因此,我的老家“刁舍村”渐渐成了“远逝的村庄”。虽然“刁舍村”作为独立的农村基层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但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及不同历史时期从“刁舍村”走出去的人,都习惯于将自己的老家说成是“刁家舍”或“刁舍村”。这不仅是一种怀旧心理和历史记忆,更是一种寻根情结和一种家族文化情怀。
清末及民国时期,村庄里走出去的文化人
如前所述,原籍苏州阊门的刁耀先(家中排行老三)因洪灾迁居位于江北的苏中里下河地区。因此,刁耀先就是刁舍村的始祖。第二代刁之贤,是刁耀先的独子(即弟兄一人),他是刁舍村第二代传人。第三代弟兄四人:老大刁万言,老二刁万进,老三刁万树,老四刁万宏。这弟兄四人所组成的家庭,后称“老四房”。自此以后,刁舍村刁姓家族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归属于这四房中某一房的名下,即从始祖刁耀先、二祖刁之贤那里,形成四个分支家族。随着家族史的延续,分支家族的增生,家族成员越来越多。清末及民国时期,近现代学制的建立,重教尚文的村风、民风的滋生,村庄家族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人开始出现。
如果说刁耀先是本村刁氏宗支第一代的话,那么到我爷爷辈已经是本村刁氏宗支第六代传人了。我爷爷也是弟兄四人:老大刁同义,老二刁同禄(我爷爷),老三刁同会,老四刁同旺。他们弟兄四人都是农家子弟,但在家庭事务中还是有分工的。老大掌管家庭中的豆腐坊,产品既供给家庭成员,也作为商品卖给其他村民;老二专门陪同伙计下田干重体力活——罱泥、挑粪、施肥。由于皮肤黑又常年干重体力活,受阳光照射时间长,村民们都称他“黑二爹”。老三掌管家庭中耕作事务,负责耕田、放牛、看风车;老四掌管家庭中的“外交”事务,经常外出购物,帮助村民“说事打卦”,调解纠纷。
我爷爷这弟兄四人都不识字,他们仅是“老二房”中一个分支的传人。“老二房”中另一分支的传人刁同经,据说是本村刁氏宗族较早的文化人,他不仅能识字,帮助村民说事打卦,而且还是“同贤社”的地方负责人,人称“经爹”,其影响达周边几个村庄。听我父母讲,他(她)俩是姨表兄、姨表妹结婚。婚后多年无子。盼子心切,他(她)俩就请当时家族中的文化人“经爹”预先取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这就是我的名字“维国”的由来。我父母婚后十年,才生我大姐,又过三年,生我二姐,再过七年才生我。我出生时,父亲40岁,母亲38岁。可能由于“同贤社”的政治倾向问题,在新旧国家政权交替之际,“经爹”作为地方“道会门”的骨干成员被新政权地方武装请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在本地刁氏族村民心目中,他可是本村的“圣人”和“善人”。也就是说,当年应我父母之邀给我取名字的那个前辈长者在我出生时,他早已经走出这个渲闹的世界了。
本村刁姓家族第七代传人刁焕国,被村民们看成是民国时期“刁家舍”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本村刁姓家族文化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生,人称“国大先生”。解放前上的是暨南大学,解放后被安排在泰兴的一所中学任教直至退休。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泰州学院的前身泰州师范学校任教。学校里有一位生物学女教师高郊,她的妈妈刁焕兰与刁焕国兄妹俩都是本村较早走出村庄的文化人,刁焕兰在解放后是泰州城里一所小学的校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早已退休在家,时龄89岁的刁焕国老先生,口述本村刁姓家谱。本村刁姓家族第八代传人刁庆辉(时任泰州炼油厂厂长)、刁庆玺(时任泰州二布厂图纸设计员)将刁焕国老先生口述的家谱记录、整理并印制成刁舍村《刁氏族谱》和《刁氏宗支图表》,*本村《刁姓家谱》有几个版本,笔者首选这个版本。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第一手材料。与刁焕国相近宗支的另一传人刁焕墀,也是解放前走出村庄的大学生,解放后被安排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直至退休。本村刁姓家族第七代传人中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刁焕家,民国时期曾任泰州某区的区长,解放后也被新政权地方武装送到另一个世界了;还有一个是刁焕彩,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远走香港定居直到去世。不过他的儿女仍然留在大陆。他有一个孙子叫刁龙(本村刁姓家族第九代孙),是现在泰州学院的青年教师。
上述行文中所提到的刁同义、刁同禄、刁同会、刁同旺、刁同经等,在本村《刁氏族谱》《刁氏宗支图表》上,都是“老四房”中“老二房”这一分支家族的传人,纵向看他们是本村刁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而刁焕国、刁焕兰兄妹俩(其父刁怀德);刁焕家、刁焕墀兄弟俩(其父刁怀义);刁焕彩(其父刁怀道)等,都是“老四房”中“老大房”这一分支家族的传人,纵向看他们是本村刁姓家族的第七代传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村庄里走出去的文化人
2014年春学期开学前,我在浏览网页搜索备课信息时惊悉:我崇敬的长辈和恩师刁培萼教授已经于2014年1月8日与世长辞。
笔者作为刁舍村刁氏家族的第八代传人,刁培萼教授是我的前辈。据本村《刁氏族谱》《刁氏宗支图表》,刁培萼教授和他的两个嫡兄长刁培庵、刁培芬是“老四房”中“老二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纵向看他们是本村刁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他们兄弟三人的父亲是本村刁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刁同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刁培萼教授的晚辈和族侄。
在本村刁氏家族文化史上,刁培萼教授是在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巨变时期走出村庄的读书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同辈人中能够走上读书求学的人生道路实属不易。如刁培萼教授的两位兄长、两位姐姐都终身务农;我的父辈是“老四房”中“老二房”另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他们也都终身务农。如,我的大伯刁培萫是家中的长子,很早就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我父亲刁培芊是家中的老二(人称“芊二爹”),虽然他曾经在村庄里的私塾先生(刁同书,本村刁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人称“小先生”)那里念过几年蒙学,但他这辈子也只能认识几个字,会背诵几句蒙学课文的短句而已。能够走出村庄接受新式教育的农家子弟,既要得到父兄的支持也要有着较好的蒙学基础。这样的年轻人,除了“老四房”中“老二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培萼外,还有比刁培萼教授年纪略小而又比我年纪略长的“老四房”中“老二房”另外几个分支家族的传人,纵向看应是本村刁姓家族的第八代传人的刁庆民(刁同经之孙)、刁兴国和刁兴美兄妹俩、刁维圣、刁维裕、刁维俊、刁维启、刁俊卿、刁俊康、刁仁(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以及第九代传人刁得志(海军上海基地医院);还有“老四房”中“老四房”的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雁宾(曾在省商业厅工作)和刁雁卿兄弟俩。
年轻的刁培萼走出村庄后,先是在江苏省泰州中学(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是这所学校1957年的毕业生)接受新式教育。就在新旧中国政权更替的历史巨变时期,青年刁培萼又走出泰州,到省城南京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建国以后本村家族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1953年,青年刁培萼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留校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从乡村文化青年到现代文化人的人生转变;在这里,他经历了“橡树”与“桃树”之恋*凯华.爸爸、妈妈生平简介[EB].刁培萼、吴也显纪念馆,http://cn.netor.com/m/box201307/m113713.asp;在这里,“他始终如一地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做终生学人,过布衣人生’。”*也显. 终身学人 布衣人生——培萼逝世百日祭[EB]. 刁培萼、吴也显纪念馆·留言,http://gbook.netor.com/gbook/mem_113713_5493296.html
笔者作为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首届毕业生,刁培萼教授是我的恩师。这不仅是因为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刁培萼教授是我的“马列论教育”和“教育哲学”等课程的授课老师,还因为自从1980年秋学期我在南师初见刁培萼教授和他的夫人吴也显教授(吴老师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教育学课程中教学论部分的授课老师)后,他(她)俩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以及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单位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勉励我勤奋学习和工作。
1980年秋学期开学之际,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到县城所在地姜堰去乘汽车前往南京,途经村南即将走出村庄的时候,遇见一位长者,他听说我要到省城读书,告诉我他有一个弟弟在南京师范学院教书,并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两个名字:“刁培萼”“吴也显”。这位长者是刁培萼教授的二哥刁培芬。他是本村同辈人心目中的“秀才”,属于本村有“天分”的人。初见刁老师和吴老师,刁老师那学者的风度、宏大的视野、跳跃的思维、深远的智慧,使我这个生性腼腆、不善言辞的乡下孩子敬佩不已。晚辈私下猜测,这也许正是形象文雅、谈吐不凡、素质全面、著名的教学论专家吴也显老师与他相伴到白发的精神因素。刁老师给我这个晚辈和学生的第一个赠言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995年暑期,作为师范学校的教育学科教师,我到省城接受继续教育,再见刁老师和吴老师,发现退休后的两位学者和老师与时俱进,使我这个年轻力壮的晚辈自感惭愧。记得当时他俩希望我在教师专业化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
2013年10月,我那在南师读研的儿子刁益虎有幸见到刁老师和吴老师。当他俩得知近年来我正因永别双亲(我父亲1998年病逝;我母亲2012年病逝)而一蹶不振时,刁老师和吴老师又以长者和哲人的智慧开导我走出丧亲心理的阴影,完成新时期赋予一名教育学科教师的使命。几天后,刁老师和吴老师又专门打电话给当时尚在南师读研的我儿子刁益虎,送给他几本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和教学论方面的著作。谁知刁培萼教授与我儿子刁益虎(既是族孙也是学孙)之间的这次见面竞成了永别!
如今,本村刁氏家族第七代传人,老二房中一个分支家族的刁培庵、刁培芬、刁培萼这三兄弟都已经远走天国;老二房中另一分支家族的刁培萫、刁培芊这兄弟俩也已经先后离开人间。作为本村刁氏家族第八代传人的我,笔者近年来陷入深深的哀思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村庄里走出去的文化人
笔者出生于1956年,1958年~1961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生的乡下孩子,对生他养他的父母双亲,对与他一起相依为命的兄弟姐妹,对他从小赖以生存的那个村庄而终将“远逝”的惆怅,以及对具有传统家族色彩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层的体验与念想。笔者从“刁培萼、吴也显纪念馆”中得知,2013年5月,吴也显教授还陪同刁培萼教授到姜堰老家看望刁培萼教授90岁高龄的三姐(接在刁老师二哥刁培芬之后排序)。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深有感触。由此联想到比我年长10岁的大姐,她小学毕业考取溱潼中学,但由于那时我父亲体弱多病,家中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劳动力。再加之客观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所以我大姐小学毕业后就成为家中的女劳动力,直至我上初中期间她远嫁外乡。1959年,我才3岁,父亲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在村支书刁洪亮、小队长刁维和等村、队领导的照顾下住进了公社的“营养食堂”才幸免饿死。当时大姐尚在读小学高年级,比我年长7岁的二姐到村小报道后上小学才几天就离开了学校,为的是回家帮助母亲分担家务,特别是为了照顾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等到我上小学后,二姐也成为家中的女劳动力,直到我上高中期间她远嫁浙江长兴的一个山区。
1974年秋,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975年至1979年,大队和小队领导安排我兼任生产队会计,进而与我的一位族兄“老四房”中“老二房”的传人刁维和(本村刁氏家族的八代孙)成了新老搭档。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周围是河的垛田里。我还是幼儿时,青年维和族兄带领农业社的劳动力到社员门户挑粪,看到还是幼儿的我,将我抱起来举过头顶。1975年我刚任生产队会计时满19岁,而此时维和族兄已经是生产队的老队长了。1975年,村庄推荐了一位张姓回乡知识青年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他的母亲是我们刁氏家族的姑奶奶。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1979年,本村 “老四房”中“老二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德东(本村刁氏家族九代孙)考取南京卫校;“老四房”中“老二房”另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益韶(本村刁氏家族九代孙女)考取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际,还是农民兼生产队会计的我,每逢听到广播里播报全国高校招生宣传提纲,就去请堂兄刁维裕(原来的中学数学教师,后调任相邻公社中心校任总帐会计)给我找一份高考复习提纲回来背诵一下去参加高考。到1979年时离录取分数线还差3分。我干脆辞掉生产队会计,到溱潼中学参加了几个月的高考复习班,终于在1980年考取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进而在1984年,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名从1984年启用)。从1974年高中毕业到1979年辞去生产队会计,去溱潼中学复习迎考,前后有五年的农民经历。在这期间,我与生产队的社员一起栽秧、割麦、罱泥、取渣、挑粪、施肥、喷洒农药等,每年夏季烈日下都要蜕去几层皮。所以,笔者考取大学后,村民们很是羡慕,并且将我当作他们教育子女努力学习考大学的榜样,其影响波及周边几个乡镇的中小学。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也极大地调动了年轻一代读书求学的积极性。从那以后,本村考取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而且有些年轻人所录取学校的层次还相当高。例如,“老四房”中“老二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培植之子刁俊龙,刁俊农之子刁得山,刁得山之子刁勤林、刁勤华兄弟俩(本村刁姓家族的十代孙),都是县城姜堰中学的优等生,学校保送老大勤林上了大学;后来又准备保送老二勤华上大学。老二坚持自己考大学,结果考取清华大学。学成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科研开发工作。又如,“老四房”中“老二房”另一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培才,刁培才之子刁维和(我当生产队会计时的生产队老队长),刁维和之子刁春友、刁春武兄弟俩(本村刁姓家族的九代孙),先后考取南京农业大学。春友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农林厅工作;春武毕业后分配在南京蔬菜研究所工作。再如,“老四房”中“老二房”另一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培藻,刁培藻之子刁维仁,刁维仁之子刁益民,刁益民之子刁阳隆(本村刁姓家族的十代孙),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而“老四房”中“老二房”另一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培荣,刁培荣之子刁维圣夫妇俩是小学教师,他们的一子二女都是恢复高考后走出村庄的文化人。如此等等,不复赘述。
刁舍村刁氏家族文化发展的回顾
苏中里下河刁舍村刁姓家族,自清乾隆年间因太湖洪灾迁居此地,繁衍生息已历十三代,前后达二百三十余年(2014-1780≈234)。本村刁姓始祖刁耀先、二代祖刁之贤。三代祖刁万言、刁万进、刁万树、刁万宏弟兄四人各自组成的家庭后称“老四房”。自此以后,刁舍村刁氏家族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归属于这“老四房”中某一房的名下。清末民初,近现代学制的建立,新式教育的兴起,重教尚文的村风、民风的滋生,村庄家族史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开始出现。
本村刁氏家族史上的“老四房”中,“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老四房”都各有传人。在各分支家族的人才发展史上都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人。从本文所反映的家族文化发展情况看:“老大房”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出现的较早,以刁焕国、刁焕兰兄妹俩为代表。其中,刁焕国是民国时期本村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刁焕兰是本村较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女文化人。“老二房”现代意义上文化人出现的较多,以刁培萼及刁勤林、刁勤华兄弟俩为代表。其中,刁培萼教授是建国以后本村第一位走出村庄、走出泰州,并在教育学和文化学等方面颇有建树的文化人。继他之后,刁培萼的大哥刁培庵的孙女刁勤芳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考取大学、走出村庄的文化人。而凯民、凯华兄妹俩所建“刁培萼、吴也显纪念馆”则是已经走出村庄的刁姓家族后人在信息化时代对家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刁勤林、刁勤华兄弟俩是本村刁姓家族十代孙,也是学历层次较高的兄弟俩大学生。“老三房”以刁方林之子为代表,他填补了“老三房”在分支家族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的空白。“老三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巧元,刁巧元之子刁方林,刁方林之子(本村刁姓家族十代孙)在20世纪90年代考取东南大学,学成留校任教至今;“老四房”以刁克明、刁雁宾为代表。其中,“老四房”一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殿虎,刁殿虎之子刁克明(本村刁姓家族七代孙),是解放前走出村庄到外地开展革命工作的文化人并牺牲在解放前。新泰州和老泰州的烈士陵园里都有他的遗像。“老四房”另两个分支家族的传人刁雁宾和刁宝香(本村刁姓家族七代孙)也都是建国以后至文革前走出村庄的文化人。传统家族文化与村庄文化联系紧密,村庄文化与家族文化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村庄是以某一家族为主体,而有的村庄则是多种家族文化的结合体。本村家族文化虽然是以刁姓家族为主体形成的村庄文化,但那些世代与刁姓家族有姻亲关系的或在解放前有雇佣关系的异姓村民及其后代,往往与该村主体家族文化有很大的关联性。例如,凌汉媚和凌汉民姐弟俩、施福厚(农业大学)、王裕明、孙宝贵、刘长银、丁传仁、刘锋、刘杰、张德富等。他们也都是建国以后直至“文革”前走出村庄到外地读书求学的文化人。而陈庆华、张国祥、王中祥、陈万国、范小琪、移钱华、陆卫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则是恢复高考以后走出村庄到外地读书求学的文化人。因此,本村230年的村庄发展史可以看成是一部以刁姓家族为主体,刁姓家族与异性家族共同发展的文化史。
刁舍村刁姓家族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清末至民国时期、共和国初期、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每一次学制与课程改革,都提高了本村村民重视子女教育的积极性,都在本村“刁姓家族”教育文化与人才发展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外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推进,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浪潮,许多教育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新方式逐渐普及,促进本村村民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走出去的刁氏族后人的观念更新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异地流动,特别是与近现代学制和新式教育紧密相连的村庄文化人的异地流动,传统村庄的衰落与新型家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村庄留守村民与走出村庄的劳动力包括文化人所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农村教育问题、农村儿童发展与教育问题、教育文化包括家族文化问题,本村刁姓家族第七代传人刁培萼教授在他留给我们的教育科学遗产中,早已经作了开拓性思考。[1]
在传统村庄基点上思考问题,传统村庄家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家族后代走出村庄,在异地安家落户,但继承和弘扬了原有村庄的家族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另一种是已经走出村庄的家族后代,在政治经济政策许可、物质条件和科技文化素质具备的情况下,再走回村庄建设村庄,使传统村庄的家族文化得以继承并获得新生。当然也可以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外地居民迁居家族祖居的村庄,就像200多前苏州阊门刁耀先公迁居此地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家族文化也就成了一种精神的、流动的、以现代传媒手段为载体的家族历史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村刁姓家族文化史只能借助于像小说《根》那样的文学作品或借助于《教育文化论坛》这样的学术刊物储存于数据库而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了。
在“我的前半生”中,有几个历史性的“机缘巧合”。如,进大学时校名是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毕业这一年,启用南京师范大学校名。走向工作单位之初,我所工作的单位校名是泰州师范学校;到我退休时,我所工作的单位校名是泰州学院亦或是泰州大学。我在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平平,可以说是“差生”,但到了高考时,却成了大学生。我在回首往事时发现,推动我从小时候的“差生”到青年时期的“大学生”;从一个生性腼腆的乡下孩子挤身到一所地方高校的“教授”行列的人生转折,与两个领袖人物有关:没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很有可能连初中都考不上(更不用说是大学了);没有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也不可能成为大学生,更不可能成为一所地方高校的“教授”了。对于这种“机缘巧合”,本村刁姓家族第七代传人刁培萼教授的专著《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2],可以从“教育哲学”的高度作出符合“教育辩证法”的解析。从我的爷爷“黑二爹”到我的父亲“芊二爹”都是农村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如今我与我儿子刁益虎都成为地方高校的大学教师。*笔者是泰州学院的教育学科教师;我儿子从今年秋学期开始成为南京师大泰州学院的教育学科教师。我们父子俩将牢记前辈、恩师刁培萼教授的谆谆教诲,继承“刁培萼教授留给我们的(教育科学与文化)遗产”,为地方高等教育事业、为教育学科建设、为泰州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作贡献,以告慰前辈和恩师刁培萼教授的在天之灵。这中间固然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相关,但自我感觉也与笔者从小生活的那个小环境——苏中里下河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舍“刁家舍”或“刁舍村”相联系。更进一步讲,在“我的前半生”中促使一个先天素质平平的乡下孩子的人生轨迹发生几次小小的“飞跃”的正是这个村庄所具有的重教尚文的村风、民风。这也是从这个村庄中走出去的“文化人”的共同的“文化基因”。
[1] 毕世响.刁培萼教授的遗产是什么——用思维完成一个人[J].教育文化论坛, 2014(1).
[2] 刁培萼.追寻发展链:教育的辩证拷问[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