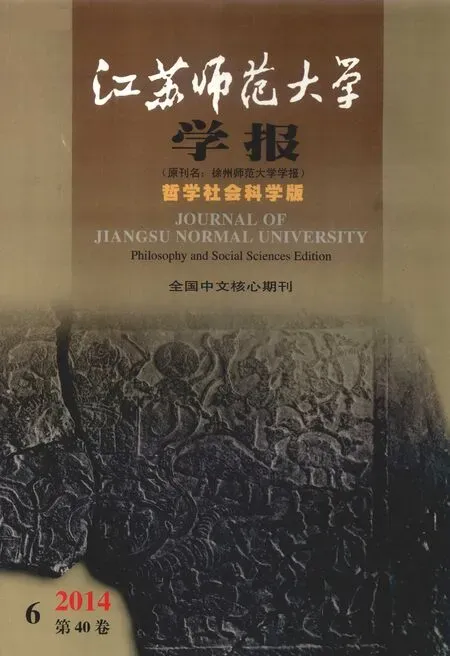从辛格的叙事策略看《傻瓜吉姆佩尔》的犹太文化主题
毕 青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从辛格的叙事策略看《傻瓜吉姆佩尔》的犹太文化主题
毕 青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傻瓜吉姆佩尔》;第一人称叙事;互文;犹太文化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代表作《傻瓜吉姆佩尔》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透过犹太个体创伤记忆的独特视角观照民族历史遭际,传达出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迫害这种敏感问题的审视和苦涩的反思。作品在情节的敷设上与《圣经》构成互文性指涉,通过对先知何西阿故事的主题的颠覆,凸显出对传统犹太教上帝观的质疑。作品叙事中蕴涵着对犹太民族历史与现实深刻的思索,是美国犹太文学流变中不容忽视的文本现象。
1978年,当代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因为其作品“以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反映了波兰犹太人的传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位31岁时才移民美国的犹太作家,辛格始终心系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存续和犹太人的现实生存境况,他一生笔耕不辍,努力“以严肃作家的笔触深切关注时代问题”[1]。《傻瓜吉姆佩尔》是辛格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也是他的作品中获赞誉最多的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辛格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通过吉姆佩尔的自我书写呈现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并且通过小说情节与《圣经》的互文指涉,传达出对犹太传统宗教观念的诘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文化向度以及作者对犹太民族现实与历史的困惑和思索。
一、第一人称叙述:个人记忆与历史书写
著名作家J·M·库切认为,当代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附属于历史书写,“为读者提供身临其境的第一手资料”,另一类则与前者构成一种对立竞争的关系,是“按照自己的步骤运行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按照历史的步骤最终得出可以被历史所验证的结论。……它发展进化出自己的样式与神话,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有可能揭示出历史的神话结构”[2]。库切所指的第二类小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诗”,它“比历史更富哲学性,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3]。而这种对“普遍性的事”的艺术表达,它的价值在于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历史,以叙事的虚构性洞悉了历史的真实。在《傻瓜吉姆佩尔》中,辛格通过一个犹太“傻瓜”的视角和声音,讲述了他憋屈的生活经历和苦涩的精神困惑,折射出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际,也蕴涵了辛格对犹太人生存问题的思考。
吉姆佩尔是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他是一个犹太人,原先在东欧小镇弗兰姆波尔做面包师,如今年近老迈,四海漂泊。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开篇从吉姆佩尔的自我介绍开始:“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可是人家都叫我傻瓜。我曾一共有过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白痴、呆瓜、笨蛋、蠢人和傻瓜。”[4]为什么吉姆佩尔会被镇上人视为傻瓜呢?概括地说,是因为他容易轻信别人。辛格让吉姆佩尔成为叙述者,用直接引语记录下了自己听到的种种谎言和遭遇的欺辱:“吉姆佩尔,月亮落到了图尔平,快去看呀;吉姆佩尔,沙皇到弗兰姆波尔了,赶快逃跑吧;吉姆佩尔,你父母都复活了,正四处找你呢。……我像一个泥偶一样相信每一个人。”[5]镇上每家生孩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所有人都会收到葡萄干作为庆贺,但每次吉姆佩尔总是得到羊粪蛋。吉姆佩尔在面包铺做学徒,每个来烤饼的家庭妇女也不放过他,把他当作笑柄取乐。
吉姆佩尔的“傻”使镇上人肆无忌惮,他们合伙骗他娶了远近闻名的淫妇艾尔卡。艾尔卡结婚不到四个月就生下了一个孩子,但她却毫无羞愧感,反而还振振有词地说孩子是早产。当吉姆佩尔就这事去求证镇上最有学问的校长时,他也哄骗吉姆佩尔说:“亚当和夏娃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世界上的女人哪个不是夏娃的孙女?”[6]就这样,艾尔卡依旧和镇上的男人们明来暗往。每次吉姆佩尔羞愤难堪,当面戳穿她的奸情时,艾尔卡总会撒泼狡辩,甚至还破口大骂:“你这个讨厌的畜生!你这个白痴!你这个野鬼滚出去,否则我要把全弗兰姆波尔镇上的人都叫来!”[7]吉姆佩尔饱受侮辱和损害,却从不抗拒。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他为什么要相信别人,是缺乏辨识能力,真的很傻吗?
如果仔细分析吉姆佩尔的讲述,读者便不难发现,从智力上说,吉姆佩尔并不傻。在叙事策略的运用上,辛格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巧妙发挥了这种叙事技巧在传达文本信息、塑造人物性格方面具有的直观性和深刻性两方面的特点。吉姆佩尔的第一人称叙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虽然他年纪大了,但对于细节也描绘得准确生动,读者不难感觉出,吉姆佩尔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这表明他不傻。与此同时,这种第一人称经验视角,通过深入叙事的结构层面,将读者直接引入叙述者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从而产生塑造吉姆佩尔人物形象的作用。
每次遭受欺辱,吉姆佩尔总是想:“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8]每次发现妻子与别的男人通奸,吉姆佩尔就会在心里自我安慰:“我决心永远相信人家对我说的话。今天你不相信你的妻子,明天你就不相信上帝。”[9]不难看出,吉姆佩尔是一个恪守犹太传统、虔诚信仰上帝的犹太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深刻的认识,而之所以处处克己忍让,是源于他对犹太教律法的深刻把握与虔诚践行。犹太教十分强调“因行称义”的道德原则,即人应该以自己的行为表达对上帝的信仰。在《摩西五经》及《托拉》中,上帝被赋予绝对的仁慈和公义等品质,所以犹太教认为,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犹太人应该履行上帝在西奈山上赐示的律法。吉姆佩尔努力在生活中通过实践律法,表达自己的信仰,他遵循圣书上的禁诫:“不可行不义、不可心里怀恨、不可随众行恶、不可报复”(《旧约·利未记》19:17-18),同时他坚信拉比的话:“圣书上写着,一生做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他们是傻瓜,你不是傻瓜。”[10]
吉姆佩尔不傻,他的行为、言谈举止与正常人没有差异,然而,他却被当作傻瓜对待,沦为别人捉弄取笑的对象,在周围人的眼中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是社会的局外人,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赋予他一个特殊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在叙事中采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便于将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向读者敞开,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深切地透视叙述者的内心活动,因此倾向于对他产生认同,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观察他周围的人和世界[11]。读者从吉姆佩尔的视角出发,便切身感触到他生活的环境是个残酷而疯狂的世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我敢说一句,‘嘿,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大家都看做是说谎的?’”[12]镇上几乎人人都以吉姆佩尔的痛苦来构筑自己的快乐。当吉姆佩尔和艾尔卡举行婚礼时,小镇沉浸在狂欢之中,“人们都喝醉了”。当镇上人得知艾尔卡生了个私生子时,小镇再次陷入狂欢,“因为我有了烦恼和痛苦,全弗拉姆波尔镇的人都兴高采烈”[13]。历经屈辱和迫害,吉姆佩尔深切地感觉到了在这个充斥着谎言和强权意识的世界上的生存危机,他只能忍耐,而唯一的期望就是:“整个市镇不可能继续这样疯狂”[14]。那么,为什么镇上的人都选择吉姆佩尔作为凌侮的对象呢?
著名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的评论帮助点明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他说:“这个受尽嘲弄与迫害的不幸民族再次在这个镇上的傻瓜身上体现出来。”[15]的确,吉姆佩尔是个犹太人,他的犹太身份成为他招惹灾祸的根由。诚如犹太作家路德维希·伯尔内所说:“真像一桩奇事,我本人身受了近千次,可总是依旧那么新鲜。这些人斥责我,因为我是犹太人。……他们好像在不可思议的犹太人的圈子里着了迷,没有人能跳出来。”[16]法国著名思想家保罗·萨特对犹太人的遭遇也曾做过类似的分析:“犹太人是根本坏的;他的长处,假如有,也因为是他的长处而变为短处,他的手所完成的工作必然带有他的污迹,因为它从头到尾每一寸都是犹太的。”[17]辛格在接受《巴黎时评》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吉姆佩尔这个人物形象,他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依照意第绪语作家的‘小人物’这一传统进行创作的。我笔下的人物,尽管不是那种在世界上起重要作用的大人物,但也并非微不足道。”[18]辛格擅长讲故事,被誉为“伟大的寓言家”。他始终强调,故事既要有艺术性也要有思想深度。他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创作观:“故事写得恰当,是指构思要精当,内容和形式要统一,描写要适宜。但还不止于此,在每一个故事中,我都试图表达些什么。”[19]在《傻瓜吉姆佩尔》中,辛格通过吉姆佩尔的经历试图表达的,就是一位以“犹太民族之子”自居的流散作家对犹太身份和犹太民族历史命运的体味和思索。
从历史上看,不管犹太人本身怎么谦卑谨慎,外部世界总是以不平常的心态、不平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自从公元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巴尔·科赫巴民族起义失败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流散”,犹太人的流散史就是一部充斥着歧视与迫害的苦难史。在宗教信仰上,自公元4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犹太人普遍被看作邪恶的化身,处处受到歧视,许多犹太人不堪忍受,只能改变宗教信仰,但历史证明,改宗后的犹太人仍然被视为“可憎的犹太人”;在经济上,犹太人取得的经济成功使他们成为众矢之的,因而总是遭到盘剥和排挤,甚至动辄被当地政府没收所有财产,并被驱逐出境。在政治上,犹太民族历来是反犹主义运动残酷迫害的对象,特别是在欧洲,由各国政党煽动、各类反犹组织计划实施、各个居住地民众普遍参与的迫害犹太人的恐怖事件严重威胁着犹太民族的生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法西斯更是丧心病狂地展开灭绝犹太民族的各种活动,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虐造成600万无辜犹太人被屠杀。
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亚历山大说过:“二战大屠杀之后,犹太人的身份便无法与历史相分离。一个犹太作家的责任就是参与读者想象力的建构。如果他把人物同民族历史割裂,他的作品无疑会缺乏生命力。”[20]辛格的许多作品都是通过匠心独具的叙事策略诠释犹太民族历史与生存的主题。在《傻瓜吉姆佩尔》中,辛格以吉姆佩尔为叙述者,通过他对自己委屈求安生存原则的娓娓诉说,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小说人物的创伤记忆,还有他本人对历史上存在的普遍性的反犹主义迫害这种敏感问题的审视和反思。
二、与《圣经》互文:诘问上帝
当代法国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评论巴赫金作品时,提出了文本间的互文性理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21]。美国批评家费拉尔也认为:“来自文本各种网络的语义元素超越文本而指向构成其历史记忆的其他文本,将现实的话语刻入他自身辩证的联系着的社会和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中。”[22]任何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一个文本在结构、行文和意义的赋予等方面,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文本的参照和关联,置身于一个开放的文本体系,并在与各个构成文本的交互作用中传达意义。
《傻瓜吉姆佩尔》是以吉姆佩尔的婚姻遭遇为主要线索展开的,在情节的敷设上,辛格采用了互文性手法,把吉姆佩尔和艾尔卡的故事与《圣经》中先知何西阿的故事相关联,形成了一个互文性叙事结构。
《圣经·旧约》中,上帝曾命令先知何西阿娶滴拉音地方的希伯来女人歌篾为妻,但歌篾淫荡无耻,生活糜烂,与别的男人苟合,生下三个私生子。何西阿羞愤难当,决心休掉歌篾。但是,上帝却授意他原谅了淫妻,何西阿听命上帝的旨意用银子和大麦将歌篾赎回,并对她进行劝导:“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想你也必这样。”(《旧约·何西阿书》3:3)
在《傻瓜吉姆佩尔》中,吉姆佩尔重现了先知何西阿的故事。镇上人逼迫吉姆佩尔娶淫妇艾尔卡为妻,吉姆佩尔深知艾尔卡生性放荡,最初他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声言“我永远不会娶那个荡妇”[23],但不久他就改变了想法。婚后,艾尔卡依旧刁泼放浪,对吉姆佩尔发号施令,而且频频红杏出墙。镇上人有的幸灾乐祸,趁机嘲讽吉姆佩尔,有的建议他抛弃艾尔卡,甚至拉比都规劝他:“别管这个荡妇,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24]面对这一切,吉姆佩尔始终坚持信任妻子,宽忍了她的背叛。艾尔卡最终患癌症病死,吉姆佩尔便把所有财产留给了六个孩子,自己只身云游四方。
乍看起来,吉姆佩尔故事的叙事架构与先知何西阿的故事似乎如出一辙。不过,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吉姆佩尔的故事和《圣经》实际构成了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辛格通过对何西阿故事的指涉,使吉姆佩尔的故事文本与前者构成一个文本参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吉姆佩尔的故事利用其对前文本(《圣经》中何西阿的故事)主题的解构,凸显了辛格对传统犹太教上帝观的质疑。
在《圣经》中,何西阿的身份是个犹太先知。而在犹太教中,先知是指“受上帝精神所感动的讲话者或布道者”,亦称“上帝消息的传递者”[25]。上帝在犹太人中拣选出虔诚智者,启示他们把神圣的谕旨传达给犹太人。作为上帝的代言者,何西阿是上帝在现世的化身,他的作为呈现了上帝的意志和品性。《圣经·旧约》中,“淫妇”作为一个象征符码,常指涉犹太民族。她道德沦丧,纵欲无度,肉体的淫乱象征了宗教信仰上的悖逆不忠,即背弃上帝去追随当时中东、西亚地区流行的其他异教神。但是,面对她的种种背叛出轨,仁慈的上帝依然宽恕她,接纳她,珍视她为自己的伴侣,并表明:“那日你必称呼我为我夫(My husband),不再称呼我巴力。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旧约·何西阿书》2:19-20)我们从上下文中发现,《圣经》中先知何西阿娶淫妻的故事昭示的主题,其实是上帝对犹太人的仁慈。然而,在《傻瓜吉姆佩尔》中,吉姆佩尔的婚姻悲剧却对上帝的仁慈品性提出了质疑。
吉姆佩尔笃信上帝会依据各人在现世的行为施行奖惩,诚如拉比的告诫,上帝将把“应许美地”赐予那些趋善避恶的犹太人。以上帝为指引,吉姆佩尔践行仁爱,始终眷顾艾尔卡,明知她不守妇道,生活窘困,仍然娶她为妻,他主要考虑:“如果(这桩婚事)对她来说有好处,那么我也就感觉愉快。”[26]婚后,艾尔卡不断给他戴绿帽子,吉姆佩尔也经常会激起愤怨,但每次都宽仁地相信了她的谎言,“她又是赌咒,又是发誓,全都具有说服力。我接受她的每一句话,尽管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27]。结婚20年中,艾尔卡共生下了6个孩子,而吉姆佩尔始终辛苦地挣钱养家,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吉姆佩尔耐心地企盼艾尔卡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并且也能真诚地爱他。但是,等待他的却是残酷的现实。临终时,艾尔卡向吉姆佩尔坦白:“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28]吉姆佩尔回忆当时自己的反应,他说:“她的话使我迷惑不解,不亚于挨了当头一棒。”[29]尽管叙述的语调平静克制,没有激愤的责怨,但我们能够体味出其中深切的悲凉。吉姆佩尔想不明白,既然上帝是仁慈而讲公义的,他为什么要苦待一个虔诚的好人,眼看他一生善良待人却总是遭受欺骗而无动于衷?结婚20年来,对于艾尔卡的每次背叛,事后吉姆佩尔总习惯于安慰自己:“今天你不相信你的妻子,明天你就会不相信上帝。”吉姆佩尔把不贞的妻子和上帝联系在一起,读来颇具反讽意味。我们感到辛格似乎意在表明,上帝就像艾尔卡一样充满了欺骗性,期望他的爱是虚妄的,结果只会是痛苦的精神伤害。
辛格从小时候起,就对上帝的仁慈心存怀疑,在自传《寻求爱的年轻人》中,辛格记录了自己和身为犹太哈西德教派拉比的父亲的一次对话。他们谈论的主题是上帝和犹太人的苦难的关系,拉比父亲说:“这是最大的秘密。就是圣哲们也无法了解。只要人还在遭受痛苦,他就无法解开苦难之谜。……在所有这一切苦难的背后,是上帝无限的仁慈。”[30]拉比父亲的解释重复了正统犹太教对上帝的诠释,但无法令辛格信服,他曾颇为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我忧伤郁闷的原因常常是对那些正在受苦和世代受苦的人们的难以忍受的悲悯。我听说过赫米尔尼基时代哥萨克人的残忍暴行。我读到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我知道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生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我不只怨恨人类,也怨恨上帝。是他让人成为嗜血的动物,时刻准备施暴。”[31]在辛格看来,上帝对犹太人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始终保持冷漠是残忍的。
《傻瓜吉姆佩尔》的开放式结尾进一步表征了辛格对上帝仁慈品性的质疑。艾尔卡死后,吉姆佩尔离开家乡,四处漂泊,他时刻在心里梦想着上帝的“应许美地”:“那儿没有纷扰,没有嘲讽,没有谎言。赞美上帝: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被欺骗。”[32]吉姆佩尔憧憬的是一个与现实不一样的世界,在那里,上帝将显露仁慈,而犹太人也会改变屈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世界只能出现在吉姆佩尔的幻想中不免显露出它的虚妄。辛格冷静地指出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这样的结尾也暴露出辛格对犹太人生存现状的无奈和他矛盾的宗教观,诚如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辛格信仰上帝不错,但他对上帝的信仰仅限于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者说,相信的是那个违约的上帝,而绝非是犹太教所宣扬的那个仁慈、公正的上帝。”[33]
三、结语
辛格是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群体中最具犹太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犹太性常常表现为对犹太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对犹太传统理念的困惑和追索。在以《圣经·旧约》和《托拉》为核心的犹太传统话语体系中,上帝是至上至尊的存在,被赋予仁慈和公义两大属性。上帝对犹太人实施仁爱,但犹太人却沉湎于纵欲、堕落,违背了与上帝的契约,因而遭受现世的苦难,这是正统犹太教反复宣示的命题,即仁慈的上帝面对的是堕落的犹太人,而苦难是他们应得的惩罚。在《傻瓜吉姆佩尔》中,辛格巧妙地运用叙事策略,向读者传递了对这种传统理念的质疑,表达出对传统犹太教教义的挑战。有研究者评论《圣经》的价值时说过:“《圣经》通过对上帝的论辩、责怨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充斥着强烈人文精神的反权威、反传统意识,开启了犹太文化中的一种重要传统,这种传统以回归人的本体为指向、以挑战传统中的不合理要素为特征,对后世犹太文化的沿革亦起到重要影响。”[34]从这个意义上说,《傻瓜吉姆佩尔》也是美国犹太文学流变中不应被忽视的文本现象。
[1]Singer,Isaac Bashevis.Nobel Lecture.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1979:3.
[2]段枫:《历史的竞争者——库切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超越》,《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
[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页。
[4][5][6][7][8][9][10][12][13][14][23][24][26][27][28][29][32]Singer,Isaac Bashevis.Collected Stories:Gimpel The Fool to The Letter Writer.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2004.5,6,10,15,11,13,6,5,13,8,6,12,7,10,16,17,19.
[1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15]Kazin,Alfred."The Saint as Schlemiel,"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ed.by Grace Farrell,New York:G. K.Hall,1996.
[16]戈登·克雷格:《德国人》,杨立义、钱松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17]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2页。
[18][19]Flender,Harold."The Art of Fiction No.42:Isaac Bashevis Singer."Paris Review 44(1968):1-23.
[20]Alexander,Edward."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Jewish Fiction:A Slow Awakening."Judaism,Summer(1976):320 -330.
[21]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2]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25]黄凌渝:《犹太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30][31]傅晓微:《上帝是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3页。
[33]乔国强:《论辛格对“契约论”的批判》,《国外文学》,2007年第3期。
[34]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4年版,第155页。
A Narr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Jewish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Gimpel the Fool
BI Q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Gimpel the Fool;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intertextuality;Jewish culture
Isaac Bashevis Singer's most famous short story Gimpel the Fool is an account of a personal traumatic life experience,which,through 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also represents a bitter examination of such a sensitive issue as widespread anti-Semitism in Jewish history.Singer constitutes a referential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Book of Hosea"in The Bible,through which he conveys his challenge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Jewish concept of God's mercy.Gimpel the Fool profoundly contains a perplexed reflection on Jewish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ewish people,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valuable text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I3/7-07
A
2095-5170(2014)06-0033-05
[责任编辑:林晓雯]
2014-06-24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散文化视阈下的辛格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750025)、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视阈下的辛格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0XWA03)阶段性成果。
毕青,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