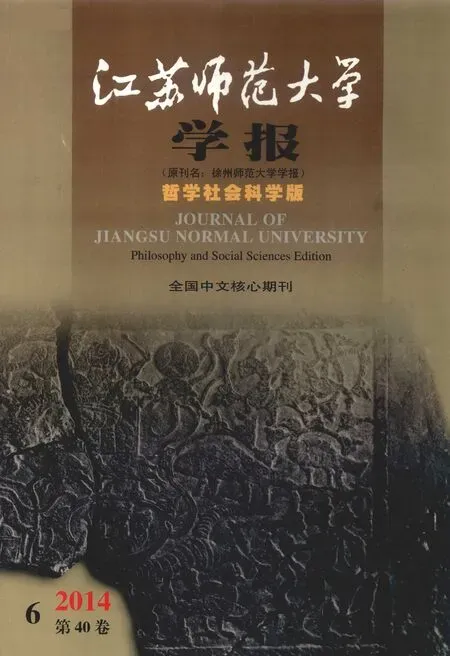德文档案中的中国留德第一人
杜卫华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德文档案中的中国留德第一人
杜卫华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留德;陈观海;巴陵会;巴冕差会
中国人留学德国这一进程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留德的中国人出于不同的机缘、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遥远的德意志,在德意志的语言和学术训练使他们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当然使者和体验者。在中国人留学德国史这一研究领域,一直需要确切的历史档案材料。本文利用德文档案和已公开出版的德语出版物,对中国留学德国先行者的足迹进行了一次重现;依据目前的材料补充论证了中国留学德意志的第一人应该是广东人陈观海。
在中国人留学德国史的研究领域,大部分学者认为李鸿章1876年派遣卞长胜等7名军官留学德国为中国人留学德意志之起点[1]。如果以中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有计划地派出留德生为判断标准,上述观点是成立的。如果以在一所教育机构有组织的学习为标准,那么中国人留学德意志的时间应该更早。早在1867年,广东人陈观海(1851-1920)就被巴陵会(Berliner Mission)选派到柏林留学,一直到1874年他学成归国为止;在他归国时,卞长胜等人尚未得到留学德国的机会。在这7年的时间里,陈观海先后在柏林(Berlin)、巴冕(Barmen)[2]两地学习神学,并于1874年被按立为牧师(Ordination)。之后他回国,服务于教会和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
目前一些中文出版物对于陈观海在中国的活动介绍的较多,而德文方面的材料则因为语言和档案问题,迟迟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3]。在原礼贤会档案馆(Archiv der Rheinischen Mission),即今日的联合基督教使团的档案馆(Archiv-und Museumsstiftung der VEM in Wuppertal)里,有专门一个档案是关于陈观海(Tschan A si)的,档案号为2.198。因为手写文字不易读懂之故,本文借助已经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杂志对陈观海在德国的学习和回国后的传教工作进行梳理,借此展现中国留学德国第一人的足迹。
一、陈观海在德文档案中的姓名
从中文材料上看,陈观海的后人陈志强2004年在《羊城今古》的文章中提供了很多线索。陈观海字赐昌,又名泗昌,号贡川[4]。而在不同的德文材料里面,对于陈观海的称呼是不同的。最常用的称呼是Tschan Asi,可能是指陈阿泗,这应该是广东人的称呼。因拼写方式不一,所以在德语中产生了很多种写法:Asi,A tsi schong,A-Si-Tschöng,Atschin,Tschan Asi,Ch’an a’Si’,Tsch’an Asi,Tschöng Asi,Tschan A Si,Tseang Si Tseong,Tschin-Asi。
除了名字之外,德语材料中一般还用一个词语进行说明,如der Chinese(这位中国人),ein Chinese(一位中国人),ein junger Chinese(一位年轻的中国人),unser Chinesenzögling(我们的中国学生),ein geborener Chinese(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陈志强的文章认为陈观海生于1851年,但是根据德文材料记载,他1850年生于广东省Hoau(荷坳村)。其父由巴陵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神父叶道胜(Pastor Genähr)洗礼为基督徒,并担任了神道小学的校长;在父亲1864年逝世后,陈观海同教会保持了联系,并于12岁时洗礼为基督徒[5]。陈观海在巴冕结识了同为中国人的梁琼羡(1851~1939),他们在巴门结婚后,于1874年秋天一同回国。梁琼羡的德文名字叫Auguste,出生于香港,后被香港的Betheda孤儿院收养,并由巴陵会带到了德国[6]。
二、陈观海在德国的学习经历
陈观海1867年10月13日由广州黄埔港出发,乘德国货船先抵纽约,后抵汉堡,最后到达柏林[7]。1868年,由巴陵会出资送他进入巴陵会的神学院(Seminar der Berliner Mission)[8]学习,巴陵会在文件中也明确提出资助他学习的目标在于“培养他以后为教会服务的能力”[9]。他在这里除了学习德语之外,还学习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以便能够读懂与宗教相关的文献。通过日后陈观海向差会提供的德语报告来看,他的德语水平很高,基本上具备了与神学院的德国毕业生同等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陈观海在德国柏林神学院学习神学的同时,也参加了一些中德官方的交往活动。1869年11月到1870年1月,由美国人蒲安臣和满洲贵族志刚带领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了普鲁士。巴陵会很重视住在柏林罗马酒店(Hotel de Rome)的中国使团,1870年1月28日,香港孤儿院院长Knak神父派陈观海去联络中国使团,并带回口信,中国使团期待同巴陵会在第二天中午会谈[10]。紧接着Wangemann神父和Knak神父起草了一份《致中国使团的信》,由陈观海译为中文。两位神父于29日拜访了中国使团,并赠送了中文版的圣经[11]。
1872年,巴冕差会接管了巴陵会在中国的传教任务。因此,陈观海由柏林神学院转到了位于巴冕的神学院(Barmer Seminar)[12]。1873年,巴冕差会出具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陈观海在柏林的神学培训与10月份的转学,差会认为:“(陈观海)将会成为中国传教事业中可靠而又聪明的工具(als ein geschicktes und treues Werkzeug im Dienste der Chinamission)。”[13]1874年,陈观海通过了神学专业考试,并在8月12日的庆祝日上被按立为牧师[14]。按立仪式从早上9点开始,共3个小时。一开始由来自Herborn的Kübel教授做主祷,之后由教区监督克施泰因(Kirschstein)做按立词,按立5名神学院学生为牧师,接着由巴冕神学院监督Fabri博士做任职致辞Abordnungsrede,最后才由新立牧师致答谢词。陈观海在致答谢词时,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教育经历,寻找基督作为信仰的进程;他指出传教的人是不会倦怠的,同时指出教会不应该忘记中国人[15]。在按立之后的9月份,他就同妻子一起乘船归国了[16],因而没能参加当年10月12日差会举行的告别晚餐[17]。
三、陈观海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1875年春,陈观海回到广东以后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881年1月6日,他在南雄基督福音堂(Namhyung)写给教会的德文工作报告中,回顾了自己在南雄传教的历程。南雄位于广东同江西交界的山区,这一教区是由韩士伯牧师(Pastor Hanspach)开创的,并先后由何必烈牧师(Br.Hubrig)和一个叫Fu Setam的中国牧师来协助他的工作。1875年,陈观海没有固定的传教区域,不过在四处传教时,他已经为4个中国人进行了洗礼[18]。1876年,南雄成为独立的教区,陈观海则成为韩士伯牧师的助手。在报告中他很得意地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从1876年到1880年他共为29人进行了洗礼,1876年7个,1877年8个,1879年4个,1880年10个;而韩士伯和何必烈两个人才洗礼了16个人[19]。同时他在报告中也写到了传教的困难:地理位置偏僻,冬天气温太低,人员不固定,五分之一洗礼者离开南雄,同美国教会相比房间和设备不完善等等。然后他笔锋一转,写到教会新培养了3位助手,并且内部凝聚力增强,而且信教的人开始接受让自己的孩子也进行洗礼。他自己也非常感谢上帝给他3个孩子:大女儿4岁(名叫Yuk-Ching),儿子2岁半(David),小女儿刚刚生于1880年4月14日(Yüt-Ching)[20]。
但这种乐观情绪在1882年的报告中就很难看到了。这篇报告以《中国的神谕》为标题,他批评很多来教会的人一看到需要不断地做礼拜就退却了,他仅仅能够为4位进行洗礼,而其中两位还是以前就保持密切联系的。接下来,他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了广东乡民的传统迷信活动,请笔仙等等活动,所用单词共741个,而报告总字数才1008个单词。然后他指出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对于宗教传播的限制,因此,只有一少部分人敢于试图理解上帝的语言[21]。
陈观海对于传教态度的转变也可以从1882年巴冕差会的另一份报告中得到佐证。1882年,巴陵会重新把在中国的独立传教权从巴冕差会分离出来;巴冕差会在一项报告中批评了陈观海的传教工作:一方面批评他因为具备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同被教育的欧洲差会的按立牧师为一体的特点,从而具有双重人格,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他同美国教会的接近,而这一点则是绝不会被巴冕差会所允许的[22]。这样,在不同传教组织发生矛盾和分裂的时候,陈观海就加入了巴色会(Basler Mission),开始了长达15年的巴色会服务生涯[23]。
四、小结
来自广东的陈观海因缘际会,在年轻时期成为巴陵会资助的留学德国的中国人。他从1868年到1874年一直在德国的神学院就读,学习语言和宗教学,他的留学生涯早于1876年的第一批留德军事学生。他虽然没有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大学就读,但是他在德国柏林和巴冕两所神学院接受了系统的神学教育,除了语言和文字学习外,他比较系统地受到了神学方面的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牧师。他的留学生涯一方面促使他回国后进行了长达20年的传教工作;同时也给予他语言和教育的技能,使他能够在另外一个20年的岁月里为中国的外事部门(也就是国家)服务。这一点也正如巴冕差会已经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个具备同两种文化沟通能力的中国人,而这一点也正是他德国留学所赐。
[1]研究德国历史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Deutschland)这一个名词是指中欧讲德语的区域。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才成立,也才有汉语中的德国这一术语。而在1871年之前,德意志的土地上存在着诸多拥有国家主权的邦国,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1871年之后,这些邦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单位,虽然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外交权和军队组织权。
[2]也有人翻译为巴门,1929年,巴门同其他城镇一起组成了伍珀塔尔市(Wuppertal)。
[3]罗彦彬:《礼贤会在华传教史》,礼贤会香港区会印行,1968年,第54、134页。
[4][7]陈志强:《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留学生陈观海》,《羊城今古》,2004年第4期。
[5]Gustav Menzel,Die Rheinische Mission:aus 150 Jahren Missionsgeschichte,Wuppertal:Verlag der Vereinigten Evangelischen Mission,1978,167-168.
[6]Missionschronik(差会大事记),载于Das Evangelium in China(中国基督教)1.Jg.1880,Nr.4,22.
[8]Julius Richter,1924:Geschichte der 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 1824-1924,516.
[9]Berliner Missionsberichte(巴陵会报)1869,194.
[10][11]Berliner Missionsberichte 1870,p.49-51,65-66.
[12]陈志强称为礼贤神道大学。
[13]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873,Nr. 6,161-164.
[14]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874,Nr. 9,S.257.
[15]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874,Nr. 9,S.257.
[16]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874,Nr. 12,S.381.
[17]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1874,Nr. 11,S.347-348.
[18][19][20]Evangelium in China(基督在中国),2.Jg.1881,36 -38.
[21]Berichte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39.Jg. 1882,67-70.
[22]Evangelium in China,3.Jg.1882,Nr.4,68.
[23]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差会杂志),Bd.9,1882,423 ff;Allgemeine Missions-Zeitschrift,Bd.10,1883,563.
The First Returned Student in Germany in the German Archivs
DU Wei-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China;Germany;Chen Guanhai;Berliner Mission;Barmer Mission;
The study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Because of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holding different purposes,they came to Germany,a distant country to the most Chinese. The learning of German language and the academic training by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nabled them to become a Sino-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player,of course by self-experience.In the study field about study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German,it needs exactly the archival materials.With the published materials in German language,the paper try to reproduce a footprint to the pioneer who studied in Germany;based on current materials,a conclusion is to be drew,that the first person as a Chinese studied in Germany was the Cantonese Chen Guanhai(Tschan Asi).
K265.62
A
2095-5170(2014)06-0007-03
[责任编辑:周 棉]
2014-06-2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中德文档案的留德教育史研究”(项目编号:14CZS042)的阶段性成果。
杜卫华,男,山东沂南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比较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