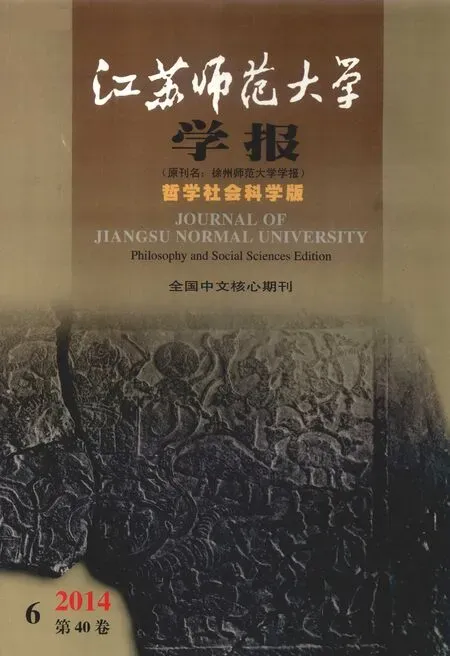从文化视野看程小青与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差异
周 渡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从文化视野看程小青与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差异
周 渡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程小青;柯南道尔;文化视野;侦探小说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福尔摩斯的行为时刻表达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选择人性的视角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凸显着强烈的个体意识。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则是将霍桑作为社会道德观念的承载者和维护者,主人公的个人价值是以对集体的依附作为实现条件的。两者的侦探小说在社会视角的选择、办案动机与方式的区分、法律与正义关系的处理、叙事时空的安排、人物类型的设置等方面,有许多显著的不同之处,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反映出东西方文化观念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实是典型的舶来品,对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之翻译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已有多位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程小青12岁时就开始阅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1916年应中华书局之约,与周瘦鹃等用文言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十二册,这是第一部按全集出版的柯南道尔作品。而程小青正式发表霍桑系列探案小说始于1919年[1],当年10月他的文言侦探小说《倭刀记》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题名前被冠以“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的字样;1930年又应世界书局之邀,再次与人合作将柯南道尔的新旧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整理成白话版本出版;次年《霍桑探案汇刊》1、2集由文华美术图书公司正式出版。这段时期恰是他侦探小说的创作高峰期,其笔下的霍桑形象已经获得了“中国第一侦探”的文学身份,由此可见其创作受到西方侦探小说尤其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很容易从表面上发现霍桑与福尔摩斯的众多相似之处。作为私人侦探,他们都具有远胜于常人的敏锐观察力,精通格斗和枪械使用,都有一个堪称知己的朋友协助办案,都能化装到连自己的老友都认不出来的程度;在侦查过程中,他们都不愿过早地向同伴透露已掌握的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在苦思案情时都要借助烟草的帮助,甚至在办案过程中遇到僵局时都经常通过拉小提琴的方式舒缓过度紧张的神经,调整自己的思路。他们的断案经历中都有失败的例子,他们在作出最后的决定时并不将法律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既然有如此多的相似点,霍桑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上述种种细节很容易使人作出霍桑探案是披上了中国化外衣的福尔摩斯探案的仿制品这一判断,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表象之下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就会逐渐凸显出来,两个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其实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
一、社会视角展现出的文化差异
米克·巴尔指出:“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因此,叙述学是对于文化的透视。”[2]从表面上看,霍桑和福尔摩斯都是令无数读者产生仰慕之情的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英雄形象,但如果深入分析小说文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英雄的区别所在。从故事情节看,在霍桑侦办的许多案件中,包朗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协助必不可少,甚至对成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还有许多人在破案过程中主动提供帮助,他们的行为都是基于道德力量的感召,可以说离开了社会中方方面面的帮助,霍桑将一事无成。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华生基本上是作为旁观者存在的,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他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经常是当他还蒙在鼓里时,福尔摩斯已经找到了答案。至于在办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绝大多数是受到利益的驱动,或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上述差异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在霍桑探案中受伤以至于住院的总是助手包朗,霍桑即便遇到蓄意枪击也总是能逢凶化吉。而福尔摩斯虽精通搏击,但遇到流氓棍棒袭击时仍不免头破血流。从各方面观察霍桑几乎是个完美的英雄,他的身上兼有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良好品质,作为私人侦探他没有受到恶劣世风的沾染,倒是经常慷慨激昂地批评国人的不良习气。虽然他拥有谦虚的美德,但总是以道德家的姿态出现,不失时机地向合适的对象发出基于公共道德原则的教诲,即使偶尔判断失误也不会造成让罪犯逃脱或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在《毋宁死》中,当霍桑说明实情时完全出乎委托人的意料,在对方瞠目结舌之时他正色规劝:“婚姻系人生之幸福,父母专擅,已违潮流;况取舍之准绳,涉及父母个人之利益,更不足为训。”[3]与之相比,福尔摩斯却有很多的坏毛病,他总是极度自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到了骄傲自满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程度。他厌恶社会上一切繁缛的礼仪,“一旦案件胜利结束,最使他感到好笑的就是把破案的报告交给官方人员,假装一副笑脸去倾听那套文不对题的祝贺”[4],他说话时常带着讥刺和嘲笑的口吻,甚至经常对无法想到点子上的好友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他注射毒品的习惯连他的忠实朋友都感到无法接受。福尔摩斯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道德楷模,当罪犯无奈地称他为魔鬼撒旦时,他并没有从道德角度进行驳斥,他甚至对违法者表示,对于其行为的道德和尊严问题,他无权发表意见。从这些方面看来,几近完美的霍桑是一个传达叙事者主张的扁平人物,在言行方面有很多瑕疵的福尔摩斯则是一个丰富饱满的圆形人物。形成这种文学现象的根源在于,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在道德和人性的不同角度之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举世闻名,对妇女礼仪上的尊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福尔摩斯并不缺少这种素养。他对待妇女非常温文有礼,但对女性的看法却是很特别。他认为由女性所带来的感情波动对从事侦探工作所需要的理性和冷静的头脑是有妨害的。当他在《波西米亚丑闻》一案中被一位胆识过人的妇女挫败时,他不禁在提到她时使用“那位女人”这样一个包含尊敬意味的称呼。无独有偶的是,在柯南道尔创作的60篇探案故事中,有60%的作品受害者都是女性对象,她们被伤害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两方面:财产争夺或情感纠葛。福尔摩斯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源自于他始终将女性作为弱者来看待,在她们的基本人权受到践踏时支持她们的反抗,他在考量她们的行为时始终从人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判断。而霍桑在办案中,同样对女性受害者表现出深深的同情,但主要源自于封建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影响造成女性受到男性压迫和迫害,以至于在生活中尤其是婚恋关系上处于弱势的社会背景。在《沾泥花》中他对堕入火坑的受害妓女的评价就是:“这女子的堕落并不单单是伊本身的罪,实在是社会的罪。”[5]对包办婚姻的否定更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突破。在《毋宁死》中霍桑正色说道:“盖黛影者实一纯洁之女子,乃父图保其禄位,遂以其女作献媚固宠之工具,此直犹原始时代以女子为货财之陋俗耳。”[6]在《双殉》中霍桑更是借当事人之口道出了社会现实:“在现社会上,男女的贞操观念还是沿着传统的眼光,彼此是不平等的。男子丧失了贞操不算一回事,女子丧失了,却仍会有严重的后果。”[7]
二、小说中办案动机与方式的区分
福尔摩斯维护法律既是受自身正义感的驱动,又明确地将其认同为公民的义务,但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既是赖以谋生的手段,同时又是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能使他充分享受到用智力解决疑难的快乐。虽然有强烈的正义感,但他经常不屑于去管那些在他看来不需要费多大脑筋就可以解决的案件,这似乎是警察的事。如果没有令他感觉兴奋的案件,他就会陷入百无聊赖的状态,他需要适合的案件来发挥那些非凡的才能。这并不是说他渴望犯罪的发生,而是在他的观念之中,犯罪来自于永远存在的罪犯的邪恶本性,犯罪也是往复循环永不终止的,因此叙事者总是刻意在文本中强调罪犯外貌上反映出的个人缺陷,这也是侦探特别注意的方面。在无案可办时,福尔摩斯选择等待,霍桑则会主动寻找危害社会的犯罪团体作为自己的办案对象。对霍桑而言,案件并无大小之分,只要是犯罪,就要尽力找出真相,惩治凶手,这样才能维护正义的社会公理。在他看来,罪案发生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源总是存在于社会之中,如《一只鞋》中凶手杀人的根本原因出自拜金投机的社会风气,触发的动因是受社会中堕落风习左右的流氓行径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背景。在总结案件时,霍桑多会发出指向社会弊端的议论[8]。如在《毋宁死》的篇末,他对包朗说:“吾欲尽其绵薄,为社会服务,凡桀骜阴鸷之徒,吾必发其复而置诸法;若制度礼教之不合时代者,吾亦必抨击而摧毁之。”[9]
作为一名私人侦探,霍桑在开始接手案件直至破案的前后过程中,从不计较自己可能或已经获得的报酬,但却常常依据社会价值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判断。在《逃犯》一篇的结尾,他对包朗说:“我所以这样子孜孜不息,只因顾念着那些在奸吏、土棍、刁绅、恶霸势力下生活的同胞们。……我既然看不过,怎能不尽一份应尽的天职?我工作的报酬就在工作的本身。”[10]在《毋宁死》中,委托人是有钱有势的城税局长,曾当面许以重酬,但霍桑在弄清对方的请求是让他寻找因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的女儿之后,就反应冷淡,办案过程中始终愁眉不展。面对包朗发问,他明确回答如果成功寻得女孩,那他就成了这个小官僚剥夺其女自由的帮凶。于是虽然他洞悉了案情,却选择隐而不宣,转而去探访包办对象的劣迹,直至当事人得以摆脱包办婚姻才公布实情。在《一只鞋》中,他像在许多其他案件发生后一样,应邀前往罪案现场,挖掘线索,探求真相,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与酬报相关的内容,被提到的是“交情”,即人物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偶然出现例外那也是为了捐助公共团体。霍桑认为,人的地位的高下在于他对社会大众贡献的多寡,他并不反对自己在破案中的作用被公开披露。当报纸上刊登有损自己社会声誉的消息时,他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同时竭尽全力去扭转局面,因为他认为这会削弱自己在社会中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与此相对照,福尔摩斯甚至在一开始就会向同伴提到即将获得的优厚报酬,或者在对案情胸有成竹时主动向委托人当面确认高昂的付费,在得到超出预期的酬报之后,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因为这在他眼中无疑是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社会对其个人权利无条件承认的必然结果。在对待社会声誉的问题上,福尔摩斯显得毫不在意,他多次主动向官方警探提出将他的破案功劳全部算在对方头上,也不希望对外公布案情时出现自己的名字,他甚至拒绝接受被英国人公认为终生荣誉的爵士封号。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时,多数是出于传递虚假信息以达成迷惑对手的目的的需要。福尔摩斯并不认为他自身的价值需要社会来确认。
三、小说中法律与正义关系的处理
在一些案件中,霍桑和福尔摩斯都选择了不将案件情况通报官方,对犯罪的人不诉诸于法律。在《白纱巾》中霍桑曾说过:“我们是不受法律拘束的,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就是正义和公道。”[11]霍桑在办案过程中的行为明显地反映出强烈的平民意识,即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又不违背个人的良知,这是当时的中国都市市民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观念。在《白纱巾》中他放弃追究凶手,因为被杀者是私贩米粮损害公众的奸商;在《逃犯》中他决定不揭出真相,因为死者是一个作恶多端危害社会的逃犯;在《虱》中他放走凶手是因为被杀死的是一个违背道德的社会败类;在《舞后的归宿》中,霍桑认为,在法律的立场上枪击王丽兰的赵伯雄应给予相当的处分,但当了解到死者乃是为了金钱刺探并出卖国家机密的特务时,他表示处分权不在他的手里。对法律和公理不能涉及的,就用市民社会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去解决。在《灰衣人》中,专帮富人作恶的律师自己从火车上摔下被轧死;在《浪漫余韵》中,打抱不平的侠士脱狱而去。福尔摩斯说:“我们作的调查是自主的,我们的行动也是自主的”[12]。福尔摩斯经常给予作案者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让他自己说出案件关涉的内情,然后再作决定。他总是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道德规范出发去对犯罪行为进行理解。在办案过程中,他采取行动时也不受社会观念的左右,只遵从于个人的判断。在《蓝宝石案》中他决定放过小偷,是因为这样可以挽救一个人;在《魔鬼之足》中他决定不向警方告发凶案的主谋,是因为认同凶手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感情,其实真正的受害者不是死者,而是煎熬在无尽的痛苦中的凶手;在《三角墙山庄》中,在犯罪方只对受害者造成微小伤害的前提下,他让对方付出经济赔偿了事,是因为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利;在《显贵的主顾》中无法用正常手段解决问题时,他选择从阴险凶恶的对手处偷走犯罪工具的方式来帮助受害人;在《斑点带子案》中,他甚至在明知会有致命后果的情况下,听任罪犯实施犯罪,在其自食其果后称可能是最好的结局。对于福尔摩斯而言,罪犯的作案动机源于个人的愿望,止于对个别人的损害,如果不公布则是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即便公诸于世也不会对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直接的影响。
四、小说中叙事时空的安排
在叙述的空间安排上,霍桑的案件多数发生在其居住地上海,而福尔摩斯经办的案件经常发生在远离他生活居住的伦敦的乡村。霍桑的探案过程总是被特定的社会氛围所环绕,叙事者时刻在强调都市中不同的空间所带来的差异,周围不断变化的行动条件迫使侦探随之进行调整,社会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福尔摩斯面对的叙事空间是具有象征性的,叙事者的安排其实是故意让福尔摩斯的探案经历远离社会,侦探个人才能的发挥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跟社会影响并无关系。不论是在英格兰或苏格兰或是国外,社会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在破案中可资利用的条件和工具,周围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提供的条件并无不同,侦探个人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时间的叙述方面,在大多数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中,都非常具体地指明了发生的年份,叙事者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这样一个特殊个体的行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同时我们可以体会到主人公的个性特征相对于不断变化的具体时间而言,恰恰是具有恒定特点的。具体年份对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而言,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符号,它的功能非常有限,往往只是帮助读者理解福尔摩斯也到了必须退休的年龄了,时代社会的变化对于他这个侦探来讲并无特别意义。而在霍桑探案故事中,则基本上找不到年度时间,《一只鞋》原稿第一句话就指明了案件发生在1921年间,这在霍桑探案故事中是极为少见的特例。如果稍作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许多霍桑探案故事中都提到具有相似点的案件。从逻辑角度看,它告知读者某案在某案发生之前,但试图进一步判断文本的逻辑顺序时就会发现陷入了混乱。这说明时间因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含在文本叙事中的社会时间。例如《血匕首》中提到“五四”运动,《别墅之怪》提到“在内忧外患夹攻之下”,《舞后的归宿》提到“我们的国家处在危急的时代”,《沾泥花》提到“异族人的势力”、“民族的枷锁”,《活尸》中提到“外侮当前的关头”,凡此种种。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与人物行为和故事情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血匕首》中的陆子华要自杀,是因为他被军阀收买成为学生奸细的身份暴露了。叙事者在暗示处于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阶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侦探的行动也映射着特定时段的社会道德要求。
五、小说中人物类型的设置
在古典型侦探小说中,通常主要有下列几类人物:凶手、受害者、侦探、次要的侦探、嫌疑犯、具有浪漫成分的女主人公、警察。侦探和次要的侦探无疑是侦探小说的中心,柯南道尔将福尔摩斯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探案天才,案件的侦破似乎全部是他单枪匹马完成的。对于福尔摩斯而言,华生只是案件的记录者和故事的讲述者,他个人的侦查才能无疑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在推理案情时他保持着绝对的自信,结案之前通常既不与人讨论案情也不提前透露自己的推断。在柯南道尔的后期作品中,侦探和次要的侦探之间的这种关系显得愈加明显,福尔摩斯往往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此相比较,程小青在处理霍桑与包朗的关系时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包朗作为次要的侦探,他的作用并不仅限于介绍和说明案情,他也拥有很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有时甚至不在霍桑之下,如在《第二弹》中,虽然在现场勘查之后包朗提出的判断被霍桑否定了,但最终事实证明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因此包朗在霍桑的探案过程中经常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程小青对侦探和次要侦探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柯南道尔起初是出于对文学的个人兴趣而开始创作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在获得可观稿酬之后决定弃医从文。柯南道尔笔下的犯罪故事虽然客观上反映了一些社会情况,但作者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描写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向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虽然福尔摩斯的言行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惩恶扬善的正义感,但柯南道尔从未将其作为改造读者思想的传声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小青,他在1945年出版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第三辑)》的序言中写道:“我在重写的时候,除了润饰、补充以外,还渗入了些时代常识,如一个公民应付事物的科学态度和对于社会、国家应有的职责等。……我相信侦探小说在复兴建国的途径中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对于青年的求知本能和推理能力具有启发的作用。”[13]上述写作意图的差别对两位作家处理作品中的形象特质和人物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人物往往个性极为鲜明,经常被福尔摩斯嗤之以鼻的官方警探时常出场,他们的年龄、样貌、个性可谓千变万化,有的人如苏格兰场警探雷斯垂得虽然备受福尔摩斯的奚落嘲讽,但他身上的优点也常被提起,他的种种表现更多地是起到戏剧化的效果,并没有让读者产生由衷的厌恶之情,叙事者绝没有将批判的矛头轻易指向司法制度,甚至在个别篇目中还出现了对福尔摩斯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能和他推心置腹的警察。不论福尔摩斯与什么样的警探打交道,他的个人才能都足以使他摆脱所有可能的阻挠和纠缠。而霍桑探案的叙述者则更多地提供了符号化的人物,连《一只鞋》新旧版本中的警署署长的姓名“墨佣”和“范通”都分别是“没用”和“饭桶”的谐音。这个人物起到的作用同很多故事中的警探是一样的,他们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侦查,常使无罪之人受到冤屈,读者对这类人物的评价不会比包朗对范通或许墨佣的感觉更好。虽然也有与霍桑长期合作的汪银林等人,但形象单薄,符号化的色彩很重,只是某类社会形象的代表。而叙述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揭示这些现象的形成原因,并使之直接指向了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制度。
在深入文本表面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直接受到西方古典型侦探小说影响的中国代表,霍桑探案映射出的文化视角与福尔摩斯探案有着巨大差异: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在建设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福尔摩斯以个人意识作为起点,以人性作为判断的依据,以个人价值作为行动的指针。而霍桑的探案行动总是以社会评价标准为出发点,以道德作为判断的依据,以社会的变化为调整行为的指针,最终仍然回到社会价值这个终点。
[1]卢润祥:《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3][6][9]程小青:《霍桑探案集(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70、372页。
[4][12][英]阿·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下)》,丁钟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339页。
[5]程小青:《霍桑探案集(五)》,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7]程小青:《霍桑探案集(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8]魏绍昌、吴承惠:《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9页。
[10]程小青:《霍桑探案集(十一)》,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11]程小青:《霍桑探案集(七)》,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13]程小青:《霍桑探案集(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Explo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eng Xiaoqing and Conan Doyle's Detective Novel from the Cultural Viewpoints
ZHOU D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society;individual;culture perspective;detective novel
The behaviors of the protagonist always express recognition with the individual value,choose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highlighting the strong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by Arthur Conan Doyle.But The detective story of Huosang by Cheng Xiaoqing considers Huosang as carrier and maintainer of social morality.The protagonist's personal value is attachment as a condi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llective.Their detective novel in the selection of social perspective,difference of working motivation and ways,the treat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justice,arrangement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the character type setting both have m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he distinct difference reflects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cultural concept.
I106
A
2095-5170(2014)06-0028-05
[责任编辑:周 棉]
2014-06-20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报·自由谈》的发展与‘星社’作家群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13SJB750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渡,男,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