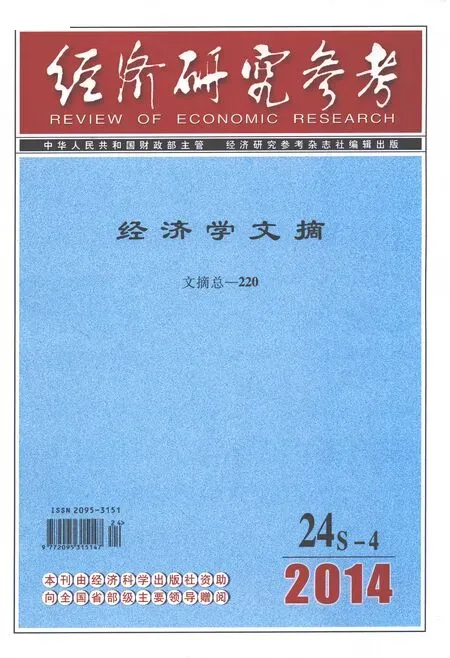用平常心看GDP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核,2013年中国GDP达到568 84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7%。这个数字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和议论,虽然它是14年来的最低增速。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把GDP增速看做“绝对优先”的指标了?还是由于整个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长趋缓),即使GDP增速低一些也不会导致失业问题,因此降低了对GDP增速的依赖?抑或,中国目前的潜在劳动生产率就在“七上八下”,7.7%恰是常态?
笔者认为,7.7%虽然算不上非常亮丽,仍是一份不错的答卷。最重要的原因是“基数效应”,即中国是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基础上实现这一增长的,且CPI同比只上涨2.6%,远低于年初3.5%的预定上限值。
按世界银行数据,2012年全球 GDP为72.44万亿美元(现价美元),中国为8.227万亿美元,中国已占全球GDP的13.36%,在这样的基数上,如果硬要追求类似以前的两位数增长,需要消耗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源和资金,实际上已无可能。
2013年中国比2012年增加了49 523亿元GDP,这个数字超过1994年中国GDP的全部,超过2001年中国GDP的一半,接近2006年中国GDP的1/4。
英国《金融时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测算出,中国2013年的GDP增量折合为8185亿美元,超过经济总量排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2012年总量为7882亿美元)。如果2014年中国维持同样的增量,这两年的经济增量加起来等于世界排名第10的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2012年为1.54万亿美元)。
中国增速是在下行。2010年渣打银行预测中国2012年增速为8%,到2030年之前的20年将实现年均6.9%的增长,从而在2020年总量超过美国,2030年总量达到美国的2倍。而在2013年11月,渣打银行调整了预测,认为中国速度会放缓,到2020年会有7%的年均增幅,2021~2030年增速将放缓至5.3%,延后两年到2022年超过美国。
只要中国经济增长是适度稳定的,不跌出底限(如6%到7%),不出十年,总量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有此判断,何必对一两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过多在乎?看待今天的中国经济,应该认识到,大的逻辑正在变化,从求速度到谋转型。例如,对雾霾中的人们来说,他们还会愿意用更多咳嗽换更高增长吗?
中国经济2013年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第三产业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1%(第二产业比重为44%);劳动生产率比2012年提高7.3%;单位GDP能耗下降3.7%;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比2012年提高0.5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2012年提高1.16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全年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233万户,比2012年增长30%。在服务业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提升和改善的迹象是可喜的。
宏观数据上和人们期待方向不太一致的,是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资本形成总额,而2012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超过了资本形成。显然,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有一定上升,投资仍是增长的首要动力。
投资不是不重要,但要校正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之间的不平衡,逐步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必由之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不久前在《求是》撰文指出,中国投资效率低下,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资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要高40%之多;中国投资率已接近5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80%。
王保安副部长在文章中还提出,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土地利用率不断下降;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很低;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依然在增长,主要靠的是庞大的储蓄和高投资率在勉强支撑。
在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倘若把高增长率作为主要目标,结果必然是透支和进一步扭曲,“好的坏的一起增长”,无法淘汰落后生产力。反之,速度下来一点,如果转向集约型发展,转向创新引领,转向优化产业结构,恰恰是正确的选择。
2013年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元年。如果2014年继续坚持这一基调,加强企业在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决策机制,打破藩篱,放开准入,则中国经济的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并涌现出更多新动力。
(晓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