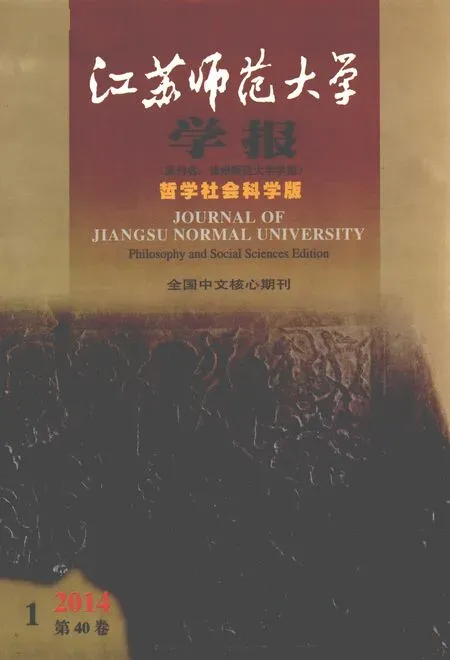论柏格森的“绵延”概念及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陈玲女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是20世纪富有感性、温情和浪漫韵味的法国式哲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期,我国曾掀起一股强烈的“柏格森热”,此后,柏格森哲学被我国学者长久地忽视。近几年,我国学者开始重新研究柏格森的“绵延”哲学,探索柏格森之生命哲学、直觉哲学、时间观等对当代社会及教育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柏格森“绵延”概念的解读,进一步阐释“绵延”对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价值。
一、何谓“绵延”
克服新困难;而本能则主要面向无意识,是一种对内容而不是形式,对自由而不是制度的认识,本能通过使用一种能自我制造、自我修复的有机工具来完成必要的工作。当我们不断用理智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时,我们便陷入了一种科学的、物理的、机械的思维之中,这种思维强调重复、逻辑和数字化,即要求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论,具有重复验证性。在柏格森看来,这是一种死的、无生命的、无时间的方式,它逐渐远离自由意识的生命进化方向。同时,理智让我们习惯于社会制度的约束,自愿地接受来自社会、学校、军队的规训,并认为这是我们签订社会契约、维持社会稳定所必须做出的牺牲。对于本能,柏格森认为:“本能是按照生命的形式形成的。”[1]它排斥附属于理智的习惯和制度的束缚,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的和自由意识的回归。正是由于本能的存在,个体意识才能逃脱理智的思维,进入一种更贴近生命本质的直觉思维。
2.从人的直觉进入绵延
本能的最佳表现形式是直觉,直觉将我们引向生命的内部,遵循生命内在的自由意识的倾向。因此,直觉是无偏向的,能自我意识,能思考其对象和无限扩展其对象,它意味着无止境的连续创造,意味着绵延。柏格森作为一位温柔的反抗者,他从不做彻底的否定。对于直觉与理智,柏格森认为两者并非对立存在,它们应该同时存在于人
(一)“绵延”是基于个体理智之上的直觉
直觉是柏格森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存在,它既非抽象的感觉或灵感,亦非模糊的感应,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法论,通过直觉所达到的“绵延”,才是个体生命进化的本质所在。柏格森认为,直觉可以让我们置身于生命内部,与生命的本能、智慧、记忆等相融合,以达至生命的绵延。这里的直觉不同于叔本华的直觉,它并非一种单纯的感性主义的存在,而是与理智相结合,或者说基于理智之上的直觉。只有这样的直觉,才是柏格森精心设计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直觉。
1.直觉的本能性倾向
柏格森认为,理智主要是一种制造和使用无机工具的能力,在无机工具面前,理智是娴熟的,它可以通过制造和使用无机工具,使个体有能力的生命之中,而恰恰是这种直觉(本能)与理智的融合,生命的绵延才得以进行。而我们的直觉知识也并非与科学知识相脱离,科学知识寓于直觉知识之中。1916年,柏格森在致H·赫福定的信中说:“原来在于利用生命的存在而起作用的本能,绝对能够从内部(尽管不是全面地,而且近于不自觉地)认识生命。因此,人的直觉便以反思的形式延伸、发展和转换存在于人身上的本能,并且可以越来越全面地拥抱和掌握生命的奥秘。”[2]即本能是对生命内部的认识,反思的形式是理智思考方式的一种,而直觉则是借用了理智的某种形式使个体的内在本能更加具有自由意识和创造性。对于柏格森而言,只有朝向自由意识的生命进化才算是真正的生命之绵延,而这种自由意识唯有通过人的直觉才能拥有。
(二)“绵延”是永恒的内在时间
任何有生命的地方就应有一本打开的记录时间的登记簿,缺少时间,生命就会是静止的,虚无的,毫无创造性的。柏格森所讨论的时间绝非数学意义上的时间,他认为数学上时间是一种可以分割的、不连续的时间,具有不真实性。历史上有人用物体的影子或者沙漏来表示时间,现代社会用钟表来表示统一的时间,这种时间的多样性正说明数学的时间并非真实的时间,而是一种主观的人为约定的时间。在柏格森看来,真正的时间应该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它与直接经验和绝对存在相关联,从直接经验中来,并在流变中不断绵延。
柏格森认为,静止是对时间存在性的否定,他借“芝诺悖论”说明,运动是一种经历着时间的流变过程,人们可以分割一个轨迹,却无法分割轨迹的形成,因为这种形成是一种前进着的活动,而不是对一个物体或几何轨迹的分割,并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隐喻——电影放映机制。电影放映机制是指电影放映是由一张张静止的电影胶片组成,将这些胶片放在电影放映机里,快速投射到屏幕上,便出现了人们视觉上的运动形象。而当我们单独看每一张胶片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运动,这就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运动由静止组成。柏格森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就是一种电影放映机制,人们往往相信生命的长河(电影)是由一个个不同的瞬间(胶片)组成,人的一生存在几个可以分割的阶段,如儿童期、青年期、老年期。这种阶段的划分实质上是对时间的分割,主观地切断了生命时间的连续性,也就造成了生命绵延在时间上的分裂性、不完整性。因此,柏格森认同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万物都在流变,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时间上。缺少时间,流变则无以完成;缺少时间,生命则无法绵延。
(三)“绵延”是个体生命的连续创造
创造即是一种发明,但这种发明与单纯无机工具的发明概念不同,它是新元素的不断“涌现”,具有不可分割性。创造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机械论的“必然性”和目的论的主观“预测性”,表现为绝对新元素的不断涌现。柏格森认为:“我们越深入研究时间的本质,我们就越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造,形式的创造,意味着全新事物的不断生产。”[3]
生命从最初的内部冲动开始,便向着进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在生命进化中,存在两种必然性:一种是能量的不断积累,另一种是自由意识。植物通常向着静止的、惰性的方向进化,而动物则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进化。生命向着自由的方向进化,始终与自由意识相联系。当生命处于自动性(非自由性)之中时,意识是沉睡的,而当意识处于创造性之中时,意识是被唤醒的,具有主动性。而人的意识区别于一般动物,正是在于人打破了自动性的枷锁,获得真正创造性的自由意识。
事实上,人的生命进化并未沿着其应有的方向进行,它逐渐偏离创造的自由意识,成为一种形式或制度存在,而非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此时,理智占据意识的上风,它让我们享受着习惯以及习惯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高效利用,同时,也让我们满足于习惯带来的懒惰和疲倦。习惯是理智的附属品,具有自动性、重复性。然而,生命的绵延从来不满于理智,因为理智天生拒斥创造。柏格森认为:“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创造……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我们之所是,但是,还应该补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4]与人的直觉紧密关联的创造以一种更贴近生命的形式,更贴近绵延。
(四)“绵延”是一种直接经验的存在
存在是绝对的,与直接经验相连,绵延从一切直接的绝对存在中来,它不需要任何中介和间接的传递。虚无是一个幽灵,是对存在的一种挑战,任何我们所认为的虚无,实际上都有那么一些东西存在着,使“虚无”成为一个伪概念。柏格森认为,存在以直接材料为基础,它面向真实的世界和形象,存在让我们直接地置身于绵延之中,不必依赖任何间接的虚无载体。
柏格森认为,正是由于时间的存在,流变才得以产生,然而流变并非凭空进行,它需要借助“存在”这个载体。柏格森区分了两种存在,即物质和生命。物质是一种无机物,是一种“死的存在”。物质具有杜撰各种可离析的“独立”系统的倾向,这些独立性包含着无限的层次,甚至最高级的有机体也不能获得其完善性,但只有在活生生的事物中才能充分实现这种倾向[5]。这种活生生的、能够作用于物质之上的行动倾向即是生命,它具有物质所不具有的创造性和自由意识,是一种“活的存在”,真正绵延的存在。尽管生命与绵延共存,但物质也并非完全脱离绵延,它分享着绵延的最低层次。柏格森认为,物质和生命同样具有绵延的性质,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层次,物质是与生命相反的运动倾向,是惰性的下降的运动,像蒸汽容器里凝结向下滑落的水珠,但始终有一些蒸汽没有凝结,它们努力向上,沿着物质性相反的方向努力保持着上升的运动倾向,从而获取了最高层次的绵延。由此,生命的存在与绵延得以共生,分享着绵延的创造性、自由性、连续性和时间性。
二、“绵延”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与人的生命和意识紧密相连,正是由于绵延的存在,人才能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一种独特的、创造的、自由的存在。学校教育强调“以人为本”,这种对人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尊重或外在塑造,更是一种对人的内在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唤醒。因此,柏格森之“绵延”对学校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严格的直觉知识
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崇尚理性,视理性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应有表现。在这种理念下,学校教育将理性科学的知识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数学符号和语言符号就像一个个图钉钉在学生的思维记忆中,使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记忆习惯地并顺从地接受外界信息的灌入,不再做任何徒劳的批判和创造。科学将一切无论人文还是自然的知识以固定和统一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使学生达到科学教育的目的——德、智、体、美的齐一性。这种齐一的科学知识在提供教学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恐慌,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被评价为“学习的机器”、“工具”。尽管如此,学校教育仍然拒绝直觉知识,他们固执地认为直觉知识毫无根据可言,它只是人之本能的偶然性触发,是模糊的、间断的,因此直觉知识不可教。
事实上,直觉知识是一种严格的知识,具有整体性、理解性和生成性。与其说直觉知识单独存在,不如说直觉知识与科学知识共存。例如,让学生认识正方形,当我们引导学生观察正方形像什么的时候,学生正是基于自己在生活中的观察和认识来比喻。这种源于生活的观察既是直觉知识的直接材料,也是具有必然性特征的科学知识,因此,严格的直觉知识并不排斥科学知识,它将科学知识融于其自身,触发人的本性和潜能。
(二)连续的创造性培养
创造是生命和绵延的必要条件,失去创造的生命没有任何自由意识可言。柏格森认为,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来说,存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永不终止的创造它自己[6]。理性过分依赖必然性,它将意识逐渐引向具有重复性、机械性的习惯。习惯是第二天性,它掩盖了“我”真正的本性[7]。当学校教育以单纯的理性和本质主义理念教育学生时,学生便成了纯粹的知识接受者,他们将习惯于任何知识的灌输,排斥创造。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惰性,学生越深陷于习惯,越拒绝创造,越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命令,而我们的教师却并没有将学生从习惯中拔出来,而是通过操控学生的意向性,让陷于流沙的孩子越陷越深。然而,生命的本质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学生的自由意识始终是一个无限绵延的过程,只有学校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自由意识和创造性的培养,关注学生的本能倾向和精神生命,只有让学生真正的本性冲破习惯的枷锁,他们才能真正回归其自身的原初自然状态,作为一个人和人的意识而不断创生、绵延。
(三)经验性的教学时间
分级式学校的重要特征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固定的内容。知识的总量一定,要使学生能够统一地完成学习内容,必然要求严格规定学习时间。然而,每个学生的成长具有独特的生成性,有其内在的经验的时间性。当前,学校中所用的任何时间往往是钟表时间,它强调效率、竞争,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柏格森认为,数学的时间恰恰是不真实的,它把钟表的空间性与真实的时间性相混淆,将我们限制在所谓的标准之中,使我们成为数学时间的附属品。当我们用钟表时间约束教学时,学生会首先依据自我经验的时间进行学习,如果这种经验的时间与钟表时间不符,就会超前或滞后地完成学习内容,从而制约了学生的自我发展倾向;在经验时间与钟表时间的冲突上,教师也会遇到同样的矛盾,每个教师都具有不同的语速和认知风格,当他们以本能的方式进行教学时所使用的是经验的时间,这就可能导致教学内容无法在规定的钟表时间中完成,如果严格限制教师在规定时间内教学,就会影响教师教学的灵活性、独创性,教学也就变成一种死板的输送符号的过程。古德莱德认为,学校教育应当打破铁床主义,让时间不再与知识严格匹配。经验的时间,在柏格森看来,即是在糖块融化过程中,我耐心地或焦急地等待的时间,是自我绵延的节奏和张力。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只有利用每个学生的经验时间来进行教学,让学生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才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对知识的学习真正抵达生命的内在本质,使其自由意识在其生命中绵延。
(四)内在自由的唤醒
生命自由与意识自由不可分割,意识的自由倾向在于冲破习惯的枷锁,唤醒其本能和创造的倾向。内在自由无关于外在制度、规定或人的束缚,而是一种精神的、创造的意识自由。德勒兹认为,问题的提出者往往是教师,学生的任务只是寻找答案,由此,学生就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而真正的自由在于让学生有决定的能力[8]。这种决定的能力更多的是让学生自己发明/创造,探求隐藏的或未知的存在,并非单纯地发现预先存在的答案。当下,大多学生认为获得个性解放、摆脱规章的束缚即是获得自由,这是学生对“自由”本身的不理解。因此,教师应强化学生的精神性自由,回归学生本能的创造性和意识的自由状态。
(五)学生本质差异的关注
柏格森认为,当我们用多与少来思考问题时,我们便忽略了性质的差异,而性质的差异恰恰是根本的、内在的差异。在以往的教师观念中,学生具有成绩高低不等、品德优劣等空间性差异;教改之后,教师观念得以改变,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同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以同样的态度,把同样的知识教给每一个学生。表面的差异对待具有严重的功利性倾向,是一种为了效率、成就而实施的差异对待,对差等生而言,是对其基本尊重权的缺失;而等同对待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教师认为每一个学生是等同的。在两种教师观念中,无论是表面的差异还是平等地对待,都直接而彻底地忽略了学生的本质差异,忽略了学生内在的多样性,尤其是这种齐一性的教师观念则更加贬低了生命的本质。由此,教师在面对学生实施教育时,应首先关注学生的内在需求、兴趣爱好、精神向往等软性特征,从学生本身的内在差异出发,对不同学生施以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教育教学。柏格森认为,性质或本质的差异具有时间性,人的意识不可能两次经历同一种状态。因此,教师在关注学生间差异的同时,也要注重每个学生在不同时间的差异,甚至对学生个体的阶段性差异的关注更加重要。抛弃一成不变的外衣,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生成、变化和绵延,这是柏格森“绵延”概念给予学校教育的重要启示。
[1][3][4]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139、16、12 页。
[2]亨利·柏格森:《生命与记忆:柏格森书信选》,陈圣生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5]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牟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6]加里·古延:《20世纪法国哲学》,辛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7]尚杰:《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8]吉尔·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张宇凌、关群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