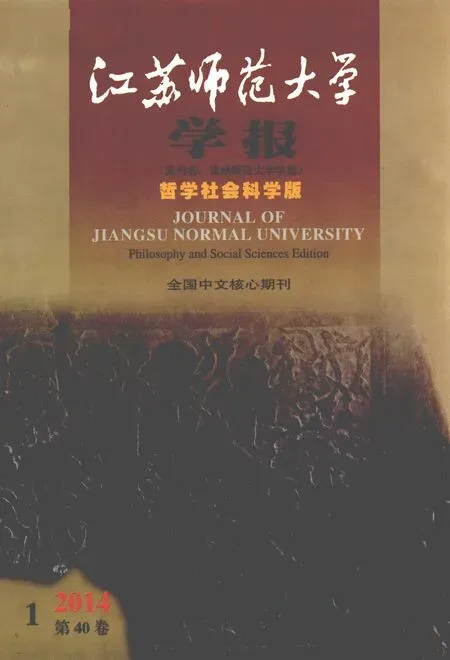民国时期詹安泰的文学本位论及其历史贡献
马 晴 李昌集
(1.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2.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詹安泰是民国时期的“四大词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词学、《诗经》、《楚辞》和文学理论等方面,颇多建树。民国时期,詹安泰对古典诗歌文学特质的理论探究颇为倾心,据詹安泰1951年填写的《广东省公私立高等学校教职员概况表》,他在民国时期即计划撰写《中国诗学》一书:“中国诗学分十章,已成体制、韵格、声律、意境、风格、法度共六章,约十万字”[1],体现了詹安泰建构系统化古典诗学的意识。詹安泰在民国时期发表的论文,《詹安泰全集》收录有《孟浩然评传》、《论寄托》、《诗的批评》、《词境新诠》、《无盦说词》,此外还有于《文学月刊》等发表的《论诗之风格》、《文学与文学家——从文学的独自性说起》、《关于词的批判》、《论诗中的理致》、《谈拙质美》等五篇论文。诸论不溺时风,独抒己见,在民国时期的诗词理论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今天的古代诗词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选取詹安泰先生的文学“本位观”与“自性”论两个命题,探讨詹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詹安泰的文学本位观与“风格”“境界”说
新文化运动以后,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向现代化,科学性、理论性、逻辑性增强,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一些学者立足于学科建设展开对基础概念、范畴的研究。蒋寅先生在《20世纪的中国诗学》中指出:这一时期“有意识地清理诗学基本范畴、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是学者们为学科建设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2]。
詹安泰的古典诗学研究是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展开的:最早的论文《论寄托》系统梳理了寄托的含义、作用、方法等问题,此后的《论诗之风格》、《词境新诠》等,相继展开了对文学范畴富有新意的辨析和阐述。例如,民国学者对“风格”一词论述颇多,由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风靡一时,论者大多认为产生“风格”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环境,如远寄的《文学与个性》认为:排除历史和社会的影响,还能余下多少“个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所谓‘人’者,究有若干异于别人的个性,究有若干值得宝贵的异于他人的个性,试一审查,恐怕是不见得就如神圣论者所想像的那样的丰富。每一个人都在历史的直线与环境的横线的两线交接上占据了一点,上下不能不受历史的影响,左右不能不染环境的色彩。所谓个性,论理应为减去此等影响、色彩及其人共同者所剩余的差。这差究有几何?这差即使为数很大,那大众值得注意的又究有几何?”[3]傅东华持论更偏激,其《风格论》引《文心雕龙》所云影响作家风格的四要素“才、气、学、习”,将“才”、“气”归纳为内在因素,“学”、“习”为外部因素,认为“才”“气”属于一种遗传,其得意发挥是外在因素“学”“习”的结果,“故实际上风格只有一种因素,就是外的因素——社会的因素”[4]。洛如的《文学与个性有关系吗》一文表述得更极端,认为文学的解读根本无须了解作者的人格:“须知一篇作品能给我们的兴趣,乃是作品中的内容抓住时代的精神,有引起我们同情的魔力而使然,并不是甚么作者的人格的表现,我们也不问作者的人格如何。”[5]在这些观点的辐射下,社会因素成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前提和研究内容。1947年,大东书局出版的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开宗明义提出:“文学为社会精神产物之一,不知各时代社会上政治之背景,即不能明白各时代文学之底蕴:本书有鉴于此,于各时代政治之兴替略叙述焉”[6]。社会环境当然对文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提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新视角,对推进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自有其贡献,但将社会因素在文学创作和解读中的意义绝对化、唯一化,忽略文学创作主体在文学生成机制中的关键作用,无视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就极易成为一种机械化、程式化和变相的“社会阐释”,从而消解了“心灵的对话”这一文学特有的功能价值,因此也就难以圆满解释作家风格多样化的缘由。
与上述强调和夸大“社会决定论”的观点不同,詹安泰提出:作家个人因素在文学创作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以“风格”作为阐释的切入点,在《论诗之风格》中首先系统梳理了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风格”的涵义,直指当时学界对风格解释的不足:“近顷论文,始侈谈风格。然辞意所属,多模糊影响,殊不清晰。其选译外籍者,亦颇踳驳,不易划定义界。(英文style,近人译作风格,傅东华谓此名词之义界几千年来批评家与哲学家聚讼不决。)郭绍虞云:‘由文之形式言,语其广义而说得抽象些,便是风格,语其狭义而说得具体一些,便是体制’。(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编第二章第二节)语意实为着实,顾亦不甚确当。”[7]詹安泰认为:仅仅从形式上定义风格,不免“以偏盖全”、“舍本逐末”,不足以多层次地说明风格的产生,“夫风格者,足以包括形式,固不限于形式也;足以包括体制,而非外于体制也。以形式定风格,既偏而不全;以风格定体制,尤拘而寡要”[8]。由此提出:风格为作者独特的性格、思想、兴趣、气质等所组成的作家“个性”,及其独特的艺术“自法”所共同作用而成,“盖人之禀赋,良有不齐,于人格所共有之通性之外,又必有其‘自性’(即所谓‘个性’);其发为文辞也,于人人所共有之通法外,又必有其‘自法’(即所谓‘手法’)。‘自性’藏于内容之中,而‘自法’见于形式之表。”“以特殊之‘自性’运以特殊之‘自法’,而风格于是乎成。故风格也者,不仅存于形式,不仅存于内容,亦可见于形式,亦可见于内容”[9]。
显然,詹安泰的观点更符合文学的特性,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历来有“文如其人”之说,作者的性情人品乃是品味和评价其文的要义之一,詹安泰的研究立场,隐含着一种“国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学术意识,在当时唯西洋马首是瞻的风气中,这种学术上的独立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基于这一学术观念,对作家独特的“自我”艺术手法的重视,成为詹安泰研究中的主命题之一,贯穿在其《词境新诠》、《文学与文学家:从文学的“独自性”说起》等一系列论文中。
《词境新诠》发表在1947年广东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文教》创刊号上,主要讨论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概念。静安先生提出的“境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但《人间词话》并没有对“境界”加以理论的阐释,遂使“境界”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朱光潜先生的《诗论》是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一部专著,从心理学、美学的角度分析“境界”系由内在之情趣与外来之意象契合而成,认为所有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强调“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10]。朱光潜的论述一时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如刘沧萍《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认为:“‘境界’之含义,实合‘意’与‘境’二者而成。”[11]叶鼎彝在《广境界论》中提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并使着真景真情融成一片,而且含蓄蕴藉,不落言诠,这就叫做有‘境界’”[12],唯此才能产生“意在言外”的妙趣,从而将“情景交融”作为具有“境界”的不二法门。这一观点符合王国维的初衷,其《人间词乙稿序》有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3]但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境界”与“意境”有一定区别,后于《人间词乙稿序》的《人间词话》所以最后确定“境界”概念而不是“意境”,足见“‘境界’一辞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处。”[14]
詹安泰早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针对当时认为“景”在“境界”中的不可或缺,詹安泰在《词境新诠》中提出了个人的独特观点:意象也有“非自然景物所构成”,“情趣是可直接描绘者,情趣本身可构成意象,不必假借任何具体意象而后表见也”[15]。考察古代诗歌的实际,并非全都是写景诗,还有很多抒情、叙事诗,如果把“情景交融”作为衡量诗歌境界的唯一尺度,那么势必要将大量诗歌排除在外。因此,“情景交融”并不是品味和衡量诗歌“境界”的唯一视角,也不是境界产生的必要和唯一的条件。情趣之触发,并不只限于自然景物,“诗心可独自生发,非必要借自然景物感兴”[16],情感直诉亦可成诗歌的一大境界。
由此,詹安泰进一步提出诗歌境界是“情趣”和“表现”的双重建构:“窃以境界形成之要素,第一为‘情趣’,第二应为‘表现’。假如以情趣属内,则表现属外;以情趣为实感,则表现为外相”[17]。这里,“情趣”成为构成境界的首要元素,而“表现”,则法有多门,既可直接倾诉,亦可“情景交融”,更可二者的结合,变化无尽。但“情趣”是第一位,是“境界”的根基所在,没有“情趣”,便无由“表现”,“情趣可以不需外来的意象而直接抒写实感,但无表现则决无抒写实感之可能,故二者实有不可离立之统一性”[18]。在《关于词的批判》一文中,詹安泰对文学的“表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所谓‘真诚的表现’,它并不像历史家一样只是很笨拙地作那实际人生的记述,而是艺术的创制。它重在表现,而且是有功能作用的表现。”[19]
可以看出:詹安泰对“境界”构成论述的根本,通向他对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视,与其文学风格论将作者“自性”作为文学风格之灵魂的观点,可谓一脉相承,互为表里。60年后,叶嘉莹先生对“境界”概念的阐述,可谓是詹安泰当年观点的跨世纪呼应,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叶先生提出:所谓“境界”的产生,“实在乃是专以感觉经验之特质为主的。换句话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及”[20]。而作家的表达能力,“乃是欲求作品中‘有境界’的第二项条件”[21]。亦即詹安泰所曰“非表现则境界无由出”[22]。这一学术上的“跨世纪呼应”,恰是对詹安泰先生民国时期学术研究历史价值的肯定。
二、詹安泰的文学“自性”观与文学解读
文学“自性”观,用詹先生的表述即文学的“独自性”,是为詹安泰文学释读和文论研究的一个根本理念,是其以作家为文学创作的本位——“以人为本”文学观在文学阐释学上的必然延伸。代表论文为1946年发表于《新时代月刊》第一卷第9期上的《文学与文学家——从文学的“独自性”说起》。文章开篇云:
文学,不论新或旧,都有其和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独自性”。因之,研究文学的人,尽可以站在哲学的观点或利用科学的方法,却不能不懂得这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自性”。换言之,必得针对这特有的“独自性”去研究文学作品,然后才能真切了解这作品的真相而收到研究的实效。
什么是文学的“独自性”,詹先生没有以今日习惯的“理论”语言予以“系统”阐释,而是以一种民国时期普遍的“白话论文”风格,以平常话语娓娓道来,征以吾国前贤之语,间引西方理论,举以作品解读实例,读之轻松而时时令人深思。以今日理论术语和表述方式概括之、提炼之,所曰文学的“独自性”,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文学作品字面描述的事物——即文学的“直观图像”,与作家心中要表达的内容——即“图底指意”,并不一定直接对应和统一。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以诗词为最典型,其描述的一切形象,在本质上都是表现作家思想情趣的一种“意象”,“文学的世界”并非“实际的世界”,而是作家将“我心”融入客观世界后,重新创造的一个新的世界,是一种特殊的“唯物”和“唯心”的奇妙统一。因此——
其二,文学接受的根本机制,是接受者进入诗人的情境后,与诗人生活感触的交流和对诗人之心的感悟。因此,对诗词的释读理解,人们津津乐道和锱铢必较的典实、本事乃至诗人的生平故事,只是接受中的桥梁,而非接受的根本。也就是说,文学接受真正应该得到的是“人”而不是“物”。文学“是作者的生命溶液所结成,渗透了作者人生的全部”[23],接受者应当将诗人和作品合为一体,“不容分开对待”。
以上从文学创作和接受两个维度说明的文学“独自性”,贯通其间的共同一点,即“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本质,是一种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现、回味和“阐释”人的心灵的“文”学。由此根本认识出发,詹安泰对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提出了完全与众不同的见解:
文学作者和作品既不容分开看待,所以虽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文学作品,读者仍应看出作品中间的事而揣摩出它象征或所影射的究竟是什么,而不应把它和作者划分鸿沟,有所歧视。因之,一般所谓“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根本也就不很正确。“境”由“我”出,那有无我之境?“我”融“境”中,即我即境,既无所谓“无”,又安所得“有”?“境”与“我”是不可分解也不必分解的,一分解便不免陷于偏执了。[24]
今日读这段话,也还有“惊世”之感。平实而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是就“表现”方式而言的,“有我”指“我之色彩”直接显露于语面;“无我”则指语面上的一切仿佛都是一种客观的“自在”,此“自在”,并非就是纯自然,而是一种文学的“境界”,同时亦即“我”的一种人生境界。因此,“无我”只是将“我”隐藏起来,并非是“我”的真正消解。而詹安泰则从其所持的文学本位观和“独自性”出发,以一种对文学的“哲学”思考,否定文学有“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区分。严格说来,两种观点并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对话,但詹先生对“有我”、“无我”之境的否定依然是有意义的,其给以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面对西方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论提出的“纯客观叙述”时,当我们将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到文学领域的理论探究时,当我们深思“自然是人类的最终决定者”这一人类的终极法则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上的一切都因有人的存在才产生意义。从这一角度而言,“有我”是一切文学的“意义”得以产生的根本依据,詹安泰曰:“我融境中,即我即境,既无所谓无,又安所得有?”[25]其深层指向的意味即在此。
因此,詹安泰的文学“自性”论,是其“以人为本”的文学本位观的一个子命题。由此延伸的另一个子命题是文学作品的解读方法论——“文学,不论新或旧,都有其和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独自性’。因之,研究文学的人,尽可以站在哲学的观点或利用科学的方法,却不能不懂得这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自性’。换言之,必得针对这特有的‘独自性’去研究文学作品,然后才能真切了解这作品的真相而收到研究的实效。”[26]而要达到“真切了解这作品的真相”,从文学的“独自性”理解每一个作家,必须“把他所有的作品通统看透了,然后打定观点,才不致陷于以偏盖全的错误”[27]。如此,才能确当地“诗外推求”——在把创作主体的整个“人”理解透彻的基础上,才可能将“诗外”的历史环境予以“知人论世”的确当阐述,才能避免仅凭一己之“会意”而对“寄托”的过度阐释。
上述詹安泰的“文学解读方法论”,基础和核心在“真切了解这作品的真相”,否则其他的一切都是奢谈。这一朴素的“方法论”,当然不如当前“阐释学”之类那么“理论”和深奥,但却切实而有效。姑举其对唐代温庭筠[菩萨蛮]一词的解读个案,以具体领略其“了解真相”之“法”: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
这首词,《国文月刊》第36期上刊有学者的如下笺释:
此章写别后忆人。“凤凰”句意,不易知其所指,或是香炉之作凤凰形者,李后主词“炉香闲袅凤凰儿”。金缕指凤凰毛羽,犹前章之翠翘金缕双鸂鶒也,或指香烟之丝缕。或云:金缕指绣衣;凤凰,衣上所绣。郑谷《长门怨》:“闲把绣衣泣凤凰,先朝曾教舞霓裳。”不知孰是。“牡丹”句接得疏远,参看《忆秦娥》讲解中“趁韵之法”。歌谣之发句及次句,有此等但以韵脚为关联之句法。另说:牡丹非真牡丹花,亦衣上所绣。微雨是啼痕。“意信”彊邨丛书作“音信”,是。四印斋本误,当据改。燕以春社日来,秋社日去,曰“双燕回”,见人之幽独,比也。[28]
对此,詹安泰评曰:“笺释了许多,前段只‘或云:金缕指绣衣;凤凰,衣上所绣。’算是不错,此外所说的都成废话,根本就看不清这词的作意。后端只最末句‘微雨是啼痕’说得不错,以前所说一无是处。这词在飞卿各词中是比较易解的一首,怎么解得这样吃力而仍说不到它一贯的线索来呢?”再看詹安泰对这首词的释读:
飞卿这词是写一个女人对其所爱的男子别了太久想念得很难堪的情事。首两句写夜绣难堪之情况——第一句写夜绣,第二句写难堪。凤凰指所绣之物,……金缕,绣丝之由金黄色者。着一“盘”字,则绣时之情形如见。相对,犹第一首“双双金鹧鸪”之“双双”,第九首“金雁一双飞”之“一双”,惟其“相对”,才足引动幽独之人的念远之怀,更由念远之怀之难堪而垂泪,已引入下文意。第二句牡丹指女人——即夜绣之人。把牡丹和美人对比,在词里有人用过,……“微雨”即指泪痕,着“一夜经”三字,……可见出终夜不眠的情状,同时,暗中也逗出下文晨妆。第三、四句是写晨妆及顾影自怜的情况。鬓轻,……鬓而言轻,有两层意思:一者表示思念远人太久了,鬓不觉就稀薄了,近于“鬓凋”的意义;二者表示相爱者不在,倦于修饰的意思。……“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不在,则画得油亮也枉然,不如其不画,历久不画,就淡薄——也即是轻了。……双脸长,是表示瘦了,瘦到欧阳炯词里说的“瘦得不成模样”的意思。……经一夜的悲啼,双脸就不得不长了。第五六句言久别的情况。栏外垂丝柳句包含两种意味:一种是属于时间,一种是属于心境。言前种柳,今已垂丝,别久不归,何以为情!我这儿加添一句前时种柳,不是无根之谈。古人感怀今昔,时时要把种柳做材料,……如欧阳修词“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都是实例。……则此句虽写景物,也富有恋别的情味了。末两句言不但人不归来,连音信也杳然无踪,而社前的双燕又故意飞回,惹起人之羡慕,恼乱人之心曲,写到这儿,把热望与难堪,全盘托出了。飞卿词多数以景结情,极有余味。说双燕是“比也”似太胶执。[29]显然,詹安泰的释读圆融而贴切。两种解读,有繁简之分,在“模式”上则无区别。但在“解读意识”上,却有耐人寻味的差异:詹安泰是将词中人的行为、动作、情感、心理和场景贯穿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释读的:“首言夜绣流泪,自成一串;次言照影自伤,又是一串;次言晨妆后触物怀人又是一串;最后以热望和难堪收结——通首体法,均以两句成一小段,而段段互相衔接。前阕抒写情事;后阕两串均一句情事,一句景物,而两串中的情事和景物又各自紧密地黏合着。层次分明,天衣无缝。”[30]
詹安泰释读的基本立场,首先是把词中人作为一个“活”的人,以“人的观照”为释读的前提和指归。而这“观照”,既是作者的,又是读者的,也就是说,读者和作者首先在“人的观照”上取得了一致。由此,词中似乎“不易知其所指”与“不知孰是”的语、句——其语面“图像”与客观形象不能直接对应的“文学的形象”,便得到了真实的还原而获得了圆融的解释。可以看出:詹安泰对这首词的解释,正是对其提出的文学“自性”特有的“表现性”与接受机制的具体演示,也是其“以人为本”文学本位观的具体展开。
今天,詹安泰的这种释读被称为“鉴赏”,似乎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释读基础,能够进入“高层次”的、具有独立见解的研究么?例如,提倡“不隔”的王国维十分推重冯延巳,认为温词是有点“隔”的,故谓温词犹如“画瓶金鹧鸪”,颇有堆砌之嫌。而詹安泰则在释读温词的基础上指出:“飞卿的词,虽然镂金错彩,华藻纷披,看似费解,实则命意谋篇,均走正常的路子,且偏于严谨缜密,并没有什么很费解的地方,在唐五代词中,较之冯延巳的词多用惝恍迷离的意境者还易解得多。”[31]两种观点,见仁见智,当然还可继续讨论,但如果没有释读功夫建立起来的学术自信,便不会有胆量提出与学术大师的不同观点。再看时下的不少“研究”,每对作品仅仅蜻蜓点水便作种种“高深”的理论发挥,詹先生的作品释读——基于对文学“本位”与“自性”深度体认的释读,恰是一面对照反思的明镜。
詹安泰在民国时期提出的“文学本位观”和“文学自性”说,是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个脚印,其深层意味和启迪我们反思的是:文学中的“人学”命题,是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本根命题。对“文学即人学”这一简赅而朴素的命题所持的立场和观念,决定着对文学的释读和理论阐释的立场和路径。詹安泰先生的观点,并非这一命题的最终解答,随着当代学术的进展,进一步的思考和学术实践必将继续。
[1][15][16][17][18][25]詹安泰:《詹安泰全集》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2、282、281、283、284、28 页。
[2]蒋寅:《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傅东华:《风格论》,《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1号。
[4]远寄:《文学与个性》,《微音月刊》,1931年第1卷4期。
[5]洛如:《文学与个性有关系吗?》,《突进杂志》,1932年第1卷5期。
[6]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大东书局,1947年版,扉页。
[7][8][9]詹安泰:《论诗之风格》,《龙凤月刊》,1945 年第 1 卷1期。
[10]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1]刘沧萍:《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人间世》半月刊,1945年第17期。
[12]叶鼎彝:《广境界论》,《国文月刊》,1945年第49期。
[13]《人间词·人间词话》,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19]詹安泰:《关于词的批判》,《民主时代》,1947年,第1卷2期。
[20][21]《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119 页。
[22][26]《詹安泰全集》第5册,第284页。
[23][24][25][28][29][30][31]詹安泰:《文学与文学家——从文学的“独自性”说起》,《新时代月刊》,1946年第1卷9期。另:为省篇幅,引文中的若干具体释例以省略号代之。
[27]浦江清:《温庭筠菩萨蛮集解》,《国文月刊》,1945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