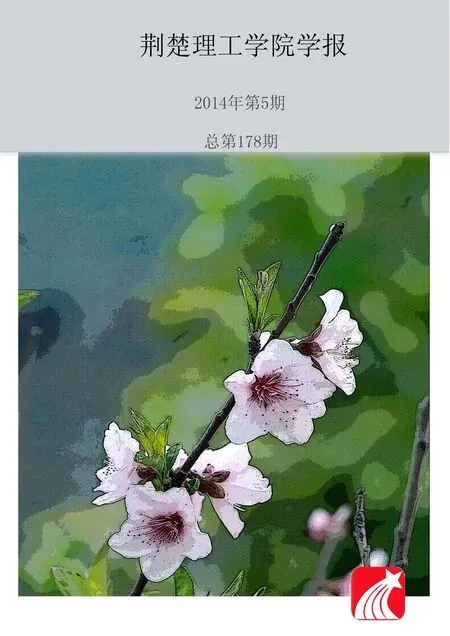建国初传记故事片的身体寓言
叶志良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 311231)
建国初传记故事片的身体寓言
叶志良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 311231)
建国初期拍摄的传记故事影片,对传主人物的选定与处理,以及由传主身体统率整个故事叙事所要承载的内涵与寓意,本身受制于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的深刻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无论是对历史人物还是对当代英雄的传写,当代身体寓言的建构,承担着政治意识的隐喻功能。
传记;故事片;身体
在中国当代电影中,“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1]。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身体是性别建构和再现的最重要的载体。不同性别身体上的不同表现并非是自发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因此,身体是文化最为直观的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历史、社会身体真实呈现的电影传记意识普遍觉醒,以身体书写为目的的传记故事片呈现蓬勃兴旺的态势。从旧时代过来的跨代的电影工作者,企图通过传记电影传写真实人物来阐释历史,于是三类展示不同身体的传记故事影片横空出世:一是率先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的《武训传》;二是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如《宋景诗》、《李时珍》、《林则徐》等;三是革命英雄传记电影,如《赵一曼》、《董存瑞》、《白求恩大夫》、《聂耳》、《刘胡兰》、《雷锋》等。然而,传记影片诞生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这自然也缘于传记人物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体表演。苏珊·波尔多在《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现》中论述到,身体是被文化所规定的,文化价值(如政治、经济等的价值)对身体的想象都镌刻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身体不是文化价值的“自然”起源,身体本身是被文化塑造的[2]。显然,建国初期传记故事片传主人物的选定与处理,以及由传主身体统率整个故事叙事所要承载的内涵与寓意,本身受制于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的深刻影响。用皮埃尔·布尔迪欧的话来说,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它也是社会控制的实际和直接的中心所在[3]。
一、《武训传》的身体批评与政治批判
故事片《武训传》是横跨新旧两个中国、两个时期的作品,也是在旧中国孕育而在新中国最早推出的传记故事片。对《武训传》的肯定与批判,是新中国意识形态控制的必然结果。这场运动的核心,无疑是围绕着影片中武训这个人物,或者说这个人物的身体展开的。因此,《武训传》事件,实际上就是一件身体的事件,身体是电影《武训传》命运的政治隐喻与宿命。让编导孙瑜意想不到的是,这部由他和他的团队精心谋划多年且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品,公映后却遭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这场在1951年开展的持续半年之久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是建国后新中国文坛上第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毛泽东主席对思想文化界发动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
《武训传》电影筹拍工作可以追述到1944年的国统区重庆,陶行知送《武训先生画传》,希望电影导演孙瑜能据此把“兴义学”的武训的事迹拍摄成电影。作为一名留美归国的优秀导演,孙瑜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拟将影片定位为“历史传记电影”[4]。孙瑜以《武训先生画传》为蓝本,修正了历史上武训的形象,将其由历史上的“苦大仇不深”改为“苦大仇深”,并且添加了许多有关阶级斗争的元素。因此,电影中的武训,首先是一个艰苦奋斗、“行乞兴学”的道德圣人,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符号。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有过孤儿乞讨、少年扛活的经历。因为没有机会上学,一再受到“知书识礼”的张举人的欺负,萌发出穷人要有文化的强烈念头。于是坚韧努力,终办“义学”。电影的主题是通过表现传奇人物武训以穷苦之身兴办“义学”的壮举,用生命来实现朴素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孙瑜所说的“他(武训)是心甘情愿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真正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4]。同时,筹拍过程中新中国的成立,在告别旧世界时,又使这个道德符号有了必要的政治包装。孙瑜在《编导〈武训传〉记》中指出:“《武训传》描述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虽然他的兴学在当时不可能解放穷人;他的那一种个人的、苦行僧式的、到处下跪(这是武训限于历史条件下他能力范围内所采取的斗争方式)的斗争方式不足为训,观众可从影片里看出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正确领导之下,才可以铲除封建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4]。于是,电影《武训传》由正剧改成了悲剧,对武训求乞兴学定性为“悲剧性反抗”,并对传主采取了“批判与歌颂”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对他不革命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歌颂了他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从道德层面到政治层面这样的赋形,深藏创作者的良苦用心,赋予了武训这么一位古人新中国电影主人公的身份证。甚至虚构标签阶级斗争的周大造反,还让女教师说:“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电影史学家启之认为:“这一改换是意味深长的,这里既可以看出旧上海的电影艺术家向新政权诚心诚意的归附,又可以看出叙事艺术在应对政治话语时的笨拙生硬,同时,这里面还包含着‘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试探与讨好。”[5]121
《武训传》于1950年末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公映后,一时颂声盈耳。上海的报刊杂志首先长篇大论地发表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极为夸张”的颂扬文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谓好评如潮,口碑载道,迅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化热点。但这个热点的形成有点“不合时宜”。尽管电影的编导拍摄《武训传》是为了“配合文化建设的高潮”,但武训不惜以毁损自己人格的方式来乞讨兴学,大力颂扬武训这样的“奴才”,与毛泽东的斗争反叛性格水火难容。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修订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言辞颇为严厉:“《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6]《人民日报》社论一锤定音。毛泽东选择从这部电影入手,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启之认定《武训传》“批评与歌颂结合”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达话语。“两种话语提供了两种历史观,两种历史观有着不同的政治选择,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动力的历史观自然要选择革命,而承认阶级合作者自然要赞同改良。因此,影片在提供了两种历史观的同时,也提供了对革命与改良的不同阐释。孙瑜和他的同事们、领导们以为,加上周大造反这一条线,就可以使影片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然而,这一文、一武之间的关系却成了陷影片于政治灾难的陷阱”[5]117。在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武训实际上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1),“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7]。
《人民日报》社论和社论后掀起的批判运动,上升到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给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彻底定性。一场文艺讨论一下变成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影片宣扬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二是影片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三是影片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作用,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连孙瑜也公开承认了错误,认为“《武训传》犯了绝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8]。在刚建立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内,整个政策自然延续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脉络,但社会诉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瑜在晚年留下一段话,表达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困惑:“在批判的当时,曾有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曾在中国解放前起过相当影响的一个进步‘电影公司’,一个一贯拍摄‘反帝反封建’的电影的昆仑影业公司竟会在解放后拍摄一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鼓吹‘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武训传》来呢?会有这种可能吗?”[9]现在看来,完全有可能。这不是因为影业公司的立场和创作者思想的偏移,而是导致这部影片命运历史性转折的关键在于建国前后新旧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冲突。当1944年开始构思、创作剧本时,在旧的社会机体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武训显然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者与启蒙者,作为一个来自平民的苦行者,完成对传统文化秩序的重振。这自然是一个值得颂扬的正面形象。但当这部在解放前构思在解放后完成并正式公映时,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全新的意识形态,刚刚获得合法身份的无产阶级需要文化重建为新生政权的合理性做出注解,诠释新政权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此时的《武训传》仍然沿用解放前的思想定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改良主义,显然是一种反动乃至是对新生政权的威胁。当无产阶级需要继续革命的时候,武训作为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确是旧有文化、旧有秩序的维护者。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娴熟地运用“革命”、“斗争”话语的毛泽东,自然不能认同改良主义的武训。对武训的承认,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认新生政权不过是对旧有秩序的恢复与维护。所以,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话语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尝试,更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原有秩序的批判和对建立新生秩序的努力,是新中国面临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新生政权对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10]。
二、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的身体改造
对一个历史人物身体的否定,必然要从另一个历史人物身体中寻找提振的方法与路径。对《武训传》的批判,无意中催生了电影《宋景诗》的诞生。调查组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将武训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同时,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在武训行乞兴学的第二年,他的家乡爆发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的农民起义。《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开篇就将宋景诗与武训作了比较:“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所污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致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致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1)
在建国初期传记故事影片的创作中,《宋景诗》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如果能再造一个体现毛泽东农民造反观、创造一个让毛泽东满意的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岂不是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形象的最有力的批判,也是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最好反映。于是,在整批孙瑜《武训传》的同时,“为了批判武训,竟发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领袖。于是立即成立班子,搜集有关资料,特请名剧作家陈白尘挂帅。剧本反复修改,上抓下赶,终于完成。因为《武训传》是上海拍的,《宋景诗》的拍摄也应该由上海担任,即所谓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也是最好不过的自我批评。在落实导演人选时,理所当然地考虑让迫切要求拍戏的上海导演郑君里来担任”[1]。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知道受批评的孙瑜的低落情绪,衷心希望对中国电影有过重要贡献的老艺术家不要从此消沉,力邀孙瑜与郑君里联袂导演《宋景诗》,借电影的拍摄,让孙瑜和整个文艺界乃至广大群众都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视。显然,选择编导以及编导的身份问题与选择题材、人物同等重要。如何让自己获得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革命者”的身份,并且让自己和自己创作的作品获得主流的认可,必须肃清自己不堪的过去,而让自己纳入到主流社会轨道之中,无疑需要寻找能够甄清自己立场的人物形象。而衡量的砝码无非是“领袖意志”和“政党伦理”。“政党意识形态——伦理——国家的织体建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形式民族国家的社会实在和日常生活结构,这三个要素是互相关联并在结构上相互支持的”[12]。既然政党意识与政党伦理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那么深处其中如履薄冰的老一代艺术家,无疑陷入更大的困境。孙瑜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曾请缨执导《宋景诗》,但“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伪投降’。问题是这一‘伪投降’至今仍然是个大问号”。“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9]。孙瑜满怀希望真诚为新中国电影再立新功,并借此在思想上彻底改造自己,却因《武训传》和《宋景诗》彻底摧垮了自己的肉体和精神。
原因自然还在宋景诗本身。身体问题再次成为政治事件。宋景诗在中国数百次农民起义中,寂寂无名,此次让其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颇费斟酌。根据史料记载,宋景诗这位农民领袖形象上存在很大的污点,真实的宋景诗曾经向清廷投降,还帮助朝廷镇压捻军、长枪会、回民起义军等,因屡立战功擢升参将,赏戴花翎。尽管《武训历史调查记》明确宋景诗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但对孙瑜乃至这部影片的其他主创人员来讲,却不能视历史真实于不顾而草率地站在所谓的“无产阶级立场”改写历史。因此,因为传记题材影片传主选择,也直接成为孙瑜身体与身体政治的直接事件,也是该部影片是否能够正常上映的身体原因。身体之所以可以强有力地反映“政治伦理”,并成为社会控制的中心,是因为身体可以无穷无尽地被操纵,无论是作为编创者的身体还是作为题材对象的身体,都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塑造、设计与改建,可以变迁,以符合社会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显然,《宋景诗》是创作者对身体的革命化叙事和影像的政治化修辞,粉饰与美化宋景诗,是毛泽东将农民革命拔高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制高点的必然,也是承担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宋景诗以自己的身体变迁与身体形象,展示了新中国电影的农民英雄的政治化编码过程与表现形态,影片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实写了宋景诗革命与反抗的正面动作,而虚写了宋景诗“伪投降”后的行为。宋景诗的身体明显被赋予革命化的仪式功能,身体成为转述革命的政治符号。影片中的“树旗”一场,宋景诗与乡民开粮仓、焚官书,农民满怀喜悦,背粮回家。宋景诗承担“指路者”的重任,他站在高处,俯视群众,要求大家不要拿着粮食四散而去,而是要团结起来闹革命,和官府斗争到底。宋景诗完成了对群众的革命理念的“启蒙”,于是我们看到,群众纷纷将要拿回家的粮食放回谷堆,群情振奋,举起大刀长矛。宋景诗撕下黑布,树起“黑旗”,众人欢呼,革命仪式就此完成。显然,影片很自然“把身体概念化为一个符号系统,即把它当成社会意义或社会象征符号的载体或承载者”[13]38,从而完成影片革命叙事主题的建构。
英国文化理论家丹尼卡瓦拉罗认为:“当身体被作为个体所考虑时(即作为个体的身份的显现),它也可以同时被作为集体而思考(即作为共同的身份的显现)。一个共同的身份,依次来说,既指具体的身体(如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也指一个抽象的身体:也即,通过意识形态宣称和巩固的信仰、神话、法律和仪式上的身体。”[14]《宋景诗》中的身体,既是他个人的身体,也是高度抽象集体的身体。意识形态化的身体编码和身体的意识形态化,均是为了阐释经由人物的身份姿态,呈现出蕴藏其中的价值指向。如影片中的宋景诗与僧格林沁,他们是强有力的对手。作为个体,僧格林沁杀害了宋景诗的母亲和妻子,他们之间有“家仇”;同时,作为集体,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他们之间有阶级仇恨。宋景诗是农民革命的代言人,僧格林沁当然是清王朝统治者的代名词。因此,僧格林沁最后的死亡,就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人类身体是有关社会组成和瓦解的隐喻的重要源泉。于是瓦解的身体表现了社会的瓦解”[13]39。僧格林沁身体的瓦解,实际上是清王朝统治的瓦解。而宋景诗的胜利,则意味着农民革命的完胜。影片用此,实现了历史人物传记故事片的身体改造,并完成了宋景诗革命英雄形象的身体建构与叙事内涵。
但《宋景诗》没有获得预期的轰动。相反,剥离意识形态直接标签和强制的“政治伦理”的其他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如一心为医、不图功名、用30年心血完成《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坚决抵抗外寇侵略、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这两种身份的传主,反而成为新中国历史传记影片的主打。郑君里的《林则徐》虽然不直奔政治隐喻,但也表达了彰显集体力量的时代精神内核。影片的明线是林则徐反对投降、力主抗英,而暗线则表现了人民共同禁烟的力量,成功地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历史功绩提升到林则徐个人能力之上。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古代科学家传记影片的《李时珍》,则突出了他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影片尤以三次“逆水行舟”的隐喻来表达励志奋进的主题:人生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影片在同代历史传记片中,颇受欢迎。顾仲彝说:“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中真实人物有他的局限性,参考资料非常贫乏,古装人物在电影里的表演方法也还在摸索中;比较来说,这部影片的古装表演方法,能脱出舞台的传统表演方法的‘身段’,而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已是极不容易的了。”[15]但尽管如此,借历史人物表达当下的政治诉求,显现了身体在实在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被动铭写性。当下的社会规训与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身体总是卷入到纷繁的政治领域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6]。在这些历史题材的传记影片中,历史身体被无原则地凸显乃至夸大为表达当下政治伦理、传达意识形态信仰的重要载体,成为强绑在时代战车上的附庸。
三、革命英雄传记影片身体的图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身体叙事的特点,是身体的阶级政治化。人的身体被赋予了特定的、明确的政治内涵并被纳入无产阶级价值等级秩序之中。在对历史传记影片的矫枉过正的行动之后,新中国传记故事片转而将重点转向了对同一政党、同一阶级的英雄人物本位的传写上,传记人物无一例外地纳入到当下价值秩序的轨道并赋予政治化的标准身体。于是,革命英雄传记影片《赵一曼》、《董存瑞》、《白求恩大夫》、《聂耳》、《刘胡兰》、《雷锋》等的出品,成为承载政治理想与政党伦理的“合法”的电影作品。这些影片的“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7]。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人民一个巨大、辉煌的胜利。这种胜利的情绪一直支配着所有参加、支持或同情中国革命的人民。因此,人民敬仰英雄、崇拜英雄,赵一曼、董存瑞、刘胡兰等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雷锋、黄宝妹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自然成为新中国的观念身体而被不断地塑造着,而身体的塑造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塑造,它体现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有着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崇仰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18]。呼唤英雄,爱慕英雄,并且充分发挥英雄的当下效应,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图腾。
进入革命英雄传记故事片视野的传主身体大抵有三类。一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民主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志士、革命烈士,开创了塑造共产党员“钢铁身体”光辉形象的传记传统。作为民族书写、历史记忆的有力形式,革命传记影片将在战争时期的钢铁战士刻入历史铭文,完成承载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神圣使命。“因为争取电影对民族特性乃至民族历史的重写,以唤醒民族的记忆与身份认同,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电影理论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19]。被钟惦棐看成是“真实斗争摄取题材的影片”的《赵一曼》[20],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反映革命军队女领导的传记故事片。影片以朴素的手法,通过传主赵一曼在战场、监狱、医院、刑场等不同环境中经受的考验,多侧面地表现了东北抗联时期这位女英雄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同样用电影铭写女英雄的,还有《刘胡兰》。这是一部以编年的方式编写而成的个体的身体成长史。身体的成长史不仅仅关注人的身体,而且还关注身体所牵挂的历史,而身体所带出的历史是很富有社会意义的。影片从刘胡兰的幼年时代说起,童年时与地主冲突,酿成对地主的仇恨;日本鬼子入侵,地主与鬼子勾结,怀有对日军的仇恨;护送伤员,被捕牺牲。这是一部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红色叙事逻辑结构而成的革命传记影片,无时无刻书写着党的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作用。在红军时代,从孙同志讲述的故事中懂得革命的道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群众工作,支部书记经常告诫要“好好工作”;敌人劫烧村庄,书记教导她要“拿起精神来”。正因为这样,传主刘胡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对革命、对党的崇高信念,大义凛然,壮烈殉国。刘胡兰个体身体、生命的成长,与其说是物理身体的成长史,毋宁说是个体皈依党的道路的精神的成长史。《董存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个体归附群体的成长史。影片没有刻板地把传主董存瑞刻画成成熟的定型化的英雄人物,而是通过这个要求参军的热血小伙,对参加革命的浪漫设想,在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矛盾关系冲突中,最后奋不顾身舍身炸碉堡,展现其思想的升华和性格的完成过程。传记影片《董存瑞》,“给我们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如何创造正面人物,如何克服公式化老一套的光辉的范例”[21]。二是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模立传。《雷锋》,就是第一部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早逝英模立传的影片。早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毛泽东主席发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全民学习雷锋活动,雷锋的事迹家喻户晓。雷锋的成长尤其是雷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平凡岗位上所做的好人好事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经成为新生共和国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22]。有关雷锋事迹的书写,必须得到新中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国民的“群体支持”。这种政治伦理化的叙事指向,遂使影片《雷锋》成为传主做好事的“集锦”,且把雷锋的好事集中到一天中来呈现。在高度集中的时间和空间内,完成了对当代、同代英模雷锋的革命叙事。三是对健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模范的传记。《黄宝妹》突破了传记只传“盖棺定论”人员的惯例,而直接将描写对象“特写”到坚守在岗位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上。《黄宝妹》以传主自己的身体,演绎了一段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一代建设者的新人新事。黄宝妹是新中国确有其人的劳动模范,影片带有较强的纪实性,采用采访的方式,以记者采访传主为纵线,以勤学苦练、技术革新等场面为横截面,将影片拍摄地置放于黄宝妹所在的工厂,群众角色由所在工厂的纺织女工饰演。显然,黄宝妹是新中国树立起来的劳模,传主的行为和精神堪为时代的楷模,也是时代的精神追求。而真人出演,传真纪实,记录还原,在传记影片的创作上可以说是一个崭新、大胆的尝试,但其树立典型、弘扬正气、传递精神能量的意义,远远超过拍摄一部“记录性艺术片”本身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传记影片,正是通过这样三种人物身体类型的建构,传递出主旋律影片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建国初期的传记故事影片中,身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常常成为国家/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从而超越了身体本身的所指。这种政治隐喻在新中国初期的影片中早已出现并比比皆是。身体成为祭品,成为政治、政治伦理的祭品。作为祭品的身体越纯洁,越是作为一个特定时空的精神信徒,就越要摆脱欲望身体的宰制,将身体的自然力量减至到泯灭的状态。以自己真实物质身体与精神身体同时出场的黄宝妹,其内在逻辑是:黄宝妹不仅是新中国劳模的典型,而且是新中国女性解放、“男女都一样”的典型。若要取得男人一样的劳动特权,女人必须要以男性的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同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于是,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抹去了自然性征,而只获得符合社会主流的“去自然化”的精神性别。他们都是英雄,能够超越自我,无私奉献,勇于献身,没有“自我”。这种“无我”的精神趋向,让他们可以忘却自己,忘却自己的性别,只留下为党为国奉献一生的万丈豪情。就像影片中雷锋说的:“我明白了,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这些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他们没有七情六欲,只有“公”字当头。“共产主义……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也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23]。
显然,革命是唯一的政治,斗争是唯一的通行证。在新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个人的潜在欲望被否定,代之以培养起革命的、理性的、对理想社会向往的主体”[24]。在影片《赵一曼》中,失去丈夫的赵一曼以妻子和战士的双重身份,秉承丈夫的遗志继续抗战。与抗战伟业相比,情感永远处于配角地位,英雄的牺牲成为传主继续斗争的莫大动力。而在《刘胡兰》中,为了体现刘胡兰“生的伟大”,影片把胡兰子的儿童时代处理为生活在阶级仇恨之中,具有浓烈的阶级意识。影片采用了编年史的方式,表现女革命者短暂的一生,强调了其童年时代种下的信念与意识,直接为她的英勇牺牲做出了合理的铺垫与解释。基于这样的阶级逻辑,刘胡兰就义前慷慨激昂地说:“敌人的枪、刺刀没有让我们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会有很多的人替我报仇的,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低头,我们在日本鬼子手里就没有低过头,国民党反动派算什么!他们活不长了,咱们的队伍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刘胡兰把个体身体、生命献祭给崇高的政治信仰的时候,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崇高姿态,牺牲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含义。刘胡兰赴义前,有一段劝降的场面,敌人说,你那么年轻,死了不可惜吗?而这种对个体肉身的悲伤在建国初的政治语境中被视为反讽,因为肉身随着信仰的提升而被贱视,越是肉身献祭的惨烈越能呈现精神信仰的崇高,越能彰显“死的光荣”的意义。在这里,刘胡兰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体与生命,作为预备党员,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一个意识形态团体,在牺牲,在革命,在号召人民。当刘胡兰被赋予意识形态使命之后,她自然就具有了政党的身份,并成为国家/政党符号化的象征。刘胡兰不断地被赋予“更高的意义”,政党伦理与意识形态书写通过银幕实现了对话。刘胡兰成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历史上始终影响中华儿女的价值取向、思想品格以及道德风尚的英雄之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时代符号。
注释:
(1)《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连载。
[1] [英]布莱纳·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M]//汪民安,译.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0.
[2] Susan Bordo.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M]//Unbearable Weight:Feminism,Western Culture,and the Bod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165-184.
[3] 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94.
[4] 孙瑜.编导《武训传》记[N].光明日报,1951-02-26.
[5] 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6]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N].人民日报,1951-05-20.
[7] 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N].人民日报,1951-08-08.
[8] 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J].大众电影,1951,(22).
[9] 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N].中国电影时报,1986-11-29.
[10] 杨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1,(1):13-23.
[11] 沈寂.从《武训传》到《宋景诗》[J].电影新作,2000,(2):52-54.
[1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90.
[13] [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14]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3.
[15] 顾仲彝.评影片《李时珍》[N].人民日报,1957-03-31.
[16]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27.
[1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18] 郁达夫.怀鲁迅[J].文学,1936,7(5).
[19] 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5.
[20] 钟惦棐.看了《赵一曼》以后[N].人民日报,1950-07-09.
[21] 王若望.英雄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谈国产故事片《董存瑞》[N].人民日报,1956-03-18.
[2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2.
[2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91.
[24] 姚晓濛.电影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1.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9-05
叶志良(1964-),男,浙江杭州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务处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I207.5
A
1008-4657(2014)05-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