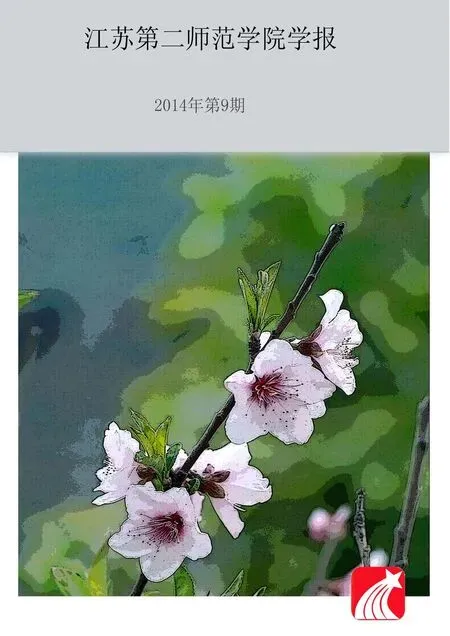一座自由孤独的花园——论《他们眼望上苍》中寻找“他者”的珍妮
郭雨微 焦晓婷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0)
前言
“他者”概念相对于自我,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他者与自我的辩证关系平行于客体对主体二元对立的关系。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具有不可知性、陌生性和他异性。列维纳斯在其著作《存在与存在者》一书中谈到他者,“世界上的他者只是一个穿上了衣服的客体”,或者叫“穿上了衣服的存在者”。[1](P.29)他者是流动的,无限的,即使他者换了衣服,换了形式,自我永远不会真正认清他者;换了陌生的“面貌”的他者是陌生的,即使是熟悉的面貌的他者会有自我所不知的面貌;即使有着同样面貌的他者也是有差异性的。女人(Woman)作为男人(Man)的一个相关项,宣告了女人的他者身份,女人是他者,男人的他者。与此观点相反,列维纳斯批判男性中心主义,主张女性的绝对性,而非男性的相关项并提倡女性书写自己的差异性。
佐拉·尼尔·赫斯顿是曾经轰动20世纪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是黑人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讲述黑白混血儿珍妮经历三次婚姻寻找自己爱情的辛苦历程。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女权主义,自由的追求,反抗意识的觉醒,都将珍妮视为男性丈夫的他者,但是珍妮更多地是她经历的主体,是个寻找他者的存在者。她正是列维纳斯欣赏提倡的书写自己性情的女性,更是超越他者寻找他者主体的女性。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她的三次婚姻只不过是她对他者的三次否定,她在寻找他者的途中玩弄着他者的存在。珍妮无时无刻不在建立着爱情的花园,在臆想的爱情中寻找他者,当花园开始腐朽时,她会说“生活在别处”,寻找他者之路在别处。
一、春之篇:序幕
一切似万物开始的春天,珍妮也似春天的少女,对爱情还很懵懂。珍妮怀有希望地打开她的花园,准备种植自己的爱情。她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有欢唱的蜜蜂的世界,等待有个他者进入她的花园。
约翰尼·泰勒是珍妮的第一位他者,珍妮睁开眼就将眼前出现的吊儿郎当的约翰尼·泰勒视为她的蜜蜂,这既是荒谬的也是合理的。珍妮只是在臆想中的爱情寻找他者,若奶奶不阻止泰勒的在场,泰勒作为珍妮的他者的时间会更长。
列维纳斯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人类本质首先不是冲动,而是人质,他人的人质。”[2](P.252)如果说一开始在奶奶未去世前,珍妮的自由是受到他者奶奶的限制,那是因为珍妮成了奶奶的人质,之后奶奶为珍妮找了一位他者——洛根,于是珍妮成为了洛根的人质。
奶奶让她与洛根结婚,而洛根的形象根本不属于珍妮这座花园。洛根就是一潭死水,而珍妮是一汪活水。洛根的死水只能浇灌60英亩的土地,而不能给与珍妮的花园以营养。对于珍妮而言,洛根永远不会招爱,他与珍妮也不会有爱情,因为洛根没有给她想要的甜蜜的东西,像蜂蜜一样甜蜜的东西。风琴和60英亩土地都不是她想要的,稳定的生活也不是她所看重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洛根的爱慢慢褪去,他开始让她流汗。他者眼中的他者珍妮是个不懂事的小不点,而真正的珍妮自我却是天真浪漫的花朵。珍妮已经超出了洛根的认知范畴,洛根这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自我不符合珍妮的公式。当洛根准备往她的花园里拉头骡子时,珍妮开始否定他者洛根的存在,为了不让洛根进入珍妮的花园,珍妮选择逃避,选择离开。当珍妮告知洛根她要逃跑离开他时,他者洛根对主体珍妮却进行着“不抵抗的抵抗”,他只是用言语教育她没有别人能养活珍妮,因为洛根相信不会有其他的他者来供养珍妮的主体性存在,但洛根不知道下一位他者正在珍妮的花园静候着。
二、夏之篇:继续
在阿妈去世之后,珍妮有了一种解放感。她再次期待,期待爱情的籽粒落在柔软的土地上,落在她的花园里。她是一个花朵,等待着蜜蜂的到来。
乔·斯塔克斯的出现是出于纯粹的偶然性。一开始乔是没有注意到珍妮的,是珍妮自己故意弄出声音吸引了乔的目光,即乔是珍妮自己寻找到的他者。两人相识是因为清水,而清水正是珍妮的花园所缺少的养分。巴士拉在著作《水与梦》中说“水吸收众多的实体。水吸引众多的要素。”[3](PP.104-110)同样水也吸引着水。水本身就是女性物质,珍妮本身就是水。但是珍妮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水和水是不能联姻结合的,水与水结合仍是水,水和水结合只会让彼此看不清对方的主体性存在,她明明知道乔不是日出,花粉,和开满鲜花的梨树,但她仍以为乔会是她的蜜蜂,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两个人20年的生活也像无味的水一样没有波澜起伏。
列维纳斯认为,爱情并不消融他者,而是维持他者;爱欲的本质不在于合一,而在于分离,在于他者的显现与维持。列维纳斯写道;“爱的情愫在于一种不可克服的实存者的二元性,它是与那个总是滑开的东西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使他性中性化,而是维持他性。”[4](P.78)当珍妮选择乔时,乔成了珍妮的他者,结婚以后珍妮是乔的他者,而乔没有维持珍妮的他性,而将珍妮消融在自我陶醉的“影子爱情”与自我设计的菲勒斯中心世界中。乔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要让所有他者围绕着他运行,像行星绕着太阳一样,他陷入了对自己的菲勒斯崇拜。珍妮像一只蝴蝶落入了乔所设计的蜘蛛网,陷入了名为空虚的深渊。
起初乔给她贵妇般的对待,让她坐上高高的市长夫人的座椅,花粉与春光仿佛撒在她的花园里。之后乔不让她参加门廊的聊天,不让参加拖骡子,乔将珍妮花园里粗俗的杂草都铲除;不让她露出头发,乔用厚重沉闷的乌云将花园的阳光遮挡。而珍妮是天性的使者,想笑就笑,想说就说。正如利奇和山姆讨论的“谨慎”和“天性”一样,乔是“谨慎”,对事业和自己的妻子珍妮都谨慎着,而珍妮确是“天性”的,是天性告诉她去说,去笑,去爱。她的花园需要的就是这些快乐的杂草和微笑的阳光。乔对事业的热情和对她的冷漠,让珍妮觉得孤独。乔因为没做好的一顿饭而重重打了珍妮一耳光,让珍妮的主体性觉醒。她发现了自己自我的缺失,自己一直都是被乔当做一个自在的存在,一直被置于物质性的附属地位。珍妮有自由选择再一次逃跑,再一次离开,但是35岁的她不知逃向何处,因此她只能“像土地一样默然地接受一切。无论是尿液还是香水,土地同样无动于衷地把它们吸收掉”。[5](P.83)最终,珍妮玩弄了乔的存在,她将乔他者性的衣服剥开,当众羞辱了乔的性能力减退并和旁观者一起蔑视,嘲笑。乔的他者性陷入了面貌的裸露中,此时的他者乔已不是其过去所是,但珍妮也成为无关乎他者的自我主义者,珍妮已不关心病床上的乔,她对乔死前说的话是为了同一他者乔,也无不体现了她对自我的享受。随着他者乔的死亡,珍妮立即复活。正如珍妮对弗奥比说的“我就是爱自由自在的生活”,她爱的是对自身的享受。于是她再一次敞开自己的花园,等待下一位他者的到来。
三、秋之篇:转折
第三次遇见他者甜点心就是珍妮的秋天,不仅收获了豆子,更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乔的相遇相同的是,甜点心也是向珍妮借东西。与乔的相遇不同的是乔借的是水,而甜点借的是火。如果是乔是水,那甜点就是火,水与火具有“化学的婚姻特征”,“在逻辑上一者呼唤另一者,在性方面,一方渴求另一者”,“水就应该‘把自己献给’火,火就应该‘娶’水”。[3](PP.104-110)即甜点心是珍妮的另一半,两个人是应该合为一体的爱人。
甜点这个陌生男人,对于珍妮一点也不陌生。她和甜点很能谈得来,从见到甜点开始,她的花园里有了月亮,浪漫的月光将花园的土地染成烂漫的颜色,滋润了她一个人的太阳,花园里的太阳可以大笑。这位他者在珍妮眼中是位夕阳的儿子,他弹吉他,钢琴,唱歌,给她的花园播撒种子与爱意;他能看透珍妮,“你的罐子里装着世界,却装作不知道”他就是她花园里的蜜蜂,携着芬芳,让珍妮感到自己的存在;他带来的一切对珍妮都是新鲜的,开心的:杂草,射击,掷骰子,大沼泽,豆子,甘蔗……“在无聊的时候,他可以拿起几乎任何一样小东西,创造出夏天来。我们就靠他创造出的那幸福生活着,直到出现更多的幸福。”[5](P.151)因此由他者甜点心自指的珍妮体会到了自为的存在,她仿佛自由地鲜活起来,仿佛之前她是幅黑白肖像画,现在忽然带着色彩活动起来;她穿着甜点喜欢的蓝色衣服,每天换一种发型,生命力全部释放出来;花园里的大树也瞬间成长壮大起来。
珍妮把乔的店卖掉,与甜点开始新的生活。当甜点出去钓鱼未回,衬衣口袋里的200元钱又不见时,珍妮开始意识到他者的不可知性。但事实证明她对他者的认识是正确的。在沼泽里的摘豆生活是快乐的,即使甜点因为特纳太太怂恿珍妮的话而象征性地打了珍妮,但珍妮却仍相信这位他者对爱的真实性。与甜点心在沼泽里遭遇的洪水更加证明了甜点对珍妮的爱。在夜的风暴中,夜与水相容成一种恐怖,吞噬者万物,珍妮与甜点心等待上帝的怜悯,他们眼望上苍,将目光从水平方向转向垂直的上帝,作为他者的上帝。上帝就是他性,是一种无限,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目光”。虽然看不到上帝的面孔,但珍妮一直转向作为他者的上帝。“上帝卓越地存在着,它意味着一个高于任何高度的高度。”[2](P.252)面对风暴,珍妮毫无畏惧,因为上帝已经为她带来了等待中的爱情,带来了她最爱的他者,此刻的甜点心得他性已超越了上帝的他性。珍妮和甜点在水中与风暴抗争,因为珍妮就是水,她是融于水,属于水的,因此她是不会死在水中,而甜点心是火,水会使火熄灭,使他的生命窒息,甜点的死亡是必然的。赫斯顿对风暴意象的巧妙运用早已预示了甜点的死亡。其后甜点因为被疯狗咬得恐水病,而被珍妮拿步枪射死。虽说珍妮是出于自卫,但是步枪是她提前准备的,甜点是为了救她而死,也是被她杀死的。正如甜点以前对珍妮说的“你掌握着天国的钥匙”[5](P.118),仿佛他应经预示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珍妮的手里,他要为珍妮而死。可以说是珍妮吞灭了最后一位他者。
四、冬之篇:尾声
珍妮的名字从珍妮·梅克劳弗德到珍妮·梅克利斯克,到珍妮·斯塔克斯,到最后的珍妮·伍兹。她的名字经历着变革,珍妮的他者之路也经历着季节般的轮转。从爱情启蒙的茂绿春天,要往她的花园里拉骡子的洛根,到在爱情澎湃似火开花的夏天,把珍妮封闭在一个鸟笼里的乔,到再收获爱情的橙红的秋天,给珍妮带来浪漫和蜂蜜的甜点心。经历春,夏,秋般色彩变幻的婚姻后,珍妮不会问自己:爱情啊,你姓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为了种植一座自己的花园。
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哲学讲座中提出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在本质上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共群中的田园式的和谐关系,也不是一种将我们置于他者之位的同感;我们认为他者与我们相似,然而他者却外在于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即是与大写的神秘的关系。”[6](PP.75-76)由此可以说,珍妮与洛根不是共同劳作的和谐关系;珍妮与乔不是将她置于乔之位的同感;最后一位他者,甜点心与珍妮相似,又被珍妮杀死,甜点与珍妮是神秘的关系。但同时,珍妮是一个不完整的存在,她是一座孤独自由的花园。现在珍妮是个身心寒冷的冬天,因为她的花园不会再开花,即使她有甜点心留下来的菜籽,她的太阳已不存在,意义总是消失在远方。她知道生存在的窄狭局限,抛开它的尘世存在的偶然关系和至于艺术本身是否会消亡死掉,我们完全不用抱活在别处,她又将走上寻找他者之路,但他者是否会再现,经历过真正生活回来的珍妮不知晓,无人知晓。
寻找他者之路的真相揭开了珍妮身上的西西弗斯性。珍妮一直举着主体性这个大石头,石头上刻着“爱情”两个大字,可是石头不断往下掉,主体性不断下落,她一直不断在重复着这个过程,直到最后。只要她不将自己的主体性抛开,这个过程会一直下去,直到她的花园枯萎,没有春光。不过与西西弗的石头不同,珍妮的石头的重量是变化的,所耗的时间每次也是不同的。从其踪迹中可以看到珍妮的存在,珍妮的花园经历过不同的风景都见证了是她的存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列维纳斯.存在与存在者[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加斯东·巴什拉.《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M].长沙:岳麓书社,2005.
[4]Emmanuel Levinas.Les temps et l'pautre,Qua-drige1[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3.
[5]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6]E.Levinas.Time and the Other[M].Pittsbukgh:Duquesene University-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