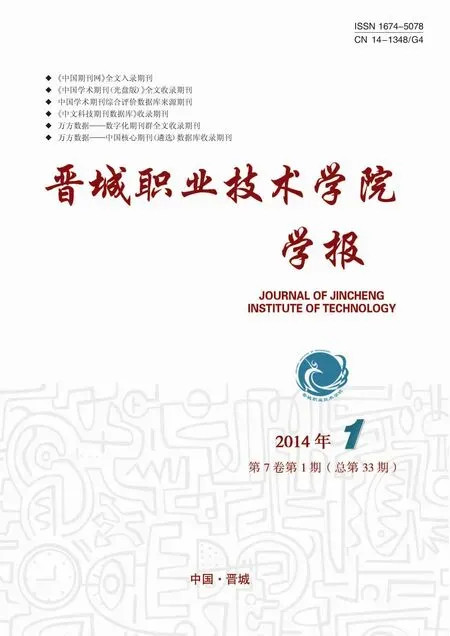战国封君问题探析
马云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 450001)
众多史料证明,春秋末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卿大夫、贵戚、功臣、名将乃至他国降将,因为宗族关系或有功于国受到诸侯王的赏识,进而被封赏,且封赏至尊至贵者多冠以“君”的封号。自春秋末期起,称“君”现象开始出现,至战国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战国时期,群雄并起,为争夺霸权赢得他国臣服,各国之间结盟对立、对立结盟开始了它们200多年激烈地兼并战争。先是大国吞并小国,代之而起的是几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加剧及自身实力的增强,各路诸侯纷纷称雄称王。但不可否认的是,各诸侯国的强大与封君制度的延续和逐渐强化的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依托这些封君,各诸侯王加紧对外征服与扩张,同时借助他们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总之,纵观战国时期,封君之风不但未有削弱之势,反有日盛之形。下文将对封君受封的封号形式、受封原因加以叙述,并且在对各国封君考证基础上尝试求证各国的封君数量,以求对封君制度研究有所裨益。
一、封君封号的形式
关于战国封君名号的形式问题,刘泽华,刘景泉在《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一文的战国封君概况中已做过较为详实的叙述。此节为达到行文流畅,顺应上下文的承接关系,每一种名号试再各用别例加以对应,使其论据更加详实完备。
(一)以封地作为封号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1]《索隐》云:“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
(二)以“谥”作为封号
“(赵襄子)封伯鲁之子周为代成君”[2]1794并且授予其代地。“代”为地名,由此推之,则“成”可能为其谥。田婴,孟尝君之父。“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婴卒,谥为靖郭君。”[3]《正义》中注有孟尝君亦为谥号。又楚考烈王即位“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4]一句,《正义》为其注曰:“然四君封邑检皆不获,唯平原君有也;又非赵境,并合号谥,而孟尝是谥。”[4]此论在史家研究中尚有争议,但无论争论如何激烈,观点如何相左,战国时期有些封君封号以谥号命名,则是不虚。
(三)以雅号作为封号
《史记·赵世家》载:秦攻打赵国“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2]1823《正义》注曰:“长安君者,以长安善,故名也。”[2]1823长安君当是雅号。
(四)以发迹地或原籍作为封号
齐国封君中的钟离春其原籍即为无盐,故齐宣王封赏其功时,将封其为无盐君。受封于燕国昌国之地的乐毅父子皆称昌国君亦是此理,由此得之。
二、封君获得封号的原因
学界专家普遍认为,封君封号的获得之缘由以“因功得封”与“因亲受封”两种观点为主。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以上两种因素之外,亦需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才能使其原委更加完善妥当,现陈述于下。
(一)因功得封
“主父(武灵王)及王游沙丘”,然而公子章趁机叛乱。“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因平叛有功,封“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2]1823《赵国史稿》中也有记述李兑因平乱有功、辅佐赵国朝纲而在赵惠文王时被封为奉阳君的内容。又《史记·赵世家》云:“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于下,赐号马服君。”[2]1823由此得证,赵奢是因功得封无疑。邯郸之围后,燕攻赵,廉颇为将,大破燕军。“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5]故廉颇亦因军功而受封。再者,上文亦有提到“秦惠王八年,封樗里子右更……”后数立战功,“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1]《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6]由此得证,严君亦是因功得封。
(二)因宗室得封,即亲亲得封
各国封君中获得封号较早者即为赵襄子时期的代成君,其为赵国分封的第一位封君。“(赵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诱代王,以金斗杀代王,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7]赵襄子封伯鲁之子主要是由于赵襄子对其失意嫡兄伯鲁的同情,故将其子周封于代地,以作弥补。[8]平原君亦因亲亲得封,“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而以国人无动,乃以君为亲戚也。”[9]“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10]又有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赵豹为平阳君”[10]《集解》注曰:“《战国策》曰:‘赵豹,平阳君,惠文王母弟。’”由以上三例推之庐陵君(赵孝成王母弟)、春平君(赵故太子)皆因其为赵室宗亲而得封。之于秦国在秦昭王少时,宣太后大权独揽,封其二弟为华阳君、三弟为泾阳君、四弟为高陵君,此三君与穰侯(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一起号称秦国“四贵”,再有魏国信陵君(魏安厘王之弟)皆因亲亲得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旧有分封原则即“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11]的继承。
(三)因归降或献土得封
战国纷争不断,且消耗或伤亡巨大。为减少伤亡,各国多封敌国降将为君,此不失为两全之计。既能收敌国之将,又能保存实力减少伤亡,甚至还能收到震慑他国之效。《史记·赵世家》载“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封地”,[2]1823《集解》徐广曰:“故秦降将也。”又有燕国乐毅受齐田单反间计之困,畏燕惠王之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关津,号曰望诸君。”[3]直接原因就是“尊宠乐毅以警动燕齐。”[10]另外,又有献土得封;赵孝成王四年,韩氏上党太守冯亭将韩国的上党郡“再拜入赵”,[2]1823《汉书·冯奉世传》曰:“赵封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距秦,战死于长平。”[12]
(四)因逃亡得封
田忌与成侯邹忌不善,恐诛,亡齐而之楚。“邹忌代之相齐,恐田忌欲以楚权复于齐。”田忌谋士杜赫使计劝楚宣王令田忌留楚,并“封之于江南”。[13]
(五)因色、宠得封
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又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可见安陵君坛为楚宣王宠臣。后来为了稳定个人地位,以色相侍奉楚宣王的坛,不惜用宣王死后以身殉葬的誓言来打动宣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13]赵国的建信君也因受赵悼襄王宠幸而受封。[13]另外,《战国策·赵策四》“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向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14]杨子彦在《战国策正宗》中注曰:“春平侯,赵国宠臣,当是因宠得封。”[13]但因宠得封最著名的当为龙阳君,此点在《战国策·魏策四》的《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一篇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
三、“君”号下各国封君之数量
关于战国时期封君数量问题,前人做过一些研究,如杨宽《战国史》中所附《战国封君表》对各国封君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笔者依据此表将封君的定义标准进行了再统一,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封君定义标准及赵国封君数量
关于赵国封君,各家对封君数量的考订观点不一。杨宽在其《战国史》中记述赵国封君有27位;何浩认为赵国封君有26位;白国红认为赵国封君有21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家定义封君的标准不同。白国红分析,封君与封地根本不同,有封地的不一定有封号。如:齐国的田文在赵国拥有封地武城,却并没有被赐予封君封号。反之,有封号的也不一定有封地,如建信君就是有封君之号而实无封地。杨宽将田文、黄歇、魏无忌、秦之长安君(分别被赵赐予武城、灵丘、鄗、饶为食邑)也都归为赵国封君。他们的定位标准是先得出何为封君的结论,再讨论具体人物是否为封君。这一点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有的受封者仅仅是被赐予食邑,并不为受封者所有;另一方面,有些受封者纵然获得食邑也只能食其租税,并无政治、军事等特权;再者,若受封者也无封号,那么将其划入封君之列也未免有些牵强。在这里,根据受封者的实际情况,有封地的称号未必是“君”,而称“君”者未必一定有封地。所以,笔者去除这类有封地而无“君”号之称的受封者,总结赵国封君共有22位,但封君有失考者或无载者(如张孟谈、平陵君、襄安君、晋君等),实际受封者的数目肯定是要多于此数。
(二)楚国封君数量
关于楚国封君,其一,《战国策·楚策四》有提到蔡圣侯。杨子彦考之,认为历史上无蔡圣侯,当为高蔡国(在楚国西南)的国君。故不列。其二,苏秦亦为封君。《战国策·齐策三》下《楚王死》一篇中载有:“又使人谓楚王曰:‘……今人恶苏秦于薛公,以其为齐薄而为楚厚也。愿王知之。’楚王曰:‘谨受命’因封苏秦为武贞君。故曰:‘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也’”。[15]由此推之,苏秦当是楚国封君无疑。其三,《战国策·楚策一》中《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篇》有云:“昔者叶公子高,身获于表薄,而财于柱国。”[16]杨子彦注曰: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楚昭王司马沈尹戌之子,字子高,封于叶,所以称叶公子高。既然叶为封地,则其可能也是受封者之一。因其为孤证,存疑,故不列。其四,对于郎陵君的身份学界有过一些争议。何琳仪认为郎陵君当为春申君;李学勤根据江苏无锡前洲公社出土的三件楚国郎陵君有铭铜器认为:“墓主是郎陵君王子申,封地必在无锡附近,只能在春申君黄歇被李园刺杀以后,即公元前237年之后。他可能是楚幽王之子,也可能是其弟。”经何浩所证,当从李学勤之意见。故楚封君数量为30。
(三)秦国封君数量
秦国封君人数仅次于楚国封君,有20余人。其中尚有存疑者:其一,孙国志所列的被封于平阳的秦公子白。《仪礼·丧服》有云:“君,谓有地者也。”[17]但前文已经提到封君与赐地完全是两回事,并且有众多事实证明有封地的不一定是封君。虽《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卒,“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6]但并未有史料明言其为平阳君。再者,秦武公(前697—前678年)时正处于春秋早期,新式的地主阶级封君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即使到了春秋末期也未兴盛,传统的宗法分封制仍是惯制。公子白被封于平阳当是分封制的表现,即诸侯分封卿大夫(大宗分封小宗)的表现。将封地作为他们的食邑,有封地之实,而无封地之号,故不列公子白为平阳君。由此推之,《战国策·韩策三》所载之南郑、梗阳、平原列于此也属牵强,当存疑不计;其二,白起有封号而无封地。白起之封为武安君乃因其军功,渐次被封。按,秦功拔武安在昭王四十八年,且为王齕伐取,白起为武安君时,秦未攻取武安之地,秦不可能封白起于未得之地,故武安之封与封地无涉,当为封号而已。其三,秦国封君中较特殊者有芈戎、公子煇二人。较其他封君不同的是,二人不仅各有封地二处且有两个封号,且均有史明载,遂计封君数为4。故统计秦封君总数为23位。
(四)齐国封君数量
齐国封君中较为特殊者,首先,当为无盐君钟离春。其为一女子而受封,不仅拥有封号而且拥有封邑。然其封号封邑并非因色得封,缘于钟离春恰恰是一丑女子,四十岁不得出嫁,自请见于齐宣王,陈述齐国危难四点,为宣王采纳,立为王后。于是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进直言,选兵马,实府库,齐国大安。如此功劳,在战国纷争的年代里,男权主义极强的环境下,泛泛之辈实难为之,更何况一女子。这正是无盐君钟离春的特别之处,非龙阳君等受封者所能比之。其次,即靖郭君与孟尝君的封号是因地得封还是因谥得封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云靖郭、孟尝曰谥;鲍彪为《战国策·齐策一》做注亦言“靖郭君,田婴谥”,[18]《正义》言孟尝亦为谥;然钱林书在《战国时期齐国的封君及封邑》中根据司马贞《索隐》、梁玉绳《史记志疑》、陈直《史记新证》持靖郭、尝为地名的观点,二者当是因地得封。三家所证皆能自圆其说。然因史料不全,争议尚存,不可轻下定论。暂陈于此,留待考证。再次,是苏秦亦在齐国受封,《战国纵横家书》十七有载苏秦为武安君而相秦,当时齐闵王末年(公元前284年)。当时有人游说主持伐齐的秦国御史起贾,提到此时齐国如投靠魏国,是“武安君之弃祸存身之诀也”[19]此与苏秦在赵国受封在时间上较为契合,当亦是齐国封君无疑。最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云:“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20]此句注曰:“盖(ge),齐国地名,是陈戴的食邑。”陈戴虽有盖地,但史料未明其封号,划为封君与否,当待论之,故不列。则齐国之封君所能明证者除陈戴外,可考者当有6位封君。
(五)魏国封君数量
关于魏国封君,其一,虽将魏襄王时的公子劲列入封君,然其封号、封地因史料不全,并不尽知。《史记·秦本纪》载:“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6]《索隐》注曰:“别封之邑,比之诸侯,猶商君、赵长安君然”。由此看出,魏公子劲在此受封之前其实早就有自己的封地,此“诸侯”并非指宗法分封制五等爵制下的诸侯,仅是其地位与诸侯的地位相当,则公子劲为魏之封君无疑;其二,成侯当有封地。《战国策·魏策四》载魏安厘王时,安陵君对信陵君的大使说:“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大府之宪”,[21]由此得之。则魏有17位封君。
(六)韩国、燕国封君数量
韩国封君大多考证详实,共计7位封君。关于燕国封君,其一,昌国君有两人:一为乐毅,一位乐间,二人为父子关系,封号、封地为承袭关系。燕惠王时,乐毅为燕将于公元前284年攻破齐国70多座城池,因功封为昌国君;后因齐反间计燕惠王使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奔赵。惠王后来极悔,又以乐毅之子乐间承其封号,为昌国君。封君之世袭在燕国极其少见,而乐间之世袭乐毅为昌国君,确实又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其二,苏秦亦为楚国封君。《史记·张仪列传》有载“……苏秦,封武安君,相燕。”[22]燕昭王于公元前295年派苏秦出使齐国,以武安君封之,并受之以相国之尊位,可谓备受恩宠与器重。后来苏秦献书燕王云:“以求卿与封,王为臣有之两,臣举天下使臣之封而不惭。”由此得之。其三,襄安君之“襄安”作为一个名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一书中:“县阴以甘之,循有燕以临之,而臣待忠之风,事必达成。臣又愿足下有地效于襄安君以资臣也。足下果残宋,此两地之时也,足下何爱焉?”[14]“襄安君”是燕国王族,燕昭王时封君,为燕昭王之弟,昭王曾派他到齐国活动。此“襄安”系作为人名出现。是否以封地为名,燕国的封地又如何会在楚地,这些问题均无从查考,故虽云“襄安”,实在与襄安这一地名联系不上。概计燕国封君为6位。
四、结语
封君制度自创立之始,就成为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封君封号的形式主要有封地、“谥”号、雅号、原籍四种;封君获得名号的原因主要以“因功得封”及“亲亲受封”为主。通过分析封君封号表现形式及获得名号的原因,可以感受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总结的:一因功受封;二因亲亲受封。[23]此法颇具概括性,不无道理。但有些封君毕竟既非因地受封,也非亲亲受封,或因献土得封,亦或因色受封,故不应当简单划于前两点之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两种受封形式中所占比重最大,是战国时期最主要的受封形式。正如苏秦所言“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11]也如《管子》中提及的“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名者,割壤而封。”[24]另外,关于战国时期各国封君数量的考证表明:楚国封君最众,其次为秦国、赵国,封君最少者为燕国、齐国。从中也不难得出楚、秦、赵三国封君制度较为发达成熟而燕、齐二国则较为缓慢滞后。
[1][汉]司马迁.樗里子甘茂列传(《史记》卷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08.
[2][汉]司马迁.赵世家(《史记》卷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司马迁.孟尝君列传(《史记》卷七十四)[M].北京:是中华书局,1959:2352.
[4][汉]司马迁.春申君列传(《史记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5:2394.
[5][汉]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史记》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5:2448.
[6][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0.
[7][汉]司马迁.六国年表(《史记》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5:694.
[8]沈长云,等.赵国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0:576.
[9][汉]司马迁.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5:2369.
[10][汉]司马迁.魏豹彭越列传(《史记》卷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5:2589.
[11][汉]司马迁.苏秦列传(《史记》卷六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45.
[12]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汉书)[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1617.
[13]杨子彦.战国策正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4][西汉]刘向.赵策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67.
[15][西汉]刘向.齐策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70.
[16][西汉]刘向.楚策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15.
[17]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61.
[18][西汉]刘向.齐策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05.
[19]谓起贾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69.
[20]杨伯峻.孟子译注(全二策)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9.
[21][西汉]刘向.魏策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15.
[22][汉]司马迁.张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92.
[23]刘泽华,刘景泉.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J].北京师院学报,1982(3).
[24]谢浩范,等.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