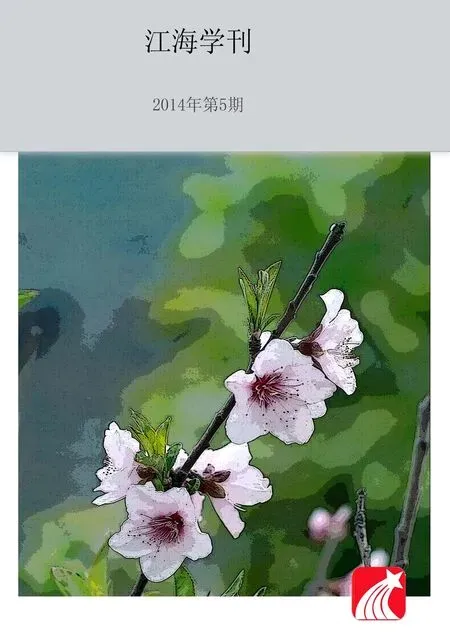“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张 军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词,在美国学术界广为人知,但国内学术界却提及不多,特别是在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章里很少提及。随着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的盛行,对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英国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欧洲大陆其他相关理论家和相关理论的研究都在陆续展开,但学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引起激烈讨论、至今在美国高校仍然掌控主流话语权的“政治正确”却罕有提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高校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也是各种思想争鸣的地方,“政治正确”能在美国高校占据主流话语的位置,足可见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曾经提及马克思主义就让人色变,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阵地,其主流话语竟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虽然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等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但其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却是肯定的。本文将对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关注。
一
关于“政治正确”的起源,在美国一般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词源学的角度;一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词源学角度来说,“政治正确”最早出现在1793年美国最高法院齐斯霍姆(Chisholm)起诉佐治亚州(Georgia)的庭审上,但当时“政治的”(politically)和“正确的”(correct)这两个词并不是固定词组,也非固定的用法。①因此,更多人倾向于第二种看法,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政治正确”自1920年代开始为马克思主义者广泛使用,它成为“党的总路线”的宽泛的同义词。到了1980年代,在美国和西欧很多国家,“政治正确”是指在学术观点、政治、社会生活中遵循扶持弱势和尊重边缘群体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尊重各少数族裔文化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却潜在于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里,成为人们行事的一个指南针和道德规范。遵循这个路线,即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如果违背了这个“总路线”,则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
要体现和确保这样一个“总路线”,需要一定的政策来保证,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就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它最早源于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签署的行政命令10925(Executive Order 10925),要求政府部门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不能因为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原国籍原因歧视应聘者,要采取肯定性的行动确保应聘者被录用,并且在聘用期间不能因为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原国籍原因而受到不公平对待。几经修改,1967年的行政命令11375在歧视原因中增加了性别,把妇女包括了进来。
除了政府的政策,高校也在形成这样的“总路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玛丽安·阿依姆(Maryann Ayim)认为:政治正确的核心是指当代美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提议,通常都和大学有联系。这些提议包括公正使用语言的政策、招聘中的肯定行为、关于性骚扰和种族骚扰的立法、更多的有色人种和妇女进入课程等。②美国高校一般都要求师生不能使用歧视性的语言,包括性别歧视语、种族歧视语、恐同歧视语、残疾人士歧视语等,很多高校在录取学生和招聘员工的时候还会有关于应聘人员的种族等背景的配额即肯定性行动计划,也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作家进入教材,取代了传统白人男性经典作家的地位。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对师生“政治正确”的潜在要求无疑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要影响。即便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如总统选举,也得严格遵守“政治正确”的原则。如果候选人能打好“政治正确”这张牌,就能吸引到更多群体的关注和支持,而一旦违背“政治正确”的原则,刺激了特定群体的敏感神经的话,则会遭到该群体甚至是更多相关群体的抵制,而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媒体既为“政治正确”推波助澜,本身也得遵循“政治正确”的原则,无论是其立场和观点,还是所使用的语言或其他符号,都不能与这个“总路线”相违背。如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选之前公开声称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当时分析人士指出他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在其竞选团队预计选举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为了更多地吸引中间选民而出的险招,但在美国国内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可和接受度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也是更多地倾向于其积极意义。奥巴马最终击败反对同性婚姻的对手罗姆尼而成功连任,说明他和其竞选团队熟谙“政治正确”原则在美国政治生活和媒体舆论中的重要影响。高校、政界、媒体——这三者对“政治正确”的重视足以说明其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和“政治正确”联系紧密的就是“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术语在今天的美国学术界仍然处于话语的核心地位,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和结果,以至于很多学者常把三者相互替换。如杰弗雷·布雷谢尔(Jefrey D.Breshears)就认为,“尽管‘政治正确’有时被称作‘文化自由主义’,但更准确地来说,‘政治正确’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述”③。丹尼尔·格瑞尔(Daniel Guerriere)则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在更多的时候就是指政治正确”④。文化多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各种族文化、亚文化的平等与共存,这和“政治正确”的总路线是一致的,而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关注社会中各阶级、群体的权利和平等,主张文化多元主义,也往往遵循政治正确的原则。三者在这一意义上互为关联。因此,理解了“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当代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涵和诉求。或者反过来,如果阐明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也就明白了“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涵义和意义所在。
文化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层面入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析西方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现实。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不同,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了主流,由经济基础所衍生出的阶级斗争的路线已经无的放矢、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相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和隐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工具理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肆虐,使得人性饱受摧残,人异化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大机器的一部分,工具理性也在文化领域蔓延,原本是人类重要精神生活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变成了机械生产的文化工业,其生产文化产品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大众别无选择,只能被动地消费文化工业所推销的无艺术价值的商品,久而久之,大众则会变得麻木和失去辨别力。因此,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大肆批判,希望通过有创造性的艺术来唤醒被文化工业所毒害的大众,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认清社会的现实,从而改变之。同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同时在1960年代作为学生运动精神领袖的马尔库塞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其生产力来说,本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使人们生活得更自由,但由于其众所周知的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未能满足人的各种自然需求(即爱欲),反而附加给人额外压力,使人性扭曲、异化,因此,马尔库塞号召受压抑的人们特别是年青人为爱欲而战。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弥补马克思主义对个体的忽视,以爱欲与文明的矛盾来替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文化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的锋芒由经济基础转向了文化领域,其结果之一便是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一般有三种理解:美国的文化多样性、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政治正确。⑤本文所指为第三种含义,即作为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关键词之一的文化多元主义。它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关注由经济转向文化层面的结果,也是“政治正确”的题中之义。虽然进行了文化的转向,但文化马克思主义还是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社会公平的主张。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全人类分为两个阶级: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或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受压迫阶级和被剥削者是工人。但今天,这样的划分和现实已经有了出入。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从新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剖析与批判。他们同情黑人、妇女、同性恋等弱势群体,呼吁社会给予这些弱势和边缘群体关注和帮助,使他们能获得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同等的权益。在政治上主张身份政治;在社会生活中,主张各文化群体的平等权益;在教育中强调文化的多元存在和少数群体的特殊的教育需求。
二
要进一步弄清“政治正确”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回顾它的历史起源,审视它的分析方法和它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它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曾经引起的广泛争议。
如前所述,“政治正确”实际上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它的出现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转换,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意大利葛兰西的著作的发表以及1923年在德国社会研究所的创立(即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1930年代为逃避纳粹,社会研究所的许多学者到了欧洲各地和美国,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构筑我们的国家》一书里对美国文化左派即文化马克思的形成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认为,美国的文化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在此之前,美国的“左派”是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公正的国家。⑥他们相信能够通过美国的民主体制来纠正和避免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如通过选举理想的政治人物,通过促成相关法律的制定,就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的民主和各阶级以及社会团体的平等。但是,越战的发生动摇了他们的信念。“越战使得一代美国人对实现美国建立之初的目标产生了怀疑,认为那场战争是永远不可原谅的,美国是有罪的……”⑦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调查,认为越战中美国完全是侵略国的学生由1969年16%猛增到1970的41%。⑧学生们因此丧失了作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上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家的影响下,60年代的激进分子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建议,也就是发动“文化战争”,即通过控制文化来间接获得政治权力。同时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和美国建国之初的理想背道而驰,应该超越国界,对整个人类负责,做文化世界主义者,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因此,这个“新左派”又叫“文化左派”,也即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文化左派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尔库塞被看作是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学生运动的锐利武器,学生们把对政府和其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化作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彻底批判,其中传统白人男性的价值观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遭到最为猛烈的攻击。虽然学生们的“反文化”运动导致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吸毒、性解放等,但其批判精神却在激进运动之后作为美国文化的宝贵财富遗留了下来,并与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中对种族、性别等社会公平的诉求相结合,成为“政治正确”的主要内容。运动结束之后,文化左派的代表们由于并不主张从政治经济体制入手,而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批判,所以他们辞别工会,逐渐远离政治,开始在学院里研究“差异政治学”和“身份政治学”,重心也从社会学系转向文学系。他们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相结合,后来也加入语言学理论创造了批判理论和“解构”理论。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并且通过高等教育,使“政治正确”得以产生。
到了八九十年代,许多参加了60年代运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开始掌权,学界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指出,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学生们视大学为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工具而进行造反,1980年代时,许多当年造反的学生已经成为高校职员,他们展开了新的攻击,即对课程和大纲设置的攻击,认为这是导致大学堕落的主要原因。他们对经典的攻击最为猛烈,认为其代表了美国陈腐的价值观体系,并意图以对少数族裔的关注取而代之。⑨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大量的系部和项目,这些系部和项目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政治正确”的意识,致力于通过宣传培养学生对“文化多样性”的敏感。他们在大学招生中设置了种族和民族的配额以保障处于社会弱势的种族和民族的平等权益。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编撰文学教材的时候,也增加了种族、性别或其他被压迫者的身份标准,来尽可能选择各群体代表的作家让学生阅读,而不仅仅是遵循经典文学的传统路线。他们认为伟大的作品选集总是需要增加新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压制或未被重视的作家作品,应该被重新发掘。他们还提倡师生注意语言的得体性,拒绝使用歧视性的语言,比如“美国土著”(Amerindian)和“残疾人”(handicapped)就被认为缺乏敏感性而遭到禁用,而以“美国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和“能力殊异人士”(differently-abled)加以代替。
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成长为高等院校的主导力量,“政治正确”也慢慢地成为主导高校学术话语和社会日常政治生活实践的一种潜在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涉及不同种族、民族、性别和其他群体差异和利益纷争的时候,应该同情和扶持弱势群体,以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虽然,“政治正确”在美国自8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了主流话语,但对它们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事实上,20世纪80、90年代学界曾对此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即便是今天它也仍然是人们反复争论的话题。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者来说,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尚未成功。相反,美国是一个严重种族主义的、男权的,整体上是压迫性的社会。因此,必须重铸,使之变成为各种族平等和各民族文化都得以保存和发展的社会。支持者认为“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虽然不是法律上的硬性规定,但能对人们的日常政治生活和道德行为进行规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保障各种族、各民族和各边缘群体的平等合法权益。⑩他们也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具有合法性,其目的是通过对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人给予优待,来促进社会平等。通常这些人处于劣势是由于历史原因,比如受压迫和奴役。肯定性行动计划致力于达到以下目标:实现就业和薪酬的平等,增加受教育机会,国家、机构和行业管理人员的全面多元化,纠正过往的错误和伤害,特别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社会不平衡。
而“政治正确”遭到的非议和指责主要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政治正确”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主义和对自由的限制;二是二元对立思维和逆向歧视;三是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政治化。
首先,批评者认为“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提倡的平等是一种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文化多元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公平的主张,他们要通过政府权力来消除所有可能存在或发生的不平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理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不相同,独特性便排除了平等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把“公平”(justice)界定为平等(equality)是不对的,认为社会主义者要使每个人处于平等状况,就必须不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来说,独特的个体只是在作为被压迫阶级或相反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所谴责的不平等是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真正关心每个个体的平等权利。
按此逻辑,文化保守分子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就是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激进自由主义者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必须把某类人指认为受压迫者。自1960年代以来,受压迫者依次为黑人、妇女、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同性恋者和残疾人。虽然期间也有其他群体被提及,但主要还是以上群体构成了被压迫阶级。更广泛地看,被压迫阶级还包括了大多数第三世界,甚至是地球母亲。而“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关于人的二分法决定了他们所高歌的平等并不是每个人的平等,而是二分法中某一阶级的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根据此二元对立的思维,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白人异性恋男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阶级,根据具体情况把他们控诉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反犹太主义、恐同主义、仇外主义的实施者。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政治正确”导致了对白人异性恋男性的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即为了公平对待过去曾遭受种族或性别歧视的群体,而在客观上形成对先前享有优待的群体的歧视或不公平对待。他们认为肯定性行动贬低了受优待群体所获取的成绩,因为他们被聘用不是基于他们的资历,而是基于其属于某个群体的原因;肯定性行动是以错纠错,反而会阻碍群体间的和解,鼓励个体承认自己处于劣势,哪怕他们实际上不是处于劣势。2008年德克萨斯当地白人学生艾碧嘉儿·费希尔(Abigail Fisher)控告德克萨斯大学,声称她因为是“白人”而未被该大学录取。在录取中,种族成为了录取与否的重要因素。费希尔认为这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美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苏维尔(Thomas Sowell)在其书《全球肯定性行动:一次经验研究》中也指出了以种族为基础的肯定性行动的负面影响,认为肯定性行动往往使得受优待群体中最幸运的那些人受益(如中、上层黑人),而使得非优待群体中的最不幸的那些人利益受损(如贫穷的白人和亚洲人),因此使得这两类人都缺乏动力做到最好,前者是因为没有必要做到最好,后者是因为做到最好也是徒劳。这一方面对社会是损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们对于优待群体的仇恨。圣地亚哥大学的法律教授吉尔·赫若特(Gial Heriot),在《华尔街日报》(2007年8月24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肯定性行动的结果使得黑人律师的数量反而降低了7.9%。他分析,黑人进入比自己实际应该进入的大学更好的大学后,往往会因为跟不上学习进度而导致辍学。
对“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第三个责难是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将种族、民族问题政治化,容易导致冲突和战争。保守主义者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是把种族和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危险。在这些区别被给予政治地位的同时,对立、冲突、谋杀,甚至战争也随之而起。他们认为卢旺达、斯里兰卡、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都是例证。现在种族或民族的政治化以及他们为了权力的争斗就被称为“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而与“美国化”相反。雷蒙德·V.雷恩(Raymond V.Raehn)也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世界的混乱。他举例说,津巴布韦以前由白人控制,后来白人不再控制后就是满城饥饿、到处是残酷的部落屠杀的景象。
三
保守主义认为平均主义违背了自由个性和自由发展的原则,而实际上“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等于平均主义。对弱势群体如黑人、妇女等的关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虽然确实有些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有时会走向极端,但也不能因此而被完全否定。事实上,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确实对他们有实际的帮助,也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有其社会历史原因。肯定性行动计划就是为了扶持弱势群体,使他们能够获取和其他群体一样的社会权利,只有获取公平的社会资源,弱势群体才能充分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发展本民族或群体的文化,以丰富整个社会文化。可见,“政治正确”并不以压抑个性的平均主义为其目标。
保守主义者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会导致逆向歧视的观点也存在疑问,比如文学课程中作家的选择标准,当然要以其文学作品的价值为首选标准,但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本身也没有定论,往往以欧美白人男性的价值标准为基础。以这样的标准,黑人和妇女作家入选的几率就要小得多。因此,很多美国高校在选择作家时增加了作家的身份配额,就是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要改变欧美白人男性为主导的价值观,这个举措就是必要的。再者,语言是社会的反应,对非歧视性语言的提倡,恰好显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正面意义。用“美国原住民”替换“美国土著”,不仅能够避免引起印第安人的不快,也能够培养学生在文化方面的敏感性,从而实现文化多元主义。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因为表达自由本身也得遵从社会道德和礼仪,比如学生不能用骂人的词语,这难道也是语言警察吗?在语言上顾及曾经长时间遭受歧视的黑人的感受,顾忌其他弱势群体的感受,难道就是法西斯和总体性控制的体现吗?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当然,对语言敏感性的培养也应该适度,过度则会违背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语言混乱。
保守主义者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评似乎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矛盾,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因此,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全社会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阶级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没有阶级的存在,完全的公平也就实现了。另一方面,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才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关注各弱势群体,提倡各种族和各利益群体的平等权益。关于逆向歧视,玛丽安·阿依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逆向歧视这一指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要构成逆向歧视,就必须是不公平对待,而反政治正确者所控诉的例子,如某大学出于配额考虑而对黑人教授的优先录用,不是以其专业价值来衡量的,因此会使得教授的整体水平下降。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一是价值标准本身就是具有争议的问题;二是对黑人教授在聘用上的优先考虑和以前大学优先考虑白人应聘者的情况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白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具有相对于黑人的明显优势。在聘用黑人教授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脱离黑人问题的历史背景。结合历史分析,当前大学要优先聘用黑人教授的压力和当时大学要优先聘用白人教授的压力,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白人所处的优势地位是整体性和体制性的;而当前对黑人的倾斜是个体性和政策性的。我们也从未听说过,有白人仅仅因为是白人而被高校拒绝,或不能享受社会福利,控诉者的文本中也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所谓的“逆向歧义”只是断章取义和夸大其词。保守主义者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把种族问题政治化的指责也显得牵强,种族、民族平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如果是为了争取平等权利导致的战争,则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指责说到底还是白人中心主义,还是一种种族优越论,如前文提到的雷蒙德·V.雷恩的观点。
实际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问题保守主义者并没有指出来,而美国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蒂却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罗蒂认为文化左派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在政治上的疏离和不参与。“他们退而观望自己的国家,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把它‘理论化’。他们选择了文化政治,而不是真正的政治。他们对认为民主机构可以促进社会正义的观念加以嘲笑。他们选择了知识,而放弃了希望。”正因为此,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被冠以“乌托邦”的称号,不仅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遭到右翼分子的责难。无论是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都过于注重文化的能动性,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政治领域的关键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单向度人”的控诉虽然发人深省,但在警醒世人的同时却没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语言学转向之后许多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沉溺于理论术语的发明创造,而离社会政治实践越来越远。因此,虽然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和学术界越演越烈,似乎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权,但在政治领域却没有相应的建树,“政治正确”也只能在道德的层面发挥作用。当然,这并非如罗蒂所认为的只是“观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改良左派也同样忽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只是从微观政治入手,注定他们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罗蒂希望构筑的真正民主公正的、作为世界之典范的国家。事实上,就美国社会内部而言,从196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的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和权益有了显著提高和改善,但整体上始终是不能和白人中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因为政府的政策始终以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中心,这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对外来说,不管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还是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精神旨趣相左的。就伊拉克战争而言,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2004年6月份,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4%)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场错误,但是“政治正确”在这个时候并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来左右政府的决定。所以,“政治正确”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在道德的层面上起作用,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关于“政治正确”的争论其实质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自1960年代以来不同主张的集中体现,其中难免有极端情绪的发泄,但两种不同观点的相互牵制客观上使得“政治正确”的运用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走向极端。这恰好也反映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被美国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收编,注定了“政治正确”只能在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范围内起作用,而并不能从根本上,即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维护各种族的平等权益。
①“Politically Correct”, Add. 3.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 3 ed. 1993.
③Jefrey D. Breshears,ABriefHistoryofCulturalMarxismandPoliticalCorrectnes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2000, p.1.
⑧Tod Gitlin,TheSixtiesofHopes,DaysofRage, New York: Bantam Book, 1987, p.395.
⑨Simon Frith, “Political Correctness”,CriticalQuarterly, Vol.35, 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