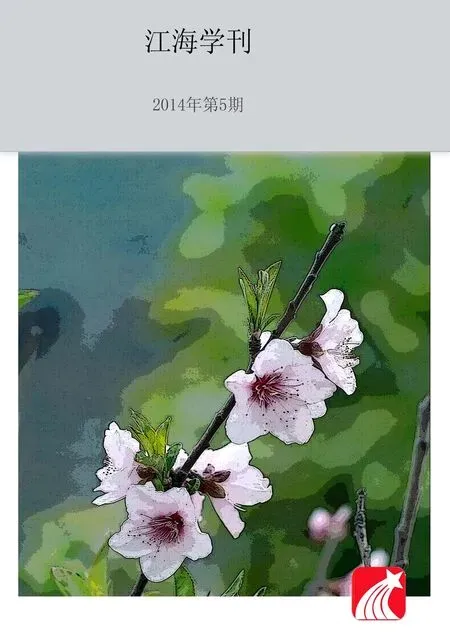海德格尔“时间性”视野下的“存在”问题*
宋惠芳 李静含
“存在”问题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却是个至今未决的问题,当哲学的理智思维致力于将自己变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时,无形之中,“存在”的本质成为了“存在者”式的存在。当“时间”成为哲学专题性的叙述对象时,它也被当成一种“存在者”,并且还是衡量“存在”与“存在者”的标尺。虽然很多哲学家都对“时间”进行了界定,但他们的“时间”都只能用来说明变易的现象而无法解说“存在”和时间本身,这种未将“存在”与“时间”的意义事先考察的做法,使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诸多困境。海德格尔力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和“时间”的种种规定,以“时间性”为切入点,展开了研究“存在”问题的新视野。为此,本文将从传统形而上学的时间谈起,通过时间观的流变来阐释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意义。
传统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论困境
对于哲学的起源,人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它开始于米利都学派泰勒斯式的思考。康福德说:“跟随在更早时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哲学的历史从这里开始。……我把这个新纪元说成是发现自然的时代……当人们将宇宙看成是一个自然整体、有其自身恒定的方式时,科学就开始了。”①康福德对于哲学开端的描述至少为哲学思考其自身提供了以下几点提示:与神话时代的暧昧不同,哲学的思维是理智的;与神话时代的观念不同,哲学视世界为宇宙的整体,并试图观察它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与神话叙事不同,哲学倾向寻找自然整体的基本质料和动力,对于明确因果联系的探寻,使得哲学成为一切科学的源出。
早期哲学的性格为以后哲学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调。理智思考、对象化静观、追求事物的根据,这三种性格使得西方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理智致力于抽象,排斥感性的杂多,试图寻找不变的统一;静观使活动着的一切退居到背景位置,世界和事物单独凸显出来;追求根据的做法将存在着的一切建基于一个固定的、恒久的某个存在上,哲学所追求的“始基”就呈现出永恒的本质意义。显然,这三种性格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规定的。从“始基”问题到“存在”问题的提出正反映出哲学开端性格的必然结果,我们循着赫拉克利特到巴门尼德的道路就可以看清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时间意识随着这种哲学性格也把自己带到突出的位置了。时间意识与运动、生成、消逝等物理现象相关联,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时间伴随的是物质世界现象的流变,一切变都随着时间,一切时间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变本身。“时间”在这里昭示了它的二重地位:一是作为尺度,二是作为本体,这样一来,时间本身是永恒的,世界的始基必须能够与时间并驾齐驱,那么始基必须是永恒的。赫拉克利特说这个始基是“逻各斯”式的“活火”,适用的是物理意义上的自然,而当人的认识因素参与进来时,思想就需要对自己的对象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是按赫拉克利特的说法,面对物质的世界,当我们说“是”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了。如果我们无法把握它的“是”,那还能说“有物存在”吗?巴门尼德认为,理智的思想一定对应了它能把握的对象,能够被思想的东西必须能够存在并持续存在;理智的思想不会被混乱的感官所欺骗,生灭变换的事物是不真实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当思想高于感官、不变高于变化时,“存在”优越于“非存在”。他说:“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它完整、不动、无始无终,它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而是整个现在作为单一和连续性;因为你在哪里寻找它的来源呢?它是怎样生成,在何处生成?绝对不能这样言说……”②就这样,在理智思维的模式下,“存在”为了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始基,需要在时间性上取得优势地位,于是“存在”确立自己与“时间”一样永恒,并且与时间统治下的现象相分离。
这样一来,“时间是什么”的问题也随着存在问题的发展被专题化地探讨了。柏拉图首先对于“时间”的产生做了描述,说它“和天体一同产生”③,相对于真实存在的“理念”,“时间”只是永恒理念之影像的动态标记,并且属于生成物的现象。他还将巴门尼德对“存在”依靠“一种时间”的言说方式更明确地规定下来,“我们常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只有‘现在是’才准确描述了永恒者,因而属于她。‘过去是’和‘将来是’是对生成物而言的。它们在时间中,是变化的”④。在柏拉图规定了“存在”的超越时间的永恒性言说方式后,亚里士多德从另一个角度对时间和存在进行了规定,这体现在他专门在“物理学”的意义上讨论时间。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比一切在时间里的事物都长久……永恒的东西不存在于时间里。”⑤这突出显示出时间的“容器”性质。他还写道:“时间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⑥这是物理意义上的计量化时间。他同时在《形而上学》中划分了一般的存在物和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并认为研究后者是这样一种科学——在研究了具体存在物之后,要研究它们之所以如此存在之原因的科学,即“物理学之后”,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不言而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存在”既然要成为存在物的原因、根据或者什么别的本质结构的东西,它就不会处于时间这个容器中,而是超越时间的永恒性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学说一方面使“时间”成为物理现象的标尺,使人们设想可以有无限计量的一维线性时间;另一方面,使“存在”的学说致力于成为超越时间现象的“永恒真理”,哲学研究“存在”的同时也致力于成为超越所有科学之上的科学。这一点在近代哲学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近代哲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看法,也继承了传统哲学的性格——使自己成为所有科学的基础。“存在”作为“实体”的学说贯穿了近代哲学的讨论,虽然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的性质及之间的关系问题居于讨论的中心地位,但其前提的观念乃是:无论是心灵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实体的本质是不变的,这样才能作为支撑现象的基底。因此从根本上说,“存在”问题是站在物理现象的对立面,与“时间”对立,然而反过来,“存在”被时间规定为“永恒”的“现在是”,并且还要成为物理现象的基础。这正是从古典到近代,哲学陷入困难的地方: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像一条鸿沟,分裂了“存在”与“存在者”,如果“存在”完全超越了物理世界,它自己怎么回过头来再去给现象一个说明呢?
我们注意到哲学开端的性格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时间”和“存在”被专题化地把握之时,传统哲学中的时间没有尽头,也难以寻找它的开始,“存在”也成为一个空中楼阁的问题。如今,科学的发展专注于具体的存在物,它们被看作遵循因果链条的自然,将它们一网打尽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哲学的“存在”在具体的科学面前似乎只是一个假问题。如果“存在”问题还是试图使自己成为一种依靠“物理学之后”得到规定的科学,而“时间”也只能根据物理现象得到理解的话,哲学将使自身陷入逻辑困难。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生存着的人的活动,曾一度被标识为最“幸福”的活动,而人们却看到它已经很少关心人,既然它实际上只是简单粗暴地将人类视为肉体与灵魂的结合,继而规定了理性、感性等机能的工作领地;但似乎所有“善”的东西都属于时间之外的超验领域,那样的“存在”又是否肯委身自己给有限性的人接触一番呢?然而真正的问题则是:已经被规定了的“时间”与“存在”各自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楚的说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都不可能像“存在物”那样被把握,却以一种晦暗的关系相互规定着,至少说是试图相互规定。如果问题出在哲学的源头,那我们必须重新对“存在”问题做另一角度的考察。
海德格尔存在问题与“时间性”的提出
“存在”问题重新被提出之后,要求一种与传统哲学性格不同的新方向。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提到“存在论差异”⑦的问题,即“存在”与“存在者”的不同。他认为传统哲学在提出“存在”问题后,就将之遗忘了,对“存在”的讨论不过是拘泥于“存在者”的讨论,具体科学从一切现成存在者身上考察其存在方式,以至于哲学只是为了给具体科学提供一个理论根基而绞尽脑汁地对“存在”进行规定。“存在”问题不将自己依附于科学性的研究之上再试图超越它,就必须改变哲学问题的制定方向。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不是关于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者存在论”⑧,而且也“并不以设定的方式肯定与这样那样的存在者相关”⑨。科学之所以能着眼于现成存在者进行研究,乃是因为已经有什么东西被给出了,已经有一种事先的但非科学的对于“存在”的领会了。
对于这种先于一切具有规定性的存在者的“存在”,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存在”不关涉任何某个确定的存在者,它看起来就像“无”——“人们能对自己表象诸如存在之类吗?这么尝试的时候我们没有晕眩吗?事实上,我们立刻不知所措、晕头转向了。存在者——那是某物,桌子、椅子、树木、天空、物体、语词、行动。存在者如此,可存在呢?这存在看来就像无。”⑩于是,在考察初期,海德格尔说,“径直承认:关于存在我暂时无法思维”。但另一方面,在对动词“是”(存在)的每一次运用中,我们都思维了,并且以某种方式领会着存在,虽然不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它。由此可以看出,“存在”问题的实际重要性——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领会它,而如今在科学的概念化思维下,“存在”的意义晦暗不明,许多哲学理论暗中将它设定为一种物。于是,海德格尔希望扭转哲学开端的理性化、概念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将“存在”问题从“物理学之后”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为此,他的存在论要求一种非科学式的新方向,这种新方向讨论的不是现成化的东西,不问它“是什么”而是追问其意义。与此同时,与传统哲学“永恒存在”的言说方式息息相关的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随着“存在”问题的重新发问也要被重新定位。
事实上,对“时间”的重新言说在哲学史上不是没有过,传统哲学在它的继续发展中也曾有过一种非科学式的、非物理性的“时间”,但是其言说方式仍然无法摆脱存在问题的困境。在奥古斯丁与康德那里曾有过一种将“时间”不依附于物理现象进行解说的意图,他们将“时间”依靠人的认知形式来解说。在时间起源这一点上,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态度是一样的,“时间”是被造物,这解决了上帝的至高权威,但在时间现象的解释上他与柏拉图不同,如果说柏拉图的“时间”是对客观事物的标记,那么奥古斯丁的“时间”则是一种主观化了的心理时间:“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他认为“过去”与“将来”都要依靠“现在”得到界说,而“现在”是持续的当下的注意,时间以心灵的这种注视得以存在。如果时间只是我们自己心相的改变,那么有所变化的就不是外在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本身不存在任何变化,所以罪恶的产生只是人类心灵的错觉。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第一次将时间与人的思想活动结合在一起,但他并没有解决心灵的时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试图做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康德的时间观综合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他划分了属于“存在”领域的本体界和属于时间统治领域的现象界;在奥古斯丁的意义上,他把“时间”归结为人的先天认识形式以沟通人对时间现象的认识。“时间”在康德这里就具有了二重属性,是经验的现象也是人的思想形式,康德试图用“时间”作为纯形式与先验图型沟通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认识中的感性与知性因素,这在认识论上做得很成功,但当康德再要前进一步,进入到本体界就出现了困难——无论是作为认识形式的时间还是作为现象表象的时间,都无法与本体界沟通,而康德却坚持本体是现象的原因,可一个无时间性的东西如何成为一个有时间性东西的原因呢?
因此,海德格尔注意到,无论是把“时间”归结为主观还是客观都无法解答存在问题,因为传统哲学的“时间”归根结底是依靠“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衡量的时间流动,它预设了时间是从“过去”经过“现在”流向“将来”的一维线性之流。对于这种时间,人们追赶不上它,对于“存在”的领会又由于首先依靠传统的时间性存在者——常常是从它们的对立面来领会,把“存在”设定为永恒之物。如果传统哲学将具体的存在者设定为处在时间之流中的时间性东西,那么传统哲学的“存在”就致力于成为一种“无时间性”的东西;然而,只要“存在”是依靠“时间”被言说的,它就根本不可能是无时间的——“‘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看来也是‘时间性’的”。传统哲学表明,“时间”是“存在”的一种言说方式,人属于时间之流的活动主体。人们对于时间之流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无限和无法逾越,反观那种时间,人看到的或者只有冷冰冰的物理时间及其现象,或者抽象它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类的尺度,还用它划分出永恒的真善美的世界与变易的生灭轮回的“不真”的世界。但是,这么做究竟有何道理?晦暗的时间观念导致了“存在”问题的遮蔽,因此,要重提存在问题,澄清“存在”的意义,就必须对“时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与存在
那么,究竟如何把握“时间”?“究竟可以沿着哪条道路向存在之意义推进呢?”介于这两个晦暗的问题,海德格尔走了一条迂回的路。他首先指出,任何“存在”都是存在者的存在,要考察“存在”,须从存在者入手。而在众多的存在者当中,有这么一种存在者,不仅在它的存在中是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或者说它的本质不是现成规定的,它总是能超越自身在生存中不断地获得自己的本质,而且它能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把这种存在者称之为“此在”。“存在”意义的领会属于“此在”的生存活动,那么构建存在论的任务就要首先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入手,原原本本地解说此在的各种生存样式和它的整体结构,存在的意义领会就随着此在的生存显示。由于存在问题的新提法,被称为“此在”的人的存在,也必须脱离传统人学的现成化规定,此在不是“理性的动物”,也不是“意志”这些种种片面标签的东西;此在也不是相互分离的灵魂和肉体聚合在一起的影像,其中每一部分有自己分配好的功能;此在也不是为了建立什么道德的伦理学才进行各项生存活动。相反,现存的一切此在的活动遗产,物质的或理论的,都源出于更源始的东西,那就是此在本真或者非本真的生存活动,领会又属于此在的生存活动。而要清楚地阐明此在的生存活动,就不得不从新的“时间性”视野出发。在此,海德格尔将“时间性”赋予新的涵义,并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时间性——被海德格尔称为“时间状态内的”。海德格尔将这一任务总结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领会时间。为了摆明这一层,我们必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时间和此在,都要因为“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而加以重新解说。
时间性与此在的生存活动密不可分。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一种“存在先于其本质”的存在,即是说,只要是此在式的生存,它就必然超越自己已经获得的实际性,并且这种超越活动是基于自身的选择,并在这种超越性中不断获得自己的本质。此在的整体存在被阐释为操心,整体的操心结构由“向死存在”这一现象规定,死亡从生存论上体现了此在的有终性,也体现了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恰恰是死亡这种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凸显了此在的时间性。海德格尔对操心的此在的规定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这就分别对应了“将来”、“曾在”、“当前”三种时间样式,同样也对应着此在的三种源始展开方式:领会、现身、沉沦。时间性被提出来作为贯通操心各个环节的可能性条件。
海德格尔将时间性阐释为动态的“到时”,时间不是传统哲学中那种线性结构与均匀流逝的时间流,而是“将来”、“曾在”与“当前”的三维统一到时,这三种样式并不与传统意义上的将来、过去、现在一一对应,反而是后者的规定要依据于前者时间性的统一到时。“将来”并不指未曾到来的将来,而是指先行于自身的此在本真地是“将来的”,当此在本真地先行到死中去,依其可能性生存,能在地成为它所未是的,将一切可能性收回到自身之中。此在只有存在于“将来”,才能将本真的自己带入“曾在”。此在一向是被抛的,这意味着此在本真地是如其一向已“曾是”的是此在,此在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这似乎有些费解,过去如何源出于将来?“曾在”不是指过去了,因为此在只要在它就不得不在,因而它不会过去。而曾在的此在一向被抛,此在承担起自己的被抛境况乃是担负起生存的自由,此在被抛入的不是别的,而是自身的能在,被抛入了“将来”,因此,只有此在本真地是“将来的”,才能本真地是它的“曾在”。此在又总是沉沦在世的,当它操劳于世,作为“寓于……之中”的存在,此在就是“当前”的,而之所以能够当前存在,乃是因为此在生存着能够有所行动地让周围世界来照面,此在才有所当前化。此在在最本真意义上先行入死亡,这是此在的“将来”持守于某种可能性而生存;此在的“曾在”则是不得不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它经受着这种可能性,在本真意义上“重演”自身;此在的“当前”就是让此在作为自身存在并且一直作为自身存在。海德格尔说:“‘先行于自身’奠基在将来中。‘已经在……中’本来就表示曾在。‘寓于……而存在’在当前化之际成为可能。”“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此在的“当前”将自己的“曾在”与“将来”贯通。
可以看出,“将来”在时间性样式中居于优先地位,因为此在本质上先行于自身,为它自身筹划着生存,先行等于说是超出自身从将来得以返回,生存论建构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而这三种时间样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三向度的线性规定,它们从根本上是一种此在的生存展开的样式,时间在这种三维立体结构中统一到时。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的三样式是同时到时的,它们没有先后之分;正如此在的三种源始展开方式一样,时间的三样式也同样源始开展着;时间性就是此在生存活动的展开。将来、曾在与当前显示出“向自身”、“回到”、“让照面”的现象性质,把时间性公开为“ecstasis”,上述三样式被称作时间性的绽出。ecstasis具有“站出去”这一涵义,这与此在的生存“existence”相联系,我们可以说,唯有此在生存,时间性才绽露为如此的三种样式;而此在的生存具有这三种时间样式乃是基于时间性的统一到时。
时间性作为此在生存的可能条件,也是此在领会“存在”意义的视野。那么从此在的时间性如何去把握存在的时间性呢?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继续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作,试图阐释时间性本身是如何于“存在”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他说,当时间性作为领会条件发挥作用时,就称之为“时态性”。此前,“时间性”被阐明为绽出样式,因此,海德格尔将此在领会的可能条件又称为“绽出之境域性图型”,此时,对于“存在”的“时态性”解说突出的仍是此在生存活动的本源建制。但他对于三种绽出样式的注意重心却从“将来”转移到了“当前”。在后期的《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则刻意略过了此在的时间性而直接谈存在的时间性,并且“当前”这一维度还似乎成了存在的优先状态。
“存在”的时态性被领会为“在场性”。“在场”状态与时间性中的“当前”密切相关,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结合着此在生存的“当前”这一环节对存在的时态化领悟加以述说。虽然“将来”在此在生存上处于优先地位,然而,此在的在此需要借助当前得以实现,当前使曾在的此在从将来回到自身。但此在的生存首先并不是本己的,而是一向从操劳活动中领会世界,根据打交道中照面的存在者来筹划时间,“操劳活动借‘而后’道出自己之为期备,借‘当时’道出自己之为居持,借‘现在’道出自己之为当前化”,世内存在者在当前化的此在生存活动中作为上手之物被达到了,这种时间开展出了世界之为世界,从而得以让世内存在者作为时间内状态来照面,让存在者作为“什么”来照面。也即是说,此在的非本真时间到时,将存在者赋予了时间规定性,同时此在也借存在者来领会时间。当此在遗忘了自己的本真时间,仅仅从“当前”的变式“当下即是”来领会的时候,“存在”的意义就被规定为具体的“存在物”,我们判断它是“在场者”,但这种规定都源出于时间性境域的“出场呈现”。并不是由于“在场者”才有“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在场者”需要通过“出场呈现”才是可能的。“出场呈现”属于时间性绽出的境域,属于超越着、生存着的此在活动的时间性本身,因此是一种比“现在”、“当下”、“当前化”更为本源的现象。正是这种“出场”,才使本真性的当前时间到时,“当前”显示为“让在场”,这是存在的“在场性”,即显现,也就是使世界、存在于此在生存活动面前自行解蔽。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是“存在”的时态性筹划才使人们对具体存在的对象化把握成为可能,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就出现在时间性领会的差别之中,与对现成存在者的实证科学式的研究不同,存在论就被海德格尔称为“时态科学”。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继续讨论“存在”与“时间”的问题,由于他“企图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以至于在《存在与时间》中的道路在这里就走不通,放弃了对于此在之于存在领悟的这样一种关系,直接的问询显得玄妙而晦涩。其中强化了的观点是“时间”与“存在”都不属于“存在物”,以至于海德格尔要求放弃“存在存在”与“时间存在”的谓述,而称“存在”“不存在”、“时间”“不存在”,排除了这种将“时间”与“存在”陷入现成的对象化概念描述的危险后,海德格尔说:“有存在和有时间”。对于这个“有”和“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从哲学的开端,就思了“存在”而却未思“有”。“从早期的西方-欧洲思想直到今天,存在指的都是诸如在场这样的东西。从在场、在场状态中讲出了当前。按照流行的观点,当前与过去和将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的特征。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这种在场性的存在被解蔽为一种可说也可思的事情,《存在与时间》仅仅是对这种在场性存在面貌的恢复,即将存在的在场性从现成状态的在场者上恢复到“出场呈现”上去,它展示了对“存在”与“时间”的本源性遗忘,却没有思那个“给出”存在和时间的“有”。因此,《时间与存在》里的问题问的是:如何在场?如何存在并活动?这个“有”是如何的?“存在”与“时间”的意义论说在这个“有”中显得艰深且难以理解。
海德格尔“时间”视野下“存在”问题的意义
虽然海德格尔对于“存在”问题的“时间性”述说十分晦涩拗口,在《时间与存在》一文中他自我辩护道:“演讲一直只是用陈述句来言说的。”这不禁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这种试图清晰说明一切的企图的失败不见得是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存在”问题不同于科学,“时间性”问题也不属于物理学领域。传统哲学的时间不仅与此在的生存活动无关,更与存在的意义无关,因为传统哲学中的时间、此在与存在都是静止不变的,具有现成规定性。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观念,是因为传统的流俗时间观将“时间”作为一种存在物,同时也作为一种尺度,用以划分“存在”与“非存在”;同时也将“存在”设定为“存在物”,因此“存在”的意义问题就被掩盖住了。
时间性问题突出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对西方几千年来传统哲学的颠覆。传统哲学的开端性格导致它从“存在者”出发探讨存在问题,对存在遗忘的同时也是对本源时间的遗忘,存在本身应该就是它自己,而不会是一个“什么”,这种“什么”只有在此在的非本真时间到时中才会发生,因此,无蔽存在的自行显现应当是一种本真时间的统一到时,存在于当下的样式统一到时,让自身作为自身存在。属于“出场呈现”的存在,是给出意义的“存在”,它必然不同于封闭性的被规定的“在场者”式的存在,因为“没有哪一种在场必然是当前”,它是在此在的生存之中见证“解蔽”的存在。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探讨第一次详尽地涉及对此在式的人的生存分析,而传统哲学对科学的关注以服务于人为目的时,执著于工具理性的哲学恰恰是对本真的人的生存的忽视。时间性被纳入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条件的分析,传统人学对于人的种种规定被解除,人属于此在式的生存,是具有超越性、充满可能性即自由的,就体现在它的生存是向着“将来”这一不确定性维度进行才是有可能的。
①康福德:《苏格拉底前后》,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②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③④柏拉图:《蒂迈欧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5页。
⑤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