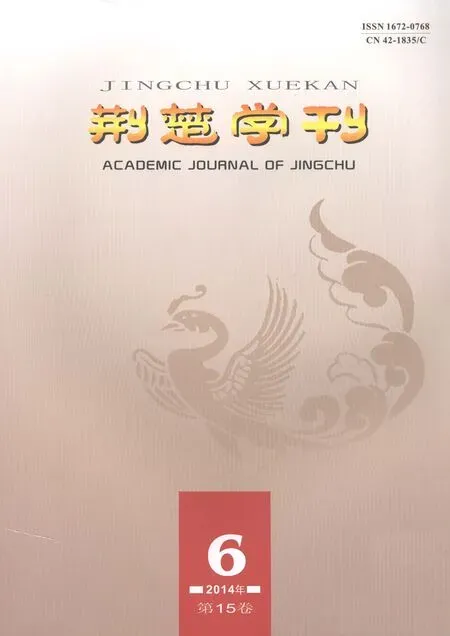论《晋承汉统论》所见习凿齿正统史观的双重维度
曹 林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东晋史家习凿齿临终上疏《晋承汉统论》,以改易正统、代魏继汉为全文旨归。此文计一千一百余字,以普通文论的篇幅来说,尚显简略,然而此文意蕴深幽,笔带霜风,不可小觑。所可道者,乃是习氏在此文中对正统史观的发挥,暗含了对强权政治的回应,体现出习氏正统史观的双重维度。
一、《晋承汉统论》的文本分析
《晋承汉统论》全文,本传录之,不载题名。清初著名辑佚学家汤球所辑《汉晋春秋》取论中首句为名,题为《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这里借用台湾学者雷家骥的提法,且就全篇主旨名之为《晋承汉统论》。习氏作此文的目的,历来都被认为是尊晋抑桓,是典型的借史倡言之举。这种以史学参预世务的做法也是魏晋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借用正统论来匡正人心并不是《晋承汉统论》中唯一要表达的心声,因为其立论是为晋争正统,其逻辑却落脚在了强权政治上。
观此论主旨在于“越魏继汉”(1)[1] 2154-2157。《晋书》本传记其临终上书言其“怀抱愚情,三十余年”,可谓执平生之念于一也。正如习氏在《汉晋春秋》中将三国历史,特别是蜀汉以外的历史,汇总为汉晋之际过渡期间的不正常时期一样,他在《晋承汉统论》里也表述了相同的看法。此论开篇即云“汉终有晋”,而“汉终”却不能立刻“有晋”,个中道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这就给汉晋之间的历史地位定了一个较为低平迂回的调子。接下来习氏大谈汉末如何政局纷乱、民不聊生,赞美司马氏终结战祸、还民太平,同时反复表露出对三国政治兴亡的某种低视和对宗汉的蜀汉政权的基本忽略: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歭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提到蜀汉政权时使用了“劲蜀”二字。历来史家文人皆以为蜀“弱”,而未有人以为蜀“劲”。其实这个“劲”并非指蜀汉的军事经济实力,而是指它在道统上所取得的独步天下的资本。蜀之“劲”在于其“杖正”,此之强正显出彼之弱。问题在于,既然习凿齿早已为蜀汉正名,为何在此文中发相悖之议论呢?
习氏对于正统所归的理解,是基于一个政权是否得民心和是否平天下来确立的,故曹魏凭其实力而不能纳入帝王序列,“未始于为一日之王”,是因为魏武“德不素积,义险冰薄”;而三国交争五十余年,仍是“各有偏平”的局面,则天下亦“实乱也”。汉晋之间,既无终极强力者结束混乱一统天下,各政权治下属民也未尝享受真正的和平,所以在习氏看来,无论魏、蜀、吴都不能真正堪当大统,如此,晋的作为就显得格外地气魄宏大了。所谓“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云云,将司马氏篡魏之后的事业描绘得气象万千,几欲与周汉比高。
但是,以上只能说明晋承汉统具备了一定的充分条件,却并不能说明代魏是必要的。对于后者,习凿齿的论述逻辑是这样的: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仗义而以贬魏哉?
这段话宣称曹魏因为未能灭吴蜀而定天下,所以曹魏继统无名。曹魏无名,在于其不能定于一,不能定于一,间接证明其君无道,如此则曹魏君亦非君。司马懿出于曹氏而悖于曹氏,既不必故作忠心以事无道之君,亦不必求虚妄之名荣显身后。曹魏不君,司马亦可不臣,因此借曹魏之资本充盈自身亦可,断曹魏之法统而溯求于汉亦可,故实在无须对“空虚之魏”抱持不必要的怜悯心。在习氏看来,晋之所以能代魏而立,是因为魏本就无可立之名。这就是习氏认为晋可代魏的根源所在。他又接着说司马氏“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把事曹魏与事天下分开来,将司马氏的篡逆当事天下(事汉)来讲,从而洗白了晋的出身。正因为晋得了天下,做到了“静乱”,做到了“功实显然”,才有“勋足以王四海”。这就在实际成就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把汉晋间其余不能“静乱”的诸强打倒在地。只有这样,晋才有“义可以登天位”的必要。
总体来看,习氏作《晋承汉统论》是从两条线索展开论述的。两条线索合而为正统论的方法论,借此指出晋代魏继汉的必要性。第一条谓“汉终有晋”:习凿齿借谯周所谓“炎兴”说,以图谶证明晋之统为汉统。然而以图谶迷信来揭示历史规律,完全是伪命题的做法,而习氏执意勉强,足以体现出他对僭乱的态度。第二条谓“静乱”:以司马氏取曹氏而后平天下,基本结束了自汉末以来的纷争局面,因而获得了建立正统政权的合法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曹魏、孙吴非正,则蜀汉亦不为正。倘若三国均不为正,则晋何以自立?而晋实则以曹氏自养,而后窥曹氏以自为,则以晋代汉如何能够成立?
此外,“吴魏犯顺而强”,晋也是如此。三国诈力相向,晋与魏、桓氏与司马、刘宋与东晋也是如此。如果说曹魏不君,司马亦可不臣的话,那么司马不君,天下可不臣者至多矣!因此,表面的正统论并不能掩盖内里的权力逻辑。晋竞力而兴、取衰而代,政权交替在实质上,和前人如曹丕,后人如桓温、刘裕,本没有太大区别。习凿齿“尊晋抑桓”的初衷要顺利展开,只能抛开“汉终有晋”的糊涂账,将晋的地位永久性地拔高,哪怕借以谶纬,借以曲论,也要完成匡济政治和理正人心的任务。
二、习凿齿正统论的双重维度
《晋承汉统论》体现的是习凿齿的史学理念和政治关怀。《晋书》本传云:“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每谓”者,谓其言多也;“三十余年”者,言其论积时之深。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起《汉晋春秋》的一大旨归,即为蜀争正。《晋书》本传所云: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以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裁抑桓温、以史学经世的目的来看,它与《晋承汉统论》是互相矛盾的。然而,为了抑桓尊晋,势必要强分魏晋,贬魏而崇晋。虽然《晋承汉统论》和《汉晋春秋》共享同样的解释范式:以汉晋为正,以吴魏为伪。但是《晋承汉统论》秉承《春秋》经世之意旨,在理论上将东汉以降诸政权作了高低贵贱的排列,以汉续周统喻晋续汉统,以殷灭周兴喻魏灭汉兴,是以强调代魏承汉乃古意而非新出。而以曹魏不臣、不道作为司马氏取而代之的堂皇理由,则在表面上输出了所谓代汉之正统的价值观,而实质上彰显了强权即是公理的信条。
这种悖论也表现在习氏的天命观中。习氏正统论强调“天心”[2]。《晋书》本传云习氏著史,“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天心”,在两汉、魏晋的著作中,含义达三种之多(2)。《潜夫论》云:“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3]《淮南子·泰族训》云:“故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4]这里的“天心”,当是指天帝、天君的心。按照孟子心性论的阐发,强权本不可扭转“天心”;但在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中,“天心”却顺应了强权。
习凿齿“越魏继汉”的立脚点在于对司马氏立国基业的肯定。故论中曰:“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但真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司马氏的皇位,始于阴谋篡夺;晋朝的基业,本是填补私心。司马懿的诛曹爽,司马师的诛曹髦,是权力欲使然,与“天心”又有何干系?至于司马宣王的臣节,连《晋书》本传都要借王导之口略书其“狼顾”“猜忍”之貌[1]20,然则所谓“纯臣之节,毕命曹氏”“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无乃过乎!正如饶宗颐所作的评价:“其抑魏即所以尊晋,要皆取媚于本朝也。”[5]
更重要的地方在于,正统的修正与改写,涉及继承者王位与统治权力的法理问题。西晋初立之时,陪臣多为曹魏旧臣,正统的厘定当以魏为宗才能稳固人心;而到了东晋,朝廷流亡失所,士民再承丧乱,本来就纷乱的人心此时更加不定。从维护本朝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若不打破固有的正统格局,以一更为强盛的王朝为国祚的依傍,则不能巩固新政权的法统,所以周秦汉魏之辩、周汉汉晋之统,是得于习凿齿政治理性的理解,而不是历史理性的理解。标榜所谓的“天心”,也只是抹平历史差异求得政治共识的工具罢了。
因此,习凿齿的晋代汉统之论,反映了他解读正统的双重维度,或者说两种标准。正统和僭伪这对概念被习氏把玩于手,从一个强加因果的正统序列开始,生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最后又暗中回到了原本所批判的立场上去。诚然,习氏的苦心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塑造,是对汉统不绝如缕的发挥,但是,习氏的正统立场,影响了他对历史解释的架构,扭曲了他对历史事实的读解。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晋都不必贬魏以代汉,魏晋之间的名实关系昭昭,而习氏强为分割则不免昏昏,其尊君的立场,恰恰与向强背弱的态度暗渡陈仓;而种种宣扬崇晋立场之举措,又不免造成了对史实的过度阐释和渲染,有伤史学自然之理。
三、习凿齿正统史观的历史理据
从史学的演进路径来看,习氏的正统史观没有局限在魏晋时期厘定正史和国史两大概念的统续之中,相反,其论述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公元四世纪中后期以来史学观念的转向过程。这倒不是说习凿齿以史学经世的理路是独创的,而是比较与他同时代的史家群体而言,真正把史学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的,乃至于从某些程度上来说牺牲了中古史学直笔与求实传统、大开后世讳史饰史之途的,正是习氏之正统史学。这个过程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由完全的天意史观向人文层面的靠拢,二是经学的政治解释和道德劝诫功能向史学的过渡。
儒学衰退后,史学渐成为经世的重要学术。中古史学演进到魏晋时期,单纯的天意史观已经不适用于新的情势。公元四世纪中期以后的史家如袁洪、孙盛、习凿齿等人都看到,史学不仅仅是要展现传之后世的遗迹,更是要传播若干“政治正确”的价值。此种“政治正确”,既包括了孙盛对枋头之败的直书不讳,也包括了习凿齿为证明越魏代汉所作的“曲论”。习氏笔法《春秋》,然而较《春秋》更显隐晦,因为他敢于将汉晋之间五十余年的文化与政治论争一笔勾销,将司马氏从曹魏的陪臣之位挪移到汉室家庙之中,以僭伪之僭伪为正统,以非君之非臣为忠义。然而此文传世一千七百余年,毫无笔墨鞑伐之事,一是因为习氏的主张取得了道德的制高点,二是因为正统论作为一种表面上排他性的政治文化理念,它本身也是一种弹性选择。这是因为正统与僭伪实际上并不是一对单一指向的概念,这对概念所依附的诸如民本学说、五德终始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等等,虽然表面上是与上古以来的人事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同时他们也是可以改造和修正的。因此,在实际施用的过程中,正统也好,僭伪也罢,几乎都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产物。
从这种思考出发再来看《汉晋春秋》的述作,或许可以理解习凿齿的一番苦心。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一方面是要借远喻近,裁抑桓温“觊觎非望”;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兴王迹”,拔高晋的历史地位和晋诸帝的历史贡献。这条脉络也为《晋承汉统论》所继承。但是,后者出于全力匡正世道的理想,将个人的政治意见强加在原则上持中立态度的史学中,导致在“越魏代汉”的旗帜下,输出的却是强权政治的足音。雷家骥先生对此以为,习氏取强而向,虽然“动机或可悯,然而此行为效果则不可谅”[6]。习氏之后,统治者的意志对国史和正史的渗透、干预和制导已成定局,史学被迫走上了回护政治人物、剪裁历史事件的道路。官方修史所导致的虚美隐恶问题,或许都要回溯到习氏利用史学进行个人意识标榜的行为才能旁观者清。
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史学的政治功能化角度来评量,习凿齿对后世的正史观念和大一统王朝的国史结构的形成是有影响力的。而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又使人感到“曲论非理”的本质也不过是习氏试图就他所经历的近代史上纷泊而芜杂的政治局面做一次回应和总结,以使后世明断时人之思。《晋承汉统论》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人面对世乱的不安和思考,以及表现在史学观念上那种极力想要从禅代之朝和剪伐之际抽取一些理性和规律的成分而做出的努力。这就如同后世对正统的叙述及其改写,充满了叙述者、改写者的思想世界与所处时代之间的交锋和张力[7]。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习凿齿只是剥取了他所属于的时代精神,他的作为也恰恰映射了这种精神。
注释:
(1)本文所有关于《晋承汉统论》的引文均引自《晋书》习凿齿本传,恕后文不再一一注出。
(2)这里借用田浩对天心的研究心得,见田浩《跟随史华慈老师研究宋代思想史:论朱熹和天》,出自许纪霖、朱政惠《史华慈与中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60-161页。
[1]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张承宗.《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J].史学史研究,1996,(2):35-40.
[3] [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M].[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88.
[4] [汉]刘安,高诱.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4:347.
[5]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7.
[6]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M].台北:学生书局,1990:355.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4.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