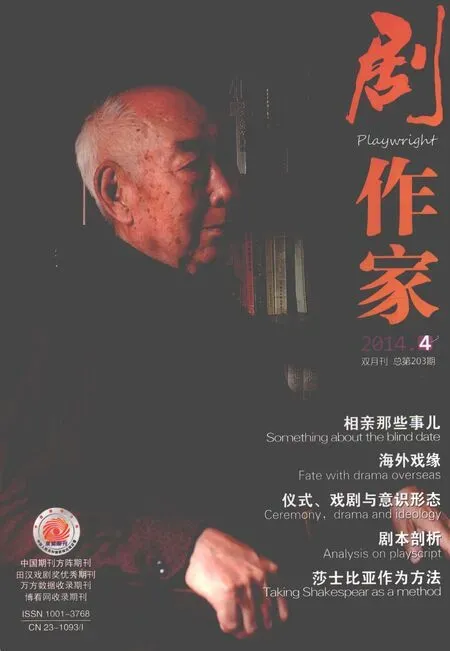剧本剖析剧作原理及技巧(续)
黄维若
剧本剖析剧作原理及技巧(续)
黄维若
在《马拉·萨德》一剧中,宣告者在介绍人物设置时,有时会引入哑剧或木偶式的表演。比如在本剧第四段,他介绍完马拉之后,又说:
“诸位请看我们这出戏里的科黛
(指科黛,她正在抚平衣裙,系牢胸巾)
她是卡昂人,外省贵族出身服饰漂亮,鞋子摩登
(指鞋子)
她正在系牢胸巾
(指胸巾)
根据史家的见解和我们的意见
她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
(她站起身来)
可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本院病人
既患梦游病,又患抑郁症
(科黛闭上眼睛,脑袋后仰)……”(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版,第242页)
科黛这样一位激情而执著的暗杀者,由一个有梦游和抑郁症的病人来扮演。我们前文已说过,因为她许多时候嗜睡且昏昏沉沉。于是这位女刺客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人指使被人支配被人挟持着去完成舞台行动。该人物设置的后边,有着深刻的语境。世界上所有的暗杀者,无非两种:一种是为了钱,或者因为承诺与契约;另一种因为某种信仰、冲动、幻想或狂热,其实被自己的主观意念所支配。科黛是后一种类型,是一种激情杀人。从历史上真实的科黛刺杀马拉,到她被捕、被审、被断头的完整过程都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剧中科黛的扮演者,因为梦游或嗜睡,使得她身上的激情、狂热、幻想被消融得一干二净,再也没见过这样一位萎靡不振、昏昏沉沉的刺客了。剧中的她,基本上是被精神病院的强力护士支配着去干这一切。难道这精神病院就没有别的人选?没有兴奋狂热型的病人?挑选她是一种故意,而非偶然。形成一种借喻:所有的暗杀,无论是因为利益还是基于狂热偏执,其实都是某种强迫症,都是不正常的人类行为,体现了被扭曲的人与自己,或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悲剧。就历史上的科黛而言,彼得·魏斯在剧本后边所附“对剧本历史背景的说明”中说:
“夏洛特·科黛可是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她的计划,寺院生活养成了她出神玄思的习惯,她单独一人出发,一心想当贞德和经外书里的尤迪特,把自己变成了圣徒。”(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版,第247页)
历史上的宗教狂热和主观幻想支配着生活中的科黛去杀人,与剧中疯人院的强悍护士,支配着戏剧人物科黛去杀人,把生活与戏剧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逻辑通约,将两者联系了起来。这是《马拉·萨德》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与此同时,用哑剧形式表现歌队叙述内容,也是叙事剧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我们还记得,前文分析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第一段结尾处,因为带着那个孩子又麻烦又危险,所以格鲁雪想不管他,可是良心又使其不安不忍。于是:
“(歌手唱)她坐在孩子身边,守了很久,
傍晚了,夜深了,
黎明了。她坐了多久,
就注意了多久,
均匀的呼吸,娇小的拳头,
直到天明的时候,诱惑变得太强了!
她站起来,低下头去,叹口气,抱起了孩子,把他带走。
[她(格鲁雪)作歌手所描述的动作。”
(见《布莱希特戏剧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276页)
此段是人物塑造的一个关键节点。忐忑不安内心煎熬的格鲁雪,她胆小,与此同时危险在逼近,使她不敢去抱这孩子;但她的善良,又使其不忍离去;她的某种天真与自欺欺人,还使她内心盼望会来一个什么人,她可以将孩子弄到别人手里,走之大吉了,良心再无负担了。歌手把应该由格鲁雪表演出来的内心活动,及产生的幻想,还有一夜当中她的进退无措,全都唱了出来。此时人物格鲁雪存在于舞台上,在歌声中“她作歌手所描述的动作”。我们曾经总结说,这是一段哑剧式的表演。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段木偶戏表演。歌队就是那些牵线的操纵者,人物格鲁雪就是个人偶,说唱这种叙述成了核心的表现手段,演员扮演的格鲁雪,其表演完全被说唱所牵领,以身体去将说唱内容变为可视的舞台形象。这就是所谓间离化手段。如布莱希特所说:“间离化的表现是这样一种表现: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其题旨,但同时又使它显得陌生。”(见斯泰恩《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第三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716页)
可以看出,《马拉·萨德》中宣告者对人物设置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加索灰阑记》上述手法一脉相承。即此时的科黛如人偶一般,将宣告者的叙述内容,变为可视的舞台形象。这类表演似乎还有更久远的来源,但非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要强调的是,《马》剧中作者的意图还不止于此,他将此种哑剧或木偶式表演,扩大到科黛的整个舞台行动中去,比如上场、下场、说台词、完成舞台动作等等方面,很多时候都要由护士们拖来拽去,由他们挟持或指使。其实真正的支配者是那个宣告者,他手里的指示棒一指,护士们就会有所行动。她的嗜睡,必定使得她在全剧都被人支配,这个问题涉及到宣告者这样一种特殊的单人歌队,对全剧语法的解释与执行。这一点,我们下文再细谈。而就此节而言,哑剧或木偶式表演,也不仅仅只用于科黛,而是扩张至几乎每一个被介绍的角色,如剧中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雅克·鲁,这是前神父。他的戏不多,且其袖子被扎住,手不能伸出来,即受限制的精神病人穿的那种衣。但是他一旦有所动作,所有的病人都会被狂热地鼓动起来。介绍人物设置时,宣告者这样说:
“瞧那个教士,他挨近舞台背景
(指向雅克·鲁,他把两个胳膊肘向两侧拉开,并仰着脸)
他被隔离是因为政治上太激进。
雅克·鲁这一角色由他扮演
马拉的革命需要这种人。
他在戏里的言论
检查官删削得实在太狠
当代制度的维护者认为
他的调子太过分。
(雅克·鲁张大嘴,使劲用两肘向两侧拉开)
(库米尔伸出食指威胁他)”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版, 第243页)
仍然是哑剧式表演。但是与科黛不同。科黛是因为嗜睡,不得不被人挟持与支配,这个雅克·鲁不同,他本人没有任何病,只是因为“政治上太激进”而被隔离在这里。他被人强迫变成一个木偶,决不让他自由发挥。这不是宣告者的主张,他没有这个权力。但是他介绍了这个人物设置时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雅克·鲁在戏里的言论,检查官对之十分警惕,只要认为他的话有危险性与煽动性,就必须限制。剧本是无可奈何地“删削”了,但是扮演这角色的政治激进分子,会不会临场发作,趁机把舞台变为政治战场?看来谁也没把握,于是让他穿上疯人衣,强制木偶化。可见本剧中哑剧或木偶似的手法运用,又还有目的和功能的区别。其所以称为“哑剧或木偶似的”表演,而不称为真正的哑剧表演,是因为此剧还有真正的哑剧表演,那些饰演群众的疯子,有时又要充当哑剧演员。剧中还有几段真正的哑剧段落。说实话,这剧的戏剧形式与人物设置过于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其缺点之一。正因为如此,假使没有这个宣告者,本剧人物设置的介绍,还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见,在特定体裁中,歌队作为介绍人物设置的主要手段,是非常有效且极具特色的。
《马拉·萨德》中这个宣告者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充当该剧戏剧语法的解释者与执行者。
戏剧语法是一个自创名词,需要对其概念进行说明。戏剧由人物及人物关系、戏剧事件、台词、结构等等构成。这些内容都有其假定原则、逻辑结构、使用规范,也有它们的构成规律,及运用过程中的限制性。与此同时,它们要力求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机统一。所有上述这些原则与规范的实施,就构成戏剧语法。
戏剧语法一般体现在人物的舞台行动中。但有时也用剧本所附的说明,还有舞台提示等等予以宣示。用歌队对本剧语法进行解释和执行,是一种有意味的特定手法。《马拉·萨德》中的宣告者即是典型的例证。先来看本剧第十七段“科黛与杜佩雷的首次对话”:
“科 黛 (试图摆脱杜佩雷的拥抱)
(两名女护士插手,拽掉杜佩雷的双手)
你快去卡昂,
巴巴卢和比佐需要你
今天就跑
不要等晚上
到那时,你插翅也难逃。
杜佩雷 (激昂地,以咏叹调吟唱如前)
亲爱的夏洛特,我的岗位就在此地
(跪倒在她面前,双臂抱着她
的腿)
我怎能离开这个城市
我认识你就在这里!
亲爱的夏洛特,我的岗位就在
此地。
[不能自制地使劲抱住。宣告者用棒捅他,随后用棒击地。
宣告者 (提词)我为什么非得逃
杜佩雷 我为什么非得逃,
目前的局面长不了。
(使劲抚摸科黛)
英国舰队已经在
敦克尔克和土伦港外抛锚。普鲁士人
宣告者 (纠正他)西班牙人
杜佩雷 西班牙人占领了鲁西荣
巴黎
宣告者 (纠正他)美因茨
杜佩雷 美因茨已遭普鲁士军队围攻康德和瓦朗西安已被英国人
宣告者 (纠正他)奥地利人
杜佩雷 奥地利人占领。
旺代暴动。
(以火样的热情拚命亲热)”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75-276页)
科黛受吉伦特派影响,产生圣女贞德一般的自我认定,才来刺杀马拉。剧中杜佩雷,代表吉伦特派对她产生此种影响。这个人应该对科黛有一种政治感召力。从现在被打断得厉害的台词来看,这是剧本的原意。比如科黛要杜佩雷赶快逃走,因为这里太危险,到了晚上就“插翅也难逃”杜佩雷说他不走,他的岗位就在这里,他不能离开这座城市。这是非常崇高的政治信仰者形象。与此同时,因为饰杜佩雷的演员也是精神病院的病人,是个色情狂。色情狂不是街上的流氓,而是一种不可自制的病态。所以这段戏一展开,杜佩雷就经常会离开规定台词和动作,专心致志搞他的色情行为。他对科黛身体的欲望,远远超过他对戏本身的兴趣。这同样也是剧本的原意。两种意向交织在一起,作者想说的是,吉伦特派的政治狂热与不可压抑的色欲焚心混同一体。吉伦特派的政治行动与白日宣淫,也没有什么区别。激昂的政治信念表达,与色情动作的见缝插针,一定要同时进行,互相缠绕,两者都必须生动而清楚。这就是本段的剧本语法。如果完全是政治上的互相激励与崇高再现,这段戏就没有达到目的。如果完全是色情表演,又成了夜总会节目。所以必须有一种手段,使其平衡而清晰。这个手段就是宣告者。他一上来便宣布:“为了符合规矩而又得体,剧作者现在规定这么办。”(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73页)那就是给科黛配上杜佩雷作伴。这两人搭戏就意味着革命与色情配对,当然宣告者知道杜佩雷是色情狂,所以早早地便向他说:“别滥用你扮演的角色,你的爱是柏拉图式的。”但是要求色情狂理解拍拉图式的爱情,岂不是缘木求鱼?那人只要有机会就出手猥亵科黛,这就忙坏了宣告者,他要不断地提词,使戏不至于出错,不至于中断,而且饰杜佩雷的疯子色情动作太过分时,他就要制止,不行就用那根指示棒去捅杜佩雷,如果还不行,就打。本段中杜佩雷不仅“偷偷用手抚摸她(科黛)的腰和胯骨”,还“亲热地把手按在科黛的胸脯上”。最后他抱住科黛要激吻,宣告者只好动用护士上来“不客气地推开杜佩雷”,结束了本段。但是实际上,宣告者又要给杜佩雷以空隙,让他有色情动作。不然的话,本剧语法未见得能清晰实现。可见,本段中宣告者任务繁重,要使吉伦特派的革命台词,与杜佩雷的色欲表现处于互为表里的平衡状态,将作者定下的戏剧语法执行到底。因为剧中主要人物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精神病患者扮演,所以宣告者的类似活动,在剧中比比皆是。
《马拉·萨德》因为使用疯子演戏,除了戏剧语法出现复杂状况之外,失控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这就需要一个正常演出体制的维护者,这个任务也落到了宣告者头上。比如前文提到过的第十四段:“遗憾的意外事故”:
“[背景前一个病人,戴着神父的褶叠领,突然毛病发作,蹦到前面,双膝跪倒。
病 人 (急得结结巴巴)
祈祷吧,祈祷
向他祈祷
你,地狱里的撒旦
你的王国来到人间
你的意愿在人间实现
损害我们的清白
拯救我们从恶弃善。”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66页)
于是精神病院长库米尔一跃而起。男护士们扑向这个病人,把他捆上,拖到后面,强迫他站立在一个莲蓬头下。此时宣告者站出来“摇动拨浪鼓”,说:“这类事故在所难免,它活生生地显示我们所受的痛苦。”说这个人曾经是一名传教士,还主持过一所著名寺院。这次歌颂撒旦的发作,可看作“是他的一次回忆”。然后再摇拨浪鼓表示结束,戏回到正常的轨道。真是一次事故吗?此种语境后边,其实宣告者是有观点的。他认为这位著名寺院主持人,其魔鬼崇拜并非疯癫,而是对生活的真实回忆。未见得这是对宗教的批评。因为那位前传教士以反讽的语气,说我们的现实世界已被撒旦把持,魔鬼的愿望已在人间实现,大家都已“从恶弃善”。这是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所以作为监视与审查者的院长库米尔会“一跃而起”,勃然大怒。反过来我们从戏剧语法观点上再来看这段戏,其实它是作者故意安排的,从结构上来说,这样一种“意外事故”,会打破剧本的单调板滞。而从实质上来说,它对现实的强烈批判,仍然与本剧主旨一致。我们可以这样看:这段戏,本来是前传教士突然发作,破坏了戏的正常演出程序。但是宣告者拨转机锋,使其回归演出规范,同时使它仍然巧妙地体现本剧主题。
《马拉·萨德》中除了疯子们会时不时地闹出意外来,好些时候,他们对演出程序,比如什么时候出场,该谁进戏,谁该跟谁搭戏等等,也多有愚钝木讷之处。疯子演戏,你能要求他们什么?所以这时候就要靠宣告者来指挥他们。还有,此剧表现手段繁杂到堆砌的地步,专业人员演来尚且麻烦,何况不正常的人来演出?因此宣告者的临场调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会在剧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场面:
“宣告者 (用指示棒击地三下,指向科黛)
(西蒙娜站在浴缸前保护着)
(科黛首次登门)
[乐队奏起科黛主题……”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52页)
这是对人物上场,及音乐音响相互配合的调度。但有时候宣告者会故意不干预舞台上的严重混乱场面。比如第十八段“萨德对一切民族嗤之以鼻”,先是萨德对浴缸里的马拉一通驳斥,接下来宣扬他的个人主义:
“萨 德 ……我早已放弃了这种英
雄主义
我对这样的民族嗤之以鼻
我对其余一切民族也都嗤之以鼻。
[背景前传来一些嘘声。
库米尔 (在嘘声中高喊,竖起食指)注意!
病 人 (在背景前)拿破仑和民族万岁!
[台下爆发一阵尖利的笑声。
科科尔 (在背景前喊道)历代皇帝、国王、教皇、主教万岁!
[台下骚乱
波尔波什 清水汤和束缚精神病人的上衣万岁!
罗西诺尔 马拉万岁!
萨 德 (在骚乱中也高喊)对于循环不止的群众运动我也嗤之以鼻。
[台下响起尖利的口哨声。一个病人开始疯狂地转圈奔跑,第二个、第三个病人加入。男护士们跟在他们后面奔跑。
萨 德 对只能钻进死胡同的一切善良意图
我都嗤之以鼻。
对为某一事业而带来的一切牺牲我都嗤之以鼻……”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77页)
先解释一下舞台格局。这个剧场是疯人院里的澡堂子临时挪用的。所以水龙头浴缸等一应俱全。表演区的后部被称作“背景”,就是靠墙的地方。所有的未上场的角色包括群众演员都候在那儿。严阵以待的男护士女护士也都站在那儿。院长库米尔与妻女坐在舞台右侧的看台上。估计还有一些疯子作为观众也坐在表演区以外的地方。上引段落中的科科尔、波尔波什和罗西诺尔,是四人歌队中的三个成员。
本段戏因为萨德那种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激情演说引起疯子们的共鸣,所以大家乱哄哄地狂叫乱跳起来。大家高呼万岁。被颂万岁的对象们有拿破仑、民族、皇帝、国王、教皇、主教、清水汤和束缚精神病人的上衣。这些对象并列在一起,人们认为国王与拿破仑与疯人院里非人的伙食,还有疯人衣,都是一回事。万岁是假,强烈讽刺是真。大家未见得真正同意萨德那一套无政府主义说辞,但对否定现实中的一切,众疯子兴奋无比。场面变成疯狂大乱。本剧其他时候,每有此等情况发生,宣告者会马上出来,用指示棒击地,发出尖利的哨声,喝止这种骚乱。不行的话,他会支使护士们强力使疯子们回归本位,安静下来。他在剧中十分积极而繁忙。但是有好几次这样的大骚乱场合,他都一声不吭,根本看不出他的存在。这是故意的。这是作者的意图。对现实的严重不满,及疯狂而骚乱的群众运动,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某一个侧面,作者要影射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宣告者在这种场面时不作为。失去他的主动指挥,强力护士们也混乱无措,效率严重下降,只能跟在疯子们后边追赶。这是宣告者维护演出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需要说明一点,演出体制仍然属于戏剧形式范畴。
宣告者在本剧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面对苛严的审查者进行解释。院长库米尔要展示自己是文明与《人权宣言》的维护者,他允许演戏,自己也来看戏。可是戏中大凡有一点点与当局的政治规定不合,对现实进行批评的地方,库米尔必定得干涉。他有权力,可以禁演这戏。他有暴力,所有男女护士都是他的忠实部下。他与这个疯人戏剧演出群体,时常处于对立之中。于是宣告者便成了一个调解者。但是宣告者有自己观点。他会将库米尔不能容忍的戏剧内容,说成合理。比如本剧第十一节“死神的胜利”,舞台上表现大革命中处决犯人,被斩者的模型脑袋被斩下来后“像皮球似的被人抛来抛去”,众疯子兴奋至极,狂呼乱叫。这时精神病院院长库米尔干预了:
“德·萨德先生
这样可不成
这怎能叫做教化
这不能医治本院病人
……
[ 萨德不理不睬,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扫视着舞台。”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57-258页)
库米尔认定这种血腥暴力场面是不能被允许的。不见得他在为病人着想,而是当局禁止表现这种暴乱。疯人院里也不行,况且这里还隔离着许多政治岐见者。而萨德则明显对他抱有敌意。但两人如果争执下去,库米尔是可以禁掉这出戏的。于是宣告者出来说话:
“宣告者 (用指示棒击地并回答库米
尔的话)
我们只表演本城的往事一桩
它无疑发生过,非凡热闹。
因此我们不妨放心往下瞧
因为我们鄙视当年干的那一套。
在认识上,与那永不复返的时代比较
我们今天聪明得不知有多少。
[用指示棒指着行刑场面。长久的急速击鼓声。又带上几个新的死囚,他们站着准备就刑。”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258页)
那意思是说,这样一种场面是本剧风格体裁所决定的。舞台上的暴戾血腥场面,是历史生活中真实的事,表现那样的内容,不过是说今天比过去要好得多了。这倒不完全是诡辩。前文提到过,此剧本与真实历史有关系。于是库米尔也没再说什么,斩首戏得以进行下去。宣告者不是导演,剧本明确说明坐在一边的萨德是导演。所以宣示者作为特殊歌队,在此面对监视与审查,作出合理性解释,暂缓了监视者院长与导演的矛盾。宣告者也穿着病人的衣服,但是他是全剧最没有精神病症状的一个人。或者他是被隔离在这里的政治性人物?如果没有他的智慧,萨德是不可能将这戏演下去的,虽然他又是编剧又是导演。
作为单人歌队的宣告者在本剧中还有另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对该剧假定性原则的解释。假定性原则,我们仍然把它看作是剧本形式的重要内容。前文说过,《马拉·萨德》的假定性情况颇为复杂,所以宣告者的解释成了不可或缺。如剧中第三十段“科黛第三次即最后一次登门”,其内容说的是科黛第三次来到马拉家里,假装说要告发吉伦特派的暴动,终于走近到马拉的浴缸边,摸出她的刀,暗杀即将实现,这是全剧的高潮:
“科 黛 我来了,马拉
可是你看不见我,马拉因为你是死人。
马 拉 (半裸着,直起身子,叫喊)巴士
把我向你口授的写下来
一七九三年
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致法兰西民族......
[科黛面对面站在马拉身边。她的左手贴近他的皮肤,从他的胸部移到肩头移到头颈。
[马拉坐着,身子后仰,倒向浴缸的靠背上躲避,右手握笔。
[科黛从胸巾下取出匕首。她双手握匕首,高高举起,准备刺去。
[宣告者吹响一声尖利的口哨声。
[病人们、男女护士们在原地不动,科黛瘫倒。马拉又伏在板上作休息姿态。
宣告者 这纯属德·萨德先生的艺术技巧
他有意要在这里中断一下
好让马拉临终前数秒钟内
从我们的嘴里听到
他身后发生的一切
而台下的诸君当然全都知道。
[指观众
[乐队奏起快速军队进行曲。四个歌手走到台前。”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 版本同前,第335-336页)
这是舞台上的高度假定。所谓戏剧的假定性,人们有这样一些解释:
“戏剧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假定性的特殊表现范围和表现方式。如处理舞台空间的假定性方式等。‘假定性’的含义在于对生活的自然形态进行变形与改造,使形象与它的自然形态不相符。在戏剧艺术中,诸方面的假定性程度唯一的限度是与观众之间的‘约定成’……”(见谭霈生所作的“假定性”解释。转引自王晓鹰《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版,第11页)
王晓鹰对此概括道:
“戏剧艺术的‘假定性’实质上就是戏剧演出与戏剧观众之间关于‘真’和‘假’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契约’。演员在一个摆设齐全的‘客厅’里寂然独坐,观众不认为自己可以凑上去与他交谈,因为他们有过那样的‘契约’;演员优雅舒展地舞弄一根马鞭,观众却认为他是在骑马疾行甚至是征战沙场,也是因为他们有过那样的‘契约’。”
(见王晓鹰《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版,第12页)
我们前文讲过,《马拉·萨德》的假定性情况比较复杂。众人在精神病院演戏,这是剧本提供的第一层戏剧假定。那么在澡堂舞台上演出什么戏呢?这戏叫《马拉·萨德》,说的是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领袖马拉被刺杀的事情。或者还可以延伸出萨德与马拉的政治争论。这是剧本所提供的第二层戏剧假定——这是一出戏中戏。而本剧的第三层假定,是假定演出这个戏中戏的演员们,他们都是疯子或半疯子。他们在扮演人物的同时,还会时不时的失控,回到他们的疯癫状态上去,或将他们的疯癫带入到对人物的解释上来。所有这三个层次的假定性,都是演出者们与观众,达成约定俗成的契约。也就是说,开场后不久,观众都看明白了,承认这样三个层次的假定了。但是戏进行到上述科黛要刺杀马拉的一瞬间,突然戏中断了,停了下来,“病人们、男女护士们在原地不动,科黛瘫倒。马拉又伏在板上作休息姿态”,说是要让马拉在死前数秒钟知道,他死后发生的事。这是非常诡异的。中断刺杀,并让被杀者死前知道他死后的事,不完全符合前述三个层次假定性的约定俗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仍然是疯人院澡堂子里演的戏。但并非事先约定的马拉被杀的戏剧内容。也不符合到现在为止此剧本身的逻辑,同时它也不是疯子们的失控所致。所以必须让宣告者站出来进行解释:“这纯属德·萨德先生的艺术技巧,他有意要在这里中断一下,好让马拉临终前数秒钟内,从我们的嘴里听到,他身后发生的一切……”所谓解释,无非是要与观众重新达成新的契约,让观众在新的假定逻辑上来看戏。于是乎,杀人的科黛放下高举的匕首,沉沉睡去,惊恐地“倒向浴缸靠背上躲避”的马拉,又伏回到板上作休息姿态。也就是说,戏不仅仅是中断或暂停,它还退回去了一点,回到科黛举刀要杀人之前一小会儿的状态上去了。趁此机会,歌手们与乐队把现场变成了一次狂欢,闹腾着在军队进行曲中,演唱着马拉死后发生的一切,说是人们镇压了保皇党,砍了三千多人的脑袋,演唱者们说:“马拉,你向我们鼓吹的一切,如今正在解决。”又说他们后来还杀了丹东,罗伯斯庇尔也站不住脚,一命呜呼。这种血腥战争中拿破仑崛起,自立为皇帝。然后:
“[宣告者用指示棒给了一个信号。
宣告者 谋杀!
[ 科黛突然清醒,举起双手作猛刺的姿态,把匕首捅进马拉的胸膛。所有的病人一齐惊呼。
[萨德站着,得意洋洋,无声的微笑颤动了他的身体。
[所有的人站在浴缸周围,显示出一幅英雄气概的静态画面,具体组成如次:马拉倒挂在浴缸沿上,右手在外,如大卫那幅经典性的图画上的形状。他右手握笔,左手拿纸。科黛还握着匕首。四个歌手从后面抓住她,使劲将她的胳膊往后拽,绷开了她的胸巾,袒露出胸脯。”
(见《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338-339页)
全剧高潮以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其艺术个性非常强烈,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它将叙事剧的表现方法扩张到叙述学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如果从舞台是生活的再现的角度来说,此种假定是有疑问的。戏怎么可能到关键时候停下来,甚至又退回去一点点?一个将死的人,怎么能听到人们向他描述他死以后发生的政格局的大变动?但是如果舞台上是人们在讲叙生活,这种逻辑就可以成立。讲叙者——作者、演员等等,他们可以讲到某处停下,然后倒回去补充某些内容,还可以讲叙死者身后之事,这不妨碍暂停在那里还没死的死者听到这些。当然他们是装扮人物进行表演,用戏剧动作来讲叙。而这后边假定性的约定俗成,则由宣告者来完成。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从本质上讲,戏怎么样写、怎么样演都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这样做之前,一定要与观众达成假定性的契约。而在这种约定的后面,仍然要有自圆其说的逻辑。或是生活逻辑,或是叙述学逻辑,荒诞派戏剧也有它的哲学逻辑,中国戏曲有自己的写意逻辑……而采用歌队来进行假定性原则的解释,及与观众达成协定,甚至补充协定,不失为最直截了当的办法。直截了当不是简单粗糙,《马拉·萨德》中的宣告者就生动地诠注了这一点。
但是宣告者对本剧假定性的解释与推行并未就此打住。接下来的”收场“一段,他向观众宣布说,在观众退场之前,他们要把这戏的内容再概括一遍。于是死了的马拉又出来,把他的信仰主张又说了一遍。科黛也出来,把她的动机与想法也说了一遍。激进社会主义者雅克·鲁也出来,照样否定这一切,而且煽动性极强。男女护士照样把他拖了下去。萨德也谈自己编导这戏要达到的目的,库米尔也把他代表官方的观点说一遍。本来这样做是架床叠屋,重复且啰嗦,戏是往下掉的。但是这个戏往往不按常规出牌。这些人的话让所有的病人与歌队躁动起来,他们开始齐步前进,嘴里歌颂拿破仑,其行动却是否定这一切。他们全体:
“(合着行进节奏,交错着乱喊)夏朗东,夏朗东,拿破仑,拿破仑,民族,民族,革命,革命,结合,结合!……
[音乐,叫喊,跺脚,喧嚣尘上,汇成暴风雨一般。
[库米尔溜回他的看台,敲响警报钟。
[男护士们拔出短棍向病人们打去……队伍踏步向前。病人们陷入行进舞的疯狂之中。许多人欢喜地蹦跳旋转。
[库米尔示意男护士们使用极端暴力。病人们被打倒在地。……库米尔绝望地打手势让人拉幕。
[幕落。”
(见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第四卷,版本同前,第343-344页)
本剧属于高潮与结尾基本重叠的类型。这样一个闹得乌烟瘴气的结尾,实际是高潮的延续。在疯子们的狂热与骚乱面前,马拉、科黛、雅克·鲁还有库米尔们严肃而凛然的政治理想,都显得那样可笑,那样不着边际。不仅如此,就是上一段的那些内容,即人们告诉马拉,他死后形势如何发展,拿破仑如何带来气象一新的格局等等,这一切都变成了疯子们的狂呼乱叫与护士们的暴力镇压。由此,我们看到这出戏所展示的法国大革命,与政治教科书上的结论不太一样。作者对这场革命,对马拉、对萨德,对科黛,有着奇诡的呈现。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明显表露出来。我们只是看到疯狂、混乱、诡异、崇高、执著、妄想等等混合在一起。观众或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如此一来就可以产生枝读(branch read)这是现代艺术的特点。大体看来,在本剧呈现过程中,宣告者这样一种单人歌队所起作用,仍然是对剧本形式的阐释与实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马拉·萨德》几乎不可能在舞台上立起来。
以上所谈,是戏剧中的歌队,作为剧本形式的组织者与表达者的大体情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
C. 关于戏剧中歌队的反讽与抒情功能
1.戏剧中歌队的反讽功能
反讽,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词典》是这样说的:“‘反讽’一词在大多数现代批评使用中仍保留了其原意,即不为欺骗,而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掩盖或隐藏话语的真实意义。”接下来他还进一步指出:“言语反讽,指的是说话人话语的隐含意义和他的表面陈述大相径庭。这类讽刺话语往往表示说话人的某些表面的看法与评价,而实际上整体话语情境下则说了一种截然不同,通常是相反的态度与评价。”(见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反讽说白了就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
反讽在古典和现代定义上有一定的差别。反讽在现代修辞学中,变成了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都不展开,而取其上述最基本含义。
反讽在戏剧中出现很早。古希腊喜剧中就经常有人正话反说,或聪明话傻着说。而我们在前文谈到过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弄人,就是一个最惯于进行反讽的人物。而这个人物我们前文说过了,属于半歌队。
弄人在《李尔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他,李尔王作为戏剧人物许多时候会运转不灵;同时,李尔王的一些性格侧面,和内心的隐秘之处,没有这个弄人也无从表达。这弄人叫什么名字?从何而来?有多大年纪?长成什么样子?剧中一概不提。他是李尔的奴仆。除了偶尔与肯脱等有些对话之外,基本上是不参与到剧情中去的。他大体上保持着与李尔单独的人物关系。即令他与李尔以外的人物有对话与交流,其话语指向仍然是李尔。
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其实在中外戏剧中比较多地存在,绝大多数是主人和奴仆,小姐和丫环,官员和家丁,皇帝与太监,娘娘与宫娥等等。基本都是下人与主人。此种戏剧人物关系有两个特点,一是此种关系中有先天的身分不平等。主人有地位,下人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二是下人基本上只与主人产生戏剧关系,而不进入或很少进入别的戏剧情节中去。比如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春香。她因杜丽娘的存在而存在。她在剧中基本只与杜丽娘产生人物关系,她的行动都是为表现杜丽娘服务的。如果此类人物突破了他们与主人公的专属戏剧关系,而有了自己的自觉意志,有了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他们就成了相对独立的人物。比如前文提到过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波西霞的侍女聂莉莎,她在大部分时候,可以看作是波西霞形象的补充手段。但是她有自己独立的自觉意志与行动,她也为自己找了一个爱人。又比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娘,她在身份上是崔莺莺的丫环,可是这个人物的自觉意志非常强大,其行动有着极大的独立性,作为艺术形象,她一点也不次于张生与崔莺莺。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物在戏里的社会身份都是仆役,从属于他们的主人。但是他们在艺术上都是独立的人物形象。他们都不属于“半歌队”。
或者可以这样说,“半歌队”其实是戏剧中并不完全独立的人物。我们重提艾布拉姆斯的话:
“现代学者用唱白人这一术语指代那种作为剧中人物但又不介入情节的角色,他通过评论剧情为观众提出认识剧中人物与事件的特殊视角(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视角)。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和弄臣……”(见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我们现在涉及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戏剧中的奴仆角色与主人的关系,一是戏剧中歌队的反讽功能。戏中奴仆与主人的关系非常有意思,是一种非常固定的人物关系类型。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但不是本节我们要谈的事情。我们想论述的话题是:戏剧中的反讽,有一部分是由戏中充当半歌队的奴仆一类人物来执行的。
《李尔王》中的弄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剧中他与李尔的对话,大部分话语都是反讽。比如该剧第一幕第五场,此前李尔分掉自己的国土,在大女儿贡纳梨的城堡里已住了一段时间,受了一肚皮气。所以一上来,他就要乔装后投到他手下做随从的肯脱,送一封信到他另一个女儿吕甘那里去。肯脱说他马上就去,信送到之前决不打一次盹。这时弄人说话了:
“弄 人 要是一个人的脑生在脚跟上,它会不会长起脓疱来呢?
李 尔 嗯,孩子。
弄 人 那么你放心吧,幸亏你的脑筋安在头上,尽管路再有多远,它也不用拖了鞋跟走路。”
(见《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弄人对李尔分掉国土放弃权力的行为极不认同。他认为李尔愚蠢极了。他在这里就是骂李尔的脑生在脚跟上。但是他反话正说,说李尔“幸亏你的脑筋安在头上”,所以走多远的路,也不会拖着鞋跟,长出胞疱。也不知道李尔是真老了,有点迟钝,还是故意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下边他的台词是“哈哈哈!”
李尔在位多年,一路走来,免不了战事,政争、危机等等,因为是胜利者,业绩辉煌,所以相信人们对其热捧之词,自己把自己神化,认定自己是伟大的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但现在到了第一幕第五场的时候,李尔恐怕心里已经有些明白了,他不是神,他不是不可侵犯,他丢失了权力以后,此前好话说尽的女儿贡纳梨,已对他施以轻蔑与刻薄。他其实做了一件蠢事。可是当此之际,李尔作为国王的自尊与虚荣还没有丢弃,其性格中的自大与高傲还没有消退,他不承认自己错了,又还幻想着另一个女儿会对他好一些。如果是这样,他心里边那种不安与自责,就永远不会表露出来。于是有了弄人的反讽,让我们看到了李尔内心的微妙与隐幽。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