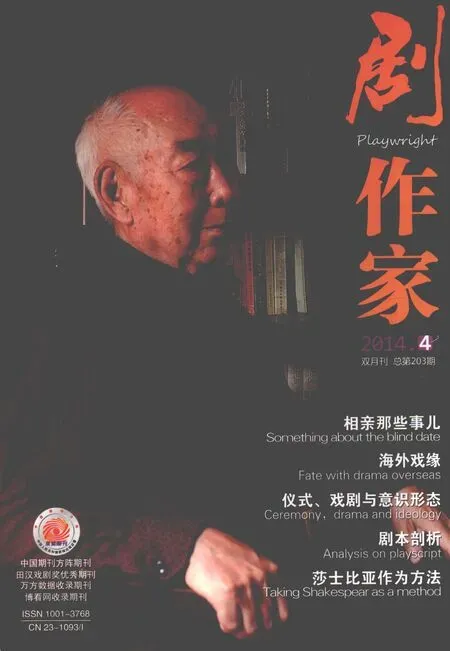文气雅趣入剧稿——表演艺术统领下的梅兰芳戏剧文学
池 浚
文气雅趣入剧稿——表演艺术统领下的梅兰芳戏剧文学
池 浚
京剧作为皮黄腔家族的成员,具有花部乱弹戏民俗性、通俗性的固有艺术质地。京剧大师梅兰芳受到了齐如山、李释戡、黄秋岳等传统文化功力很深的文人影响,以雅俗共赏为目的,将中国古典审美原则注入到京剧中。梅兰芳的剧目中透着一种古意的文气和雅趣,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京剧作品不太一样。他的很多戏在形式上融雅入俗,内涵上深入浅出,让雅俗相互渗透达成互补,和而不同;在风格上更像作为雅部的昆曲,却不太像作为花部的皮黄。
由于中国的文与艺之间相互勾连的传统,艺人是文人的一种延伸,词是诗之余,曲在词上进一步强化音乐性,词曲的基础上赋予人物形象,敷演成戏。“我们今天谈这些艺术形象,都不能离开梅兰芳的演出而只谈文学本,仿佛这些文学剧本中的形象就应该是梅兰芳演出的这个样子。”[1]梅兰芳的表情丰富和拓展了文学剧本的内涵,使文学赋予了具体的形象。他在无形中就传承了中国文学的文脉,这种传承不是有意的追摩,而是潜移默化的,这是本质上中国的文学跟戏剧内在的相通,让梅兰芳作为一个戏曲家,承担了传播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做到的,这就是梅兰芳用戏剧的名义传承文学。
一、文学行走在歌舞表演里
传统的剧本是载歌载舞的,把所有的动作、身段都写在本子里了,把导演的功能完成在编剧里,而皮黄的本子是没有身段、动作注释,没有那么详细的舞台提示。齐如山认为不写表演提示的剧本是一种退化,写了词不写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歌舞一体化的剧本。“长于排戏的名脚(从前没有导演这个名词)又在旧戏剧本中,把应有的动作身段都详细注明。……我们要效法它,仿佛仍然还是复古的性质。这并非复古,正是创作。”[2]梅兰芳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所排的载歌载舞的戏,仿佛仍然还是复古的性质,但又并非复古,又是创作。把传奇载歌载舞的思想,用在一个本来并不载歌载舞皮黄的这门艺术上演的具体应用是一种创新,而对载歌载舞的思想本身是一种继承。齐如山实现了传承与创作的统一,传承的是表演方式,但方式的具体运用是一种创作,将对传统法则的继承用在新的艺术形态上,就有了创作的意味。齐如山从剧本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把歌舞写在里面了,然后才能用传奇的创作方式,具体落实到了皮黄的本子里,让皮黄本来不载歌载舞,也变得载歌载舞。这不是文学为表演留空间的问题,空还是实是同一个标准下的结果,空不是由写了词没写词留出来,写出词来,也是留出空来让演员唱。从头到尾编剧自己都是留着空的,而不是只在没有的地方留空,从来编剧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协助表演位置上写作。不是演员在作者不写的地方去发挥,是哪怕写了词的地方,也是用来给演员发挥的。不能简单地把有词跟无词,有字跟无字当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那就是否定了歌舞一体化的风格,既然歌和舞都是表演手段,那有词跟无词的地方就没有区别。这是戏曲文学没有真正回到作为戏曲文学的功能上来,戏曲文学首先是戏曲,既然首先是戏曲,戏曲是以表演为中心的,用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文学至少不能只当作独立的文学题材来看。
黑格尔曾经指出有两种演员艺术,一种是演员适应剧作家,一种是剧作家“适应演员的自然禀赋、技巧能力和艺术”[3],中国戏曲演员和剧作家的关系属于后一种的,京剧表演对诸如剧本、音乐、舞台美术等其他构成因素,有着强大的能动作用。“我国传统表演艺术和西洋演剧最大区别之一是,在舞台艺术的整体中,我们把表演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虽然也有表演中心理论,而且是主要的学派,但终不能象中国学派这样把表演看做是唯一的。欧洲戏剧的发展规律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剧本写作形式,剧本写作形式,又在主要地支配着表演形式。戏曲却是时代的美学观点支配着表演形式,表演形式主要地支配着剧本写作形式。我们的传统戏剧文学,为表演效劳,但描写绝不为表演代庖。我们的传统表演艺术,尊重作为基础的文学剧本,但表演绝不止步于基础,而要在基础上建起堂皇的宫殿。”[4]文学、导演、音乐、舞台美术等部门各安其位,作为“基础”来为表演效劳,表演则既尊重又不止步于“基础”,共同以表演艺术为核心创建有特色的表演风格,是梅兰芳得以形成自己风格的重要先决条件。
“戴着镣铐跳舞”写出来的文字,作为戏剧组成部分的文学看起来好像失去独立性,但最后戏都留下来了,文学本身也以存在于戏剧的方式存留。因为文字跟表演是一回事情,只不过有文字的地方是可以唱的,用唱的表演手段去表演,没文字的地方是用做的表演手段去表演,但唱做没区别,唱做都是表演,不能认为唱是文字,而身段是表演,因为唱词连着唱腔,把唱词跟唱腔连在一起做文学用了,而把那些没词的地方做表演艺术,就等于把唱、念从表演中抠出来了。编剧要在程式的统领下,在构思的时候,就在考虑这里适合用唱、念、做、打的哪种手段去表现。他从最开始构思一直到整个写完,整个贯穿的都是要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程式化、行当化、流派化、个人化、风格化这一系列的东西已经在里边了。剧本成功与否就看对表演了解多少,甚至对演员了解多少。
《穆桂英挂帅》是从豫剧移植的,豫剧的重点场次是“出征”,因为这里可以安大段的唱腔,可以把前因后果都回顾一遍,豫剧又是一个很擅长大段演唱的剧种,马金凤在出征那一场一口气唱了一百多句,观众没觉得这种复述体很絮叨,用这个情景、用这个词是为了让她大唱一回,因为观众爱听她的腔。“移植兄弟剧种的剧本,也应该根据本剧种的特点、风格加以变动。有些变动的地方,不一定是为了好坏问题,而是各剧种的风格问题。我最近演的《穆桂英挂帅》,就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在豫剧的末一场里,穆桂英有几十句唱词,台下听得很痛快,可是放在京剧里,就不能这样安排了。我只唱了八句【原板】,这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怕多唱,即便是其他青年演员来演,也不可能唱几十句,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关系。”[5]一出戏的“戏核”是戏剧性跟歌舞性共同高潮的地方,最好的状态是戏也达到高潮,技巧也达到高潮,最出戏的地方也就是最有技巧的地方。如果出征再大段的唱,就显得戏的高潮跟技的高潮就不统一了。京剧作为一个唱、念、做、打比较综合的剧种,移植的精神不是简单地把戏拿过来,把唱词改成京剧的格律,把唱腔换成京剧的唱腔就可以直接演的。他和他的团队把京剧看成一个是唱、念、做、打,从文本到舞台,从思维到技术,从演员到观众都相对独立的完整剧种系统。剧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系统,要按照京剧演,必须是从编剧法到唱腔设计,包括观剧的心理期待,完全按京剧的走,这样才能算是演成了京剧。从京剧善于表现人物复杂内心层次的角度出发,梅兰芳将这个戏的重点场次前移至了“捧印”。“在技术安排上,要不同于马金凤的同名豫剧。马最突出的技巧,是连续几个大段唱腔,搁在了最后一场‘点将出征’。这种方法有如马连良的《借东风》,在剧情已经明了的情况下,在最后平稳放进一个总结性的唱段。自己打算把戏的重心前移到‘捧印’一场,让穆桂英为‘肯于接印’还是‘不肯接印’产生疑虑,自己就在这个‘地方’插入一段哑剧般的舞蹈。”[6]移植是非常难的大事情,移植的好坏并不在于两个剧种之间的关系,成功与否主要在于对于自己这个剧种是不是够熟悉,对于自己剧种的规律是不是能够把握的很透彻,什么戏拿过来我都能演成京剧了,那才是移植。移植并不在于对其他剧种有多了解,而是在于自己站得够不够稳,站得够稳就可以海纳百川,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化成自己的形象,化成自己的样子。梅兰芳并不是把自己迁己就人,用自己的风格用来适应各种风格,当然也是要遵循各个路子的不同风格,但也是在非常自觉地把各种路子演成梅派的样子。连这样跨剧种的戏他也拿过来京剧化,青衣、刀马化和梅派化,最后人家看到的还是梅兰芳,这就是坚守自己的风格,而不是简单地以所谓塑造人物为目的进行表演。整个剧本就剩两句话是跟豫剧一样的:“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两句话是整个剧本中最俗的两句话,但也很给力,就这两句保留,结构、场次、出场人物全改了,动得非常大,除了题材相近,简直就两个剧本。这番动作是必须做的,做的理由不是因为穆桂英的人物形象,而是京剧的演剧法则和梅派的艺术风格决定了要动这么大的手术。仅从文本上来说,京剧《穆桂英挂帅》剧本也是梅派风格的,梅兰芳才能演得了。
二、剧情结构熔铸在技术结构中
梅兰芳、齐如山以皮黄编剧的技法去写传奇的意蕴,以流行的形态去写经典的意蕴,使得经典和时尚达成了统一。用当下流行的,有正副场子的,有重头戏和过场戏的结构去编剧,使得这种已经经过历史选择的新的剧目结构更受欢迎,但又不放弃里面的味道,但从精神层面上,是延续着古人的方式。梅兰芳作为京剧文化的集大成者,把古与今、传统与时尚、继承与创造穿在了一起。
齐如山的剧本很清楚地看到传奇跟梆子、皮黄之间结构的差异,传奇的剧本比较均匀,每一个曲折转弯的地方,都写得很清楚,由于过去流动性的观众,在每一场大体上得让观众看到一些亮点,又不能够每一场都特别使劲,因为还得存着后一场,每一场也都不能太亮,传奇比较平均。但皮黄相对来说详略、轻重幅度比较大,有明显的重头戏和过场戏的区别,是由于观演关系决定的。观众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只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狠狠地来一下,其他的时间观众也休息,演员也休息。齐如山在这两种不同的结构中,以梆子、皮黄的轻重详略相对比较分明的方式为主,当然也吸收了传奇的结构和写法。
齐如山在整体的理念层面上延续了从南戏到传奇到花部的地方戏的路子,这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后期越来越倾向于传奇本子的写法。在技法层面上,他又继承了皮黄梆子的这一路,分出正副场来,并不平均使力、不平铺直叙的写法,以让他保持京剧的风格和适合时代的审美观。“这可以说是梆子、皮簧的结构又有了进步。它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于正场要极力地发挥,尽量地描写,对于不甚重要的事迹也要顾及,而只点明便妥,不必用力。”[7]他继承传奇的意蕴,而编剧法仍然是皮黄的,因此达到了一个感觉上是传奇,精神上是继承了传奇的东西,而在技法层面上又体现了皮黄的特色,这两者的统一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不按皮黄的路子写,就不会流行受到时人欢迎,也不是纯正的京剧,那就真的把京剧演得跟昆曲似的,但如果不继承传奇的文脉,又没有深刻文化的含量。这样又好看又带有古典气息,把流行和经典这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这也是梅兰芳的新戏能够取得成功,在文本上的一个基本条件。从编剧结构上,从观演结构上,从技术铺排上是按皮黄走的,但是里面透着继承了传奇的那些美学精神、人文精神、文化内涵和作为中国人的古典审美,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如果梅兰芳只要今的形式而不要古意,他就变成一个纯技术化的演员而已,就不会成为一个文化名人,一个文化人。如果他只要古意而不要受人欢迎的技术,会成为一个蹩脚的表演艺术家,会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不具备传播的能力。有句话叫“文成法立”,文章写成了,写文章的法则就立起来了,实践的过程就是研究理论的过程和立论的过程。如果梅兰芳不去以时尚的方式去做,他的文就不成,文不成则法不立,自己的创作理念就不能实现。梅兰芳高超的技艺就是齐如山等人作为编剧跟他合作共同铺设的轨道的具体实施,能够既是古人又是今人,站在今古相通的地方。考虑整个场次结构的问题,一要考虑根据主题,以哪个段落为高潮,二要考虑兼顾剧情结构和技巧结构。“技巧线尤其突出,甚至在生出爆发力的那一刹那,能够淹没故事线的存在。演员的最大职责,就是使两条线有机地结合起来;‘爆发’是应该的,‘淹没’却是不大好的。”[8]技巧线和故事线最好是能够结合起来,最好能在技巧线爆发的时候,也能够凸显故事线。
《霸王别姬》“在虞姬自刎之后,本有霸王再与汉军大战的一场,为杨老板大展身手的一场,与虞姬舞剑的一场前后映辉有异
曲同工之妙。但观众之中还是捧梅者多,而且为时也太晚,已到了鸡鸣早看天的时刻。许多观众都抽了签(中途离坐谓之抽签)。所以霸王这场鏖战等于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杨老板虽然是忠于艺术从不泡汤,但是唱完了这出《别姬》之后也不免有些牢骚,回到后台在卸装时以玩笑式的口吻说道:‘这哪儿是《霸王别姬》,简直是姬别霸王么!’”。[9]当时梅兰芳风华正茂,很有光彩,才气很足,正在走上坡路,还没到顶。从功力上来讲,那当然是杨小楼炉火纯青,他们合作也确实精彩,但出现“姬别霸王”的情况还不能简单地说是杨、梅之间此消彼长的问题。这首先是结构的问题,戏的高潮已经完成,最后的乌江自刎没有办法进行,因为前面九里山会战已经非常火炽了,没办法进行再一个很有看点的开打,情节又是为大家所知的,最后就有了一点狗尾续貂的感觉。“剧情演到该结束的时候就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谁违背这个真理,谁就要遭到观众的离席而去。梅兰芳的高明之处,正好说明他不但深谙艺术规律,也是深谙观众心理学的大师。”[10]这个戏的结构本身就让最后的乌江自刎就成了鸡肋,任谁演都有鸡肋的嫌疑,哪怕杨小楼也撑不住,这首先是文本上的问题。“小楼只能敷衍了事,草草终场。梅先生心中说不出来的难过,但是群众的决定,无可奈何。此后再演,索性在虞姬自刎后,干脆就‘撩幕’……霸王的生死,成了一个谜。……杨、梅是并重的,因为霸王的戏多,可能还偏重杨点,但是一班人经过了虞姬舞剑的高潮,他们的需要满足了,就不愿再看下去。”[11]第二,有的观众专门捧梅兰芳而来的,梅兰芳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观众群,那当然是梅兰芳演完就走了,当然这里也包括了他的能力在增长。第三,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杨小楼认为是伤了自尊心,在后来在虞姬自刎之后那几个场次里,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就越来越消极地去完成任务。第四,因为他们两人把“别姬”那一场演得太精彩了,以至于杨小楼自己都没有功力用后面的戏把前面的戏托住了。后来梅兰芳在自己的梅剧团再演这个戏的时候,从金少山到后面刘连荣,包括其他的霸王,最后就是很简单地一个过场戏。按理说高潮完了以后应该有一点余绪,霸王自刎作为一个尾声,而不作为一个完整的一场戏结束,作为一个尾声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霸王别姬》在已经内部彩排和贴出广告,确定了两天演完的结构以后,梅兰芳听取了吴震修的建议,不惜修改了已经打出的广告,而重新回到对剧本结构的改编上。“照例事先再响排一次,请他的朋友提意见,不料看了排演以后,梅的一位银行界至好朋友吴震修独持异议,因为这戏分两夜演出,吴认为非并做一夜演出不行。他的理由是戏的重点在‘别姬’,第一夜的观众见不到‘别姬’,第二夜的观众见不到戏的过程,失去‘别姬’一场戏的应有效果。”[12]吴震修的理由是这个戏的重点在别姬,在整个第一天里,号称是《霸王别姬》,却看不到别姬那一场,观众不满意。而如果只看第二天,由于不知道前因,别姬的气氛推不上去,就到不了“别姬”这一场应有的效果,也是不完整的。只有用前面的戏不断地进行铺垫,推到“别姬”这一场,效果才能出来,这必须是一天完成,不然戏就折了。吴震修两天并一天的思想,非常像起因、经过、高潮、结局的完整戏剧结构的思想,当然,吴震修秉承的是起承转合的思想,转的部分是戏的高潮部分,将起承和转合分为两段,势必在起承的时候,由于看不到后面的转,那起承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如果第二天上来就是转,那就没有起承的过程,转是无法把戏剧的力量推上去的。不管是中式的戏剧结构还是西式的戏剧结构,都有一个伏笔、铺垫,近似于三翻四抖。铺垫了一定程度,扔出该有的包袱,才能有戏剧效果,而这个过程是连贯的和前呼后应的。梅兰芳不惜得罪齐如山而采取了吴震修的建议,不惜把已经打出的广告又重新收回,修改了演出预告而坚持用一天演完。这不是说简单说长就不对,是技术结构规定所致。
三、不避雅冷的迎难而上
梅兰芳的不少剧目题材来自于古典小说,梅党的文人对于古典小说非常熟悉,小说给戏剧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但《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排名第一的小说,在京剧的剧目中却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哪怕成功也是局部的成功。正如梅兰芳所说:“存在着两种困难:(一)那时各戏班的组织,也还是包括了生旦净末丑各行的角色。花脸一行在红楼戏里,很少有机会安插进去,相反的旦角一行要用的角色,倒又太多了。不能为了我排一出新戏,让别的几行角色闲着不唱,又要添约了许多位旦角参加演出。这是关于演员支配上的困难。(二)《红楼梦》在旧小说里是一部名著。对于书中人物的刻画,也极细致生动。可是故事的描写,偏重家常琐碎,儿女私情。编起戏来,场子过于冷清,不像《水浒》《三国》的人物复杂,故事热闹,戏剧性也比较浓厚。大家又经过几度的考虑,就打消排演全本的企图,先拿一桩故事,单排一出小戏。这才决定了试排《黛玉葬花》。”[13]像宝黛这样的爱情,比较容易把戏演冷了,行当主要是旦角为主,没有行当的冷热关系。小说的水准固然会对戏剧改编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原作的成功并不直接等于戏的成功,简单地把题材跟最后的效果联系在一起恐怕很难符合戏剧的要求。因此,梅兰芳从整本中选出一个片段,以情节不太流动的情景剧方式,展示人物在某一个横断面上的内心。梅兰芳演了三个《红楼梦》戏,都是从全本中抽取的很小的段落,人物都不一样,《千金一笑》是晴雯的,《黛玉葬花》是林黛玉的,《俊袭人》是袭人的。三个戏都偏冷,而最后被搁置起来,偏冷的问题,是在排之前就已经预见到的。
梅兰芳在青年时代冒着冷场的危险,有意地去对京剧的文化定位进行调节,将京剧这种大众、通俗、流行艺术向着高雅、经典艺术的方向拉近,而他的调节是用实验戏剧的方式进行的。“从前中国银行有一位汪楞伯君,他背地同别人说,我把梅兰芳当作试验品。”[14]事实上这种采取文人化的手段对京剧进行雅化,直接扭转京剧基本风格的尝试,很难做到又走群众路线又走高端路线,又打内又打外,又打雅又打俗,因而失败的例子居多。“从文化上看,这些戏虽然雅致了,并无多少新意;新意只在载歌载舞的表演与新式古装的人物扮相,营造了崭新的审美形态,为观众所欢迎,如《天女散花》《廉锦枫》等。”[15]虽然梅兰芳在将中国古典审美原则注入到本来是有些粗野的乱弹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仍然没有改变京剧作为一种民俗性、通俗性艺术的固有质地。虽然梅兰芳的目的是把见棱见角的表演磨“圆”,把生猛泼辣的气质冶炼得“中和”,打造雅俗共赏的境地,但由于京剧本身作为花部乱弹的俗文化属性,与雅致的风格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调和。从某种程度上,这是本属于市民和农民的民间艺术在贵族化、都市化道路上出现的不稳定、不匹配,这个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很容易使京剧远离现实,不接地气。
注释:
[1]安葵:《梅兰芳对京剧剧目建设的贡献》,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部主编:《梅韵麒风: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01页
[2]齐如山著:《国剧漫谈二集》,梁燕主编:《齐如山文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3]黑格尔:《艺术哲学》英译本第4册,第290页,转引自叶秀山:《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问题(研究提纲)》,叶秀山著:《古中国的歌——叶秀山论京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320页
[4]焦菊隐:《〈武则天〉导演杂记》,《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47-148页
[5]梅兰芳著:《我的电影生活》,《梅兰芳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6]徐城北著:《梅兰芳百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7]齐如山著:《国剧漫谈二集》,梁燕主编:《齐如山文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8]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02页
[9]齐崧著:《谈梅兰芳》,黄山书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23页
[10]任明耀著:《京剧奇葩四大名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2页
[11]许姬传:《别姬之霸王》,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282页
[12]吴开英著:《梅兰芳艺事新考》,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267页
[13]梅兰芳述,许姬传、许源来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梅兰芳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90页
[14]齐如山著:《齐如山回忆录》,梁燕主编:《齐如山文集》第十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15]龚和德:《京剧对我们会有什么期待?》,《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3月26日
责任编辑 原旭春
——以《皮黄》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