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亲戚[短篇小说]
文/刘晓珍
一
我们的亲戚从农村进城很突兀,事先连个风声都没有,先是舅舅家的表姐二英两口子不声不响地到来,过了几年,她的哥哥生子一家、大姨家的表弟三子一家也滴里嘟噜来了,三子还带来了他以后叱咤风云的老婆山杏。
山杏从农村进城晚,二英表姐一家先把我大姨家的三子带进了城,山杏嫁给了三子,也从农村向城市迁徙了。山杏后来蜕变得比城里人还城里人,住上了大房子,还率先开上了小汽车,我们这些真正的城里人在她的光彩下,显得灰头土脸的。
二英姐和姐夫大柱会点医术。大柱的父亲是个懒汉,在乡村里这种人是很吃亏的,不能在田里下死力地干农活儿,当然要有自己独特的谋生之道,表姐夫的父亲就当起了游医,仗着自己那点东游西逛趸来的皮毛医学知识,走街串巷给人治个病扎个针,小打小闹地治个头痛脑热的,大病他是不看的,他知道自己那三脚猫医术的成色,看出了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轮到大柱长大了,虽然这时农村土地已经都承包了,能吃上饱饭了,可柱子表姐夫早就看出来了,土里能混个肚儿圆,却永远也刨不出金疙瘩。光能吃得饱,充其量是一头猪的理想。他要过“好日子”,属于人的高级好日子。一个年轻的农民,走哪条路才能通向致富呢?他打小就耳濡目染了父亲的医道,肩上背个药箱比起扛把锄头来说毕竟轻松得多,还受乡亲们的待见,到哪里都有人给端茶倒水敬烟搬凳子,奉若上宾,享受着村干部的待遇,这是个不孬的活法。
在乡村折腾了一阵子,大柱子就带着老婆二英进了城,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开了一家夫妻诊所。表姐夫是主治医,负责看病,表姐就担负起了抓药、打针、输液、理疗、针灸和打扫卫生等一应杂活儿,护士兼勤杂工。夫妻分工明确。医师资格证、护士资格证,干这个行当需要的一切手续都没有。我们家所在地只是个小县城,那时候这方面的事也还抓得不严,不似现在非法行医的人在城市里像过街老鼠,无处生存。至于表姐他们暗里使用了哪些小聪明小伎俩,才得以安然地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只有他们知道。
诊所开在城乡接合部,来这里的主要是城市里的低收入者,下岗的失业的、无固定收入的,以及进城农民工。大柱姐夫和他爸一样,虽然人懒脑子可不懒。他爸在乡间游走了一辈子,从来未出现过一次哪怕是药物过敏类的医疗事故,凡事求稳妥;表姐夫夫妇开始也是依葫芦画瓢,他们只给输液、打针,收入少些,可稳妥、保险。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政工干部,就是退下来这些年,也还是每天要戴了老花镜,看《人民日报》《求是》。父亲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讲:现在世道真是乱了。病是啥人都能看的吗?医院是啥人都能开的吗?一个农村游医哪天出了事,可是人命关天哪……受父亲的影响,我们一家人也成天担惊受怕的,生怕哪天电话丁零一响,传来的是表姐诊所的坏消息。
舅舅每次来电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叮嘱,多帮帮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在城市里生存不易。我们家一接到舅舅的电话,都无一例外地加重不安,父亲每次放下电话都要皱着眉头说一句:说得轻巧,这样的事谁帮得上忙?
舅舅不止一次地夸奖过他女婿的高明医术,舅舅是个实诚人,为了表达他的一片无私亲情,还颇认真地告诫我们家人,得病就到表姐的诊所去看,自家亲戚,只收成本,不会多要的。
舅舅毕竟是个农民,不晓得城里的事,父亲原来是个领导,可退下来已经近十年了,当年在官场上累积的人脉早已随着他退出政治舞台烟消云散了,不然我们家就不会妹妹妹夫双双下岗不能二次就业了。可怜舅舅对我们家的记忆还保持在十多年前父亲在位时,每次一家老小回老家,必定是坐父亲的专车,有专职司机,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穿着体面,每次省亲都轰动十里八乡,都知道老刘家当官的亲戚衣锦还乡了。
姥姥姥爷早夭,我们一家回老家就是回舅舅家或大姨家,舅舅那时最计较我们一家回去是先到他家还是先到大姨家。要是先到大姨家,舅舅会气冲冲地跑到大姨家,当着一屋子人就会不管不顾地和父亲理论,埋怨父亲没把老娘舅放在头里。
论理说我们先到大姨家也没什么错,母亲兄妹三人中,大姨行大,舅舅行二,先到老大家谁也不应该挑出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可舅舅搬出了他的老娘舅身份。每当舅舅计较到这种程度,父亲只有举手投降的份儿。一个忘恩负义的形象谁也承受不起,何况父亲当年还是个领导,是有身份的人。
好在大姨是个宽厚之人,她倒不计较先后次序,只要我们回去看她,她老人家就会高兴,捯着一双小脚忙不迭地把家里储存了大半年的腌猪肉、风干羊腿、炸油糕、渍酸菜都拿出来,忙着给我们做上一大桌好吃的,看着我们吃得嘴角冒油,脸上堆着微笑,她便心满意足。后来就形成了惯例,我们一家回去省亲,先到舅舅家,后到大姨家。
舅舅对父亲的记忆止于父亲的辉煌时刻。父亲退下来后再没回过老家,舅舅也没再来过我们家,退休后的父亲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在舅舅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所以到现在竟然还提什么请求。父亲自退下来后,曾经还为了妹妹妹夫下岗的事厚着脸皮求了几次过去的老部下、老同事,这些人现在还是当权者,还在“台上”风光得意着,父亲遭遇了几次不阴不阳的官腔后就一蹶不振,不再愿意出去了。在母亲看着无所事事的小女儿再次请父亲“发挥余热”出去求人时,父亲冷着脸一阵长吁短叹,从此家里就再也没人敢提让老革命出去“发挥余热”的话了。
父亲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闲居在家。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看着电视节目打盹,等着中饭。中饭后睡一个雷打不动的午觉,醒来后再对着电视打盹,等着晚饭到来。晚饭后还是和电视机两两相望,然后等哈欠像烟瘾一样到来时进入睡眠。这样一天天打发漫长无聊的日子,没有电视,真难想象父亲的一天会多么空虚,多么难熬。
也许是老天看父亲实在闲得难受,适时地赐给了他疾病,他中风了两回。父亲的生病让他的闲暇时间饱满充实起来,他开始不停地出入医院,求医问药。这样,他无须再操心别人的事了。
二
表姐一家很忙,为了生计。
就是再忙,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正月初一是照例要到我家看望姑姑的。我们一家几乎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两个节日的来临。看着表姐两口子提了寒酸的礼品风尘仆仆规规矩矩地来了,我们提了小半年的心这时才悄然放下。他们的到来表示他们没有出问题,依然坚强无比地在城市里生存着。有时我甚至觉得好笑,我们等待他们的到来就像是官场上某领导最近没出来,坊间疯传他出事了、进去了,然后他就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在电视里露一下面,表示他还安然无恙地在官场上屹立着,并没倒。他的露面其实是作秀,但这个秀作得很重要,非作不可。
我们自然要问下表姐一家的生存情况,母亲的第一次问话是这样的:“生意咋样?”母亲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她直杵杵的问话方式让表姐表姐夫面面相觑。他们自认的治病救人的崇高行当,被姑姑简化成了“生意”,这是从哪里说起?偏偏又是自己的亲姑姑,连气也无法生。姐夫的脸上略微泛红,身子拘谨地挪动了一下,局促不安地张张嘴,他舔舔舌头又闭上了嘴。表姐到底大方些,客气地点点头说:“还行,有了一些固定关系。”他们说自己的医术好,服务态度也好,收费还低,病患就愿意来。表姐没说是病人,也没说客户(那样就彻底钻进了母亲“生意”的圈套里),而是选择了一个中间称谓:关系。
母亲又直问:“卫生上的人没找你们麻烦?”这回是精明的表姐夫回答了:“早把他们都打点好了。”开门做这个,工商、税务、卫生都得打点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还开个啥张?每逢年节,都事先给他们准备了辛苦费,现在与他们相处得像是哥们儿。说着话,姐夫一双灵活的小眼睛狡猾地不停眨着,显现出了农民式的狡黠。
接下来就是吃饭。每次知道他们要来,我们的家宴都准备得异常丰盛,肥鸡大鸭子,大鱼大肉,表姐夫和表姐也不见外,吃起来格外放得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副景阳冈好汉的豪爽样子。
表姐两口子尽了例行的礼节,我们尽了地主之谊,家宴圆满结束,表姐两口子接着回到城乡接合部做他们的“生意”。母亲望着他们的背影担忧地说,就怕他们哪天出事。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奇了怪了,他们进城四年了,好像站住脚了啊。这一点其实我也感觉到了,从他们的穿扮、带的见面礼上就可以看出。第一年中秋他们两口子上门,穿的都是地摊上几十块钱的便宜货,表姐一脱腈纶外套,里面的腈纶毛衣噼里啪啦直蹦火星子,活像孙悟空一个筋斗从银幕上翻到了我们身边。表姐夫的西服皱皱巴巴的还不合身,大概下过水后抽得厉害。他们带来的见面礼叫作月饼的四块东西又黑又糙,硬得像石头一样,里面居然是拿黄豆做馅的。不知道是哪个暗无天日的小作坊里生产出的假冒伪劣产品,摆在那里像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物。
也太抠门了,忘记了这是去她亲姑家,忘记了我们过去回老家是怎么给他们带高档货的。大姐和小妹看着那几块古董样面目可疑的点心,发出了不甘的愤慨。看二英两口子的吃相,怕是半年都没碰过肉呢。父亲发出了同情的慨叹。他们真的不易,从农村洗净了脚上的泥巴欢天喜地地进了城,城里并没有温暖的大房子、美味的食品、质地上乘的漂亮衣服等着他们安然享用,他们站住脚还成,打拼得不好,最后还得灰溜溜地回到他们万般嫌恶的村庄里去和土地做伴。

第二年二英表姐一家带来的是两瓶罐头,还有一斤点心。虽然点心是散的,也不是名店名品,可比起硌牙的月饼来起码是松软的。第三年来又进了一大步,是两盒成盒的糕点,里面有蛋糕白皮酥萨其马,一看就是在正规点心店里买的,大概要五十块钱。今年是第四年,两口子不仅带了一箱特品盒奶,还带了一箱桂圆莲子八宝粥,都是地道的名牌货。两口子穿得也好些了,表姐夫是一身灰西服,混纺料子的,虽然不是纯毛名牌,穿了倒也不起皱,板板正正、像模像样。表姐穿了件紫红黑花羊毛衫,领口还镶了一圈夸张的人造毛。表姐自豪地告诉我,要二百多呢。
席间,表姐面色平静地说她和姐夫都考取了资格证书,表姐夫考得了医师的,表姐考得了护士的。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医生和护士了。
晴天打了一个大霹雳,全家人都惊呆了。我们当然都知道,表姐只有可怜巴巴的小学三年级文化,表姐夫比她强些,也只是勉强初中文化。这样的资格证书好多医学院毕业的科班生还考不下来呢,他们这样可怜的文化程度怎么就……
表姐喝了两杯酒,颧骨上浮起了两朵俏皮的红晕。变得漂亮妩媚的表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两口子有多苦,白天诊所里忙忙碌碌一天,晚上身子累得要散架,还要拿了砖头厚的医学书啃呀啃。冬天煤贵,有病人时我们还生着炉子,病人走了我们就熄火冻着。困了拿辣椒顶,每天都是一两点,两三点。大柱考了两次,我三次,终于都过了。
表姐嘴唇哆嗦,眼里飞花。
表姐夫神情自豪肃穆,脸上绽放着得意的红光。
表姐接着说下去:这个本本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虽然定期打点工商税务卫生那些家伙,可他们每次上门,我们的心还是咚咚跳。他们每次来都不空手,几十块钱一盒的好药,一拿就是三五盒,我们心痛得抽筋,也得忍着赔笑脸。没那个纸片片,就老有尾巴攥在人家手里。出来混了几年啥名堂也没混出来,又灰溜溜地回去了,乡亲们该怎么看我们啊……
表姐捂着脸耸动着肩膀像个受了欺负的女孩子呜呜地哭起来。
表姐夫揽过表姐,疼爱地说:别哭了,我们不是好起来了吗?病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不是开始有了重要病人了吗?前两天那个水利局的黄副局长不是都带着他老母亲来了吗?听说咱们医术好,收费低,还没有假药,以后不仅他们家人要来,还要介绍别的病人来……
表姐夫安慰老婆别哭,他的眼圈却忍不住红了。这次表姐和表姐夫都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服务对象称为病人、患者,而不是以前含混的“关系”了。
三
表姐两口子不仅有了身份,经济上也战绩辉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原来租的两间底商已经嫌小,又把旁边一直风雨飘摇的小烟酒店盘了过来,打通,分出了接诊室、药房、两间病房,还买了大医院淘汰下来的二手医疗器械,医院俨然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了。表姐一家的生活出乎我们意料地一路高歌猛进,又过了两年,他们居然不声不响地买了房子,八十多平方米,两室一大厅。虽然在城乡结合部,位置不太好,周边环境也不太好,可那毕竟也花了十来万。他们在城里打拼了几年,终于站住了脚。
惊天雷一个接一个,表姐又生了儿子。老大是女儿,表姐夫一直觉得不美满,虽然在城里买了房子,没儿子,回老家还是会被嘲笑绝户头。被笑为绝户,人生便塌陷了一大块。何况现在有了房产,没个正宗传人,百年之后可便宜了哪个呢?
现在计划生育管得这么严,不怕罚款吗?我们家人惊奇地问。表姐夫不当一回事地淡定一笑,这个规定那个规定都是给你们这些城里人制定的,我们农村人,哪个不超生啊,哪家没儿子成啊?
表姐夫一家自进城以来混得越来越好,能量越来越大。能明目张胆生二胎,能给二胎报上户口,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办到的事啊。现在看一个人混得好不好,不是单看他口袋里的钱,还要看他能不能办成一些普通人办不到的事。
相比较,我们自己家这几个城里人却活得艰难。房改时我掏了几万块钱买下单位的一套五十几平方米旧房,一直蜗居至今;大姐住的平房要拆迁了,回迁要再拿十几万,她家人愁眉不展;妹妹一家自打下岗后就一直和父母挤在一起,根本没做过买房的梦。再说生二胎的事,别说我们没门路、没手段报户口,即便能像表姐那样偷梁换柱改成少数民族,我们生得起、养得起吗?
四
站住了脚的表姐一家,生活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他们把生子、三子两家人弄进了城里。
八月十五又到了,表姐一家、大表哥一家、三子一家齐刷刷地拥进我们家时,场面确实是很壮观,十多口子人把我们家不大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无处立足。酒过三巡,父亲望着黑压压的一片脑袋,疑惑地问他们在城里怎样生存。表姐夫扑哧笑了,抹了把泛油的脸,说,大哥到驾校学了驾驶,贷款买车跑出租,嫂子摆摊卖菜;给三子一家在农贸市场上租了个摊位,让他们两口子卖鸡卖鱼。父亲自从高血压冠心病缠身后很少喝酒,那天却破例喝了一大杯。父亲心绪复杂地看看几个表亲,再看看自家几个儿女,想说点啥,却终是啥也没说。
几个亲戚走了,家里的气氛陡然压抑凝重起来。父亲并没有像以往吃过饭回卧室睡觉,而是窝在沙发上若有所思。母亲也是郁郁寡欢,然后不快地数落父亲没本事,孩子下岗窝在家里,要工作没工作要房没房,都没法出门见人;人家这几个农村孩子,倒一个个活得像模像样起来……我想制止母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母亲刺激人的话已出口,想追都追不回来了。我对母亲很不满,难道不知道父亲自退下来后是什么状况吗?为什么还要拿刀子划他的伤疤呢?
父亲长满老年斑的脸慢慢地变红,眼睛也变得兔子般赤红,粗黑的眉毛急遽抖动着,突然,“砰”的一声,父亲摔了手里盛满水的杯子,玻璃碴儿和滚烫的开水溅满地,妹妹发出了尖促的惊叫。
“怨我?怨我!要是没有我这个曾经当过官的老子,他们说不定不会下岗,或者下岗后早就再就业再上岗了!你的亲哥亲姐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能帮孩子啥忙?这几个孩子不都是靠自己吗?!”父亲怒吼着又把锋利的目光突然转向了妹妹妹夫、大姐和我,他锋利的目光划得我们不敢迎视。
“那些活儿都不是咱们孩子该干的,咱们孩子应该干体面的事儿,反正就是你没本事,你别抵赖……”母亲还不依不饶地嘟囔着。
“妈——”我拖长了声音,不得不出面制止了母亲。
父亲好容易止住了抖动,哆嗦着说:“我不是一点儿用都没有,我现在退休金还不少,你们还能靠着我,等我蹬腿那天,看你们还想靠谁!你们张嘴等着接西北风喝去吧。”说罢,父亲就站起来,喘着粗气,谁也不睬,颤巍巍回了卧室。父亲的拐杖声音很重,杵得地板咚咚直响,杵得我们心惊肉跳。
五
谁也没想到,表姐把生子表哥一家办进了城,兄妹两家的关系不仅没有越发亲密融洽,竟然渐渐产生些隔阂。嫂子红梅看不惯妹夫大柱对自己男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也看不惯自己男人在妹夫面前低声下气。拿红梅嫂子的话说:妹妹妹夫一家是帮了咱,可别忘了,咱都是农村出来的,老理儿还得讲不是?说破大天去,生子都是他大柱的大舅哥不是?别说他该敬着咱了,他要是惹咱二英妹子不高兴了,咱生子都有资格打他骂他,对他动家法和他理论不是?
这话传到表姐夫耳里,他自然不高兴,黑着脸对表姐说:我有病啊,脑子被驴踢了啊,求人花钱,费劲巴力把他们一家弄进城来,给他们租了房,买了车,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上了学,敢情就是让他们对我动家法的呀?
二英推了丈夫一把,嗔怪道:都成功人士了还长了个针鼻儿大的心眼!我嫂子那人刀子嘴豆腐心,她就是叨叨几句,咱对他们究竟咋样她心里还能没杆秤?就是她不懂事,我哥那人可不浑哪,实心眼的老实疙瘩,他心里肯定念咱的好。
为了几家能有个帮照,生子表哥、三子一家的房子都租在二英表姐的诊所附近。生子表哥在驾校学了一段时间,拿到了本子。第二天二英两口子早早起来开门待客了,看生子表哥家还没动静,表姐夫按捺不住了,去敲他家门,催促他出门做生意。生子表哥揉揉眼睛,抬头看看黑洞洞的天打个哈欠说,启明星还没隐脸哪,这时候有啥生意呀。表姐夫不满地嘿了一声,说:开出租就是挣两个辛苦钱,必须像早起的鸟儿一样才能啄到虫吃。五点多,去开发区上班办事的、出门赶火车的、去医院看急诊挂专家号的人都出动了,这是第一笔肥活儿,你得瞄准这些人挣头份儿钱。等到天大亮了,你的同行成片地出来了,活儿就不好抢了。人们把出租揽客叫成扫街,没人扫时你才能扫到好货呀,等大家都出来你还扫啥呀。再说,你这车背着十几万的债,你不愁啊?
表姐夫又转脸对红梅说:还有嫂子你,你的菜摊更是个鲜货生意,卖的就是个水灵、鲜嫩,人家干这个都是半夜三四点起来就到批发市场上货去,你要睡到阳婆晒屁股才去,都剩蔫巴叶子了,上点这些老太太菜卖给谁去呀?红梅嫂子不爱听,面无表情张嘴使劲儿打哈欠。
二英两口子走了,红梅嫂子开始对丈夫发牢骚:咱农村多咱不是睡到阳婆当头照才起呀?到了城里可倒好,啥福没享到,连个香觉还不能睡了。
生子表哥白了妻子一眼:柱子说得对,你别忘了咱现在是上班,得有时有点,这和种地不一样,种地还得赶节令呢。我赶紧出车,你赶紧去上菜。
生子表哥发动着了车子,忐忑不安地上路了。妹夫说得对,这个铁疙瘩卧在这儿,不是卧着一块铁,是卧了硬生生的十几万块钱哪!
三子一家倒是不懒,两口子都起得早,三子开个三马子到水产品批发市场去上鱼上鸡,山杏守摊。三子拉来了活鸡活鱼,山杏帮着往下卸,山杏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和咕咕乱叫的鸡,心里没底,担心没有顾客。
“二英姐一家刚到城里时要愁没人找他们看病,还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你先别愁那些没用的。”三子说着话顺便抬头看一眼老婆。这一看他大吃一惊,老婆第一天出摊居然是如此隆重,眉毛黑黑,脸蛋粉白,嘴唇红红,还戴了一双粉红套袖。再加上那袅娜的身姿,要不是那又黑又厚的橡胶围裙包裹着,看上去就是一个大美女。
表哥和三子家进城半个月的一个周末,晚上三家人在三子家的出租屋里欢聚。山杏安排大柱姐夫坐在首座,安排生子表哥和自己丈夫一左一右挨着大柱姐夫坐了。三子端起杯,话没说,眼睛先红了,哽咽着表达对表姐、表姐夫的感激之情,大柱姐夫截住他的话,拍拍他的肩说:“放心我的好兄弟,只要信得过你姐夫我,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我既然把你们拉扯出来了,就得管到底,不会让你们再回去的。咱都把根在城市里扎下来,让咱的子孙后代都做堂堂正正的城里人。”几个男人叮当乱响地碰着杯,把热辣辣的酒都灌进了肚子里,一时眼眶都有点儿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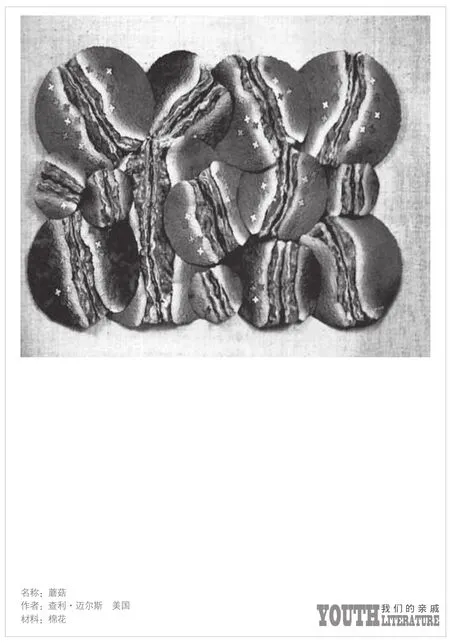
山杏给自己倒了杯白酒,二英关心地提醒她说你是女的,喝点饮料意思意思成了。山杏摇摇头说,酒满心诚,必须是酒。山杏端了酒杯说:“姐夫你知道你这个妹子没文化,嘴笨,可心里明白着呢。我就一句话,没有你和姐姐就没有我和三子。等啥时候我们也像你和姐姐似的,买下城里的商品房,我请你们上城里最高档的饭店吃去。”说着把满满的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大柱看着面若桃花越发漂亮动人的弟妹,似是无意碰了一下她裸露着的白嫩胳膊,说:“好!和三子好好干,等你们挣到些家底,姐夫再给你们寻个比这轻巧的营生,起码是守在屋里挣钱的。”
山杏左右翻看着自己的两只手,确实惨不忍睹,十个手指让鱼鳞扎得像是毛刷子刷过,冻得都是血口子,比在乡下时还糟践得厉害。大柱似乎随意地摸了一下她的手,嘴里说:“啊哟,是遭了不少罪啊!弟妹好好干吧。”
接下来有些冷场。二英看看自己丈夫,想让他和自己一起给大哥一家敬酒,大柱似乎没看见她期待的眼神,只顾自己吃菜。红梅低着头,连生子叫她一起给妹夫敬酒也硬邦邦地推辞了。
大柱姐夫本来还想再劝劝哥嫂,被嫂子不冷不热的态度噎住了。半晌,才转过头来对三子一家送上几句鼓励和夸奖。山杏听了,乖巧地站起来,忙给大柱和二英满上酒,自己和三子恭敬地举杯再表谢意。
红梅和生子表哥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红梅立刻倾倒自己的牢骚,她怪大柱不懂规矩,没有给大舅哥先敬酒。又骂丈夫是个窝囊废,沉不住气,反倒先跑去敬他。生子倒不生气,闷头往床上一倒,说:“咱和三子两家都是大柱一块儿拉扯出来的,人家山杏两口子都带头敬了,咱不敬好像咱不懂事理似的,你瞎计较个啥。”
红梅气呼呼地倒在床上,枕着双臂大声说:“告诉你,我到城里来就是过好日子来了,要是吃苦受罪,我就在农村种地了,种地还比卖菜轻巧些呢。卖菜这活儿就不是我干的,起五更睡半夜,我哪禁得住这么折腾呀?从明天起我不去了,就在家里给你们做饭,伺候孩子上学。山杏那小媳妇就不是个老实货,你妹夫更是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对山杏动手动脚的,别人没看见我可不是瞎子……”
生子闷声闷气地制止了老婆。他睡意蒙眬时,脑海里闪过妹夫酒后失态的样子,这一细琢磨好像也不太对劲儿。
六
生子表哥的出租车没跑多久就出了事。
一天他开车逆行,本以为躲过了交警和摄像头,偏偏就出了事,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
骑车人不依不饶地跟他算账,他知道自己碰上了麻烦,得出钱私了。
生子找大柱借钱。妹夫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这是被碰瓷儿的敲诈了。
赔完了钱,生子躺在床上生闷气,也不出车了。他觉得这城市不适合自己待,不是每个农村人都能像妹夫一样如鱼得水地生存下来。刚一进城就背了十几万的债,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刚跑车两个多月就被人讹了钱,谁知道以后还会碰到啥?老婆不肯去卖菜,儿子到了城里功课也不好,自己在城里该怎么生活下去呢?他萌生了去意。
生子临回老家前把妹妹二英拉到一旁,悄声嘱咐她留个心眼,注意着点柱子和山杏。
其实大哥本不想说得太明白。那天他临时拐到妹妹的诊所拿点药,恰巧妹妹去接孩子放学,只有妹夫柱子和弟媳山杏在。他们的慌张引起了生子的警觉。要走了,还是决定提醒一下妹妹。毕竟,妹夫和弟媳都是外人,只有他和妹妹才是血亲哪。
七
钱越挣越多,生意越做越大,二英姐和大柱姐夫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了。表面看起来当然还是因为山杏。
自从生子大哥临走时留下那句提醒妹妹“留心”的要命话以后,二英心里就开始犯嘀咕。
又是一年春节了。表姐一家、三子一家一起到我们家拜年。山杏穿了件过臀的大红毛衣,胸前绣着恣意怒放的金黄菊花,刺眼的颜色,呼之欲出的乳房,深陷的V形乳沟,臀部被包裹得紧紧的,山杏晃得男人睁不开眼。我注意看了一下她的手,她的手不再粗糙,白皙细腻,凑近了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你擦了什么牌子的护手霜,这么好闻?”我随意问道。
山杏——不,现在的雅梦两只眼睛立刻像通电一样明亮起来,目光炯炯地放出噼里啪啦的火花。她告诉我,女人不仅需要化妆品,更需要吃保健品。
转天,大姐一家请我们吃饭。大姐在厨房里忙活儿,姐夫在客厅里接待我们。无论到了谁家,雅梦都能喧宾夺主,利用一切机会推销神乎其神的保健品。
雅梦雄心勃勃地开拓事业,我们和她的距离却远了,都有些烦她。甚至连大柱姐夫也忘却了旧情,这对二英姐倒是件好事。相比较,我们还是喜欢原来刚进城时那个腿脚勤快、能吃苦的山杏,现在这个有车有房的雅梦让我们感觉不真实。
亲戚们再见面要到八月十五了,想到随时随地强行推销商品的成功人士雅梦女士,不知道怎么,我们的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大家都有些怕再见到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