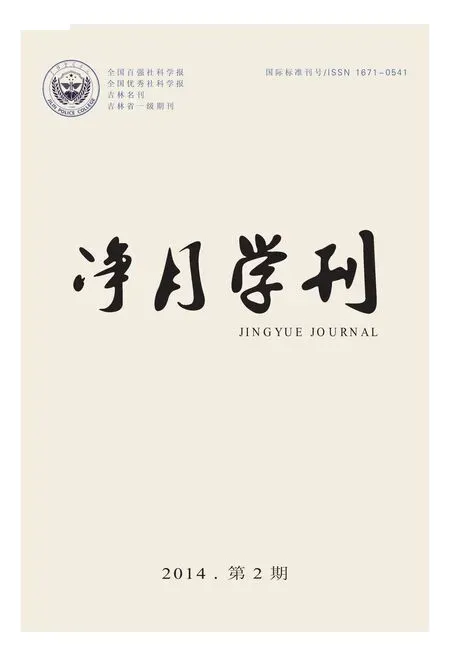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治展开
——以知情权实现为视角
黄佳宇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吉林 长春 130012)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治展开
——以知情权实现为视角
黄佳宇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吉林 长春 130012)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涉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范围与程度。科学与合理地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将是社会成员知情权实现的开始。以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为目标,整合现有的法治资源,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法治展开,将是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建构的必然需要。
信息公开;知情权;法治建构
一、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流动性已成为常态。信息的共享性与有用性客观上要求信息流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拥有庞大公共资源的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的客观发展与法治理念的进步,已经充分地昭示政府信息及时、有序公开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法治的范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行政立法的必然趋势。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在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进程中,都已经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度体系。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步较晚,但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可以说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规范文件,也凝结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成果。
《信息公开条例》借鉴了域外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精髓,彰显着充分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我们要客观地看到,《信息公开条例》尚有诸多不足,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究竟如何界定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 (例如,申请公开某官员工资情况是否应为公开的范围)。笔者选取知情权这一视角,以保障社会成员知情权合法、及时、有效地实现为主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重新审视。
二、关于知情权及其实现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是知情权理论,知情权(right to know),又称为了解权、知悉权。知情权理论伴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知情权运动”,[1]逐渐成为深刻影响世界范围内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重要理论。
从《宪法》角度来考察,知情权应该是广义上“人权”的当然内容,在北欧以及德国的宪法性规范中都明确地规定知情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之一。即使没有明确将知情权规定为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亦间接地指向知情权。人权作为人之成为人的基本权利,除了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等之外,获取政府所掌握信息的权利亦应该是人权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考察,知情权应该包括:以报道自由(采访自由)为内容的权利以及一般意义上信息相关方寻求、接受、收集、获悉、选择、传递有关信息的自由。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是官方的抑或非官方的。知情权体现着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渴望,知情权理论的提出是社会成员权利意识、自治意识与法治意识进步与发展的必严要求。对于社会成员知情权的认同与保障,已成为当代民主与法治国家不能回避的“命题”。
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一切民主权利要想得到尊重与实现,其前提必然是社会成员充分地享有知情权。没有知情权,选举权、参政权以及对公权主体的监督权都无从谈起。正是基于对社会成员民主与法治呼声的回应,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为知情权的实现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架构。社会成员的知情权是通过行政主体主动公开信息以及社会成员主动申请公开信息来实现的。简单地说,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就意味着作为公权力掌握者的行政主体要履行公开之义务。但作为行政公权的行使者往往不愿意,甚至是害怕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成员知悉其所掌握的信息,总是有将信息置于秘而不宣的倾向。社会成员急切要获取信息的愿望与行政主体在信息公开中的遮遮掩掩,就客观上使制度化、法治化的信息公开成为必然需要。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法治化就是在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程度与方式上寻找平衡点。也只有制度化、法治化的信息公开,才能调和社会成员知情权愈大实现与权利行使受限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应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所在,而政府信息公开本身仅仅是手段、途径与方式,决不能为了公开信息而去公开。“信息公开的制度得以确立,则公民的知情权才有了现实的保障,进而公民对政治的充分参与、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的关系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 ”[2]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知情权主体与公开义务主体的争议的重要焦点之一,就是所涉信息是否义务主体应该主动公开,抑或是否应申请公开的范围。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争,是政府信息公开整个过程的起始与核心,这一焦点也直接关涉社会成员知情权能否实现以及能否在权利受损时得到有效的救济。这就需要我们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分析,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来考察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应然状态。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应然法治状态的展开
新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起步较晚,在2008年的《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前,主要是政策层面规定,例如“政务公开”、“透明政府”等。《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雏形基本形成。《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只有38条,但是凝结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实践的成果。随着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前行,特别是在海量信息与网络飞速发展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成员民主与法治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使《信息公开条例》从立法到实践的诸多不足逐渐暴露出来,需要我们从实然与应然角度对《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信息公开范围进行重新审视。
(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治实然状态:模糊与操作性缺失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主要采取列举式来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俄罗斯更是明确将国家元首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3]我国关于信息公开范围的规定与外国主要立法例相类似,我国的《信息公开条例》也采取了分级列举公开范围与法定豁免公开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信息公告开的范围。《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从第10条至第12条是分级公开信息的范围,第13条是“兜底性”规定,第14条是豁免公开的范围。
基于对《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考察,笔者发现《信息公开条例》看似概括与具体相结合,实则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清,这也必然造成信息公开实践上的操作性缺失,对于社会成员知情权的保障更无从谈起。
1.可公开的信息范围规定模糊,规范在概念界定上缺乏明确性,实践上较难把握。《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2项规定“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是公开的范围,但对何为“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的信息,没有进行界定。2012年备受关注的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表叔)事件,公民申请公开其工资收入,相关机关的回应是“工资收入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表叔”事件一时间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热点事件,我们是否可以援引《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申请公开其工资收入情况,如果将这一问题放入法治的角度来考察,《信息公开条例》的模糊性规定造成了实践操作中信息公开申请主体的无奈与无助。
《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除本条例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这在形式上一方面规定了主动申请公开信息的内容,另一方面起到了“兜底条款”的作用。但这样的规定仍然是让社会成员“一头雾水”,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科研需要”如何界定?如果以生产、生活、科研的需要申请公开行政主体所掌握的关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行政主体是否可以援引豁免公开的规定而不予公开,在实践中仍然较难操作。更重要的是,该条规定与第14条豁免公开的规定在适用上效力孰高孰低,规范本身并没有给我们答案。
2.豁免公开的范围过于概括,缺乏必要的解释。与其他国家相类似,我国的豁免公开内容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涵在规范本身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我们寻求《保密法》以及民商事法律来界定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多问题:其一,《信息公开条例》与《保密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法律位阶与适用的问题;第二,由于对概念界定的缺失,使“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密”成为行政主体拒绝公开信息堂而皇之的“挡箭牌”。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再一次被制度的缺失无情地践踏。具有《宪法》特质的知情权在规范的实践运作中成为“空中楼阁”。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法治应然状态:位阶提升与规范细化
规范对于信息公开范围的模糊界定,已经背离了规范创设的目的——知情权的保护与实现。信息公开范围的法治实然状态昭示着在实践基础上信息公开规范的应然发展路径。
1.信息公开制度的规范位阶应提升,这是解决信息公开法治诸多问题的前提。《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规范的位阶是行政法规。与信息公开有关的《保密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规范的位阶是法律。两者发生适用冲突时,《信息公开条例》自然要甘拜下风。规范的位阶不提升,一系列从立法到实践的问题都很难解决。
2.信息公开的规定仍需细化。对于现有制度规范的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于《信息公开条例》范围的界定,应该本着规范制定的目的——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来进行。首先,应该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明确概念的具体内涵。可以是《信息公开条例》自身的完善与解释,也可以借助外部规范的整合来实现。其次,在实践中,对于信息是否属于公开的范围,在没有规范的明确规定时,我们的行政主体出于相对人知情权实现的考虑,可以结合信息本身的特质(是否关涉社会大众利益)、社会关注度来考量(例如长春市“3.04”婴儿被害案,长春市公安局及时回应社会关注)。此时,我们可以引入权利社会一般的法治价值来判断,只要是规范没有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行政主体都应该积极地回应信息公开的申请。与此相对应,只要是规范没有明确规定不予申请公开的,社会成员都可以申请该信息的公开。这种价值判断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实现。
(三)对于公务员财产信息的艰难抉择
严格地讲,公务员财产信息公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之所以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展开中阐述这一问题,是基于如下考量:公务员财产信息公示与公开是社会成员广泛关切的,特别是随着网络反腐的不断发展,网民在深挖“表叔”、“房叔”、“房婶”、“房媳”的时候,关于建构公务员财产公示与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务员财产信息公示与公开制度被称为一把“反腐利剑”,是制度反腐的“头道关”,对预防、遏制腐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对民间反腐呼声的回应,从2009年的新疆阿勒泰开始,我国在地方政府层面正在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与公开的制度建构,进行积极的尝试与摸索。
从制度建构的发展规律来看,实践的摸索将成为上层制度建构的宝贵经验,将推动国家层面上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域外公务员财产信息公示的法治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将公务员财产信息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我国关于公务员财产信息公示与公开的制度实践起步较晚,尚处于尝试与摸索前行阶段。与之同时存在的却是社会大众对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的热切关注与强烈诉求。如何能调和制度的缺失与社会大众法治诉求之间的失调,我们可以在立足我国法治资源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法治资源进行整合。尝试将公务员财产信息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之内,将公务员财产信息列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特殊条款,既可以回应民间的知情权实现诉求,又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法治资源,辅之以《公务员法》及反腐败的相关规范,[4]不失为一种可以考量的选择。这种“抉择”也许是较为曲折甚至是漫长的,需要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的共同努力。
四、结语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建构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在这一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解决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开放的、透明的、负责任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是整体法治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将在荆棘中共勉前行。
[1]〔美〕威廉·R·安德森.美国《信息公开法》略论[J].当代西方研究,2008,(2).
[2]刘兴业,王强.中美信息公开制度的比较与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9,(1).
[3]贾乐蓉.俄罗斯信息公开立法与实践[J].国际新闻界,2006,(1).
[4]黄佳宇.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法治维度[J].学术探索,2013,(7).
(责任编辑:王星元)
D922
A
1671-0541(2014)02-0080-04
2013-10-20
黄佳宇(1979-),男,吉林长春人,中共长春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