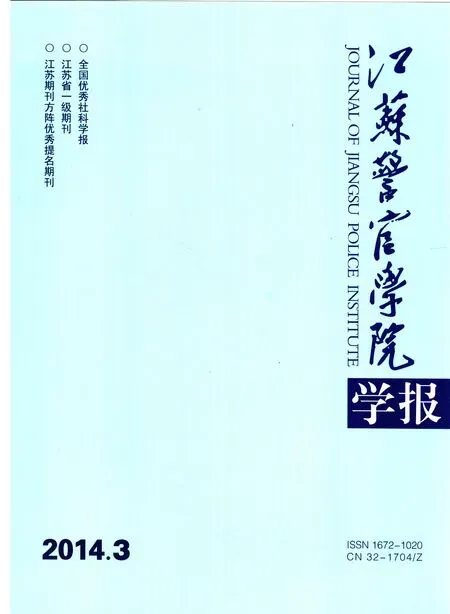论准中止犯——兼评大陆法系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
张 玲 高 峰 刘天虹
中止犯的立法具有鼓励犯罪人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及时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积极作用,因而享有“架设返回的金桥”的美誉。然而,中止犯作为“反过来的犯罪论本身”①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第324页。,其成立条件也像犯罪论所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那样严格,必须符合自动性、彻底性、时空性、有效性四个条件。尤其是以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为最终判断标准的有效性要件,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性质,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准中止犯问题,并对中止未遂的有效性要件进行评析。
一、准中止犯的概念
准中止犯是指行为人在行为人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过程中,主观上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犯罪行为,客观上对于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只是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而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的情形。
在刑法理论上明确提出准中止犯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以林山田为代表的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认为:“侵害结果之不发生与行为人之防止结果行为之间,须具因果关系,始能构成中止犯;惟行为人对于防止结果之发生如已有真挚之努力,只因被害人自己或第三人之行为,先于行为人之中止行为,有效地阻止结果之发生,或因行为系自始即不可能发生结果之不能未遂,而使结果之不发生与中止行为之间不具因果关系者,则在通说上认为行为之真挚努力,本足以有效防止结果之发生,在刑法上应与一般之中止行为获得相同之评价,故仍论以中止犯,此即所谓之准中止犯。”①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只是在中止犯的成立条件中讨论“中止犯罪的行为与犯罪侵害结果没有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构成犯罪中止”的问题,而没有明确提出准中止犯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中,准中止犯在刑法理论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一种犯罪现象存在于中止犯的理论中。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明确提出准中止犯概念,强调的是成立中止犯必须具备中止犯罪的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条件,也就把准中止犯排除在中止犯之外;而没有明确提出准中止犯概念却又承认这种情形构成中止犯的,实际上是中止犯成立条件的松动,即中止犯的成立无需中止犯罪的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
从准中止犯的概念可以看出,准中止犯除了不具备中止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一条件外,在成立条件上与中止犯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准中止犯的成立也需具备时空性、自动性(任意性)、中止行为、没有发生侵害结果四个条件。
1.时空性。在大陆法系刑法中,中止犯属于广义的未遂犯,只存在于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合,这与我国刑法将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也归入中止犯不同。由此,理论上可以将中止犯划分为着手中止和实行中止。着手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是在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前,自愿放弃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只需要放弃后续的犯罪行为,即构成犯罪中止。而实行中止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基于自己的主观意志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才能构成犯罪中止。②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第323、386页。事实上准中止犯只存在于实行中止的情形,而不可能存在于着手中止的情形。因为从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开始到犯罪行为完成的过程中,只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自动放弃继续实施犯罪,并且放弃继续实施犯罪阻止了危害结果发生,这种情况构成犯罪中止;一种是行为人没有自动放弃犯罪,而是因为其他客观因素的介入导致犯罪结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构成犯罪未遂。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准中止犯的概念不符。因此,准中止犯只可能存在于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后、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实行中止的情形。
2.任意性。所谓任意性是指行为人自愿主动放弃可能继续实施的犯罪。大陆法系刑法之所以把中止犯作为广义的未遂犯的一种,是因为中止犯和障碍未遂客观上都是没有发生犯罪结果,因此主观上有无任意性就成为中止未遂和障碍未遂区别的关键。中止犯理论在任意性的认定上,存在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四种学说。在关于任意性的具体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争议,如基于惊愕、恐惧而放弃犯罪,基于嫌恶之情而放弃犯罪,担心被发觉而放弃犯罪等能否认定为具有任意性。但这些问题在准中止犯中似乎并不存在。一方面,从任意性的理论争点来看,关于哪些情形能否认定为具有任意性的问题都集中在着手中止的场合,如行为人欲图杀人,但当其将刀刺入被害人胸口发现血液喷出时,因害怕而放弃杀人的情形;行为人欲图强奸,但当其发现被害人流血时,因嫌恶而放弃强奸的情形等。而前文已经论及,准中止犯不可能存在于着手中止。另一方面,从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看,准中止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行为人的客观行动就足以表明其对犯罪结果的发生主观上持否定态度,这从反面可以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任意性。因此,在准中止犯中,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放弃犯罪的任意性并不困难。
3.中止行为。准中止犯中的中止行为要求行为人积极的作为,即不仅仅是停止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里的问题是:在准中止犯的场合,由于不是行为人中止行为阻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那么若要对行为人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即准用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那么必须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即中止犯罪的积极行为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认为减轻了违法性或者责任。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规定来看,对于积极行为程度的要求不尽相同。德国刑法规定的程度是“主动努力”,奥地利刑法规定的程度是“主动且真诚努力”,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程度是“尽力”,日本刑法修正草案规定的程度是“足以防止结果发生的努力”。仅从条文字面意思来看,德国、日本刑法规定的标准较明确,而奥地利和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标准不甚明确,何谓“真诚”,何谓“尽力”,是以行为人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实施的最大努力为标准(主观标准),还是以足以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为标准(客观标准),从刑法条文不能得出结论。在刑法理论上,承认准中止犯应当按照中止犯减免刑罚的观点一般都要求行为人必须做出“真挚的努力”。①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第405页;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再版,第202页。但笔者认为,“真挚的努力”本身不具有法律语言所要求的明确性,不能作为评价中止行为的标准;但其对中止行为的认定提出了比积极行为更高的标准,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对真挚的努力进行解释,以进一步明确其含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所谓真挚的努力是指行为人“至少做出了足以独立防止结果发生同等看待的努力”。它是学者针对“中止犯中的行为人是否必须独立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一问题提出的。他们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不需要独立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必须至少做出了能够与独立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效力相同的努力才能被认定为中止行为。②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7年版,第398-399页。这是以阻止结果发生为标准的客观标准,这样的标准对于认定中止行为过于严苛。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化程度提高,人们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业都很精通,因此,尽管有些行为是能相互替代的,如在放火犯罪中,行为人点火之后,即使没有其他人将火扑灭,行为人自己也能将火扑灭;但有些行为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外科手术只有医生才能实施,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则不能胜任。在故意杀人犯罪中,行为人中止杀人行为后,对其杀人行为造成的被害人流血不止的状况不能独立阻止,无论其采取什么措施,其欲图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也不足以与医生实施外科手术阻止被害人死亡的行为相提并论,不能被评价为“足以独立防止结果发生同等看待的努力”。对于后一种情况,不认定为犯罪中止显然不合理,因此客观标准过于严格。笔者认为,以行为人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实施的最大努力为标准即主观标准可能更为合理。一方面,社会分工导致的行为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不能苛求行为人实施相同的行为以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以行为人的个人能力为标准较为公平;另一方面,以行为人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实施的最大努力为标准,可以证明主观上行为人确是自动彻底地放弃了犯罪。上述两个例子中,前者行为人只要积极地参与到救火中即可认定为有真挚与积极的努力;后者行为人只要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到医院即可认定为有真挚与积极的努力。
4.没有发生犯罪结果。准中止犯的成立要求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但不要求中止犯罪的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根据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将准中止犯划分为三种类形。第一,因第三人(包括被害人)行为介入形成的准中止犯。如,行为人将被害人杀伤后,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急救车来抢救伤员,但在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前,刚好有一案外人(第三人)开车经过现场,见到受伤躺在地上的被害人,于是径行将被害人送往医院;者被害人伤势并不严重自行前往医院,最终被害人转危为安。在以上情形中,没有发生犯罪结果,就是因为超出行为人意志之外的第三人或者被害人的行为介入,但是由于行为人打电话请求急救车抢救的行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没有第三人(或者被害人)行为的介入,行为人打电话求救的行为也能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而应当与中止犯获得相同评价。第二,因自然事实介入形成的准中止犯。如,在放火犯罪中,行为人已经点燃了媒介物,而目的物尚未形成独立燃烧的时候,行为人心生悔意而决定中止犯罪,赶紧采取措施灭火,在灭火过程中下了一场阵雨,将火扑灭。该案例中,犯罪结果没有发生,是因自然事实的介入而导致,但行为人采取灭火措施的行为表明其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即使没有下雨,行为人凭借自身的能力也能将火扑灭,因而应当与中止犯获得相同评价。第三,因行为自始不能发生结果的准中止犯。如,在故意杀人犯罪中,行为人意图采取投放危险物质的方式杀害被害人,结果由于认识错误,将白糖当做砒霜投入被害人的食物中。在被害人食用含有砒霜的食物之后,行为人心生悔意,转而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但事实上白糖根本不可能致人死亡。在上述案例中,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行为人采取了一种自始不能导致犯罪结果发生的手段,而不是其中止犯罪、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急救的行为。但是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的行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即使当时所投就是砒霜,其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也能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因而应当与中止犯获得相同评价。
5.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从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来看,在认识准中止犯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准中止犯不属于中止犯。如果承认准中止犯概念,那么就必然要坚持中止犯的成立必须以中止行为与结果不发生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从“准中止犯”概念本身可以看出,准中止犯本身不满足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只是准用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第二,准中止犯不同于障碍未遂犯。中止犯与障碍未遂犯虽然都属于广义的未遂犯,但在广义的未遂犯中,中止犯与障碍未遂犯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准中止犯虽然不满足中止犯的成立条件,但也并不当然地满足了障碍未遂犯的成立条件。准中止犯与障碍未遂犯主观上有本质不同,前者是能达目的而不欲,后者是欲达目的而不能。第三,准中止犯的成立要求结果没有发生。作为广义的未遂犯的中止犯,要求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如果结果发生了,即使主观上做出了“真挚的努力”,仍然不能成立准中止犯。
三、中止犯的处罚根据及其对准中止犯的影响
对中止犯处罚根据的认识直接影响对中止犯成立条件的看法,因此也直接影响对准中止犯的处罚。而且准中止犯的立法能否为我国刑法所借鉴,也取决于对准中止犯减免处罚的依据与我国刑法中中止犯的处罚根据是否符合。因此,有必要对中止犯的处罚根据及其对准中止犯的态度进行分析。
对中止犯的处罚根据,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有政策说、法律说和并合说之分,各学说之中又存在不同看法。①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笔者认为,政策说作为解释中止犯处罚根据的理由之一或许可以,但是若将其作为唯一理由则有将政策和法律混为一谈的危险;而法律说从犯罪成立要件的角度进行解释,更有说服力。因此,下文主要从法律说的角度探讨准中止犯的处罚。
由于是行为人以外的原因导致了犯罪结果没发生,所以从违法性层面来看,准中止犯与障碍未遂犯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准中止犯实施了真挚与积极的中止行为,其非难可能性减少、消灭了,所以持责任减少、消灭说的学者容易接受准中止犯。但是如果在违法性的实质上持行为无价值的立场,认为准中止犯做出真挚与积极努力的行为合乎“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那么也会接受准中止犯。由此可见,仅仅从违法性和责任角度不能解决准中止犯的处罚根据问题。笔者认为,对中止犯处罚的态度不同,实际上是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立场的分歧引起的。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及其实害,不能将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作为处罚依据,相反单纯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的消减也不能成为出罪的理由,在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已经造成法益侵害时,仍然构成犯罪。因此,客观主义者往往认为准中止犯构成障碍未遂。主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如果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消失,就失去了对行为人处罚的依据,因此,主观主义者往往认为准中止犯构成中止犯。
以德、日刑事立法为例。德国刑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坚持客观主义的未遂理论,因此体系上中止犯是广义的未遂犯的一种,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刑法改革之后,刑法已经明显表现出向主观主义转移的倾向,如是否直接开始实施行为,取决于行为人的构想;对于未遂的刑法减轻还只是选择性的。①托马斯·魏根特:《刑法未遂理论在德国的发展》,樊文译,《法学家》2006年第4期。而日本刑法仍然坚持客观主义的未遂理论。在对准中止犯的处罚问题上,德国修订刑法明确规定了准中止犯不罚,而日本刑法修正草案虽然提出了准中止犯,但由于草案没有通过,这从反面证明了现行日本刑法对准中止犯仍然要按障碍未遂处理。而且从两国关于准中止犯的条文来看,也可发现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影子:在准中止犯成立条件上,德国刑法强调行为人的主观“努力”,而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则强调行为“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有学者所说“日本比较重视对法益侵害危险性的考察,而德国则比较注重对行为人是否付出了真挚与积极的努力的考察。”②程红:《中止犯有效性认定中的两个疑难问题探析——兼评德、日两国的相关学说》,《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
四、我国刑法借鉴准中止犯立法的可行性
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成立中止犯必须具备行为人的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不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姜伟教授认为“中止犯的有效性要求犯罪分子必须是自己采取行动有效避免侵害结果。如果侵害结果未发生与行为人的行为无关,而是由其他人的行为避免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中止犯,而是未遂犯”。③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但这样处理会造成明显的罪刑不均衡。根据上述观点,行为人以杀人故意投放的毒药没有达到致死量因而不能致人死亡时,即使行为人着手犯罪行为后作出真挚努力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但由于结果没有发生与中止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成立障碍未遂;反之,如果投放的毒药达到了致死量因而能够致人死亡时,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后作出真挚努力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则由于结果不发生与中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成立中止未遂,这显然有失均衡。因此,我国刑法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刑法中的准中止犯的立法。
上文提到,准中止犯的立法能否为我国刑法所借鉴,取决于准中止犯的减免处罚的理由与我国刑法中的中止犯的处罚根据是否符合。而对准中止犯减免处罚是主观主义刑法的观点,我国刑法能否借鉴准中止犯的立法,关键在于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从未遂犯的体系来看,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不同,大陆法系刑法将中止犯作为广义的未遂犯的一种,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我国刑法从一开始就区分未遂犯与中止犯,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从我国学者对中止犯处罚根据的表述来看,我国刑法学者向来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如马克昌教授认为,“中止犯既然自动放弃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大为减少”。④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准中止犯在我国刑法中有存身的余地,准中止犯的立法可以为我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