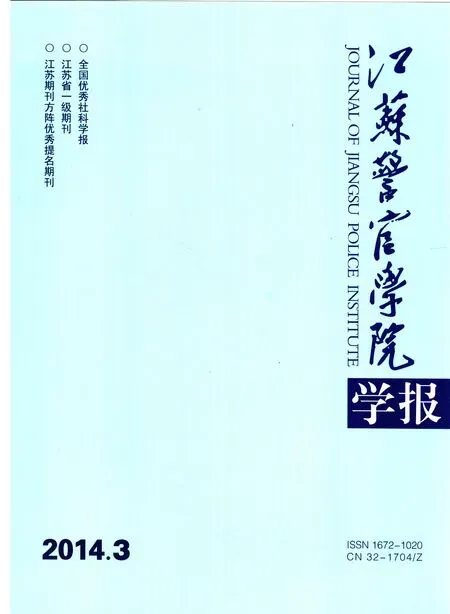新刑诉法语境下非法证据认定的现实困惑与应对
曹卿龙 曾于生
一般来说,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并非指向证据属性本身,而是指向取证的过程和方式。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收集该证据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证据。①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新《刑事诉讼法》第 54条界定了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为“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而诸多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实际上将非法证据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持这种观点。新刑事诉讼法以五个条文的篇幅(第 54-58条)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依然遭遇不少现实困惑,对非法证据仍然难以认定和排除。本文试图在分析非法证据认定中若干现实困惑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性的思路。
一、非法证据认定中的现实困惑
1.关于“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的认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该条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适用情形。从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理由,往往不是其被侦查人员暴打、火烧、水烫、捆绑等明显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等行为,而是介于肉刑或变相肉刑与一般违法之间的取证行为,如既不轻又不重、没有明显伤痕的殴打行为,长时间站立或倒立的行为,不让喝水和上厕所的行为,利用人的亲情进行欺骗的行为,对女性或未成年人厉声训斥、言语侮辱或激将等行为。上述行为能否认定为第54条规定的“等非法方法”,2010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采用回避的态度,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也存在较大分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其第8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但我们应该看到,该《意见》只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5种方法为非法方法,对于上文所提出的五类常见行为,能否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并没有明确涉及,对“疲劳审讯”的界定也不明确,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且该文件只是一个工作机制类的意见,并不是正式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效力非常有限。
2.关于对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对于认定和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实际上规定了三个条件:违反法定程序搜集;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并不能提供合理说明。但这三个条件中除了第一个条件有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之外,另外两个都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认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但其也没有明确“严重程度”的标准。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大多给予补正或合理解释说明的机会①如S市H区检察院经过统计,新刑诉法实施以来,该检察院对实物证据允许补充或解释的占比82%。,并对何为“补正”、何为“合理解释”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导致最终被排除的证据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对此如不加以控制,将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新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初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并未确立实质意义上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3.关于诱惑侦查(涉毒案件)获取的证据的认定
一般认为,诱惑侦查是指警察设置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②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就我国目前而言,诱惑侦查主要使用在贩卖毒品案件的侦查活动中。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此规定中的“实施控制下交付”可以认定为诱惑侦查中的为抓捕犯罪所设计的情景或条件。然而,该条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如诱惑侦查实施的主体为谁,实施的原则如何,适用的合法性标准如何,什么情况下应认定为非法证据等等,该条规定并没有涉及,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特别是涉及毒品的案件时,适用此项制度往往缺乏操作性。
4.关于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和混淆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概念,2010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确立了“瑕疵证据”的概念,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的区别何在?这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均违反了法律对收集证据的规定、均属不合法证据等,在司法实务中,司法人员往往对两者难以区分,甚至相互混淆。据调查,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司法人员把非法证据当做瑕疵证据来补正和解释,最终让非法证据进入审判阶段,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有的司法人员则把瑕疵证据当做非法证据来对待,致使轻度违法的证据被排除,全案证据因该证据被排除后证明标准不合格,最终导致犯罪份子被放纵。
二、应对非法证据认定困惑的思路
1.进一步明确“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外延
关于对“等非法方法”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以下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使用肉刑或变相使用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造成剧烈疼痛或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三款规定:“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3)2010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4)2013年1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但如前所述,上述规定对“等非法方法”的界定仍存在模糊性。为明确对“等非法方法”的理解和界定,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建议完善司法解释。及时完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和外延,特别是要拓展“冻、饿、晒、烤、疲劳审讯”以外的非法方法。我国已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公约》,根据该公约第15条的规定,酷刑应当扩展到虐待、折磨、服用药物、催眠,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等变相刑讯逼供的方式。作为缔约国,我国也应该确保在诉讼程序中,不把以酷刑方式取得的言词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为此,笔者建议,新司法解释对“等非法方法”范围的界定可包括以下内容:(1)虐待、折磨或者其他蓄意使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2)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如利用犯罪嫌疑人的迷信心理施加欺骗和威胁,本质上违反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国际公理,应认为属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3)服用药物、催眠。如大多数法治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均明文禁止以服用药物或催眠的方式取证。①万毅:《“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之“等”的理解》,《检察日报》2011年7月11日。(4)采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精神折磨的方法。此兜底条款适应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及发展,一切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我国承诺的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所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建议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正如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立法对该规则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给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因此,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②何家弘:《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司法判例》,《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11期(上)。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很大程度上即是司法判例制度),这对保证同案同判、统一司法标准,尤其是保障司法的可预期性和裁判的公正性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在目前全国司法界对非法言词证据存在较大争议和不统一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在“两高”层面进一步推行司法判例制度(案例指导),为各地司法机关认定和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提供有益参考。为抛砖引玉,我们试举以下司法实务中的案例。
案例 1:某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公安机关的讯问录音录像时,发现侦查人员不让犯罪嫌疑人上厕所长达近8个小时,应认定其为“疲劳审讯”,属于“其他非法方法”,对其供述应予以排除。案例 2:一名外貌凶险、身材魁梧的侦查人员殴打被告人但没有造成明显伤痕的行为,对一般成年被告人而言,其手段、后果、程度等因素达不到“等非法行为”的要求,但对于一名刚满16周岁、特别胆小、体弱、盗窃他人50元钱的女性未成年被告人而言,上述行为的违法程度和对被告人供述的强迫程度完全属于“等非法行为”。案例3:侦查人员利用亲情欺骗犯罪嫌疑人,言其亲属危在旦夕,供述后即可见最后一面而获取的有罪口供,属于重大欺骗性质的取证,应认定为“等非法行为”①李薇薇:《审查逮捕工作中排除非法供述若干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司法司务)2013年第10期。,属非法言词证据。
2.细化非法实物证据的构成要件
认定和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方法如下:(1)判断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考虑违法收集行为对证据证明力可能造成的影响、收集证据手段的违法程度、采用或不采用该证据对司法公正所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如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相关的笔录或提取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由于此种违法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构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如,如果侦查机关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也属“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范畴。(2)关于“不能补正或合理解释”的理解。所谓补正,即对证据的缺陷进行某种有针对性的修补,使其完善和符合法律规定;所谓合理解释,即通过对证据产生瑕疵的原因进行阐释,排除其非法取得或不真实的可能。如侦查人员虽未经批准实施了搜查和扣押行为,但如果能够证明此种非法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则就可以通过解释被合理接受,此份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不应被排除。对于“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理解,要事先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标准:首先,“补正”应先于“合理解释”。对于实物证据应先于补正,无法补正的再作出合理解释,因为合理解释相对于补正来说,是一种更为随意性的方式,若任意适用,任何瑕疵证据都可以通过合理解释即可获得证据能力。其次,“合理解释”的理由必须符合日常经验法则,符合生活常识,且要有针对性和充分性,足以使法官忽略证据的瑕疵。最后,证据经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一般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由司法工作人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②赵海霞、钱云灿:《论瑕疵证据有关问题及其检察监督》,《浙江省检察机关2013年理论年会论文集》,第194页。经过以上三个标准的判断,如该份实物证据不能达到以上三个标准的要求,则可认定为“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
3.明确诱惑侦查获取证据(涉毒案件)的合法性标准
笔者认为,对通过诱惑侦查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可将其全盘肯定或否定,对其合法性的判断,应综合采取以下四个标准,同时具备这四个标准的,则具有合法性。(1)行为实施的必要性标准。诱惑侦查只有在传统侦查方式不能发挥作用时,才可以被运用。(2)实施主体和对象适格标准。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主体只能是侦查人员安排的信息人员;诱惑侦查行为实施的对象只能是重大的犯罪行为(如毒品交易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能是一般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3)程序合法性标准。诱惑侦查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同时这些程序本身也应符合法治的目的,不能侵害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4)因果关系标准(关键标准)。要判断诱惑侦查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被告人的毒品犯罪意图和动机系自发产生的,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只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犯罪机会,即“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该证据则具有合法性;如诱惑侦查具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具有明显的诱发性,即“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由此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
就涉毒案件而言,侦查行为的“诱发性”并不导致一定是“犯意引诱”,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犯意确定的引诱。即被告的犯意明确无误,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比如毒贩手中有大部分毒品准备贩卖,正在寻找购买毒品的人,侦查人员若在此时假扮买主将毒品则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则其实施的是一般的引诱行为,该侦查行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二是犯意不确定的引诱。若贩毒人员有贩毒的故意但强度不大,实施犯罪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此时侦查人员若实施了诱惑行为则可能会强化行为人的犯意,使原本不强烈的犯意变得坚实,此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定,则不仅仅要看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过程,还要结合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再综合作出判断。三是对无犯意的引诱。即行为人本身无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在经过侦查人员的积极诱惑下,使得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完全属于“犯意引诱”,则为非法的侦查行为。
4.准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何谓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指在收集该证据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证据。何谓瑕疵证据?结合新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我们认为,“瑕疵证据”是指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轻度违反了法定程序,侵犯了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但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可以继续作为案件定案根据使用的证据,既包括瑕疵言词证据,也包括瑕疵实物证据。
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限,应当从人权保障价值、证据属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取证规则、证明标准等视角出发,对以下因素作出价值判断后,综合评定一份证据是属于非法证据还是瑕疵证据。(1)人权保障视角:侵犯当事人权利的性质和违法程度因素。在非法证据中,侦查人员既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等宪法性权利,也可能侵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违法行为严重;而瑕疵证据侵犯的多是公民的一般程序性权利,违法程度相对较轻。(2)证据属性视角: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影响因素。非法证据严重影响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极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想法,或背离案件的真实情况;而瑕疵证据是在取证程序或方式上有所疏漏,但这种疏漏不足以影响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可以予以补充或作出解释。(3)取证规则视角:对侦查人员取证要求的程度因素。不同属性的证据对侦查人员取证的要求程度也是不同的,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相比,对前者的取证要求无疑比对后者的要求更高。若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点违法,则其具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但如果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则可依法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属于瑕疵证据。(4)证明标准视角:相关证据的印证程度因素。非法证据往往得不到相关证据的印证,全案甚至出现重大矛盾,而瑕疵证据基本上能得到相关证据的印证。如侦查人员讯问笔录上记载的讯问时间、供述内容等重要信息,与该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在关键性内容上存在较大出入或者矛盾的,如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应认定该笔录为非法证据;但如两者只是在次要内容上存在一些出入的,应认定该笔录为瑕疵证据。
三、余论
刑事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对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和排除,对诱惑侦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的判断,以及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易混淆,直接影响了刑事案件的公正办理和冤假错案的防范。以上困惑和问题的破解,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不断通过细化完善法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司法制度、深化学理研讨、提升司法队伍素质等路径,才能寻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