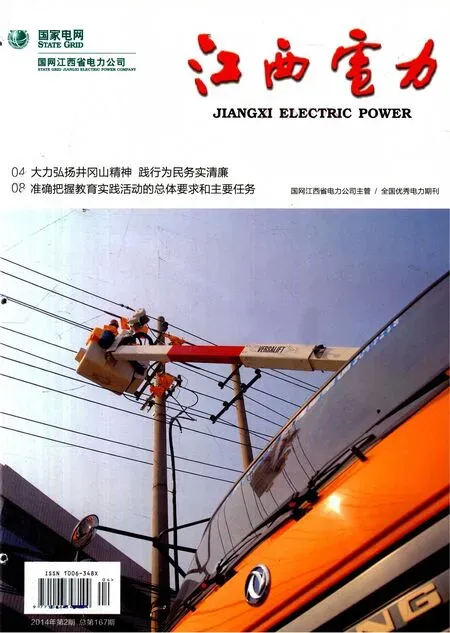春日宴
文_刘轶群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听完一夜微雨连天晓,在春无凄风,夏无伏阴的时节里,收到远方朋友寄来的信件。抽出信纸时,掉出几片粉红桃花,不解之余展开信纸,上面只有一句:致问春君,幸毋相忘。我知道这是有意曲解了那枚被误读了千年的居延汉简,却觉得此情此景,正当其时。春深夏绿时节的几瓣桃花,携着晨光雨露的气味,被放入信札迢迢千里辗转而来。
对着光将些许发黄的花瓣展开,还能清楚看到上面细碎的脉络,喧嚣似鸟鸣的温暖春光,透过一瓣干枯的桃花,似水一般倾泻而下。
想起去年此时与朋友结伴同游厦门,夜至鼓浪屿,两人靠在船尾,岸上灯火在水中的倒影如同星河,海浪起伏声似情人在耳边低语。岛上游客以年轻女性居多,素白面孔,长发长裙,在昏黄路灯投下的树影中婉约而行,像是春夜中开出的一支白玉兰。
和朋友没有目的的一路停停走走,在岛上纵横交错的老房子中迷了路,越走越人声寂寂。途中遇见几只路过的猫,只回头一望,便又轻巧地跑开。转过一段墙角,沿着开满三叶梅的长坡一直往下走,路过一处老宅,满满一墙爬山虎有如风帘翠幕。门未上锁,推门进去,便看见一方天井下,有一棵很高的梧桐树。梧桐树的树干布满苍老的树皮,枝繁叶茂一树苍翠,明月半墙,斑驳树影随风而移。这要是在白天,在春日丰沛的阳光下,枝叶迎风拂摆,绿得有如太平盛世。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一棵树上交叠着时光,旧枝叶亭亭如盖,新枝从其上引申。树是时光最好的书写者,花与叶、旧与新、往昔与现在,互相依存,它们经历了苦雨愆阳,在春日宴里互相辨认,相互等待。
因朋友临时有事,次日要先行返回,我们当晚便在岛上住下。自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数年来仅靠电话网络联系,难有见面机会,便毫无睡意地聊起天来。从大学时的校园生活到现今的工作不易,想起大学宿舍也曾长谈消夜,不禁感慨物是人非。向朋友说起少时读遍玉台花间,只爱骈四俪六,现在读到“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却心生感慨。朋友笑着说,很早我就告诉你这两句写得好,不过那时候你不喜欢。我说,以前对很多东西视若无睹,比如一年四时,比如花开树长,比如人来人往,现在却觉得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太多的东西缘起缘灭不可再得。朋友想了想说道,大概心性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正因为知道春光易逝、宴饮终散,才会心生挽留。聊了很久,临睡前转过头,看见窗外的天空渐渐明亮,像被擦去了雨水的玻璃,带着湿润和模糊的晴朗。
送走朋友后,我路过一家门口有着绿色邮筒的小店,看见橱窗里展示了一张单枝桃花的手绘明信片,我忽然起了寄信的念头。坐在店里想了很久,把朋友的地址写完,正文却不知要写什么。低头看见桌上玻璃瓶里插着一枝欲谢的桃花,春风绕过花枝穿堂而过,几片花瓣掉落在桌上,姿态轻盈一如闲潭落花。心念一动,提笔在明信片上写下“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停顿了很久,才又加上一行,“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寥寥两行,再无可写。我还记得那时走出店门把明信片投入邮筒,春光温暖得像是温柔的手,拂人阖眼。
重新叠起信纸,把花瓣丢进水杯里,看着它慢慢舒展开。窗外夹道的花木经过春雨的洗润后越发蓊郁,春日宴尾,那些枝叶在春风中招展的样子,像在和春天告别,像在和数十载的年华告别,像在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告别。
致问春君,幸毋相忘,在这场物是人非的春日宴里,我只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