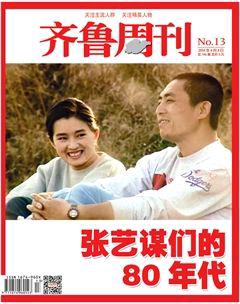阎连科:伟大作家都是绊脚石
杨百会

“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
1987年,翻译家范维信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评论家阿尔瓦洛·萨莱马说了一句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出生于1922年的萨拉马戈于1947年出版首部小说,但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直到1982年《修道院纪事》出版,才享誉葡萄牙文坛;而1995年出版《失明症漫记》后,他赢得了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是葡萄牙惟一的诺奖获奖作家。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盲流感》就改编自这部小说,2007年它也曾被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搬上舞台。
《失明症漫记》仿佛一部寓言。小说里所有的人都患上了失明症,除了医生的妻子。在极端处境下,萨拉马戈将人性的善与恶、人类的生存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展现得让人震撼。和《鼠疫》《1984》等作品不同,它把故事背景放置在日常处境中,而不是孤岛或者封闭的城中以及“铁幕”之下,然而,正因其平常,因其与现实的贴近感,它所展示的图景和困境才更加可怖。作家说:“这部作品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了一部如此冷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是很好。我的小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
阎连科在15年前读过《失明症漫记》,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情节、细节都在脑海里。“比如城市里失明的女人遭到强奸时,医生妻子说‘最糟糕的事情不是他们来强奸我们,是他们来强奸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快感。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时,无比震撼。”
阎连科常把它跟加缪的《鼠疫》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进行对比。“《失明症漫记》有那么丰沛的情感,故事是简单单纯的,但无数细节却让你一生都无法忘记。它对人性、对人情感的挖掘是那两部小说不可比拟的。”
怎么写都无法超过萨拉马戈
“它的构思并不难,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所有人失明,我们每个人都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能否回到人的最初的状态,回到生活最原本的地方?这才是最难的,也是萨拉马戈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从巨大的、荒诞的念头让人回到最初的原始,我们面对吃、面对穿、面对情感、面对一切丑恶和美好,一切都从头开始,从动物变成人,从人变成动物,相互交错。在这些细碎当中达到相当深刻的高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会成为其他作家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阎连科透露:他曾想写一部以一个特殊“失明人”为原型的小说,“我们村里那个孩子得了一种变异症,他每天晚上可以看很远,但到白天就看不到。这是写小说多么好的视角,他看到的全部是黑暗中的东西,而光明中他什么都看不到。”但看过《失明症漫记》后,阎连科至今无法下笔,他觉得怎么写都无法超过萨拉马戈。
不合逻辑的“神实主义者”
活动现场,学者止庵认为:在中国作家中,阎连科最像萨拉马戈。
因为新作《炸裂志》,阎连科被称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他自己并不认同,他把《炸裂志》定义为“神实主义”作品。“我在河南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神秘。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想起一件事情,是少年时去深山区我姑姑家发生的。姑姑家门口有一棵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皂角树,关于这棵树,有很多神秘传说。有一天,传说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现实。午夜时刻,听完一个老人讲故事,我和哥哥一起回家。路过皂角树下时,一块碗大的石头从树上轰隆落在一旁的草房上,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这些石头从黑暗的树上滚落到我们身边,我和哥哥撒腿就跑,还可以感到石头在后边追着我们滚动。后来,姑父提着马灯去找,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但我和哥哥都确定这不是幻觉。这些经历,也许对我作品中的‘神实主义会有些影响。”
在被问到写作经验时,阎连科有些无奈:“每个作家的写作经验非常少,我告诉了你我就没法生活了。”
“我不太喜欢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我着迷的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完全合情合理不感兴趣。”阎连科举了一个例子:1989年在北京美术馆,他看到一个男孩用自行车载着另一个男孩。忽然前面的那个男孩停下来朝后面男孩噼里啪啦打了两耳光,然后继续朝前走,然后又下来打了两耳光,又继续前行,如此反复几次。
这个情景看得阎连科如痴如醉,多年来为之着迷,但当有一天他看到同性恋的新闻,他好像明白了,“这两人可能是同性恋吧,像小两口吵架了,闹分手但又离不开……”想到这里他突然感到特别无趣,“一个好好的故事就这么被毁掉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