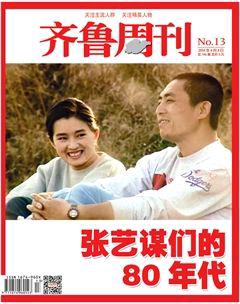向自己举起“屠刀”:北岛们的“理想国”
吴越

诗人的“后80年代”:
下海、做官、投机、赚钱
回忆起80年代,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如此“席慕容体”的诗句,竟然出自北岛之手,也是一个时代破碎的体现。
1989年,海子卧轨,戈麦投河。一个时代悄然结束。
火化时,西川在场,戈麦的脸已经紫了,打了一层石膏。朋友们的死,让他想好好活着。“他们选择什么,我一定不选择什么;他们往东,我一定往西。”
现在,西川注意穿着,一条格子小围巾,在室内也不脱掉,像个诗人的样子,但又不过度。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他签字,看文件,过问一些行政、事务类的事情,得体而富有控制力。
欧阳江河也一样,90年代,他出国,迅速抓住了另一个时代:市场经济,就像80年代他抓住诗歌一样。
现在,欧阳江河很少写诗。在北京一套高档住宅里,两个两米高的大音箱刚花掉他300万。“音质差我受不了,”欧阳江河说,他的音箱两三年换一次,这是第6次了。
每年,有3个日本人会在11月的最后一天飞到北京,从他这儿取走17~23张书法卖到日本,一张70万日元(约4.3万元人民币)。23张是上限,再多就俗了。
欧阳江河的主要业务是介绍外国乐团来华演出,他当中介人。他说自己不是“商人”,商人是要投资的,而他只分成,不投资,做的是策划、安排一类的工作。一年只做几次,其余的时间闲下来。
而他的好朋友邹静之,早已转行做了编剧——写出了电视剧收视率第一的金牌编剧。
诗歌与名气、人脉与圈子,再到机会与赚钱,如果愿意,这之间的关系,一个诗人也会很容易搞清楚。
他们下海、做官、投机、赚钱,各有归途,共同点是:远离诗歌。
顾城、北岛:诗人,万岁!
后来者无数次追问,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刘春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举了一个例子:
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光;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的“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根本无法离开,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
会场秩序还是乱了,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口:“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一些人围着顾城,如众星拱月,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有一个为了诗歌而辞掉工作的大连青年,一直跟着诗人们,要倾诉内心的痛苦。在被拒绝之后,小伙子二话没说,掏出一把匕首戳进自己的手背:“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小伙子绝对不会想到,7年之后,他的偶像(顾城)也像他一样操起了刀斧,但他的偶像砍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濡以沫十余年的妻子。
“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
诗歌大幕早已拉下,大部分人中途退场,留下来的,便已成为精英。
如果从1978年和芒克等人一起创办《今天》算起,北岛的诗歌生命已持续了36年。
而今,《今天》依然存在,主编依然是北岛。去年年底,舒婷、毅伟、王安忆、陈力川、大仙、顾晓阳、德国汉学家顾彬、法国翻译家、诗人尚德兰分别写下文字,纪念他们共同的朋友顾城。
至今仍坚守的于坚充满沧桑地说:“我们已经写了30年,我们是中国白话诗历史上写作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代诗人。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我们是有充足时间的一代诗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像古典诗那样去打造语言的永恒。”
他的信心来源于时间。80年代塑造了他们的青春期,而今,他们用时间来打磨自己的牙齿。
20多年过去,诗人们老了,又重新写起诗来,为了怀念,也为了歉意。
欧阳江河、于坚、北岛,如今他们的诗歌发表在最顶级的国外刊物上,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波士顿评论、意大利诗刊的头条。国际诗歌界称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在书虫书吧举办诗歌会的美国诗人对西川说:“你能来是我的荣幸。”
就像《今天》当年的出现是一种象征,而今,《今天》依然是一种象征。于坚就此发出追问:“我们终于有时间和事业来实现一个持久的象征,扩展它的深度和广度了吗?”
而在国内,更年轻的诗人,他们很少认识;对于年轻人来说,虽然他们依然在写作,却早已进入文学史,进入了“棺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