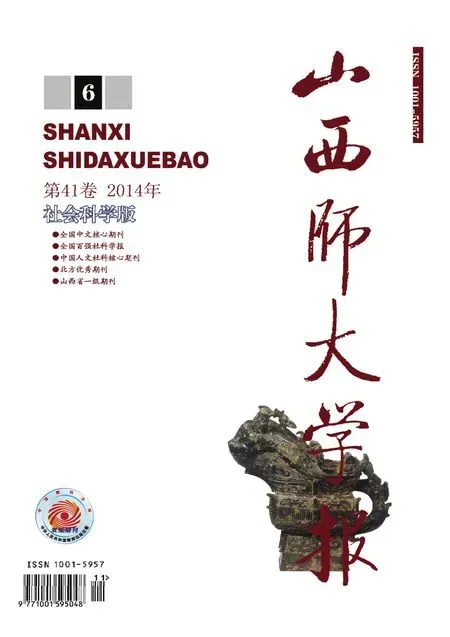中国女性作家生态女性主义观的形成之路
李 莉,肖 茹
(东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哈尔滨 150030)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态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在1974年出版的《女性或毁灭》一书中提出。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在妇女参加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已发展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它关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尝试寻求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反对父权制和二元思维方式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和剥削,提倡建立一个两性和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在论文中零星地谈及生态女性主义。21世纪初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权威期刊发表生态女性主义方面的论文呈上升趋势。虽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典范意义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早在20世纪初已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已有百年历史。
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作家凭借理想和理性创作不同,女性是用自己独特的感知进行写作的。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与自然共同遭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一个又一个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推衍出男人与女人、自然与社会需要和谐共处的真谛。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女性作家从“五四”时期的朦胧张望,到建国初期的探索实践,最终在20世纪末走出了这条生态女性主义之路。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0年代末的“拯救”情怀
20世纪之前,中国的女性文学更多地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属品而存在,不能表达女性的主体意识及生存状况。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是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富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得以萌芽和发展。知识女性成了女作家队伍的主体,像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燕京大学校友冰心与凌叔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友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早期成员白薇等,都深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五四”这个作为我国女性文学起点的时代,随着女性意识的悄然萌发,她们的创作围绕着打破封建的传统思想、拯救女性与国家命运、追求民族解放与爱情幸福等主题而展开,她们的作品开始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的内心世界,体现出对濒临灭亡的国家以及被封建礼数与父权制压迫已久的女性的“拯救”情怀,对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进行了激烈的颠覆,掀起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虽说当时整个文学界还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提法,但是从女性作家的手笔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带着朦胧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路口。
冰心便是这条路上的一位全程实践者。这位“世纪老人”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棵常青树,其创作生涯有七十五年之久。从她191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两个家庭》开始,“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2]4便成了冰心的写作目的,她一贯选择从家庭的窗口来审查社会。《两个家庭》中即从文化教养不同的两个女主人所导致的两个不同结局的家庭入笔,超前地提出了女子应受教育的重要问题。[3]51。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出冰心的作品中也不乏对自然与社会的人文关怀。由于“环保”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被提到日程上来,所以自然与女性之间紧密的联系还未被文人所关注。然而,隐约之间,她们感觉到在战火中恶化的自然与备受战争、封建父权制压迫的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且与男性的主体地位相关。在1923年1月出版的诗集《繁星》中,自然与人类,尤其是和女性之间的联系尽收眼底。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小诗中将花比喻成女性“她”,将成功绽放的花比作出人头地的女性,这一切均需经历父权制社会所带给女性成长历程的“泪泉、血雨”。我们透过冰心的早期小说与诗作文本,可以读出在强大的男性强权下,女性成长的历程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文章中流露出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女性的关怀。
庐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一位著名女作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庐隐开始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很多人评价她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这从她的早期作品中可见端倪,如1923年发表的《海滨故人》。但随着庐隐的逐渐成熟,她不再甘心只做个“觉醒的悲观主义者”,1933年庐隐在《女声》上公开发表了《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文中提及了一种家庭中理想的男女关系:“家庭是男女共同组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共同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这样的思潮是庐隐笔下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同时也真实反映出了当时一大批勇于摒弃封建意识,具有叛逆性格的知识女性的心声。[4]53她们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女人的真实面貌、女人的真实声音和女人的真正需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女作家出现了。虽然身处抗战时期,但五四精神的鼓舞与救国救民的理想使这些女作家们展现出了更浓的女性关怀与生态关注。她们的作品进一步深化对女性命运的探究,对女性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实现自我价值进行了讨论,也对国仇家难中备受摧残的自然与社会进行了刻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萧红、丁玲、白朗、葛琴、罗洪、张爱玲、苏青等。
萧红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是其代表作品。《生死场》发表于1935年12月,作品透露出了萧红内心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备受蹂躏的女性与凄美自然的同情以及意欲拯救二者于水火之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在全书十七节中,故事情节分别涉及到麦场、菜圃、屠场、荒山、羊群、蚊虫,等等,每一处场景都伴随着女性的血与泪。萧红用其女性敏锐的观察,生动地刻画出了恶劣的社会自然环境下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农家少女金枝没过门就怀了孕,受尽村里人的耻笑。而情人成业非但没有保护金枝,反而骂她“肚子不争气”。金枝在痛苦与屈辱中生下了一个女婴,后来这个女婴被活活摔死。最终,金枝为了不受屈辱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下。老贫农王婆一生饱受磨难,第一任丈夫抛妻弃子,第二任丈夫贫困病死,好不容易与第三任丈夫赵三过上安稳日子,年老之时儿子又被反动政权枪毙了。王婆绝望之余自杀未遂,最终在灾难面前坚强地站了起来,开始秘密抗日。在萧红笔下,女性是悲惨的,自然是可怜的,但王婆等人的觉醒带来了当时拯救女性的希望,体现了作家本身对自然与女性地位与生活状况的关注。
同样,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仍能体会到相同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虽然还处于朦胧阶段,但自然与女性的亲密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之后的女作家们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她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借探讨婚姻问题,反思性别权利问题,表现出在恶劣复杂的社会自然氛围中寻觅拯救当代女性与自然的情怀。
二、1950至1970年代末的“奋进”情怀
20世纪50至70年代末这近三十年的女性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七年”女性文学和“文革”女性文学。这期间的作品在选题、内容及写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作家们的创作心境也由建国前的“拯救人心”转变为世纪中期的“奋进向上”。此十余年间,有大批文学作品问世,其中数部影响广泛,是我国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七年”文学中部分作品带有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气息,既关注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又着手描写变化了的社会与自然,并且女性与自然相似的社会地位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
通过“十七年”女作家笔下对全新的人物、乐观的主题和奋进的时代精神的刻画,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有热情,有干劲,争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意气风发的时代主人翁。如作家宗璞于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红豆》,便成功地塑造了江玫这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觉醒并成长起来的女大学生形象。刚上大二的江玫被她同屋的大四学姐萧素称为“小鸟儿”,原本过着“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一年到头潺潺地流着,从来也没有波浪式的生活”[5]2。母亲与其相依为命,每逢礼拜六江玫回家,母亲就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平静却在1948年彻底改变了,“小鸟儿”的人生道路从此不再平凡。这一年,江玫与萧素的同学齐虹相恋了,但在积极进步的萧素看来,“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5]7。果然,当萧素在毕业考试的考场上被警察带走后,齐虹对伤心欲绝的江玫只说到:“干那些民主活动,有什么好下场!”[5]8最终,在一个疾风骤雨的夜晚,江玫断然拒绝了追到家里来的齐虹“一起去美国”的请求后,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5]12此时窗外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台阶下,摔得粉碎。江玫知道自己的爱情,正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最终,“小鸟儿”江玫翱翔在人民革命的广阔天空中,齐虹去了美国继续过银行家少爷的生活。相比较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品,宗璞的《红豆》具有向男性要权利、与男性争夺空间的浓重色彩。
在女作家宗璞笔下,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同的革命追求和政治追求上的,其宣扬了为大家而舍小家,扬博爱、舍私爱的独特婚姻爱情观,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普遍特点。在《红豆》中,江玫被比喻成“小鸟儿”,向往着自由。齐虹对江玫未来道路的逼迫,好似被风刮倒的夹竹桃花,结局只能是破碎。通过这些描述,宗璞表达着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与自然永远是最亲近的,男性的压迫同样的会带给自然与女性以伤害。她不仅关注女性身体和心灵被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历史镜像,而且对当代社会中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在“十年文革”期间,参与文学创作并取得较好成绩的女作家较少,张抗抗出版于1975年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可为“文革”女性文学的代表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主线,以活生生的现象和人物形象去解释政治概念是“文革”作品的主要特征。《分界线》是中国知青文学中第一部由知青亲笔写成的长篇小说,张抗抗在其中描写了扎根在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的斗争生活。围绕1973年春涝灾之下,对北大荒的伏蛟河农场东大洼这块土地的“保与扔”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品除了描写以耿常炯为代表的农场革命青年与工作组长霍丽顽固推行的所谓错误路线做斗争的主线外,还生动地刻画了朝气蓬勃的女技术员郑京丹与想尽办法离开农村的“飞鸽派”青年杨兰娣等女性形象。在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张抗抗也描绘出了北大荒壮丽迷人的景色以及洪涝灾害之下土地的脆弱与无助[6]。
由于这部小说反映的是1970年代初期特殊的历史氛围,政治色彩较浓,因而突出了“人定胜天”这样的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和谐的音符。但值得肯定的是,同样的1970年代,西方诞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虽未传入我国,但我国本土的女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与人类存在着某种关系,愤怒的自然是可怕的,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部具有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的作品里,张抗抗揭露自然生态危机,反思人类文明进程,阐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生态文化理念,体现了女性作家站在时代前沿,关注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状况的敏锐眼光。
三、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追求”情怀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堪称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高峰。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女性文学作品在家庭婚姻、现代人的情感需要、人类与自然、社会关系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在男权社会苦苦挣扎的女性展示了一种新的女性生态学。“人性复归”、“两性和谐”、“精神追求”、“生态环境”等这些许久未提及的概念重新被女作家们所关注。
王安忆和铁凝是1980年代具有生态女性主义观的女作家的典型代表。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等多部小说都勾勒出了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对男女两性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人类之间相互影响的共存关系的深度思考。王安忆于1986年发表的《荒山之恋》中,没有名字的大提琴手与金谷巷女孩之间不为伦理所接受的爱情最终以荒山殉情而告终。文章结尾的一幕:躺在绿色草坪上,用彩色毛线绑在一起的两个相爱的人一起服下了毒药。场景很凄美,结局很悲凉。王安忆用震撼人心的收场方式给了世人内心的颤动。追求真爱无罪,但在人性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鲜活的生命在碧绿的草坪上终结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应该是这种反面悲痛的教训,男人、女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存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生活在此时代中的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1980年代末在女性创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时,铁凝长篇小说《玫瑰门》问世。在这部开辟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作品里,铁凝用她那关照生命的女性的独特眼光透视了一个家族三个女人的历史。铁凝曾坦告其写作原则:“我想起19世纪一些批评家曾经嘲讽乔治桑的小说不是产生在头脑里,而是产生在子宫里。我倒觉得假如女人的篇章真正地产生在子宫里也并非易事。那正是安谧而热烈的孕育生命之地,你必得有献出生命的勇气才可能将你的‘胎儿’产出。”[7]《玫瑰门》通过女性对女性的同类性别之间的感知理解,展现了女性心理、女性行为及不以男权意志为中心的女性的生存意识。铁凝通过一种不动声色的解构,瓦解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她认为男女两性世界并不是占有与被占有、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和谐的两性关系。
1990年代的十年间,受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具有鲜明生态女性主义特点的作品,毕淑敏、迟子建、马兰等均是关注自然与女性的代表作家。女作家毕淑敏在1998年发表的《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中对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打过一个极其恰当的比喻:“水是女人天生和谐的盟友,水是女人与自然纯真的纽带。”虽然这部作品篇幅不长,但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现状,都已处于作者温和细腻的笔锋里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目光下。而迟子建也是一位典型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旧时代的磨坊》、《秧歌》里都写到一个共同现象,女性希望以生育来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或者以生育作为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的补偿。虽然如此的动机是可悲的,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生育对于女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样,自然的孕育能力也对地球及人类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此方面女性与自然的姻亲关系毋庸置疑。
以王安忆、铁凝、毕淑敏和迟子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揭示种种困境和无奈的同时,也构建了生机盎然的可供灵魂歇息的精神花园。因此,她们树立了中国生态女性主义观之路上的里程碑——生态女性主义的第三大主题,即寻找精神和谐。这些女性作家在渴望女性投入自然和回归自然的同时,一直尝试着描绘男女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希冀。她们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的态度是最终达到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而通达的认识,当代女性作家开辟了既融合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又契合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之路。
20世纪的女性作家们经历了百年的探索与思考,以她们宽厚、博大、包容的女性情怀,学会了客观正确地看待自身作为女性的生理及心理特质,走出狭窄的“女性”世界,将自己融入到两性、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社会中来。在感受自身所处时代脉搏,关注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状态的同时,创造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经历百年的共同努力,开通了中国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形成之路。
[1] 陈瑶.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D].华中师范大学,2001.
[2] 冰心.山中杂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3] 阎晶明.论“五四”小说的主情特征[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4] 胡澎.近现代中日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J].当代亚太,1999,(1).
[5] 宗璞.红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6] 张抗抗.分界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 铁凝.女人的白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