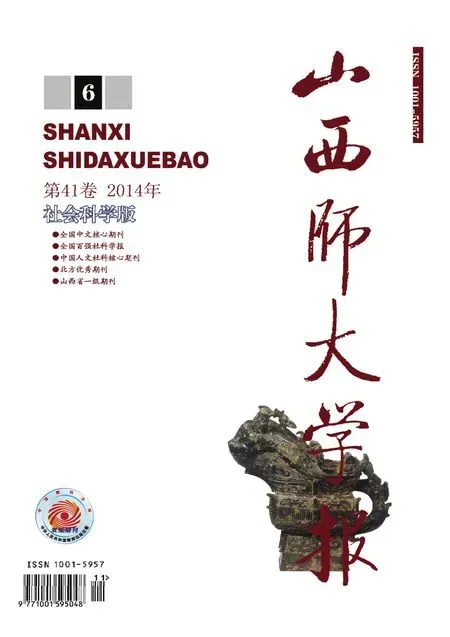论爵青小说的审美特质与人性书写
李 明 燊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在东北沦陷区作家的队伍里,爵青是一位异类,他游走在两条道路上:他既要寻找自我独立的文学世界,又要在日本异族的殖民统治下为生存而自保;他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其小说在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隐藏着一股穿越当时当地的巨大而神秘的历史感。不是每个作家都适合成为鲁迅式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斗士,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它自身的复杂性,作家的风格也必须是多样化的集合体。殖民地语境下的爵青带有他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对历史的领悟,荣格说过:“让这世界单调苍白的贫瘠在意识的冷光中升达那满天繁星的高处。”[1]34游走在现实的“贫瘠”与精神的“高处”之间,爵青的精神构架是建立在走向“个我”与走向世俗的纠葛之间,他似乎一直在神秘而暧昧的路上行走,即使是走向毁灭,也义无反顾。
一、殖民语境下的颓废都市
殖民语境下的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空间的表征不言自明,它是一种具有现代物质基础以及现代性意识形态诞生之后的产物。在西方,都市文化源自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将城市与乡村相分离,传统的农耕文明不再适合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两种文化形态造就了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发展路径。大工业时代的迅速发展使得现代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因此,现代都市文明的文化形态以及在现代性主导的时代里人性的裂变便应运而生了。
在西方世界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步源自于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市文化形态在这个千年不变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度显现了。尤其当“五四”之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存在已经十分明显,而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东北,由于其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文学发展呈现出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态势,相应地,在文化上,现代出版事业的高度发达催生了各种文学刊物以及文学形式的发展。伪满时期的爵青也在这个时候成了都市文化空间想象的代名词,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的影响,并在这种文学想象之中,插入了中国式所特有的文化意义。在中西掺杂的世界里,历史被颠覆,人性被撕扯,文化被浸染,这个光怪陆离的都市空间,在传统中国乡土文明依旧占据着绝对主导的空间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东北,上演了一场殖民统治下的颓废都市的大戏。
首先,殖民文化浸染下的哈尔滨成为爵青小说中都市文学建构的核心,这样一个近代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都市,在作者笔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格。他对哈尔滨都市空间的书写,主要集中在都市空间场景的建构、都市现代人的书写以及都市底层人的呈现方面。第一,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以及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表现手法更多地采用印象式的素描,呈现出殖民文化浸染下的哈尔滨在中西文化交杂的时代里的颓废、疯狂、躁动、喧嚣等,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具现代性的都市场景与人性的迷惘。如在《哈尔滨》中,城市的吵杂、混乱、淫靡令一个初到哈尔滨的知识青年穆麦迷惘和窒息,导致其最后出走。第二,如果说爵青对哈尔滨都市场景的建构只是作为一种铺垫式的背景出现的话,那么,其对都市现代人的书写则寄托了其无法超脱对于现代性冲击下的人性的挣扎。纷繁的都市生活赋予现代人众多的面孔,而每个人又都戴着别人无法看透的面具,每个人都是在面具的掩盖下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因此,在真实的自我与粉饰下的自我之间,现代人的挣扎在所难免。第三,对都市底层人生活的呈现是爵青都市主题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的叙事层面。对底层人的书写主要来自于命运的安排与底层人心灵内部的挣扎,困苦构成了爵青笔下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在这一叙事过程中,爵青并不太关注对权力体制造成的社会贫富悬殊的揭露与批判,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人内心深处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而揭示出在无可反抗的命运的安排下,都市社会的最底层人也没有放弃对命运的挣扎,但结果却是早已注定的。《荡儿》就是这样的一篇底层叙事的典型作品。
其次,爵青的文学创作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造就的日本新感觉派对爵青的创作风格有着不可回避的作用。中国现代主义似乎是将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世界观与西方现代派的反庸俗世界观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爵青正是这种形式的实践者,它是用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来阐释一种并非是反现代的理念。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两种立场其实并不是全然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所追寻的道路,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的理解,大工业生产和都市化进程是现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传统乡土空间模式虽仍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在文学叙事的空间向度上,不管是写乡土,还是写都市,其意向性都是偏重于对现代性的阐释。爵青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西方艺术技巧,融入了大量的都市文化元素,使其在那个还是以乡土叙事为主调的时代里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和现代性。其思想内核也并不是像西方现代派的那种对现代性的决绝的姿态,而是在文学想象的基础上,游离于对现代都市空间与精神空间的眷恋与决绝的边缘,陷入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自拔的困境。
我们可以看到,爵青小说在正常地讲故事的过程中总是突然间插入大段的类似叙事者心理分析式的独白,其内容充斥着困顿的迷惘、自信的坚守、未来的憧憬、躁动的不安等复杂的情绪,这也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的现代人格的写照。在《荡儿》、《溃走》等小说中,主人公扮演着逃出既定社会为之设定好的圈套的角色,出逃之后的“我”面对那令人兴奋的世界,最终还是逃回了这个圈套之内。显然,这是现代小说典型的娜拉式的主题,只是爵青笔下的归来者虽说在肉身上选择了“旧世界”,但在精神上,却依旧在做着痛苦而绝望的最后的挣扎。《溃走》中的吕奋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甚至不惜代价地杀害了束缚他弟弟发展的校长,而吕奋也延续着自己精神乌托邦的绝望式的建构。同时,在爵青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意识流式的文字书写较多,如“青春冒渎”系列、《斯宾塞拉先生》等小说中,通过运用内心独白和蒙太奇手法挖掘与表现人的潜意识和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其对艾伦坡和纪德小说技巧的借鉴,也使得爵青小说笼罩着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如《遗书》就充满了玄幻的叙事语境。然而,爵青的小说对于人物内心的过度分析也破坏了人物形象自身的完整性,叙事者过度地插入故事情节的进展,突兀并过多地在小说进展过程中插入叙事者的见解,破坏了叙事的完整性。并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流露出概念化的弊病,思想大于主体、概念大于内容、理性大于情感的描写,大大削弱了小说的叙事表现能力。
二、精神世界下的自我救赎与崩溃
爵青的文学世界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完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是一个“反庸俗”的捍卫者,他对附庸于世俗的人间丑态嗤之以鼻,以自我的灵感来构筑与现实相背离的自我救赎的精神世界,即使这是一种苦难的彷徨,但毕竟它是一片灵魂的净土。但是,爵青的自我救赎并没有坚守到最后,他在灵魂的挣扎中最终还是败给了世俗社会的压迫与诱惑,由自由作家变身为殖民体制内部的一部分,正像《溃走》中的校长一样,在一次内乱中得到官方的要职之后,便放弃了之前的雄心,甘愿沦为政治的附庸。
在爵青文学创作的前期,其小说到处笼罩着一种对人生苦难与悲剧的自我体认,一种阴沉的格调一直萦绕在其创作的始末。苦难与悲剧的主题,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传统,其在对社会悲剧的揭露上丝毫不亚于左翼文学的力度。例如小说《巷》、《哈尔滨》、《恋狱》等,既有对底层人生活苦难的揭示,也有对现代都市人性苦闷的展现。当然,爵青和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在揭示生活苦难、社会不公、人性困境的同时,他们无力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这不是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爵青与中国现代忧国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并不为自己无法拯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度而苦恼,他的创作只是在针对悲剧本身,并不涉及未来的路在何方。他的小说“都是捉住了超平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与非俗的故事而展开”[2],他所关注的是此在的一切,并通过对这些人和事物的审视得出一种认同苦难的结论。也就是说,在爵青的世界观里,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他并不是想借描述苦难的现实来达到抨击社会机制的目的,也不想影射日本统治下殖民化社会的残酷现实,爵青所要做的就是一种人间固有本质的再现。与其说他是在暴露残酷的现实,不如说爵青是在以旁观者的姿态欣赏着人生的悲剧。我们没有权力去要求一个作家的思想必须按照一个既定的轨道运行,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爵青一定要将其艺术世界去跟殖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文学所要思考的问题。
可能人们会说,在一个充斥着飞沙走石的民族危亡的年代,爵青的文学观完全就是一种对于时代的逃避,甚至是一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认同。如果我们以更加宏观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这其实正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可由中国古代的“载道派”和“言志派”发展而来,这两条道路对现代中国的文学依旧适用,以左翼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脉可以归入“载道”的一派,而以京派、新月派、现代派等不过问政治的一脉可归入“言志”的一派,而爵青恰恰也可归入这一行列之中,只是因为当时身处沦陷区,特殊的环境与特殊的语境,导致爵青的价值并没有被及时发现。
在爵青文学创作的后期,他宣告了前期自我救赎的惨败,这种宣告是以失语的状态显现的。在三四十年代日本殖民统治的背景下,爵青身在其中,但其文学创作中却很少能看到殖民文化的影子。当然,这要排除40年代之后其在满洲供职期间创作的几部旨在为日本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的政治宣传类的作品。表面上来看,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事,但仔细思考之后,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也正是在殖民统治深化的过程中,爵青的文学创作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日本文学去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日本文学的传统都是由一些无权也无兴趣谈论政治的平民阶层来延续的,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的边缘人,还不如说这些人本身将政治置于其文学想象的边缘地带。因此,爵青的文学理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先锋性的特点。早期的爵青曾经有一段创作诗歌的经历,并加入了当时的诗歌团体“冷雾社”。他尊崇艺术性灵的直接表达,追求一种超然于现实的性情流露。爵青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关切直接的社会现实,而是关注世俗现实之上的更为普范的人类生活的现实意义,他追求灵魂的自我求索,隐约之中带着一种宗教的意味。生活在日本统治之下的爵青,他的艺术观是对浸染着殖民文化气息的现实社会的有意背离,他试图要保持自我性灵独异于外部世界,以真实的自己来代替虚伪的现实,以善良的行为来感化罪恶的都市,以美好的人性来陶冶丑恶的人群。但似乎没有人去理解爵青对美对善的向往,只是一味地挑剔他的文学创作脱离现实,在殖民主义肆虐的当时,他的艺术观显然在现实之中不合时宜。在现实的丑恶与自我身心纯净之间,爵青做着痛苦的挣扎,被拉扯着的内心遭受着苦难的煎熬。
“冷雾”时期过后,在现实的影响之下,爵青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变化,即由诗歌转向了小说。同时,其小说创作也在竭力地寻找人类的普遍现实意义与世俗的社会现实相融合的交叉点。他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如《哈尔滨》、《巷》、《荡儿》、《某夜》等。其中,对人间恶的抨击是其创作的核心内容,他创作了一系列从罪恶的现实出走的形象,穆麦、荡儿、吕奋等,同时也是在暗示自己也在试图从世俗的现实中逃离并获得真实自我的救赎。但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在一个殖民地,爵青对当权者不冷不热的态度显然不能让殖民者满意,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政治文化上的宣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个体系本身就是要宣扬一些有利于这个体系运转下去的意识形态理念。1941年,“满洲文艺家协会”成立,爵青是协会成立时的委员之一。因此,爵青作为当时满洲地区的知名作家,其身份也由当初的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位日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现实生活的改变使其放弃了曾经坚守的心灵的净土。之后,他创作了一些作品,如《青服的民族》、《黄金的窄门》和《欧阳家的人们》等,“都没有‘投敌叛国’的内容,可是他一直被认为是文化汉奸,甚至是特务”[3]72,他没有了退路,曾经坚守的心灵纯粹的世界沉没了,自我救赎也便宣告了失败。
三、孤独路上最后的狂欢
与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一样,爵青也是一个矛盾体,对于生活的坚守,对于世俗的诱惑,他是一个平凡人,而苦闷彷徨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主导思绪,身处殖民地的爵青更是这样。烦恼在现实中无处发泄,他只有将情感寄托在小说的世界里,对于现实的政治不去过问。但在日伪统治时期,这样的态度是不会被统治者所接受的,终于在现实的压迫下,爵青不得不放弃自我灵魂的写作而走向了牢笼中孤独的狂欢。
一方面,爵青最终还是完成了对崇高自我的现实背叛。他曾经是精英领地的坚守者,他抵御着来自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体现了他反世俗的价值观。当然,对社会世俗的抵制也就注定会使一个人在社会上无所作为,甚至难于立足,进而注定会成为现实的失败者。正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爵青甘愿成为殖民地生活的“胜利者”。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因此,超脱于世俗之外对于一个社会的人而言是仅存在于乌托邦的想象之中。爵青曾经努力来捍卫这种脱离世俗的自然纯净的生活之本义,他坚持过、挣扎过,但他最后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失败者”,而成为了“世俗的胜利者”。甚至在小说中,他也嘲讽起曾经单纯而可笑的自己,成为了“一任世情的摆布”者。他曾经写道:“我听过数十种教义,听过数十种说法,把这些教义和说法灌输给我的人,当时都自信满满,毫无疑色,可惜得很,如今却都不见了。”[4]在《恋狱》中,写一个男子是如何妥协于金钱,而抛弃了痴情于他又有恩于他的舞女丽丽,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在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而丽丽也嫁给了富有的法学学士。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借丽丽的口吻这样写道:“良民们的金钱虽然罪恶多端,然而在这罪恶多端的金钱里,却像彗星一闪似得,还有真实的爱情和永远的幸福,她抓住这爱情和幸福便满足了。……伯劳已经歇业,她走过那四层楼的露台底下,还能时时想到身为夜之女王的往日吧。不坠的天使已然健在,那坠狱的苍白脸男子哪里去了呢?”这是爵青在小说中对自我的影射,在俗世的诱惑下,很少有人能彻底脱离出去,爵青也不例外,挣扎只会加剧他心灵的痛苦,却不会使他登上灵魂的圣殿。其实,从总体上来看,“与殖民统治的‘不完全’性相对应,中国人对这一殖民统治的反应也同样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中国没有出现具有一贯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反殖民话语,也没有形成由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所结成的联盟”[5]45。因此,我们没有可能对知识分子做一个统一的定位,其个人的选择也自有其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自“五四”以来,“归”与“不归”的主题一直都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母题延续着,它寄托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愁”。在现代性的都市生活久了的他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视角去反观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故乡。这其中,有对故乡的抛弃,也有对故乡的眷恋。鲁迅对故乡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故乡的眷恋而又不得不离去的复杂心境,他们痛恨故乡子民愚昧与麻木的生存状态,而城市的漂泊和孤寂之感又总是让他们追忆故乡的美好。但回到曾经的家园,眼前沉滞的一切又使他们不得不带着失望与沮丧的心境再次离开。相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归”只能存在于精神上对家乡乌托邦式的想象,即“心灵之归”;而“不归”才是现实中他们的最终选择,只是心中对那想象中美好的追忆不曾泯灭过罢了。
对于爵青来说,“五四”延续下来的“归”与“不归”的母题也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主题上,爵青不同时期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其前期的小说中,作者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巴金的青春激情式的状态,用犀利而激昂的笔法批判“旧世界”的既定秩序,意在打破旧体系的束缚,冲破传统的羁绊,从家庭出走,去到一个自我精神想象的新的世界里去,做一番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的事业。如《荡儿》中的荡儿,《溃走》中的吕奋,即使在他们出走之后发现现实并不是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生活的苦难逼迫他们不得不又回到避风的港湾,但身体的回归,并没有使他们精神上屈服于“将死的世界”,他们依旧坚持着对传统的精神上的背离,并且试图去说服新一代的青年尽快从窒息的家庭出走,甚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害一些人,而使一些人获得新生。《溃走》中的吕奋为了使他的弟弟获得精神上与肉身上的解放,去追求新的生活,吕奋不惜杀害了为他弟弟安排好了以后生活的一切的校长。
爵青的这些充满决绝式反抗的创作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对生活的向往,但这一切似乎来得都过于简单,正像巴金在经历生活的磨练与积淀之后艺术风格走向了沉潜之路,爵青后期的创作与前期相比更加圆熟了,只是思想不再有之前的先锋性了,转向了一种对精神家园的怀恋与坚守。《归乡》是爵青后期小说创作中的名篇,与其前期创作受西方影响较大相比,其后期的创作更具有民族的意味。实际上,文学生涯前期的爵青追求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先锋性,越到后期,爵青把关注的焦点越是回归到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上,这也正是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正路。《归乡》讲述的是“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处理家事的经过,全篇都饱含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年轻人以为在熟睡的父母枕畔,留一封慷慨激昂的告别信,而身无一物地走出去,便是清算了家风。其实家风之为物非常奇妙,竟有弃不胜弃的地方。”[6]191这正是久别故乡的一代人对家乡的“乡愁”,这其中的情感是复杂的,面对久别的故土,怀恋是必然的,但同时,家乡的穷困、人们生活状况的恶劣等现实场景摆在“我”的眼前,让生活条件优越的“我”又怎能消隐掉对故乡的忧思。虽然作者以悠闲平淡的笔触来叙事,但其中隐含着的恋乡与弃乡的复杂情思是可以看到的。
爵青十几年短暂的文学之路一直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度过的,不论是其建构自我的灵魂世界,还是其舍弃“孤独”而成为殖民话语政治表演的工具,我们都应该以历史性的眼光去体会爵青在那个时代的处境与心态,以客观审视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中的人物,文学需要这样的品质。
[1]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 姚运.东北十四年的小说和小说人[J].东北文学,1946,(1).
[3] 上官缨.论书岂可不看人[A].上官缨书话[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 爵青.《黄金的窄门》前后[J].青年文化,1943,(3).
[5]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 爵青.爵青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