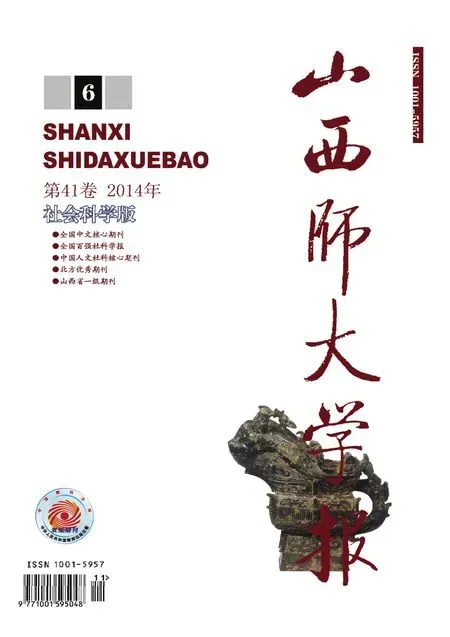清代中期男性文人支持女性文学活动的动因
秦 天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京 210097)
清代是中国独有封建制度的绝响,也是封建社会土壤上孕育的文学艺术的集大成时代。看似无懈可击自我修正能力极强的封建社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其中却发生着一系列的微小变化,酝酿新的裂变。在男性知识分子看待女性从事文学活动这一命题上,传统伦理不断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以期容纳新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却一再冲击传统伦理规范的底线,身在局中的男性或女性并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历史缓慢变迁的车轮中,因此矛盾的情绪也处处可见。
一、母教的功用增强了男性文人对女子才学的认同
女性在封建时代被普遍认为位属低下,但作为妻子的基本地位却受到法律保护。而相对于被后代屡屡触犯的妻子的地位,母亲的地位则更为尊崇。母亲,作为宗法制度的关键元素受到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保护,更在伦理道德上地位超然。客观上,母亲的地位亦是母亲在家族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母亲不仅担负妻子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当丈夫与父亲角色缺席的时候,家族继承人延续家族光耀门楣的希望,都取决于母亲的素养。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提到的《夜纺授经图》,是后来官至刑部侍郎的钱陈群为纪念幼年其母陈书“课子”事所作,而当时针对这一幅画的题咏,是士大夫间的一件盛事。其起因竟是乾隆帝的亲自垂问:
陈群刊《香树斋集》初成,一日召见,上索观焉,次日敬呈睿览,至臣敬题臣母《夜纺授经图》,特赐二绝题之,即命臣奉图呈进,上御书于图首。中使捧出,臣陈群九叩。只倾一时,公卿莫不叹羡,以为亘古稀有硕获瞻图者。[1]56
根据陆以湉《冷庐杂识》记载,乾隆帝的两首七绝为:
篝灯课读澹安贫,义纺经锄忘苦辛。家学白阳谙绘事,成图底事待他人。
五鼎儿诚慰母贫,吟诗不觉鼻含辛。嘉禾欲续贤媛传,不愧当年画荻人。
在上两首诗中,“安贫”“纺织”“苦辛”以及“五鼎儿”所带来的母以子贵的荣耀是关键词,可见在官方意志中,母亲亲自督课(“画荻”)这一行为,与纺线等家务一样,是母亲家庭责任的体现,官方希望表彰的也正是这种“贤母”的形象,而并非“母教”本身。因此,御诗中强调的是母凭子贵,却刻意忽略了母亲的才学。
根据《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陈书有画册《纺余闲课》传世,诗集《复庵吟稿》未见。但钱陈群在诗序中记述的却不仅仅是官方所表彰的内容,儿子不能忘记的是在父亲钱纶光出仕外地时,陈书完全担负起了教育的职责,“时群十岁,母授《春秋》;弟峰八岁,授《孟子》;弟界五岁,授《小学》《孝经》;辄录所授课比月,彚而邮寄信安官舍属”,“寝匆奇文难字,母训母诂,英声华词”。而沈德潜《钱香树先生属题〈夜纺授经图〉,述母德,感君恩也,谨成四章》更有“母教成师儒”一句,点出了儿子才学与母亲才学之间直接的承继关系,对母亲的才学给予更为明确的肯定。
“但问室人之贤否,因知家道之废兴。”[2]528母教对于父教的补充作用,在延续家族声望、培养继承人方面至关重要。在清代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少的早年经历都颇为相似:父亲为求功名宦游在外,颠沛之间撒手人寰。然而家道中落,很多人面临无力延师的状况。如法式善所言:
先大父以乾隆十九年罢官,家业中落,移居西直门外之海淀,无力延师,太淑人以教读自任。[3]723
因此,对于那些受惠于母教的儿子们而言,他们对女性才学的体会最为深切,认同女性才学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这通常是由经史方面开始的,如以下记载所言:
铨四龄,母日授四子书数句;苦儿幼不能执笔,乃镂竹枝为丝,断之,诘屈作波磔点画,合而成字,抱铨坐膝上教之。[4]2046
夫人故尝读《毛诗》、《孝经》、朱子小学,绍升侍卧起辄为诵其文,讲说其大义,且曰:“儿志之,它日好作一端士。”夫人又尝谓绍升曰:“吾读书,每慕古节义事……”[5]489
“贤母”的身份,让她们的文学创作很少招来“僭越妇德”的非议,如袁枚就曾记载毕沅之母张藻与其弟张苍的唱和:“少仪观察常至节署,太夫人喜晤作诗。”[6]652但张藻是被官方表彰的贤母代表,去世后还曾赢得高宗“经训克家”的褒扬,因此家族唱和士林传为美谈,钱大昕赞其为:“太夫人词翰之美流播艺林,又有弟少仪观察知名海内,白头唱和,比于思芬。”[7]685
家族对女性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为家族传承多提供了一重保障,从现实功用上将女性接受教育合理化;贤母孝子的出现,官方出于维护正统的宣传,同时又为有才学的女性争得了男性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就个体而言,受惠于母教的男性知识分子广泛存在,他们多数对女性创作抱正面态度。贤母、孝子、母教事功、官方宣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侵蚀了传统伦理中对于“妇学”的定义,使移风易俗最终得以完成——“在婚姻市场上,博学标志着一个女子成为众人争相延聘的对象,成为一个不仅能生育子嗣,还能为儿子们提供最优越的早期教育的未来母亲”。[8]78有清一代,女子教育在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地位总体来说可谓重要,台湾学者廖藤叶曾经尝试用女性作者的名字来说明,“为这些女性作者命名的家庭,通常是重视教育的,所以取名用字也极尽书香味道,……同姊妹的取名用字上,也类似男子的‘字辈谱’,即姊妹命名有规律可寻,或是和兄弟同用‘字辈谱’”[9]。女子教育为女性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女性文学就在辩论中获得了比历代更为宽广的天地。
因此,清代中期,一方面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话语从未消失,另一方面女性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的文学活动却约定俗成。在这方面最集中的反映,是随园女弟子络绮兰《秋灯课女图》的传播。
骆绮兰,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后裔。绮兰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其自述:“兰自幼从先君学诗, 垂发时, 即解声律。”后嫁金陵龚世治,“早寡无子,课螟蛉女以自遣”[10]15785。寡居中,她“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并“师事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出旧稿求其指示差缪,颇为三先生所许可”[11]695。在这种男文士与女性作者频繁交往的背景下,《秋灯课女图》也就渐渐在男文士圈中传开,豫亲王、袁枚、王文治、赵翼、毕沅、张问陶、法式善等都曾题咏此图。诸诗中,有如豫亲王之“热眼看来凄苦甚,须知极乐在清修”,空泛隔膜,略带猎奇意味;也有毕沅之“展图(枨)触,卷图泣然。白头灯影,宛在眼前”,意在颂扬寡母贤德。但不乏男文士肯定“课女”这一行为的意义。
男性知识分子对《秋灯课女图》的认可,已经超越了对于“儿子的母亲”功利性的认可,单纯赞赏母亲教女的行为与才学,某种程度上,因为受教育对象是女儿,也可以认为是男性知识分子认可了女子才学沿袭的合理性和价值。学者在广泛探讨清代女性具有解放意义的突破性尝试的时候,往往过多强调女性主观努力,而忽略了女性成长的土壤,无论是对于女子教育的松动甚至尊重,还是男性知识分子对女子才学的重视和认可,清代都可谓是历代之最,而这最终,仍是与当时社会运转的方向息息相关的。
二、女性写作纾解了男性文人矛盾处境下的精神困惑
康乾盛世之后,看似花团锦簇的大一统的中国,其实已经问题重重。统治者不思进取闭关锁国,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严格限制,社会生产缺乏动力,社会发展不复生机,提供给诗人的写作题材在萎缩,滋润诗人的写作灵感在枯竭。雪上加霜的是,清代文网高张,因言获罪比历代都要轻易和严厉,使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三缄其口,文学创作如履薄冰,一部分人因此转向考据研究,学术兴盛的同时,思想却因此更加僵化。
(一)诗歌创作的困局。上世纪初,梁启超批评清诗:“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12]101以天崩地裂后的新社会新眼光去看清诗,当然会得出这样感情色彩相对强烈的结论,然而就当时人物而言,即便他们不具备历史前瞻性,也未尝不深知诗歌发展之弊:
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触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13]321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14]1
清代四大诗歌理论——神韵、格调、肌理、性灵,归根结底,都是针对诗坛陈陈相因、缺乏活力所开出的药方。
诗歌理论家费尽心机调和“理”(“学”“法”)与“才”(“性”“情”)之间的比重,却仍然无法避免诗歌这一体裁的日益衰落。
清代中期的“性灵说”以晚明“性灵派”为宗绪,可见其思想基础仍然是晚明商品经济发展下兴起的心学。性灵派诗人强调诗歌创作由心而发,抒写真性情,如“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15]262、“真诗多出性灵中”[16]151等,性灵派的诗人们创作了相当一部分的艳体诗,因为袁枚就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可见,性灵派本身就是一种便于女性参与的诗学观,它强调的“性情”与“灵机”十分适合扬女性天然未凿之长,而避女性缺乏学养阅历之短。笃信性灵的陈文述就相信天地之间,杰出优秀的女子必然不少,他极端服膺宋谢希孟所言:“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甚至还强调“三复此言,益信斯言之不诬矣”[17]56。
在男文士为疗救诗歌之病做出革新的时候,无意中来到了女性所擅长的领域;当男性知识分子被迫放弃了以往崇高的政治理想,撇除了社会生活,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与女性所掌握的资源近乎相等。这种天然联系让性灵一派诗人对女性作者自然产生亲近和赞赏,造就了孙原湘与席佩兰、徐达源与吴琼仙这样双双拜入随园门下的诗侣,给予更多女性作者展现诗才、获得声誉的机会。
(二)立身处境的困局。诗侣的出现,即“士人与室人”的唱和,取代了明末清初士人与妓家的组合,成为这一时期“才子佳人”生存理想的主要呈现形式。随园、心斋、碧城女弟子中,许多都源自这种家庭,孙原湘与席佩兰、徐达源与吴琼仙之外,任兆麟与张允滋、陈裴之与汪端、陈基与金逸王倩、张铉与鲍之蕙、叶绍楏与陈长生……时人赞赏之为“徐淑秦嘉之风”,袁枚屡屡评价他的女弟子“徐淑之果胜秦嘉也”(《随园诗话》卷八评席佩兰,郭麐《吴琼仙小传》提及袁枚评吴琼仙)。丈夫是将闺秀诗人引入诗坛的重要媒介,如席佩兰、吴琼仙、金逸结识袁枚都是通过各自的丈夫,张允滋诗歌入选《撷芳集》也是因为任兆麟以清溪诗示钱大昕、钱大昕又推荐给汪启淑。陈玉兰认为,清代江南士人所遭遇的政权的打击空前酷烈,所忍耐的思想的桎梏和心灵的压抑也空前沉重,闭门自守于家庭这个柔波荡漾的安全港湾,生活重心由社会转向家庭,于是栽培、扶植合乎审美理想的闺侣,以求得心灵的相通、情志的谐和,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1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之阐述为,“边缘文人以崇尚妇才为风雅,把自己对理想佳人的向往或红颜知己的期待,转化为对女性文本的偏好、推崇与关爱,甚至不惜投入人力物力去编选、品评、考古和刊刻,为此形成了清代特有的文人文化时尚”[19]。
对现实社会的失意,诚然成为一部分男文人接纳乃至扶植女性作者的心理动因,但通过对当时社会形态做更全面的考察,从事女性文本编选和刊刻的又并非只是“边缘文人”。在乾嘉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对文字作品的整理刊刻成为显学,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尤其像江南这种经济富庶地区,出版印刷业更是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官刻系统中,以朱筠、毕沅、曾燠、阮元为代表的学人幕府网罗了大量失意科场的士子,“播弦歌之雅化, 以文章名冠天下”, 流传后世。一方面幕主与幕僚意气相投,频频雅集,诗文唱和,风雅一时;另一方面,幕主与幕僚大多与闺秀文学存在渊源,对才女与女子诗文的态度比较友好,彼此交流评点时也不乏各自家族女性诗文的内容——如毕氏和阮氏家族女性都能诗文,袁枚、王文治、王芑孙是曾燠题襟馆的座上客,洪亮吉与钱孟钿家族有旧等。而受到乾嘉学术风气的濡染,这些早年科举得意的封疆大吏们都着意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如地方志中的列女才媛对女作者的名字作品进行著录,《两浙輶轩录》则收录了闺秀诗作。此时的官方意志从文字集大成的角度将闺秀文学搜罗其间,并对当时数量众多的幕僚身份的文人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男女处境的此消彼长是造成清代中期女性文学繁荣的根本原因,没有男性在政治角力中的失意和退守,就不会有女性在家庭微观环境中的地位改善,更不会给予女性发声的机会。因此两性关系在这一命题里体现的是彼此依存而不是对抗紧张。当后人探讨这一时代女性文学活动的意义时,既不从无限上升到妇女解放的层面,也无需因为其迅速销声匿迹而贬抑其存在的价值,毕竟女性作者的处境比前代有了明显改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非开风气之先,却也留下流光溢彩的一瞬。
[1] 钱陈群.敬题家慈《夜纺授经图》.香树斋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钟于序.宗规饬女妇.丛书集成续编7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
[3] 法式善.先妣韩太淑人行状.存素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47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忠雅堂集校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 彭绍升.先妣宋夫人述..二林居集[M].续修四库全书.146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袁枚.题词.培远堂诗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 钱大昕.畹香楼诗序.潜研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438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9] 廖藤叶.清代闺阁诗人名字所反映的社会文化[J].人文艺术学报·创刊号. 嘉义大学人文艺术学院,2002,(3).
[10] 钱仲联编.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1] 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A].江南女性别集二编[C].合肥:黄山书社,2010.
[1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 王士祯.渔洋文集.卷三.带经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14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沈德潜.说诗晬语[M].续修四库全书17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 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船山诗草[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 孙原湘.题小云澄怀堂诗稿即送之娄东赴其师萧子山之丧.天真阁集[M].续修四库全书17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 陈文述.姜晓泉儿女英雄画跋.颐道堂文钞[M].续修四库全书15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 陈玉兰.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3).
[19] 王绯,毕茗.最后的盛宴最后的聚餐:关于中国封建末世妇女的文学/文化身份与书写特征[J].文艺理论研究,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