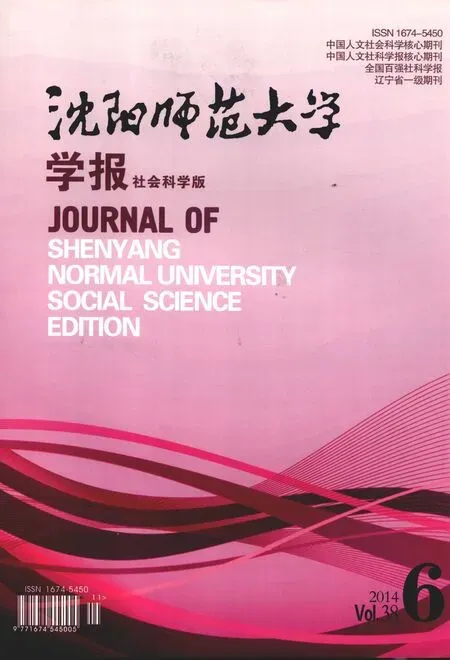论奴化教育的特点及其本质——文史教科书视域下的伪满洲国教育
孟庆欣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4)
“认同”最早属于心理学范畴。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认同作用是一人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它可以随着其他人所带来的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新感觉而产生。“这种共同性质愈重要,这种局部的认同作用也就愈成功。因此,它也许代表了一种新的情感联系的开端。我们早就推测,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属于这样一种认同作用,它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情绪的共同性质之上的。”[1]1976年,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中又提出“政治认同”的概念:“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 (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2]在这里,我们引入“认同”等重要概念,以满洲国时期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主要考察对象,在文史教科书的视域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伪在我国东北所进行的“奴化教育”的特点与本质等问题试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与评价。
一、剥离孔仁孟义,异化儒学,移植日本文化,重构文化认同
日伪在东北所建构的思想体系,包括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本文仅分析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建构的奴化教育体系。
(一)解构儒家思想体系,将博大的内容异化为忠孝有序
儒家思想是由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时时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它有如河床堤坝般一直对中国民众的思想起着既引导又约束的重要作用,同时孟子浩然天地的大丈夫气节为中华民族挺直脊梁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钙质。日伪执政者深知儒家思想的作用以及其中的孔仁孟义、孔柔孟刚之别,对待儒家思想采取“尊孔轻孟”“删孔去孟”的剥离之术,尤其满洲国教科书过渡期结束、统编的“国定”“审定”本出台之后,留孔之仁爱忠恕、去孟之义勇不屈,精心选取以忠君为核心的《论语》和全本的《孝经》概为儒家思想的全部,并以之为重新建构“王道”文化、集中体现“忠孝”“尽臣节”伦理规范的教本。“王道者,孔圣之大道也。其主要之原理,曰忠曰恕,皆治世之良方、息争之妙策也。”[3]“《论语》之文字,字字珠玑,尤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语为千古名言,应拳拳服膺者。……我辈国民无论其为男女老幼能不相率恭奉明诏以尽臣节乎?”[4]63
为了掩盖和调和民族矛盾、推行“民族协和”政策,日伪执政者将孔子所言诗教作用之一的“群”抬高到空前的高度,号称“智、德、体、群、美”五育并举。日伪大肆尊孔祭孔,其实就是要以孔子的“忠恕”思想束缚不肯认同、不断反抗的民心。“我国成立,政主王道、教本儒宗。而王道之本,在乎忠恕,忠恕之道,悟自孔子。”[5]“本王道治国之精神,实行大同主义,以道德孔教规范人心,上下一德,振兴庶政。”[6]1099
(二)建构日本文化体系
1.建构日本语的教育教学体系,极力宣扬日本文化。语言是意识形态的标志,语言是族群认同的密码,语言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日伪在课程设置上,将日语当做国语,并占有大量的课时。在弱化汉语、强化日语的过程中,又以日汉杂糅的“协和语”进行铺垫与过渡,极大地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在建构日本文化体系中,教科书更是主要渠道。如初级小学校第四册《修身》内容:开篇是《皇帝陛下》,讲建国宣言,然后就是日本“圣人”、学者、道德楷模、商人等故事,此外还有民族协和、满日亲善,最后以忠君爱国收尾。《满语读本》则有野口英世、保己一、中江藤树、乃木将军及其夫人的故事;还有《天长节》《神风号》等内容。在有些日语教科书如大出正笃著的《新撰日本语读本》中,还专设《日本事情》编,目的在于教以日本风俗、习惯、风景。
2.在国民意识中强化日本宗主国的地位,进而奴化学生与民众。置于教科书扉页的《诏书》总以臣服之口吻道出对日本宗主国的敬畏。《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一卷)日满一德一心》详记溥仪访日途中向“东天遥拜”的情景;第二次访日回銮之后,满洲国开始称日本国为“亲邦”。教科书中也是公开宣扬“我满洲帝国国民之使命,当以日本帝国国民之理想为理想,以期实现道义之世界”[4]153-154。
3.宣扬不平等的日本种族优越论,建构不平等社会阶层关系。人为地制造不平等的阶层关系是实施奴化教育的基础。日伪执政者将东北境内的“满洲人”列为第四等级国民,还宣扬是“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日本赶走了“鬼畜米英(米英二字均加反犬旁)”,保护了满洲,维护了亚洲的利益。“观夫友邦日本,乃以其卓越之力、独揭此理想之旗,迈进于道义世界之建设者也。我满洲帝国,既趋于此旗帜之下,且得友邦之指导援助。”[7]
二、对日伪所建构的奴化教育体系的评价
日伪所构建的奴化教育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统治意志的狭隘性
1912年7月,蔡元培先生深刻剖析了封建教育之弊:“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教育者本体上着眼,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8]这段分析评价里,包含着正反两个十分深刻的教育理念:教育应该“从教育者本体上着眼”,就是今天说的“以人为本”;教育不应该以“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思想意志主导一个国家或整个地域的思想意志进而强制全体受教育者或全体民众都要服从这一个领袖人物特有的政治意志,即反对“教育党化”。因此,他提出“教育独立”的先进理念,提出“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兴办“超轶政治之教育”,“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9]同时,也反对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某一民族文化去同化另一民族。
反观伪满洲国时期教育意志,正是蔡元培先生等反对并已摒弃的;从时代性上考量其与先秦时期的教育思想大致相当。“盖王者,以德化民。……教本与德,而民乐从;从之所归,文之功也,历代相承,于今未替。……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6]11937年3月,满洲帝国教育会理事长皆川丰治在《满洲教育》发表《建国五周年感言》总结道:“满洲建国后,文教部确立教育方针,排除三民主义教育,禁用排外教科书,准则于建国精神、归源于东洋道德,以图五族协和、日满不可分、王道立国主义教育之实现。”无论如何表述,其理论基础均为“王道”与“神道”。可以说,二十多年之后,满洲国的教育沉渣再起,其教育意志的独裁与教育思想的狭隘远不及于民国初期之开放与多元。
(二)教育思想的落后性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乘东渐之风,已经出现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学校制度与教学方法被系统输入,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推士、麦克尔等纷至沓来,民国早已以美国为参照重心进入健全的发展阶段,正在开始“适应时代的要求、力图与国际教育和现代化潮流接轨”[10]。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炎培以及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大家辈出。蔡元培总长于民国元年九月任职伊始就扬弃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确认了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即“五育并举”[11]。指出教育即“发展个性、崇尚自然”,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反对以“群性”抹杀“个性”,反对只求“近功”不求“远效”。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早在1826年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美国语文读本》已开始摆脱殖民教育、建构美国人的现代价值观,塑造着包括热爱国家、崇尚勇敢、真诚正直、追求自由与公平、理性精神和热爱自然的国民性格。
而此时伪满洲国的思想文化违背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性,无视现代意识,落后于时代和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其教育宗旨已退回到封建时代。“普及建国鸿旨、实行王道教化”仍是第一要义;“今我国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以爱国与军国民等主义为鉴戒。以仁义道德,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6]551-552就其教育方针的本质而言,就是以封建的旧道德、旧礼教为麻醉剂,祭孔读经、崇信王道神道,让东北民众羞于反抗、甘心认同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精神重构体系,情愿接受日本殖民统治者施行的奴化教育。多种教科书每册卷首都刊以溥仪皇帝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或《国本奠定诏书》。“忠君者,乃为我国民普遍、最高、绝对之道德也。”[12]在课程设置上,清末民初尚且设置旨在尽量发展学生个性的选修课程,而满洲国初等中等教育中的课程基本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必修课程。
(三)培养目标的工具性
日伪执政集团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出发,以巩固殖民统治为奴化教育的最高目标,教育成为法西斯执政集团的政治工具、经济工具,受教育者则成为愚顺的劳动工具。日伪的奴化教育虽然也声称“实行全人教育”,但其“全人”的内涵是所谓“忠诚、善良、强健、勤勉、有用之国民”,说得通俗些其实就是老实听话、体格强壮、手脚勤快、能出苦力的活工具,与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毫不相干。
一个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国家要想对于一个正处于农业化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系统培训廉价劳动力是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所以,日伪注重职业教育和体育卫生教育,但其目的不过是培养经济掠夺过程中熟练高效、体格强健的劳动工具。
三、日伪在建构奴化教育方面的三大手段及其本质
恐怖暴力与愚弄欺骗以及封闭封锁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实施暴政与专制之执政者的通用手段。满洲国时期的执政者亦无例外。
(一)恐怖手段
1.颁发各种法令法规体现出强大的决策力,泯灭治下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从法律上进行精神控制。1937年5月2日,日伪公布《国民学校令》,从政令上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1943年8月18日,日伪颁布《思想矫正法》《思想矫正手续令》等,对具有反满抗日思想者进行“洗脑”提供法律的依据。1944年6月12日,紧急颁布的《时局特别刑法》首次列入“思想犯”“国事犯”罪名,使逮捕与极刑达到随意的程度。
2.组织机构具有强大的教育执行力,对违背其教育意志、反抗其教育行为者进行恐怖镇压。从1933年初夏起到1945年仲夏,日伪宪兵特务在吉林、沈阳、长春、黑山、哈尔滨、铁岭、安东等省市捕杀戮害教育界人士几近千人。据战后国民党安东省教育厅所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教育人员及家属受害情况调查表的不完全统计,仅安东教育界人员就达113名,遭迫害致死者71人[13]。
3.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监管审查制度下极力发挥督导监察力,建立各级教育“指导监察”机构。教育督导、视学委员会委员、警察机关、日本教员、汉奸“眼线”,都成了监视中国师生的“补强机关”人员。教员每年年底还要到警察机关呈交履历表,“以备归档审查”。当局还经常号召学生揭发检举教师员工反满抗日思想。
此外,广泛的教育团体和教化团体充分体现出了强大的社会教育的影响力。
(二)愚骗手段
中国人历来注重历史,思以史为鉴、行以史为据,国民的价值认同总与当时的主流历史观且行且相生。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讲得深刻:“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日伪执政者也深谙此理,所以,他们在否定传统与继承、实施去中国化策略进而解构本土文化、进行精神重构时,总是从撕裂文化和教育入手,利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历史学为先导,进行剥离中华文化的政治、道德、语言、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奴化教育。
在日伪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中国东三省各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东三省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是融汉、满、蒙、日、鲜为一体的独立国家。讲东三省的历史总以肃慎为源。讲的比较直接而集中的是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一卷)中的《建国》:“我满洲地方,地理上固与支那相离而独立,历史上则与支那相并而发展,此昭然之事实也。”在同册《民族协和之精神》里,日本侨民竟然已经被改扮成中国东北地区的“原住民族”。这种史观甚至都渗透到民间的历书中。这种论调,看似多样风声,其实均源于一穴——《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该教科书的《建国前史》部分,“我国实有三千年之独立历史”是其要害;而《建国后史》部分,“满支两国迥殊”是其核心。可以看出,日伪执政者的历史观,先是将中国古代东北地区与已经被日本吞并的朝鲜—高句丽历史合二为一,进而形成满洲国是与中国并存独立之国家的包藏祸心的结论。
歪曲历史事实之处更比比皆是。仅就“九一八”事变而言,就有《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 建国后史》中的“张学良……竟受意部将王以哲之军队,拆毁距离奉天不远南满铁路之柳条沟一段。于是友邦忍无可忍,慨然兴吊民伐罪之师。纪元前一年九月十八日,友邦仗义兴师,先击退北大营匪军,夜间遂占领奉天。”还有《初级中学校国文教科书(第四册)我国建国》、《国民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五卷)建国》、《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一卷)建国》、同册教科书中《从新京到奉天》等多处;而同册教科书中《日本语》是篇自供式的文字,通过宣扬皇道、欺世盗名、篡改历史、透露反抗、反苏反共、哄骗国民、直书侵略、推介日语等多方面内容将日本军国主义面目与内心全面地展示了出来。可以说,在奴化教育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愚”与“骗”。
愚骗的教育与舆论宣传又常常结为一体,它既倚重学校教育又倚重社会教育,在宣传上具有大众化、普及化的特点,形式多样同时也是无孔不入的。
(三)封闭手段
1.禁锢思想,禁止民众睁眼看世界。除了建立由日本人掌控实权的从总长到学校自上而下的教育组织体系之外,1932年10月,日伪颁布实施《出版法》。该法规定了报刊出版前的送审制,并规定对于违反者给予罚款甚至判刑。对于具有民族意识、反满排日意识的书刊则一律查禁。据有稽可查的资料,仅1932年3月至7月,满洲国在东北焚书达650余万册[14]。“教育方针制度,须恪守部省规定办理,不得自为风气。”[6]294编审“国定教材”,若发现有不使用伪满洲国统编教科书者“撤惩不贷”。
2.封锁消息,统一媒体口径,制造“铁屋子”社会。在封闭的满洲国里,民众和学生常误以为“风景这边独好”。“我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之前,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不了解……所以,毕业出来的学生对自己的祖国真是陌生得很,这种情况颇似在英国长期统治下的香港人。”[15]78-79“由于奴化教育的封锁、愚弄和欺骗,我对中国基本上一无所知。”[15]120“不让学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关于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鬼子在东北杀死无数中国人的事情,学校封锁消息很严,根本不让学生知道。”[15]33到日本投降前,全奉天只存一家报纸《康德新闻》(日本人办)
至此,通过上面的陈述、分析和概括,我们可以对“奴化教育”进行新的本质上的界定:所谓“奴化教育”就是执政集团将其特有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志,以恐怖、愚骗和封闭三大手段,从建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价值认同入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强行泯灭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使治下全体民众驯服地接受被奴役的现实进而实现民众精神重构的教育行为。凡是符合上述界定的教育无论发生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均可视为“奴化教育”。
实际上,恐怖与愚骗、愚骗与封闭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恐怖与愚骗是对反抗的弹压,愚骗与封闭是对真相的掩盖。中外历史事实多次证明,恐怖、愚骗与封闭手段下的奴化教育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实施者的自掘坟墓——“恐怖”“愚骗”与“封闭”的破产,不断发展的社会必然以不断的思想解放而呈现出“觉醒”“反抗”与“开放”的态势,因为“人实在是生来就是为了过自由生活的唯一动物”[16]。
[1]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7.
[2]威尔特·A·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陈鸿瑜,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1.
[3]高硕.王道主义为东亚和平之先[C]//国文选粹.奉天:幸福记书局,1942:79.
[4]伪民生部.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一卷[M].新京: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
[5]伪文教部.尊孔与学艺[C]//初级中学国史教科书.新京: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5:214-215.
[6]伪文教部.满洲国文教年鉴[M].1934.
[7]伪民生部.人类之发展[C]//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三卷.新京: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47.
[8]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C]//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62-263.
[9]蔡元培.教育独立议[C]//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77-179.
[10]李兴华.民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1.
[11]民国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总述[M].上海:开明书店,1934:1.
[12]伪民生部.忠君[C]//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第二卷.新京: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120.
[13]辽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辽宁教育史资料:第三辑[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857-863.
[14]常成.东北现代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215.[15]齐红深.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16]拉·波埃西.论自愿为奴[M].潘培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9.
【责任编辑 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