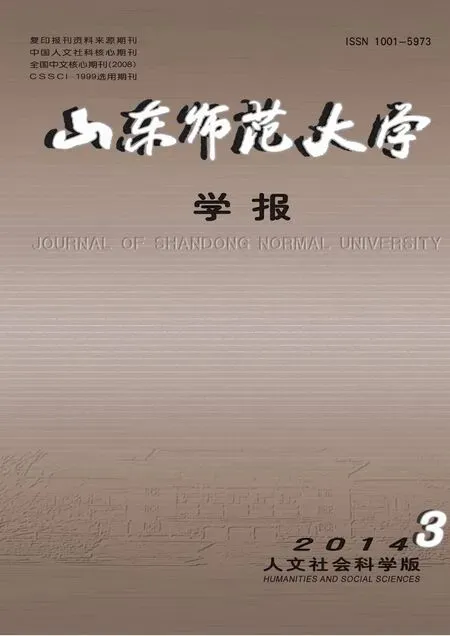《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①
张学军
(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①
张学军
(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莫言;叙事动力;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天堂蒜薹之歌》
一
1987年《大众日报》上一篇关于苍山县蒜薹事件的报道,触发了莫言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在北太平庄一个部队的招待所,用了33天的时间写出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发表于《十月》1988年第1期,1988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那么,是什么动力驱动着莫言这么高效率地投入创作呢?
莫言说:“现在我写作的重要动力是我确实感到有许多话想说……于是我想用小说这种方式,把自己对生活对当前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感受表达出来。”②莫言:《上海大学演讲》,《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有话要说是一种骨鲠在喉、蓄势待发、不吐不快的精神状态,一旦受到灵感的激发,就会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在尚未遇到发作时机的情况下,也可以长时间地隐忍不发、酝酿蓄积、耐心等待。因为作家创作活动的起因源自于自身积累起来的对人生的感悟,它久久郁积在作家心中,这是一种深沉的、郁结的、必欲吐之而后快的感悟。
莫言多次说过写这部小说时的情况,当时农村一些落后势力猖厥,一些基层干部腐败,农民群众的艰辛劳苦;几年前自己的四叔赶着牛车卖甜菜的途中被公社书记的汽车撞死的惨象,堂弟去公社讨说法时把四叔的尸首弃之不顾看电视的行为,撞死人、牛后只获赔偿三千余元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一起浮现在莫言的脑海。“我总感觉心里面压着很大的一股气,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就把生活当中自己积累了很久很久、很沉痛的一些感情写到小说里去。”③莫言:《我为什么写作》,《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这种深厚的情感力量就是莫言小说叙事的驱动力。莫言多次申明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他感同身受着农民的劳苦艰辛,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说:“我写《天堂蒜薹事件》,实际上是把我积压多年的、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④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对于农村的现实、农民的命运,他有话要说。这种有话要说的状态,就是郁积在胸中的不平之气,也就是我国古典文论中的“块垒”的概念。*“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3页。“愤怒的蒜薹”是莫言的发愤之作,这种浓郁的情感直接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为作品增加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以偶然被裹挟进蒜薹事件的高马、高羊和方四婶的经历为情节发展的线索,揭示出他们卷入事件的原因。复员军人高马与方金菊的恋情遭到方家的反对。方家为了给年过40、腿有残疾的大儿子方一君娶亲,与刘、曹两家签了换亲协议,年方20的方金菊将要嫁给45岁并患有气管炎的刘胜利。高马以婚姻法为武器去方家讲理,被痛打一顿。高马去乡里告状,又被助理员杨民政打了出去,因为杨助理员是换亲者的亲戚。后来,高马和金菊私奔被捉回,遭到方四叔的毒打,怀孕的金菊被逼无奈,上吊自尽。种种经历使高马对现实中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在蒜薹事件中,他自觉地参与其中,并高呼口号,推波助澜。被捕以后他以“我恨你们,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作答,拒绝了为他辩护的安排。在服刑期间,听到方家兄弟出卖金菊的尸骨与曹家结阴亲的消息以后,彻底绝望了,在试图越狱时被击毙。
方四叔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途中,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得车毁人亡。方四叔死后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反而遭到官府的打压。方四婶被压抑的满腔怒火爆发,放火烧了县长的办公室,并喃喃自语:“老头子,俺给你报仇了!”可见,方四婶卷入事件之中,是由于方四叔被轧死后未能得到公正的处理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的发泄。在牢房有病未得到适当医治,保外就医回家后,因两个儿子卖金菊的尸体给曹家结阴亲,方四婶愤而上吊自尽。
高羊心地善良,胆小怕事,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高羊”者,羔羊也。他赶着毛驴车去县城卖蒜薹,沿途被强行收缴了各种税费和罚款,好不容易走到蒜薹收购点,却又听到冷库已满、停止收购的通知。高马需要交彩礼,方家要为大儿子娶亲,高羊的老婆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他们都需要靠卖蒜薹的钱来维持生计。县里停止收购,又不许外地的人来收购,致使大量的蒜薹腐烂变质,等于断绝了农民群众的生路。农业税、提留费、城建税、市场管理税、计量器检查费、交管、环保、卫生等各种费用和罚款,在没有卖蒜薹之前就强行征收,没有钱就用蒜薹来抵押,致使怨声载道,民怨沸腾。怨气冲天的农民群众去县政府请愿,县长却躲了起来,并派警察驱赶群众,终于激化了矛盾,酿成了天堂蒜薹事件。高羊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事件的,不像高马那样是有意识的主动参与,虽然在砸碎了窗玻璃和金鱼缸时也有一丝的快意涌向心头,但听到这是县长办公室时,不禁使他心惊肉跳,立刻停止了行动,拉着方四婶逃离了现场。
在法庭上,军校政治教员为父亲和乡亲们进行辩护,他说:“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一个党的负责干部,一个政府的官员,如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人民就有权力打倒他!”*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这慷慨激昂的辩护词是理性的,是在为农民伸张正义;也是义愤填膺的,抒发出农民也包括自己的不平之气。莫言说过:“这个军校政治教官,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的这些演说,就是我的心声。” “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己,使你无法克制自己,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猛烈的抨击。”*莫言:《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正是这种强烈的义愤之情,促使莫言写出了这部揭露社会现实弊端的作品。
这部小说的批判精神不仅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上,也体现在对复杂人性的审视上。作者既对农民群众的不幸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也对其精神弱点进行了有力地鞭笞。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死的方四叔,是一个无辜、善良的受害者,可是在对儿女的亲事上又是一个专横残暴的封建家长。他重男轻女,为了给大儿子换亲,不惜以女儿方金菊的青春为代价,粗暴地干涉女儿与高马的自由恋爱,逼着她嫁给一个陌生的、40多岁的男人。在金菊与高马私奔被捉后,毫不顾念父女亲情,把女儿吊起来进行毒打。当得知金菊怀孕后,竟说:“我成全你们!告诉高马,让他拿一万块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女儿当作可供交易的商品,毫无父女亲情可言,致使走投无路的金菊被逼上吊自尽。可以说,方四叔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害人者。被害者与害人者、善良与邪恶就是如此纠结在一起,人性的复杂性得以深刻的揭示,人物形象也显得立体而丰满。另外,方家兄弟在方四叔死后所表现出的冷漠、麻木,在分家时的贪婪、愚昧、自私,都令人不齿,充分暴露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这也体现出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
由此可见,莫言耿耿于怀的块垒中蕴含的情意内涵,是建立在关怀民众疾苦、关怀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基础上的。这种人文情怀既有仁民爱物的博爱胸襟,也有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还有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思考。因而这种人文情怀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和情感状态,同时也是高度理性化了的知、情、意的融合状态,是一种整体人格的体现。
二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为莫言赢得广泛赞誉的作品,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韩语、越南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希腊语等出版,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人们大都关注于莫言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判精神上,往往忽略了其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其实,这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上也是匠心独具、独树一帜的。小说的结构安排是从叙述者、官方和民间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
小说的正文是叙述者全知型的叙述。小说打乱了故事顺序,灵活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手法,分别叙述了高羊、高马和方四婶一家的故事。小说铺设了两条情节的发展线索:一条是高羊的经历,另一条是高马与金菊从恋情的萌发到爱情毁灭的悲剧。第一章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高马逃脱开始写起,露出了这两条线索的头绪。第二章的故事时间则回到了蒜薹事件的前一年,即高马与方金菊恋情的萌发时。第一、三、五、七、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等章节叙述了高羊在蒜薹事件前后的经历,是现在进行时的叙述,高羊被捕,押解到乡政府,乘囚车去县里、被关押在看守所,狱中生病,法庭受审等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叙述。在顺时叙述高羊的经历时,也穿插了高羊的回忆:少年时的苦难、母亲的去世、失明的女儿、分娩的妻子、刚出生的儿子等家庭情况。第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十七等章,主要讲述了高马和方金菊的恋情,是过去完成时的叙述,换亲、私奔逃婚、被捉遭打、金菊上吊、高马参与蒜薹事件等,都是倒叙。两条时间线索在第十三章重合在一起,被追捕的高马回到家看到上吊自尽的金菊后,满腔悲愤,委托邻居处理完后事,似乎了却了心愿,于是便束手就擒。经过短暂的重合后,第十四章又是倒叙,叙述了方四叔遇车祸而亡的经过。最终,两条时间线索在法庭审判时汇聚到一起。这两条时间线索齐头并进,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而方四婶的故事则在这两条叙事线索的相互交织和推进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出来。这两条线索虽然以高羊、高马为中心,实际上是讲述了三家的故事。这种分别叙述人物故事的方法,与古代章回小说中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非常接近。在叙述中,叙事现场的现在时和人物对过去经历回顾的过去时交叉出现,错落地呈现出人物命运遭际的变化。这种叙述角度的多重转换,在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和剪辑,显示出叙事的魅力。叙述者以自己的良知、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农民遭遇的同情,如实地说明了蒜薹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小说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二十一章,是《群众日报》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交代了对蒜薹事件的处理结果、由此事件引发的思考,包括应当吸取的教训。这一章既批评了天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漠视群众利益的失职行为,最终导致的蒜薹事件发生的错误,又批判了砸、抢、火烧县政府大楼的不法行径,指出了不能用无政府主义反官僚主义,对少数不法分子惩处的必要性,从官方的立场和角度对天堂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
在小说的每一章前面,有天堂县民间艺人盲人张扣演唱的歌谣片断。张扣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他的这些歌谣呈现出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官逼民反的过程。张扣的唱词对官僚不顾群众的利益致使蒜薹大量腐烂的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义正词严,悲愤满腔,酣畅淋漓。作者在第二十章写了张扣因唱《天堂蒜薹之歌》遭到威胁被害致死的结局,这是民间的角度和立场。
从这三个角度、三种立场所作的叙述,都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张扣的唱词是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草根”话语;叙述者是精英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他们以各自的立场和各自话语的叙述,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合唱。是非曲直,有待读者评说。
同时,这三种叙述话语也形成了三个文本。这些报纸上的通讯、述评和社论以及张扣的唱词,与小说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多重文本。暗合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跨文体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镶嵌进其他文体类型,如张扣的唱词属于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也是一种口头传唱的文学语体。第二十一章《群众日报》中的文章都不是文学文体,其中的新闻报道属于新闻文体,述评和社论属于政论文体,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具有各自文体的特点。而小说的正文则属于传统的小说叙述文体。这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这些不同的文体形式,虽然处于同一小说母体之中,但依然保持了各自的独立个性,具有各自文体的话语风格,同时,又没有影响小说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通过这种不同文体的穿插、组合,突破了小说传统文体的规范,使读者在多种文体的相互参照中,感受到这种全新的文体形式带来的一种陌生和新鲜的审美体验。
小说中的这些不同的文体所形成的文本,既有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有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如叙述者的叙述与报纸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后的叙述,是过去完成时;而张扣的唱词则是即时的、现在进行时。多重文本的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展示出互文性景观,也使蒜薹事件得以立体式的呈现。多重文本的结构方式,使传统小说的封闭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张扣的唱词和《群众日报》上的文章,既起到补充小说正文(叙述者的叙述)的作用,又可以独立存在。读者可以将每章之前张扣的唱词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阅读单位来阅读;也可以直接阅读报纸上的文章,即第二十一章。对这两个文本的阅读,都能获得对事件经过的大体了解,并可以与小说的正文互相印证。这种开放的文本,能使阅读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小说就这样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立场,用三个文本将天堂蒜薹事件全面、立体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三个文本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呢?现代主义认为客观的叙事话语并不能将事件置于一个透明的空间中,这就为这一事件提供了多样性叙述的可能。莫言也没有打算再现“蒜薹事件”的过程、进而以揭示事件真相为旨归。小说的写作并不能完成对真相的揭示,但用巴特的话来说,它却创造了一种“现实效应”。这种“现实效应”也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逼真性。为了满足逼真性的要求,作者可以进行虚构。因为事件的再现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混合体。可以说,这三个文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各自视角,运用各自的话语方式的叙述,都丰富了读者对“蒜薹事件”的认识。
三
《天堂蒜薹之歌》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是很独特的一部作品。20多年前阅读时,笔者就感到像一篇报告文学。因为他揭示出天堂蒜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局,直接干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但是作品并没有以事件为中心,没有流于简单的政治说教,也没有对事件过程进行正面的描绘,仅在第十六章由高羊在受审时交代出事件发生时的场面,也就是说莫言并不以揭示“蒜薹事件”的真相为旨归,而是以理和情为中心,将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入发掘出高马、高羊、方四婶等的心理。几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鲜明,人物的遭遇和心理刻画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发展,揭示出他们走向蒜薹事件中心的心理基础。
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综合运用了联想、回忆、幻觉、梦魇等西方现代派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而丰富多姿。如方四叔遇车祸身亡后去乡里讨说法的情形,就是通过方四婶在牢里的回忆呈现出来的。第十章金菊与尚未出生的腹中婴儿的对话,第十二章高羊在梦中与母亲的相见与对话,第十三章高马与金菊尸体的对话,显然不是传统的叙事方式,而带有浓重的现代派色彩。还有第七章,高羊在监牢里被中年犯人强迫喝自己的尿,使他回忆起少年时喝自己尿的经历,到第十二章又联想到娘死后被关在大队部,治保主任强迫自己喝尿的遭遇。由喝尿而引发的两个生活片断的回忆和联想,就交代出他因出身地主而遭遇的种种苦难和屈辱,也勾勒出高羊几十年的生活道路的变化。第十五章方四婶在牢里梦中与方四叔会见,醒后回忆起方四叔死后两个儿子种种无耻、卑劣的表现,这些回忆、联想、梦魇等都是在正常叙事过程中的停顿,是在瞬间完成的,并未影响故事的行进。这些人物意识的流动,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也是虚写。但这种虚写却可以作为实写的补充,将正常的现实叙事中尚未写出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使得所叙述的故事更加完整和缜密。虚写与实写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整体。
瞎子张扣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他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同时,他又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被叙述者,高马与金菊恋情的萌发,就起始于观看张扣的演唱会。第十六章描写了张扣在广场上唱出了方四叔惨遭车祸的冤情,也为民怨鼎沸的群众指出了去找县长的出路。第二十章交代了张扣因言获罪而惨死的结局。这一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与贾平凹《废都》中捡破烂的老头有些相似。收破烂的老头唱的流行段子,显然也有着批判现实的意味。但是这一角色却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与小说的整体结构无大的关联。而张扣却是小说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其重要作用是《废都》中收破烂的老头不可比拟的。张扣的作用又与《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相仿佛,一僧一道是《红楼梦》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枢纽,每当宝玉陷入困境时,两人都会出现,在情节的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张扣却没有僧道二人的预知前生后世的能力,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明显。但他是蒜薹事件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当蒜农聚集在广场时,他唱出了“孩子哭了抱给亲娘,卖不了蒜薹去找县长”,成为蒜薹事件的鼓动者,自觉地为老百姓代言。他的歌谣中既有群众因种大蒜而致富的欣喜,也有对基层官员横征暴敛的愤恨,但更多的却是因政府的作为致使蒜薹滞销腐烂而激发的满腔义愤。
莫言并没有去实地采访,仅凭一篇报道就写出了这部成功的“愤怒”的作品。其原因在于莫言在写作过程中,调动了自己农村生活的全部经验,写的是天堂县,但作品中的场景却是高密东北乡,小说中的村庄、河流、道路等地理环境因素,都是自己熟悉的故乡;并把自己亲人的遭遇放到小说的人物身上,其境遇感同身受,充满了真情实感。这样,一部干预社会政治的作品,就成为一部充满了激情和正义、以鲜明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支撑起来的成功小说。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Garlic Ballads
Zhang Xuejun
(Liberal Arts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The spirit of caring for the hardships of the farmers and pleading for the people was the very impetus for Mo Yan to writeTheGarlicBallads, and this also led the work of his to be invested with a strong critical spirit. From the angles of the narrator, the essay carried in Daily Mass, and the words of the minstrel song of Zhang Kou, the blind man, the novel comprehensively recounted the Garlic Incident. The three angles represent the elite, the official and the folk position respectively, and constitute three narrative texts, which are of the novel narrative style, of the news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 style and of the folk art style of verse. And, from the various different styles grouped in a single narrative structure, comes into being a cross-genre novel. Mo Yan blends together Western modernistic techniques with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way of narration so as to make his narrative methods well-proportioned, and rich and colorful.
Mo Yan; narrative impetus;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style
2014-03-25
张学军(1954—),男,山东阳谷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莫言小说叙事研究”(13BZW154)的阶段性成果。
I247.5
A
1001-5973(2014)03-0020-06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