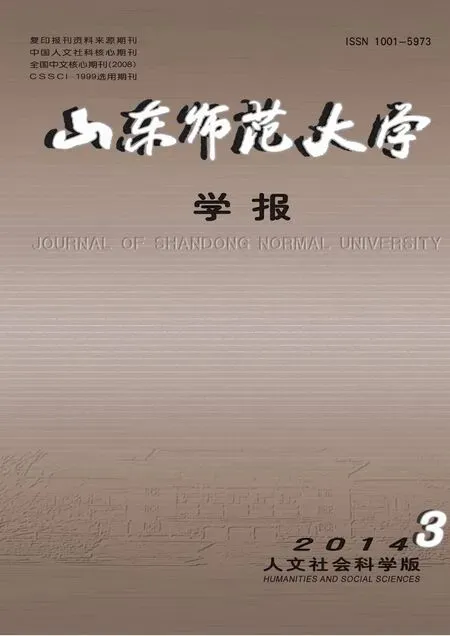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①
张玉来
(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210023 )
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①
张玉来
(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210023 )
中国语言学有3000多年的历史,富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然而,从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西方外来强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固有文化体系面临解体,学术研究深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中国传统学术从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究范式发生转型。与此相应,中国传统语言学也随之转型为现代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形式描写、结构分析、历史比较等方面突飞猛进,成果丰硕,终于跟上了世界学术研究的脚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传统;现代;语言学;转型;中国现代语言学
一、汉语的演进与中国语言学的传统
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文化悠久,语言学发源很早,研究成果丰硕,自身富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又勇于与世界学术潮流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范式。总结中国语言学的学术传统与近代背景下的学术转型进程,对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汉族、汉语及汉语共同语的形成
20世纪前,西方学者曾有人提出汉人(中国人)外来说(如出自埃及说、巴比伦说等),甚至有人举证《尚书》中的“百姓”即巴比伦语的“巴克”(Bak)的转音,黄帝是其部族酋长,凡此不一而足②李帆: 《人种与文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学说传入中国后的若干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近些年来,现代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证明,现代人类的祖先可能有共同的来源,汉民族是人类自然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霍正浩:《MtDNA与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生物学通报》2002年第8期。旧石器文化遍布我国各地,从人类遗骨特征考证,他们与现代蒙古人种相似,只是有北方型(山顶洞人为代表)和南方型(柳江人为代表)的区别。这说明,至迟在两万年前,中国大陆就有现代人类居住。后来的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分布更广,从北边的红山文化,中间的河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更能看出中华文化的融合及其传承关系。
上述事实说明,汉民族是在早期人类群体基础上产生、发展而终至形成的人类民族之一,其称夏、诸夏、华、华夏、汉等是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民族称谓。徐杰舜(1992)论述汉民族的形成过程时,勾稽史料颇丰,其结论是汉民族形成有主流与支源之分。主流:炎黄、东夷部族。支源:苗蛮、百越、戎狄等部族。④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5-67页。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呈现一体多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经历过无数的融合,但始终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它的文化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页。费孝通还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论述汉民族之凝聚及扩张尤为详明:“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故在春秋初期,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东两全省(其中仍有异族)及山西、陕西、湖北、直隶之各一小部分;及其末期,除此六省已完全归属外,益以江苏、安徽二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及战国末年,则除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外,中国本部皆为诸夏势力范围矣。”汉民族就是这样挟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礼仪优势,不断同化进入中原地区的异族,并不断扩张文化的影响范围,终至形成了文化一体的汉民族。*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演讲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135页。
汉语及其方言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产生形成的过程自然也相当悠远,但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可能是相当晚的事情。虽然,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先后相承,文化相因,但并无共同语的记录。在春秋之前的各代,共同语是否存在,当然可以探讨。从商周文字的一致性来看,也许确有共同语的存在*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5本。。到了春秋时期,才有共同语的早期形式——雅言的记载。《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2页。清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损益之,以为宪法,所谓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异,或意同而声异。综合谣俗,释以雅言,比物连类,使相附近,故曰《尔雅》。《诗》之有风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正于王朝,达于诸侯之国,是为雅言。雅之为言夏也。孙卿《荣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然则雅、夏古字通。”*[清]刘台拱:《论语骈枝》,《皇清经解》本,第107卷。按刘台拱的解释,雅言即正言,似乎还有夏言的意思,夏又有大的意思,那么这种雅言显然是通行范围很广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共同语。孔子鲁人,当讲鲁语(话),谓孔子雅言,当非鲁语无疑。孔子周游列国,多在诸夏范围,翻译之事未尝闻。孔子删诗订诗,人皆共知。《诗经》用韵系统内部一致性很强,今人多认为是丰、镐、汴、洛之间的中原共同语。孔子以鲁人身份而说中原雅言,显见此系统影响和覆盖的范围很广。汉民族在夏商周时期长期以黄河中下游的丰、镐、汴、洛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华夏核心即成长于此,雅言也当以中原某一方言为基础扩展而成。周生亚(1980)称其为洛邑方言*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李维琦(1980)称之为“镐京话”*李维琦:《关于“雅音”》,《中国语文》1980年第6期。。无论有无具体方言点,中原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元核心无疑。雅言以中原方言为核心逐渐扩大影响范围,至迟到春秋时代,雅言已延伸到燕、齐、秦、楚、吴越诸地区。
秦汉之后,中国分合不定,大致合占2/3,分占1/3,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交融,其结果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政治、文化上,汉文化都取得了优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不断扩张,以其人口和文化的优势而北上南下。因时代与区域的不同,汉语保持着众多的方言,并大致维护着雅言延续下的共同语形式,并对各方言施加影响。汉魏有“通语”,唐宋有“正音”,明清有“官话”,现代有“国语”、“普通话”,这些无疑都是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式称谓。*张玉来:《汉民族共同语形成问题》,《汉语音韵学第六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0-312页。
汉语共同语的形成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汉民族文化统一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汉语相适应的汉字,从甲骨文产生以来,就一直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是汉语书面语表达的主要手段,汉字研究也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传统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语言学发源甚早,早在先秦时代(~前221)就已发轫。先秦时代关于名实关系的讨论,就关涉到了语言的词与概念的关系。《墨子·经说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尹文子·大道上》:“名者,名实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些著名的论说,是语言学史上关于概念与词的经典论述。其他如《尸子·广泽》:“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这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先导。初创于战国时代的《尔雅》则是最早的分类语义辞典,收词多达4300余条,该书就有这样的释义:“适、之、嫁、徂、逝,往也。”(《尔雅·释诂》)。
两汉时期(前202~220),中国语言学已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扬雄的《方言》、刘熙的《释名》、许慎的《说文解字》和汉初最终修成的《尔雅》四大语言学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方言学、语源学、文字学、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注释学)的形成。东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则标志着汉语音韵学的诞生。汉代整理的大量先秦典籍,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文献根基,还开创了典籍整理的多种注释体式,影响了后来文献注释的发展路向,毛亨、刘向、郑玄等人的业绩垂传千古。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音学兴起。学者们发现了汉语存在四声,并自觉应用于文学创作;对双声迭韵的认知,促进了人们对汉语音节结构的认识;在四声和双声迭韵的认知基础上,陆续有学者编制带有小韵(音节)的韵书,如李登的《声类》、沈约的《四声谱》、吕静的《韵集》、杨休之的《韵略》等等。这些韵书直接孕育了陆法言编制的《切韵》。这个时代,还问世了很多辞书,如《广雅》、《字林》、《玉篇》等,较汉代的著作有了较大进步。
隋唐时代(581~959),汉语音韵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陆法言《切韵》的问世和流传,奠定了汉字中古音类系统的格局,成了后来韵书的典范,一直到宋代的《广韵》、《集韵》等还脱离不了它奠定的音系框架。在佛教影响下,产生了汉字式的字母系统,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汉语语音分析范畴,如清浊、韵、等、五音、内外之类,开等韵学之先河。隋唐时期的文字学在正字法、《说文》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说文解字系传》等一批著作问世。隋唐时期的训诂学成就突出,除了官修的《五经正义》,许多重要典籍,甚至佛教经典都有学者注解,如玄应的《一切经音义》等。陆德明编纂的《经典释文》是本时期训诂、文字、音韵研究三位一体的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960~1279)语言学深受理学影响,研究风格与前代有所不同,像王安石的《字说》(佚)则独出胸臆,强为立解。郑樵则宏通大气,多有创获。宋代产生了独立的金石学,赵明诚的《金石录》为传世之作,是古文字学的典范。其他如《汗简》、《古文四声谱》也是古文字学的发轫之作。张有的《复古编》则是正字学的名作。宋代开创了古音学研究,吴棫、郑庠是汉语古音学研究的先驱。唐代发轫的等韵学在宋代生根发芽,《韵镜》、《七音略》都是宋人定型的传世名著,《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则突破旧韵书的藩篱,向现实语音迈进。宋代在训诂和辞书编纂方面也有收获,有《龙龛手鉴》、《类篇》、《埤雅》等名著问世。
与宋代大致平行的辽金元三朝(907~1638)的语言学研究总体上成就不大,但也产生了著名的北音韵书《中原音韵》。这是一部记录14世纪汉语口语的语音著作。元代还产生了一部研究虚词的著作——《语助》,这是中国语法研究的先驱。
明代(1638~1644)学术昌明,语言学在许多方面都有进步,尤其是在古音学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是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古音研究的著作。在语音学研究方面,成绩尤其突出,甚至超过了唐宋时代的等韵学,如袁子让、叶秉敬、葛中选等都深明音理,他们昌明的四呼学说深入人心。各种杂论语音的著作不胜枚举。明末的语言学还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像方以智的《通雅》已经有了初步的历史语言学的科学思想,甚至作了汉语史分期的初步尝试。
时至清代(1616~1911),尤其是乾嘉学派的出现,中国传统语言学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诸多领域都超迈了前人,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名烁古今。
清末民初章黄学派崛起,揭橥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开始向现代语言学转型的萌动。章黄及其门人,在清人的基础上,有了独立的学科观念。在语言研究上,初步具备了语言系统性的思考,并开始注意学理的归纳。
综观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语言研究史,自汉代产生的文字学、训诂学、方言学及稍后产生的音韵学,构成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框架,后来的语言研究无不在汉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语言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大量的学术经典,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
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前言》里曾经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有过精辟的评价。他说:“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他又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文学;甚至在研究方言俚语的时候也带有语文学的性质,因为作者们往往考证这些方言俚语用字的来源。语文学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共历二千年,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这方面的学者。”*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王力先生把中国古代语言学定性为基本就是语文学,这是符合中国语言学实际的论断。虽然,历史上不乏熠熠生辉的名作巨制,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的语言学学科。总结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的传统和得失,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过去、把握当前和展望未来。
1.通经致用的传统
中国古代语言学长期是经学的基础学科,它的研究目的是为解读经典服务的。训诂学(词汇语义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训释经典,文字学、音韵学也主要为阅读经典服务。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答李子德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页。戴震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清]戴震:《戴震全书》第六册之《戴东原先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8页。
中国语言学通经致用的传统在学术上的表现有三:一是古代词汇语义学发达,训释字词的工具书繁多;二是以正音、正字为目的的音韵学、文字学论著繁多;三是语言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往往就是经典本身。经学是中国古代的显学,不仅是语言学,其他学科莫不受经学的支配。经学既是统治阶级提倡的意识形态,也是士人干禄的途径。语言学为经学服务也就不足怪了。
2.经验先于理论的传统
中国古代语言学着力于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很少提炼出精辟的具有概括意义的语言研究理论,缺乏理性的逻辑概括。先秦时代关于名实关系的讨论,秦以后就成绝响了。学者们可以对语言事实本身孜孜矻矻,但对归纳规律的认识,却没有多少成绩。历史上虽不乏像陈第提出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历史语言学思想,但都属吉光片羽,不成系统。陈第的《毛诗古音考》称不上真正的历史语言学著作。顾炎武对上古音用力极勤,但其《音学五书》里的《音论》还不是关于音变的理论著作。
许嘉璐曾说:“到了乾嘉,由于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分工,更由于对哲学的偏见,竟视小学与哲学为对立物。”“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与语言学的人很少。”*许嘉璐:《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这一评价是恰当的。
3.综合先于分析的传统
中国古代语言学往往是整体的研究先于切分性的研究。古代的学者一般首先是经学家,为了研究经学或其他的学问,才涉足语言学。这就注定了古代大部分语言学家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对语言的深入、系统的切分研究。也由于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语言本体,所以,古人常常把语言作为整体来观察,解剖细节的工作就做得不够。王念孙有言:“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清]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页。这本是很好的研究思路,但他的《广雅疏证》里并没有梳理出系统的词义构成、演变模式。
4.意义先于形式的传统
中国古代语言学很注重语义的研究,偶尔出现的语言形式描写也总是围绕意义展开。从汉代四部名作开始,语义研究始终是古代语言学的优先选项。解读经典,意义当然为先。语法学没有形成气候的原因,固然跟汉语的语法特点有关,但是轻视语言形式的描写,应该是主要原因。
5.书面语先于口语(方言)的传统
在古代中原汉语基础上形成的汉语共同语,在前秦时代,口语与书面语是一致的,先秦文献的口语色彩十分明显。然而,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方言分歧越来越大,统一的口语体系难以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一统的局势形成,导致汉以后书面语独大。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占据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俗语、方言、口头文化始终没有登上大雅之堂。当年,公孙弘跟汉武帝说:“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504页。这种“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的书面语就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历史上偶尔会出现研究俗语、方言、口语的论著,比如,《通俗编》、《中原音韵》等,但始终不是古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流。
中国古代语言学重视书面语而轻视口语的倾向除了深刻的社会原因之外,跟汉字的特殊性也不无关系。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词(语素),通过字形可以得知词义。语音、语义是隐藏在字形之后的,形音义都是围绕文字说的,分析汉字就等于分析了词的形音义。汉字研究强化了人们重视书面语的意识。文字学(汉字学)在中国语言学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古代几乎可代指语言研究的所有方面,直到民国早期,北京大学语言学方面的讲义还称为《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这足见文字在历史上所占据的文化地位有多高。
6.坚持本位文化与接受外来影响相结合的传统
中国古代语言学始终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历史上,汉代开始流入的梵文文化影响中国千余年;明代传入的西方宗教文化,也有上百年的影响。然而,在梵文影响下,无论汉代创制的反切注音法还是唐宋时代创制的等韵图,都没有将语音切分到音素的层级。明末西方传入的切音拼字,并没有促生汉语的拼音文字。古代的学者始终坚持着汉字的文化本位,始终没有接受拼音文字的研究范式。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极端的文字体系,放弃汉字无疑等于放弃了一种文化体系。所以,汉字的拼音化始终没有取得成功。
历史地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传统,实事求是地估量古人留下的遗产,继承优良的传统,摒弃存在的不足,我们才能更好地再出发。与上述学术传统杂糅一起的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决定了古代学者存有厚古薄今的倾向。经典存在于前人的著作里,醉心解读前代经典的学者自然就容易忽视现实语言问题的研究。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描写性的语言学著作,但至少可以说,对现实语言的描写和解构不是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的主流。这可以以章太炎为例。综观以创建语言文字学为职志的章太炎的论著,无论是《文始》还是《新方言》,仍在文献考据里兜圈子;虽不无现代语言材料的引证,但其目的仍然是考据语源。他始终没有接受外来标音的音标工具。
二是混乱的学术体系和散乱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语言学没有形成系统、明晰的研究规范,没有系统的可以操作的研究方法,学术术语体系混杂不一,这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和知识的传播。古代语言学家基本是“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规范学术范畴。同一个术语,甲和乙对其含义的理解可能相反,也可能风马牛不相及。
三是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中国古代语言学常常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对语言现象常常缺乏历史变化的观念,某些学者的学术观念里存在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弊端。唯心主义倾向最明显的莫过于唐宋以来的叶音说,这种学说背离了前代学者已经建立的音变思想。宋代学者倡导的形而上的理学,把术数理论推及语言,产生了像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这类的含有许多虚位的音系。这一流风影响了明代的许多学者,如袁子让、葛中选等人。
四是有时地观念模糊的倾向。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一部主要讲述文言虚词的著作,然而他的取材却漫无涯际:“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清]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4页。直到马建忠写作《马氏文通》的时候,他仍然“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清]马建忠:《马氏文通·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这样混杂不清的语料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质量。
我们指出的上述几点不足,主要是与西方(包含印度)语言研究传统相比较而言的,其中也存在着时空不同的问题,意在说明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自身的不足,并非要责求古人。
二、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
古代中国长期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朝贡关系为核心维系着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中国虽然自身经历过大小不等的社会动乱和国祚长短不同的朝代更替,但是一直维持着固有的以儒、道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疆域的独立主权。
古代中国虽然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撞击,但都没有改变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和本位文化的传承。
第一次是自汉末天竺佛教的传入,到唐代佛教完成了本土化,佛教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跟佛教一起传来的梵文体系孕育并催生了分析汉语语音的反切注音法、韵书、等韵学等,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影响了汉语的研究。然而,这次外来文化的冲击,除了等韵学之外,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固有的语言研究范式。
第二次是明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宗教意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切入中国实际,结合中国传统,实行汉化传教的新方式,自觉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以儒家经典阐述教义,使个别中国人皈依耶稣教。耶稣会传教士还翻译、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解剖学等西方体系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传授火器、自鸣钟等机械制造技术,促进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可是,当时西学的传播影响力极为有限,接受并理解的只不过是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少数上层士大夫,并没有广泛地深入社会大众。随着清政权的建立,西来的宗教文化式微下来。这次传教士带给我们的在语言学上的成果主要是对拼音文字体式的体认。利玛窦和金尼阁设计的汉语拼音字母,集中体现在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有所谓自鸣字母、同鸣字母,等等。中国学者方以智、刘献廷、杨选杞等都深受影响。然而,中国学者最终没有设计出汉语的拼音文字体系,汉字还是维系着自己的体式。中国语言学没有发生向西方看齐的历史转型。
由上不难看出,中国语言学本位传统的根基是牢固的,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研究范式。问题是,这样牢固的学术道统,何以在近代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历史转型呢?这是历史境遇不同所造成的。历史上的外来文化没有冲垮中国固有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当时是先进文化之一,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时候,是主动的、有选择的,采用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处于主动地位。然而,近代以来的历史转型却是在国力衰败,外来文化强势冲击下被动接受的,文化与学术衰落致使整个民族别无选择,只能在无奈的历史心气下转型。
(一)近代中国与学术转型
中国历史迈入17世纪的时候,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风起云涌。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敲开了非洲、亚洲、美洲等一个又一个国家或部落的大门。而这时,中国在动荡中迎来了清朝的建立。清朝统治上层在汉化的过程中,文化上更倾保守,少有创新,并推行文化高压政策,致使学者对宋明以来的理学兴趣不大,整体向汉代的考据学转向,产生了所谓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以汉学为标的,有宋以来的心学为之衰败,明末传来的西学也没有人再公开传播,学术创新能力江河日下。随着清朝贵族政治上的最终腐朽没落,到19世纪中叶,中国终难抵抗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英帝国主义为了轰开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的门户,把大量鸦片输入中国。1840年终于爆发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从此成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逐渐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和政治的独立,国力衰落。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凸显出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险境。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部分民族精英逐渐觉醒,先后有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1851~1864)、李鸿章等倡导的洋务运动(1861~1894)和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变法”(1898)。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1911)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在跌跌撞撞之中,中国最终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维系了国运的延续。20世纪中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37~1945)胜利,中国终于又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综观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近百年的历史,是一段固有文化传统破碎,被迫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而发生历史转型的时期。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标志着中国本位文化向外来文化的全面开放。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清]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7页。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一历史积累下的能量的总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重大历史性标志事件,从此,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向现代社会转型。“五四运动”所标举的民主、科学思想深深地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屈辱,民族精英对自身历史作出各种不同的理性反思,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和学术传统产生了空前的怀疑。在自我矛盾和斗争中,先行者们深深接受了西学的精华,逐渐建立起了新的现代学术范型,并努力重建民族文化的核心体系。
西学凭借什么优势能够打破中国2000多年的本位文化和学术传统,并能刺激中国的精英向其学习?两者之间的文化和学术道统的区别在哪里?西方文化和学术研究以实学和哲学为其特点,尤其是16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重视个性发挥,强调人文精神。西人长于分析,重视形式逻辑,善于切入细节,并能总结出理性的认识。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2~1727)等科学巨人奠定了西方社会的科学意识。然而,中国的传统学术是“通人之学”,少有专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视科学(技术)为小技,不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西人在西学的哺育下,富国强兵,强烈刺激了中国的民族知识精英。
在与西学的碰撞过程中,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全面地对中国文化和学术道统的反思。在反思中,中国学术完成了现代性转型。陈平原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也有人说近代学术转型有四个特征: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朱汉国:《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语言学的演进过程,也讨论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传统和不足。按照中国语言学自身的演变规律,在明末就很可能发生研究范式的转型。陈第、方以智等已表现出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不同风格。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延续下来,只有到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某些学者那里,才接续了明末的学术探索的精神。
王力指出:“清人在‘小学’的领域上,开中国语言学的新纪元,可以说是从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学研究,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清人的朴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江(指江永)戴(指戴震)等人经过近代科学的天文历算的训练,逐渐养成了缜密的思维和丝毫不苟的精神,无形中也养成了一套科学方法。拿这些应用在经学和‘小学’上,自然跟从前的经生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戴震是江永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是戴震的弟子,学风从此传播开来,才形成了乾嘉学派”。*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在这里,王力对清代语言学成就的评价,与我们前引他的另一段话相比,明显地拔高了清代语言学的学术水平。固然,清代江永辈对语言学有进一步的促进,但很难说他们“养成了一套科学方法”。他们离科学的方法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事实上,无论是乾嘉学派还是章黄学派,都没有真正进入现代语言学的范围,他们仅仅走到了现代语言学的门口,还没有登堂入室。中国语言学真正的学术转型,是在全面接受西方语言学思想、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历史洪流中才真正完成的。这一转型的标志是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的问世。何九盈说:“跟西方现代语言学相比,我们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泰西的‘葛郎玛’,历史比较法,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页。只有到了马建忠,中国学术界才真真正正地知道了汉语也有“葛郎玛”。马建忠之后,语言学的许多方面都蓬勃发展起来了,虽然不乏机械模仿甚至抄袭之作,但是,研究范式已经与传统语言学大相径庭。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3)、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1918)、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研究》(1929)、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1934)、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等著作相继问世,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国语言学就转型成功。
从19世纪末,中国语言学开始学术转型,到20世纪中期基本转型成功。时至今日,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仍然在探索着自己的发展路向,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语言学学术研究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短的路要追赶。
(二)近代学术转型期的中国语言学建立
中国语言学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何九盈提出了三个标志:科学化、社会化、理论化。*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页。这三点与上举陈平原、朱汉国所提出的近代学术转型的标志是一致的。如果把何先生的三点标志具体化的话,以下几点是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区别界限:(1)从经学的附庸变成独立的学科;(2)研究对象由书面语到口语、由文言到白话;(3)从零碎考据到系统研究;(4)从静态研究到历史研究;(4)从缺乏理性概括到自觉的抽绎语言结构和变化规律;(5)由少数人的学术兴趣变为职业性的专家研究;(6)由固守研究传统到接受外来的理论和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来叙述一下中国语言学转型的过程。
1.语文运动与现代国语的确立
近代中国社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大语文运动:拼音化运动(含简化汉字)、白话文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三大语文运动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发展教育、开发民智。
近代中国的先觉者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和破败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缘于语言的不统一、文言文的束缚和汉字的繁难。要普及教育,开发民智,富国强兵,就必须从统一语言、倡导白话、推行拼音文字开始。吴汝纶(1840~1903)等前辈发出了发聋振聩的呼声。王照在《挽吴汝纶文》中说:“盖先生(按,即吴汝纶)心地纯挚,目睹日本得力之端,在人人用其假名之国语,而顿悟各国莫不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至要之原。”*王照:《挽吴汝纶》,《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31页。经过无数学人的努力,三大语文运动,尤其是国语统一与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语意识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有了基本一致的共同语言;白话彻底击败了文言,成为书面语的主流,文言退居到角落,仅供个别人和个别场合使用。拼音化运动的成就虽然不如前两者,但无论是注音字母还是拉丁字母,都已经不是汉字式反切了,而是朝向音素化、符号化迈进了一大步,在注音识字方面大大便利了人民大众。
何九盈说:“三大语文运动的产生不仅在客观上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页。三大语文运动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文字的观察和认识,打破了传统的语文观念,促进了语言教育的普及。
2.中国语言学的独立——语言学/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学长期没有独立的学科位置,很难形成学科体系。承续乾嘉学风的章黄学人最早体认到了学科独立的重要性。章太炎(1906)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指出:“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讲国学》,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22页。章太炎第一次明确了语言文字学的学科“非专以通经而已”。
语言文字学挣脱经学的藩篱,独立为一个学科,是中国语言学转型时代的最强音。现在,无论称呼现代语言学为“语言学”还是“语言文字学”,都远非传统“小学”所能概括的了。两者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都已经发生了质的不同。
3.近代中国语言学各部门的形成
(1)普通语言学与国语语言学。中国古代语言学缺乏理论概括,没有多少理论著作问世。近代语言学理论是从介绍西方和日本的语言学理论著作开始的。这时期翻译的著作主要有日本安藤正次的《言语学大纲》(雷通群译,1931)、英国福尔的《语言学通论》(张世禄、蓝文海译,1937)等。也有杂取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形成自己著作的,如乐嗣炳的《语言学大意》(1923)、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1930)、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等。这些著作大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但在传播语言学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世禄在1934年出版他编著的《语言学概论》时说: “我们中国,科学向来不很发达,过去对于语言虽然有许多的著述,终究未曾组织成为一种科学,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国语和各种方言,自然必须有西洋语言学学理做个基础,我们要考明中国语的性质和历史,也必须先具有世界语言学的智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人的真实心理写照。
与此同时,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的著作频出。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3)导夫先路,嗣后有黎锦熙《国语学讲义》(1919)、乐嗣炳《国语概论》(1923)、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1923)、马国英《新国语概论》(1928),乐嗣炳《国语学大纲》(1935)等著作问世。
胡以鲁曾留学日本,他系统学习了浦氏(葆朴)、麦斯牟勒(缪勒)、亨抱而的(洪保特)、耶斯彼善(叶斯泊森)等人的著作,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汉语,多有创获,是现代汉语研究的先驱。这部著作讨论的问题有:说国语缘起、国语缘起心理观、说国语后天发展、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国语成立之法则、国语在语言学之位置、论方言及方音、论标准语及标准音、论国语国文之关系、论译名。从这些论题看,胡氏的目的是建立汉语的语言学。
(2)语音学。国语统一运动中,国语语音系统的描写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重视,以讲解注音字母的读音为主线,产生了一批用语音学原理讲述国音的语音学著作。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易作霖的《国音学讲义》(1920)与《国音读本》(1920)、廖立勋的《实用国音学》(1920)、朱荩忱的《国语发音学概论》(1922)、高元的《国音学》(1922)、汪怡的《新著国语发音学》(1924)、方毅的《国音沿革》(1924年)等。高元的《国音学》讨论的论题有:绪论;声;韵;五声;国音之特性。这些著作奠定了国语语音描写的基础。
介绍西方普通语音学方面的著作有张世禄的《语音学概要》(1934)和《语音学纲要》(1935)、岑麟祥的《语音学概论》(1939)等。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实验语音学也有很大的进步,有赵元任的《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法》(1922)、刘复的《四声实验录》(1924)、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白涤洲的《关中声调实验录》(1934)等。
赵元任发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以汉语的事实为依据,讨论了音位归纳的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成为语言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现代语音学的发展,挣脱了传统等韵学似是而非的范畴。向声学、生理学、社会学讨要学理的语音学在中国生根发芽。
(3)方言学。中国古代语言学很早就有《方言》一书问世。然而,历史上的方言研究,以考订文献里的方言词语为主要目标,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近代方言研究的手段和目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描写成为方言研究的主要手段,分析方言的语言结构(语音、词汇、语法等)、研究方言的变化、辨正方音或用来作语言历史比较的材料,成为方言研究的主要目的。
从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到高本汉1916~1926年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从1928年赵元任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到后来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与《临川音系》(1941)、陶懊民的《闽音研究》(1936)、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等论著,无不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
(4)音韵学。传统音韵学到清代乾嘉诸前辈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传统语文的材料使用和归纳达到了极致。晚清冒起的章太炎、黄侃承其余绪,虽有所创新,然毕竟已呈强弩之末,终难有大的突破。近代转型时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汉语的历史音韵研究。这个时期的标志性论著是1809年马士曼发表的《论汉语的文字和声音》,文章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的字音。艾约瑟1853年出版的《中国上海土话的文法》、1857年出版的《中国官话文法》中也关注历史音读问题;武尔披齐利1896年写成的《中国音韵学》开始构拟中古的韵值。但是,这一时段的研究虽然运用西洋学理,但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很难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此后,马伯乐、高本汉的参加,壮大了海外研究汉语的声势。
1918年钱玄同出版的《文字学音篇》,则标志着国内学者研究方向的转变。《文字学音篇》是一部用新的学理讲述音韵学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钱玄同既不完全崇尚传统音韵学的学说,又愿意接受新的音韵学研究方法,在当时可谓领风气之先。
真正以西洋学理并结合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的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是瑞典的高本汉。他从1915年至1926年用11年的时间写出了《中国音韵学研究》。这部著作的意义不在于研究了一个《切韵》音系,重要的是一种观念和方法的介绍——历史比较法的观念和方法。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描写并构拟了古代汉语语音,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实践,深深影响了转型期的音韵学研究的路向。此后,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静如、张世禄、陆志韦、周法高、董同龢等人无不在高本汉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这个时期,无论是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还是等韵学,都取得了超迈往古的巨大成就,音韵学成为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最富成就的学科,也是最有国际影响的学科。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蜚声国际的大师都以音韵学名家。
(5)语法学。中国古代语言学不重视语法研究,虽有零碎的观察,但没有产生像样的语法学著作。直至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的问世,才象征着以汉语为本体的语法学的诞生。马氏本人是基督徒,留学法国,精通法语和拉丁文,是早期的洋务派人物。《马氏文通》共讨论了四个方面的论题:第一正名,界定了23个语法术语;第二实字,即实词,分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第三虚字,即虚词,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四类;第四句读,句即句子,读即分句。马氏的这部著作,大致比附西洋语言的“葛郎玛”而成,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是,该书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为参照,第一次系统描写了汉语语法的结构系统,其历史影响是空前的。
马氏之后,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 (1907)、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1920)、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易作霖的《国语文法四讲》(1924)、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王力的《中国古文法》(1927)等等都深受马氏研究范式的影响,在西洋语法跟汉语语法的纠葛中徘徊。
1936年,王力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他批评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早前的语法研究,反对比附西洋语法,主张汉语语法研究要符合汉语的事实。他说:“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看见别人家里有某一件东西,回来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本来是可以的,只该留神一点,不要把竹夫人误认为字纸篓。”这篇文章吹响了语法学告别模仿、深入汉语实际研究汉语语法的号角,揭橥了语法研究的转向。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转型成功。
(6)训诂学的革新。训诂学本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显学,但是传统的训诂学研究范围漫无边际,研究手段零碎散乱,学理不明,目的不清,与现代语言学很难兼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科,在近代转型期也获得了新生。在学科范围、研究范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黄侃的《训诂述略》(1935)、沈兼士的《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方法》(1920)、何仲英的《训诂学引论》(1934)、傅懋责力的《中国训诂学的科学化》(1942)、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1943)、王力的《新训诂学》(1947)等论著对训诂学的学科建设都有讨论。
黄侃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这大致是向语义学靠拢。
这一时期,训诂学卓有成就的当属语源学的发展。章太炎的《文始》(1910)、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3)、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1934)等从不同的体系和角度,讨论了汉语词语之间的语根关系及语音关联,问题虽有不少,但成绩已经相当可观。
(7)文字学。近代转型后的语言学仍然关注文字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学研究有三大成绩:一是甲骨文的发现,促进了古文字研究的大发展,对许多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著作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1915)、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1)等等。除了甲骨文研究,这一时期,金文、石鼓文、战国文字甚至较晚的俗文字都有人专门研究。二是文字学理论大发展,尤其是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1934)和《中国文字学》(1949)建立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文字研究的范式,突破了许慎《说文》体系的束缚,文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三是汉字的简化和拼音化研究,促进了汉字的教学和扫盲。陆费逵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09)与《整理汉字的意见》(1921)、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1922)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
此外,在《说文》研究上,有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1928)等著作问世。胡朴安还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字学史》(1937)。
(8)修辞学。 修辞学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以篇章学的面目存在,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传续千古的名作。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修辞学的专门著作。
近代语言学转型期内,留学日本的学者从日本学者那里领略了修辞学的风采。像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1905)、程善之的《修辞初步》(1918)、唐钺的《修辞格》(1923)、王易的《修辞学》(1926)等,大致都是对日本人著作的介绍。
陈望道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第一次系统构建了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体系,修辞学才在中国的学术体系里找到了立足点。
(9)汉藏语及其他语言研究。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除了汉语研究之外,也开始关注汉藏语研究。李方桂的《龙州土语》(1935)与《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罗常培的《莲山摆夷语文初探》(1944)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培养的张琨、马学良、傅懋责力等学者后来撑起了中国汉藏语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也注意研究汉语、汉藏语之外的语言,翻译介绍了国外一些语言研究的成果。
三、对近代学术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的评价
近百年来,近代转型后的中国语言学在形式描写、结构分析、历史比较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丰硕,终于跟上了世界学术研究的脚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部门。如何评价近代转型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
董同龢曾在1965年时评价现代音韵学的成就时说:“从西洋人把他们的语言学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古音研究的进展,真是可观。我们可以说,近几十年间中外学人的收获,足足抵得上,甚或超过清代三百年间许多大师的成绩。眼界宽阔,材料增加,工具齐备,方法也更为精密;因此我们已经能从古音的‘类’,进而谈古音的‘值’;更要紧的则是,我们已经能使这门学问脱离‘童稚从事而皓首不能穷其理’的绝境。”*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原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页。这虽然仅仅是对音韵学的评价,但是,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其他方面。
现代音韵学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在于理论与方法的变革,在于人们学术观念的变革。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传统音韵学与现代音韵学的差别:

传统音韵学现代音韵学对象文字音读语音系统的历史材料文献材料文献材料、活的语言材料目的解经语音史理论语文学:考据语言学:历史比较途径音类音类与音值标音符号汉字音标
在肯定中国现代语言学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总结经验和疏失。只有这样,中国语言学才能健康发展。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1.坚持学术开放
坚持学术开放,学习外来的优秀研究经验,吸收、消化优秀的研究成果应该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张之洞早在1898年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清]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0-91页。。王力曾说:“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他还说:“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1957年第3期。
2.坚持学术多元化
中国有文化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巨大的负面作用。其负面作用突出表现在学术研究缺乏创新原动力,有时还会表现出保守的倾向,某些学者甚至对创新性的研究持有蔑视的态度,进而产生打压、诋毁的冲动。中国的封建学术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某些学者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固守某种学术道统,不思进取,这极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的研究,不过是学术泡沫的累积。因此,坚持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坚持学术多元化,自然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3.坚持本体与理论研究并重
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在学习、模仿、融会西方语言学研究中匍匐前进。这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学术研究的必有过程。模仿是创新的母体。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下,百年来,汉语本体研究的诸多方面都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民族性、地域性较强的古文字学、方言学、历史词汇研究、古文献训释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这就像中医、中餐是我们传统的国学,举世无双,研究水平也很高,但这些成就不能说明中国的医学、营养学水平就具有世界水平。同样,一个专门研究莎翁剧作或专门研究海明威小说的西方学者,如果他从中没有研究出具有认识论价值的文学理论,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研究成果就具有世界影响。
某些有民粹思想的学者常常私议:西方学者没有认出一个甲骨片上的字,西方学者解读不了《诗经》、《尚书》,西方学者的汉语水平不高,甚至汉语也说不囫囵,他们列举汉语的例子常常不合汉语的语感,等等。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语言学水平很高了,至少跟西方语言学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样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这样的认识不利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事实是,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不光体现在你对自己熟悉的东西的研究程度,而更在于你对这门学科贡献了多少理性的认识,为人类提供了多少开启智慧的方法。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缺乏创新性的理论提炼。我们在语言研究的诸多领域,仍然是跟在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背景下开展工作。只要不带偏见的学者,都会体认到这一现实。因此,如何在深入的汉语本体研究中,提炼出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理论体系,将是中国语言学任重道远的任务。
学术史学者方松华指出:“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各种思潮和学派蜂拥而起,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代,也是后来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儒、道、墨、名、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方法各异,但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仁义礼智等都有共同的研究、讨论的兴趣,特别是某个学派共同的基本信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从而形成该学派的传统,传承无数年代。先秦多元学术的这种‘范式’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惨遭终结。”*方松华:《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我们所期盼的是,中国将来也能够秉承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融合世界优秀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原创性的、扎根汉语事实的、带有民族气派的、富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语言学,真正成为世界语言学的前驱。
路漫漫其修远!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cholarship and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Modern Linguistics
Zhang Yula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00 years behind, linguistics in China was possessed of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However, beginning from the mid-and late-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inherent cultural system disintegrate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heir strong cultures from abroad.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began in its research paradigm due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the Western academic norm. Corresponding to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s has since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modern linguistics thereupon. That is, mod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es and reap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formal description, of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so on, and this has enabled it to catch up with the footsteps of world academic research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a’s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traditional; modern; linguistics; transformation;China’s modern linguistics
2014-03-25
张玉来(1963—),男,山东沂南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汉语音韵学百年学术源流”(11BYY056)的阶段性成果。
H0-09
A
1001-5973(2014)03-0005-15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