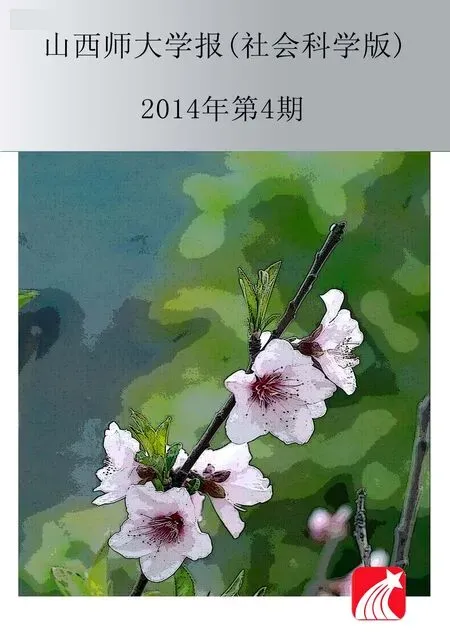中西快乐与德性之文化异同
——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崔 丽 萍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 宝鸡 721013)
快乐是一种情感,是情感中比较特殊、比较重要、也颇具争议的一部分,当然其与德性的异同也是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异同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阐释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快乐的类别、性质及其在成德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来呈现中西文化的同与异。
一、何谓快乐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都谈论快乐,那么,何谓快乐呢?《论语》中孔子提到学习之乐、朋友交往之乐、教育之乐以及道之乐、德之乐等,其中,最大的快乐就是行道、修德之乐,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孔颜乐处”。孔子志于道,将得道、成仁看成人生的最高境界,认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1]35,因此,孔子在乱世之中仍能忧道、体道、践道,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1]71也就是说,孔子关于快乐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其基础和内涵是德之乐和道之乐。快乐是一种情感体验,它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孔子称量自我人生的价值所用的砝码是具有崇高美的天下之利和万世之名的社会价值”[2] 293,他所追求的是庄重的人文道德境界,因而,他的快乐就集中地表现为道之乐、德之乐。这种思想也被思孟学派所吸收和发展。
子游认为对道德的共同喜好是君子交往的基础,如“同悦而交,以德者也”[3]139。子思也认为追求德性的人会以闻道、得道而快乐,如“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3]103。两人都从德性的角度论述快乐。孟子对快乐的论述比较全面,他提出君子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4]309。认为天伦之乐、道德之乐、教育之乐是君子的三大快乐。此外,孟子认为应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33,表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志士胸怀。但是,孟子认为最大的快乐也是道之乐和德之乐。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4]302认为最大的快乐是实现“诚”,而“诚”即为天道,即是善的道德本心,是君子修养的最高理想境界。而且孟子认为,“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4]309广袤的土地、大量的民众是君子想要得到的,但是君子并不以此为乐;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君子以此为乐,但这却不是君子的本性之乐;君子的本性之乐是自足的,不以外在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是发自于内心而表现于颜容的,使人一目了然的自然而然之乐,即所谓“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4]304的德性之乐。这种快乐是人的本性之乐,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因此,思孟学派也认为快乐的种类是多样的,但是其基点和论述的主旨是穷达不变的本性之乐,即德性之乐。此外,对于思孟学派来说,“诚”之乐、本性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而“诚”即为天道,人性为天所赋予,因此,追求和实现“诚”之乐、本性之乐的过程就是同天乐天的过程,是一种实现人的道德、社会本性和本体的形上之乐,是儒家和思孟学派最高的情感境界。
亚里士多德从批判借鉴流行的快乐观点和实现活动的角度论述快乐。他首先驳斥了快乐是恶的观点,认为快乐不是向着正常品质回复的感觉过程,而是正常品质“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5]221,正常品质回复过程中的快乐只是偶性上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使人们正常品质完善的那些快乐。因此,“即使大多数快乐是坏的或总体上是坏的,某种特殊的快乐仍然可以是最高善”[5]221—222。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是实现活动的完善,而“实现活动有好坏的不同,有的值得欲求,有的应当避免,有的既不值得欲求也不需要避免,他们各自的快乐就也是如此。因为,每种实现活动都有自身的快乐。所以,实现活动是好的,其快乐也是好的,实现活动是坏的,其快乐也是坏的”[5]301。因此,他认为“快乐不是善。或者,并非所有快乐都值得欲求,只有那些在形式上和来源上与其他快乐不同的快乐自身才值得欲求”[5]296。此外,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其快乐不能是最高善的观点,认为某种特殊的快乐可以是最高善,这种快乐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与最高幸福相伴随的快乐。最后,亚里士多德借鉴了柏拉图快乐不是善自身及德性之乐是善不可或缺的部分的观点,并将快乐与实现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快乐则与实现活动联系紧密,难以分离”[5]301,“没有实现活动也就没有快乐,而快乐则使每种实现活动更加完善”[5]299,“快乐加强着实现活动,而加强着一种实现活动的快乐也就必定属于它”[5]300。而“完善着完美而享得福祉的人的实现活动——不论是一种还是多种——的快乐就是最充分意义上的人的快乐。其他的快乐,也像其他的实现活动一样,只在此等的或更弱的意义上是人的快乐”[5]302。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从实现活动的角度界定快乐,德性、幸福实现活动所伴随的快乐是最充分意义上的、真正的快乐。其快乐的主旨和内涵同思孟学派一样是基于德性的,所不同的是,思孟学派注重德性本身之乐,而亚里士多德注重德性活动之乐。
二、不乐无德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快乐是实现德性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没有快乐就没有完满的德性和幸福。思孟学派的这一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子思的《五行》中:
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3]100
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3]101
子思认为,心中没有忧虑和思索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喜悦之情,没有喜悦之情人就会不安和焦躁,如果不安和焦躁就不会有快乐,而没有快乐也就没有德性。因此,快乐是实现德性的必要条件。孟子也认为,“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4]271对仁义忠信等善德的喜欢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说,善本身是快乐的,快乐是善的内涵之一。换言之,快乐也就是实现完善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无论是子思还是孟子,其所谓的快乐不是德性、善之外所附加的快乐,而是德性与善本身所包含的和附带的快乐,这一点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认同和强调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的行为给予爱公正者快乐,合德性的行为给予爱德者快乐。许多人的快乐相互冲突,因为那些快乐不是本性上令人愉悦的。而爱高尚[高贵]的人以本性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活动既令爱高尚[高贵]的人们愉悦,又自身就令人愉悦。所以,他们的生命中不需要另外附加快乐,而是自身就包含快乐。”[5]23本性的、合于德性的快乐属于德性活动自身,其自身也就是目的。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真正的快乐本身是值得欲求的,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如果每种品质都有其未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如果幸福就在于所有品质的,或其中一种品质的未受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就是最值得欲求的东西。而快乐就是这样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大多数快乐是坏的或在总体上是坏的,某种特殊的快乐仍然可以是最高善。正因为这一点,人人都认为幸福是快乐的。也就是说,人们都把快乐加到幸福上。这样看是有道理的。因此,既然没有一种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是完善的,而幸福在本性上是完善的。”[5]221—222那么,快乐或真正的、本性上的快乐必然是幸福的,或者说,幸福本身是快乐的,如果幸福的人不比不幸福的人更加快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快乐属于德性与幸福的实现活动,“没有实现活动也就没有快乐”[5]299,而没有快乐,实现活动本身就是不完善的,人们就不会幸福。
三、警惕快乐与寡欲
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属于实现活动,实现活动的不同决定了快乐的不同,实现活动从总体上有德性的实现活动和肉体的实现活动两类,而德性的实现活动高于肉体的实现活动,“所以,由于实现活动不同,它们的快乐也就不同。视觉在纯净上超过触觉,听觉与嗅觉超过味觉,它们各自的快乐之间也是这样。同样,思想的快乐高于感觉的快乐,在思想的快乐相互之间,也有一些快乐高过另外一些快乐。”[5]301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思想的快乐、德性的快乐是本性上的快乐,不存在过度状态,越多越好,而肉体的快乐、感觉的快乐是偶性上的快乐,是存在过度状态的。他说:“尽管有些品质和过程在善这方面不存在过度,因而也不会有过度的快乐,但是有一些品质与过程中的确存在这种过度,因而会有过度的快乐。在肉体快乐方面存在过度。坏人所以成为坏人就是由于追求过度的而不是必要的肉体快乐。”[5]223因此,当肉体快乐处于适度的状态时就是善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而当其过度时就成为恶,是我们应当避免的,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警惕快乐的观点。
此外,人们之所以要警惕肉体快乐,是因为这种快乐常常湮灭了德性的快乐而成为人们追求的首选。亚里士多德认为:“肉体快乐据有了快乐的总名。因为,它是我们接触得最多且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快乐。所以,人们就认为只存在着这样的快乐,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快乐。”[5]222所以,缺乏理性和德性的人们常常会因为肉体脱离理性的控制而使肉体的快乐趋向过度。而且“过度的痛苦使人们追求过度的快乐,一般来说是过度的肉体快乐,作为某种治疗。由于与痛苦的鲜明反差,这种快乐显得十分强烈,所以人们追求它”[5]24。但是这种过度的快乐是偶性上令人愉悦的,当情况发生改变时,以前的快乐也会成为痛苦的根源,如果之后为了消除痛苦再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就会使人陷入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久而久之就会消泯人的本性而遁入兽性。所以警惕肉体快乐,通过教育和指导让高尚的情趣、思想和德性的快乐占据人们的心灵,是实现德性和幸福的重要手段之一。
与亚里士多德以上论述相似,孟子提出了“寡欲”的观点。其实,减少欲望、勤俭节约是儒家一直以来的传统。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172认为寡和贫不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国家动乱是因为财产不均,人心不安,所以,将“固穷”作为君子的优秀品质。子思提出了对情感的“中节”观念,孟子继承了孔子、子思安贫乐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寡欲”对实现人的本性的作用,他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4]339将人的物质欲望和人的道德本性对立起来论述,认为人的欲望少所存的善性必然就多,人的欲望多所存的善性就必然少。因此,特别强调人对外在事物缺乏的自足性,尤其反对外在事物,即欲望对人的内在本性的侵蚀。如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4]271认为为了公卿大夫等功名利禄而放弃仁义忠信等道德本性必然会导致人的本性的消亡。因此,孟子特别强调“多欲”对人的本性损害及“寡欲”对实现德性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思孟学派都意识到,过度的肉体快乐和过多的欲望对实现德性的阻碍作用,因此提出了警惕快乐和寡欲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警惕快乐主要是针对过度的肉体快乐,特别是触觉和味觉的肉体快乐,对于视觉、听觉、嗅觉等肉体快乐,亚里士多德往往持赞赏的态度,例如他认为音乐、建筑、雕塑、绘画等肉体快乐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可以完善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是相同的。但是思孟学派寡欲的范围要广、程度要深,不仅强调对食欲、色欲等肉体欲望的控制和减少,而且强调对财富、利禄等外在事物的控制,往往强调外在缺乏下的内在自足,追求一种自得之乐。
四、痛苦与忧患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乐无德,没有快乐就没有完善的德性,因此,快乐是德性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人,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德性的实现过程都是快乐的。德性之乐虽然属于德性自身,但是对于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在其德性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德性的培养过程对他们来说就是痛苦的,“如一个青年人不是在正确的法律下成长的话,很难把他培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为,节制和艰苦的生活是不为大多数人所喜欢的,特别是对青年人。所以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在变成习惯之后,就不再痛苦了。然而,作为青年人只是正确的哺育还是不够的,就是正在长大成人之后还应继续进行这种训练,并且养成习惯。我们还需要与此相关的法律,总的说来,关于整个一生的法律。”[5]313也就是说,德性自身携带着快乐,但是由于德性是后天养成的,其养成的过程伴随着痛苦。换言之,当一个人对某一德性活动不再痛苦而是能够享受其中的快乐时,我们才说其真正获得了这种德性,能不能快乐地进行德性活动是是否具备了该德性的标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痛苦与快乐是相对的、相反的,痛苦的消失、快乐的形成是一德性完善的标志。
而且,这种相对立的情形还表现在不同德性的实现活动中。也就是说,一种实现活动的快乐对于另一种实现活动是痛苦的,对另一种实现活动起毁灭的作用,“不同类属的快乐,如刚刚说过的,就相当于自身的痛苦。因为,它们毁灭实现活动,尽管不是以同样的方式。”[5]301例如,爱听长笛的人听到长笛的演奏就无心继续谈话,因为他们更喜欢听长笛演奏而不是谈话,听长笛演奏的快乐妨碍了谈话活动,而这种快乐就相当于谈话活动自身的痛苦,它终止了谈话活动。一种活动的快乐是另一种活动的痛苦,快乐与痛苦在这种情形下既是对立的,同时也是相互转化的。
此外,对不道德行为的痛苦也是获取德性、实现德性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不仅喜欢德性、能够享受德性之乐是德性完善的标志,而且对于不合于德性行为的痛苦,也会促使人们回归到德性之中,这种痛苦对于德性的实现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把快乐与痛苦当作教育青年的手段。而且,我们把爱所应当爱的,恨所应当恨的看作养成德性的品质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快乐与痛苦贯穿于整个生命,对于德性与幸福至为重要”[5]289。从这个角度来看,痛苦和快乐是相辅相成的,痛苦是为了快乐,快乐伴随着痛苦。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快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痛苦出现,快乐与痛苦对于同一种德性是相反的。对于不同的德性既是相对立的又是相互转化的,而正当的痛苦、作为善的痛苦又是与快乐相辅相成的。在思孟学派的伦理学中,与乐相对立的有哀、悲等词汇,但是对于德性来说,思孟学派论述更多的是“忧”,如孔子的“忧道不忧贫”[1]168,子思的“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3]100,孟子的“忧以天下”[4]33等。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思孟学派认为德性是人的内在本性,所以德性不仅本身包含快乐,而且其实现过程是没有痛苦的,其所谓的“忧”不是指德性修养,而是指德之不成、德的缺失及天下之混乱。也就是说,思孟学派其实也承认“寡欲”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以贫为乐,都能享受德性的快乐,但是他们不讨论德性修养过程中外在物质缺失的痛苦及某些德性,如节、俭等在养成过程中的痛苦,而是认为君子应该“固穷”。而且,思孟学派的“忧”与“乐”是两面一体的,“忧”德之不成是成德的动力,这种“忧”可以带来实现德性的快乐,所以,忧乐圆融是儒家及思孟学派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与亚里士多德的正当的快乐与痛苦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注重快乐与痛苦相成的一面及其对德性的完善作用。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痛苦与快乐也有相对立的一面,而对于德性修养过程中的痛苦,思孟学派是缺而不论的。
但是,思孟学派也认为人的生存和成长应该经历磨难和痛苦,如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298因此,思孟学派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道德修养过程中的痛苦和煎熬,但间接地承认了德性的实现过程也是心志经历磨难和痛苦的过程,德性之乐也是伴随着痛苦的,只是思孟学派更为强调德性本身及德性修养过程中的快乐,对痛苦的论述不如亚里士多德直接明了。
总之,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都注重德性之乐,认为德性实现过程中的快乐是真正的、本质上的快乐,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完满德性的快乐,即幸福之乐和成德之乐;并且认为快乐属于德性自身,快乐具有加强和完善德性的作用,没有快乐就没有完善的德性和真正的幸福,快乐是实现德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肉体的快乐存在着过度,而过度的肉体快乐对德性的实现有阻碍作用,所以应该警惕过度的肉体快乐,特别是味觉与触觉上的肉体快乐。而思孟学派也认为过多的欲望会湮灭人的善的本性,所以提出寡欲,只是在程度上,思孟学派的寡欲要比亚里士多德的警惕快乐强烈得多。最后在关于痛苦与忧愁、忧虑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立论比较客观,注意到了痛苦与快乐各种不同的关系及痛苦的不同作用,而思孟学派更加注重人的精神作用,回避了,有时间接论述了德性修养过程中的痛苦现象,只将忧与痛苦限定在德之缺失及天下混乱上,提倡忧乐圆融的精神境界。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谢阳举.道家哲学之研究——比较与环境哲学视界中的道家.张岂之主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