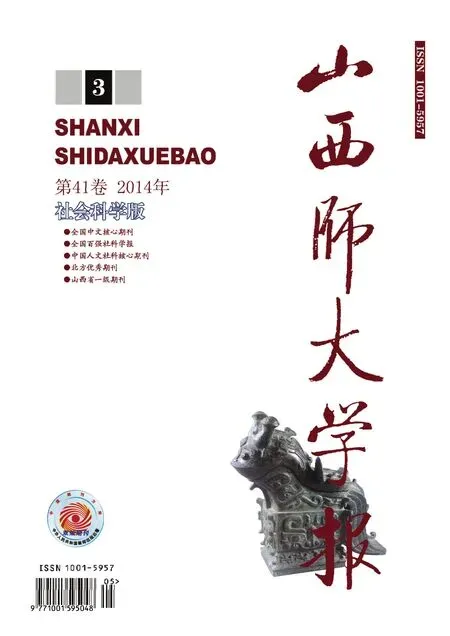论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的原因
赵 耀 锋
(宁夏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一
陈寅恪是20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大师之一,其学术代表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其《元白诗笺证稿》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陈寅恪在《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论及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时曾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270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1]185对于其“不今不古之学”的理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认为是指魏晋到隋唐时期。从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文史研究的中心是在唐代,而其唐代文史研究中又以中唐为中心,如对中唐文人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研究就倾注了大量心血。陈寅恪之所以将文史研究的中心放在中唐,其中原因既与中唐、晚近历史文化本身的特点有关,又与陈寅恪自身的家庭出身有关。具体地说:一方面从中唐的时代特点来看,此期为古代社会经济文化转变的一个枢纽,中国文化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另一方面,陈寅恪父祖生活的咸同之世和中唐都是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陈寅恪父祖的遭遇和中唐士人的遭遇有某种一致之处,因此陈寅恪欲以中唐研究来寄寓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悲愤之情。另外,晚近学术文化背景和中唐有契合之处。以上这些方面都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的重要原因。
在华夏文化史的视野中,中唐是中国文化史上“轴心时代”之“轴心”。一种文化的“轴心时代”并不是指这种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而是指这种文化形成辉煌的源头或者推动这种文化走向辉煌的动力。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轴心时代”,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唐代。先秦时期在文化方面,中国哲学儒道互补的传统已经完全形成;学术方面,诸子百家的争鸣开后世学术无数法门;文学方面,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也已经形成。唐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二个“轴心时代”,这是因为,中国国学的精粹是诗文,诗歌方面,王国维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此说包含着诗为有唐一代之文学的价值判断。闻一多先生提出了“诗唐”说[3]185,认为唐代是文学史上“诗的时代”,这也是明清以来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宋代之后,按照传统的文学观点,一般文士总是认为中国的诗歌只有“唐诗”和 “宋诗”两种类型,认为唐诗优于宋诗。散文方面,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有“秦汉散文”和“唐宋散文”两种类型,宋代之后的文士在进行散文革新时也总是以这两种散文类型相标榜。小说的成熟也是在唐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4]73,唐传奇之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小说情节营构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由此可见,唐代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而在唐代,中唐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词的产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因而清人叶燮认为,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5]由此可见中唐在整个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另外,中唐也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枢纽”。“唐宋变革”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唐时期,近代学者心目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束,“近代”社会开启。1910 年,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杂志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这样一个重要命题,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6]10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而唐宋转型的源头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的中心由北方转移至江南,中国文化的中心也转移至江南的江浙一带。在文化领域,中唐时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大量庶族优秀士人由于科举制而跻身政坛,由此造成中古以来占据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优势地位的士族地位的下降。“唐宋转型”其他诸方面的变化实际上都是由中唐时期经济、文化领域的这两项变化而造成的。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中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陈寅恪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7]332由此可以见出陈寅恪对中唐历史文化的重视。而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就是回溯法,就是追溯一种文化的源头,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运用回溯法追溯唐代政治制度及文化的源头。《元白诗笺证稿》主要是追溯明清学者心目中的“近世”文化的源头,陈寅恪认为“近世”文化的源头在中唐,这也就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从晚清至民国的时代背景来看,陈寅恪父祖生活的咸同之世和中唐都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陈寅恪父祖的遭遇和中唐士人的遭遇有一致之处,因此陈寅恪欲以中唐研究来寄寓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愤慨之情。
首先,从政治背景看,一方面,陈寅恪父祖生活的时代暗合于唐代永贞革新前后的社会特点。元和、光绪时代均为内忧外患之世,这两个时代都是一个社会改革时期,陈氏家族与元和士人均为改革派。“戊戌变法前夕的湖南新政实系由宝箴、三立父子共同擘画而成。”[8]180陈氏父祖由此而遭终身禁锢,这和中唐永贞革新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遭遇有一致之处。另外,安史之乱为胡族乱华,晚近以来,政府腐败,社会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清末民国社会也存在“夷夏之争”的问题,据说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为慈禧所鸩杀[9]45,陈氏思想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清情绪,这种思想在氏著《柳如是别传》中也有一定的体现。由于晚近和中唐两个时代的政治背景有一致之处,所以陈寅恪选择中唐文史作为研究对象。
其次,晚近与中唐都是士人命运的转关时期,因而,将中唐与晚近时代相比附,这是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情结。晚近时期,清代遗老们以华夏文化之“衣冠”自居,而实际上在新军阀对政权、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下,这些文化士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地位方面都毫无优势可言,因此,以晚清遗老及其子弟们为代表的文化士族认为,晚近是中唐以来士族文化的又一大变革时期,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近学者对此期文化变革的心态。查屏球先生曰:“沈、陈诸人深谙唐宋典故,也都以贞元、元和代指一代中兴之机。他们是以自己的人生感受来把握元和诗风的。他借元和一代士人‘酒杯’来浇自己内心中的‘块垒’。这一情思与他们的学术见识是一致的。他们以诗家之心,将元和对诗风、学术史、政治史综合在一起考察,中唐诗中枢论也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以一种命运悲剧的心态表示了对元和士人的社会使命感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中唐也是古今士人命运的一个中枢。”[10]此处“沈、陈”指沈曾植与陈衍。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也是士人命运的转关时期,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其父辈思想影响的结果。
再次,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唐元和时期与光绪之世都是传统文化失落、要求儒学复古的时期。同时,随着西学东渐,晚近和中唐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样一个文化背景。陈寅恪曰:“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11]149—150由此可见,陈寅恪认为安史之乱为“戎狄之乱华”。晚近时期,除了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元和与光绪这两个时代的士人对外来文化均存在一种矛盾的心态,韩愈对佛学既内化又排斥,民国时期,王国维、陈寅恪等学人既留学国外又不满西学,王国维甚至为传统文化而殉情。晚近和中唐这两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有一致之处,这是陈寅恪选择中唐文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在学术背景方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陈衍、沈曾植在学术研究中分别倡“三元”说和“三关”说,两说均以中唐元和时期为古今诗歌转变的中枢,这两种诗学观念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和陈衍同是同光体著名诗人,因而陈寅恪诗学思想受“三元”说和“三关”说影响很大。陈寅恪以“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合来概括元和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认为元稹《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11]63实际上以“史才、诗笔、议论”三者融合为艺术特征的诗歌就是“学人之诗”,以陈衍、陈三立为代表的宋诗派的诗歌就是典型的学人之诗,由此可见,元和诗歌符合民国时期学者的诗学理想。同时,在《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陈氏想通过确立元白诗的“诗史”价值确立中唐元和文坛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此来呼应当时诗坛流行的“三元”说、“三关”说,他认为白居易的诗歌“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11]121对中唐文学评价很高,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而他这种文化观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受晚近学术风气影响的结果。
第五,在家庭背景方面,陈寅恪父祖的遭遇和中唐改革派士人的遭遇有一致之处。“永贞革新”是唐宋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永贞革新”使得唐朝得以中兴,而此次事件中的柳宗元、刘禹锡诸君子却遭到了终身禁锢,这和陈寅恪之祖父陈宝箴的遭遇有一致之处。陈氏父子对中唐文人评价极高,陈三立《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曰:“吾观柳子厚欲为王叔文尽收奄宦兵柄还之朝廷,此为安危存亡国家切要之大计。其相与慷慨发愤挺起发难,务扫除奸盆窟穴,立不世之功,而消积害巨祸,不可谓非惊然抉大义忠唐室者矣。徒以叔文乘顺宗寝疾,窃权自相部署取败而受恶名。”[12]67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曰:“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7]332又曰:“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1]182陈氏父子对中唐文人在吾国政治文化史上的地位有着极高之评价,其中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感。陈寅恪对中唐有功之臣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曰:“杨炎以文学器用,窦参以吏识强干,俱为德宗所宠任,擢登相位,而并于罢相后不旋踵之间,遂遭赐死,此诚可致慨者也。”[11]182“刘晏为代宗朝旧相,最有贤名,而德宗以疑似杀之,斯为失政之尤。此当时后世所以咸致冤痛也。”[11]182陈氏对中唐君主对有功之臣的任意贬谪与杀戮深表悲愤,其中暗寓身世之感,对其祖父晚年的遭遇深表不满,所以,陈寅恪中唐文史研究其实暗寓对父辈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和愤慨,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深刻原因。陈氏父祖两代致力于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六君子”中好几位为陈氏祖父陈宝箴向清廷荐举,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首先推动近代以来之政治改良运动,因此遭到清廷保守势力代表慈禧的憎恨,陈氏父祖被终身禁锢。《元白诗笺证稿》中在笺注白居易《长恨歌》时,陈寅恪暗寓自己的身世之感,曰:“盖肃宗回马及杨贵妃死,乃启唐室中兴之二大事,自宜大书特书,此所谓史笔卓识也。‘云雨’指杨贵妃而言,谓贵妃虽死而日月重光,王室再造。其意义本至明显平易。”[11]35—36唐肃宗本非中兴之主,造成唐室颠沛流离者,责任并非完全在于杨贵妃,而陈氏认为贵妃之死可使唐室“日月重光”,“肃宗回马”使唐室“中兴”,此中寄寓者陈氏的身世之感。盖“贵妃”影射慈禧,“肃宗”影射光绪。陈寅恪因父祖在戊戌变法后的遭遇而憎恨慈禧,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华夏文化式微为慈禧败政之所致,以慈禧之死为中国命运之转折点,故谓“贵妃虽死而日月重光,王室再造”。光绪皇帝欲进行政治改良,支持戊戌变法,陈宝箴为光绪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故陈氏认为光绪是“中兴”之主。《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通过对《长恨歌》的笺证影射清末社会,暗寓自己对清末政局的看法及身世之感。
白居易是陈寅恪最为推崇的中唐文人,而白居易却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这和陈寅恪父祖的遭遇有一致之处。白居易之父白季庚因与其外甥女婚配,这种不伦之举为当时的礼法社会所不容,白居易一生遭际实与此事有关,陈寅恪曰:“常疑李文饶能称赏家法优美之柳仲郢,而不能宽容文才冠代之白居易,亦由于此。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至文饶所以荐用乐天从弟敏中之故,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吾人今日固不可以此责乐天。然乐天君子人也,却为此而受牺牲,其消极知足之思想,或亦因经此事之打击,而加深其程度耶?”[11]327陈寅恪认为白居易有绝代之才华,而其一生在政治上的沉沦及其消极思想之形成,实际上都与其父母不合礼法之婚姻有关。陈寅恪在元稹、李商隐等中唐文士的研究中对他们的绝世才华深为赞赏,而对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境遇深为同情,其中也暗寓对自身在民国乱世之中不幸遭遇的深切感慨。陈寅恪之祖父陈宝箴在晚清政坛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而却不见容于慈禧,陈宝箴之死扑朔迷离,陈三立为清末遗老,所以在民国时期不见容于社会,这种家庭文化背景和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中唐文士的遭遇有一致之处,所以陈氏借对元白等文士的研究来寄托身世之感。
总之,中唐是中国文化史上“轴心时代”之“轴心”,宋代以来,中国文化、经济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士族地位升降等许多重要文化现象都与中唐有关,所以中唐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宋代之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引起了陈寅恪先生的高度重视。另外,陈寅恪父祖生活的咸同之世和中唐都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陈寅恪父祖的遭遇和中唐士人的遭遇有某种一致之处,因此陈寅恪欲以中唐研究来寄寓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愤慨之情。而且,晚近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和中唐有一致之处。以上这些方面都是陈寅恪文史研究以“中唐”为中心的重要原因。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4] 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叶燮.己畦集[M]卷八.清康熙二十三年本.
[6]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A].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8] 王瑶主.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兼及陈氏一门[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10] 查屏球.“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J].复旦大学学报,2000,(2).
[1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12] 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