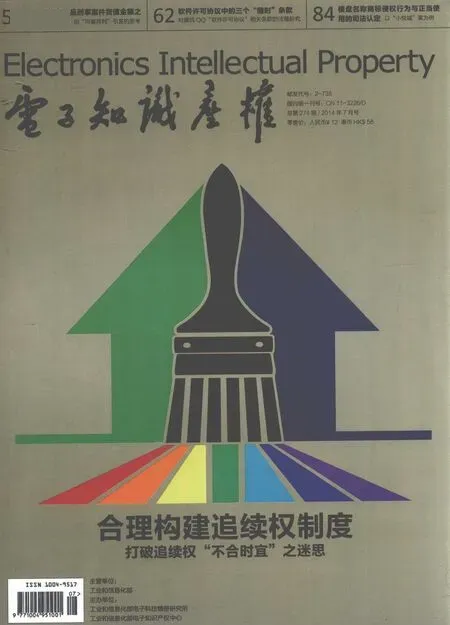软件许可协议中的三个“随时”条款对腾讯QQ“软件许可协议”相关条款的法理研究
王大鹏 /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法律研究中心
软件许可协议中的三个“随时”条款对腾讯QQ“软件许可协议”相关条款的法理研究
王大鹏/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法律研究中心
摘要:在腾讯与360的争端当中,被舆论和法学界所忽视的是腾讯通过“点击式许可”与用户签订的“软件许可协议”,它几乎赋予了腾讯公司以无限的合同权利。这个协议是两种法律移植的产物,其一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向新式IT法的移植,其二是美国式IT法向中国式合同法的移植。在技术环境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类似的移植引发了复杂的混乱局面,而我国学界对于应对这种局面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因此,在对“软件许可协议”及其附带条款的分析的基础上,为类似的争端厘清法理线索,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上提出相应对策不无裨益。
关键词:软件许可协议; IT法; 许可合同化
2010年11月3日,在经过了与奇虎360近一个月的所谓“弹窗大战”以后,腾讯“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运QQ软件”【1】(以下称“不兼容”行为),并在此后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
这场争端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矛盾,其一是软件服务商相互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软件服务商与广大软件用户的矛盾。前者目前已经在“反不正当竞争”的层面上开启了司法解决的途径;而后者,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基本的法律依据乃是腾讯与每个用户签订的一份“软件许可协议”(以下称“协议”),而根据这个协议当中的三个关键条款,广大的软件用户很有可能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合同权利。如果没有这份协议的掩护,如果没有上述三个关键条款的掩护,腾讯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罪于数亿网民。
笔者将这三个条款分别称为“随时变更条款”、“随时中断条款”和“随时修改条款”,以下将分别对这两个条款及其所属“协议”的事实状态和法律效果做一简要的描述和法理解析。
一、“软件许可协议”及其条款的事实状态
点击每一个腾讯软件的安装程序,都会出现一个安装对话框,每个对话框的第一页都是一份“软件许可协议”(以下称协议),协议的文本下有“同意”与“不同意”两个按钮,一定要点击“同意”,安装才能继续。绝大多数的腾讯软件用户可能都没有看这份协议就已点击了“同意”。
以2007年上市的QQ2007Ⅱ型软件为例,协议开头第三段有这样的规定:“本《协议》可由腾讯随时更新,且毋须另行通知。本《协议》条款一旦发生变更,腾讯将在本软件或网页上公布更新内容。更新后的协议内容一旦公布即有效代替原来的协议条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时变更条款”。这样的条款意味着:作为合同一方的腾讯公司可以不经合同另一方同意,任意变更合同内容,只需将变更内容登载在自己的网站或软件上即可。
同样以2007年上市的QQ2007Ⅱ型软件为例,“协议”第4条第2款规定:“腾讯拥有随时自行修改或中断软件授权而不需通知用户的权利,如有必要,修改或中断会以通告形式公布于腾讯网站重要页面上”。
这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随时中断和修改条款”。这一条款就是腾讯公司对用户软件实行“不兼容”处理的法律依据。
实际上,腾讯公司使用这一条款也不是第一次了,2010年春节期间,习惯于通宵运行电脑的网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电脑上被悄悄地安装上了一个名为“QQ医生”的软件。和这一次的“不兼容”事件一样,当时网络上就骂声四起,指责腾讯“强行绑定”、“强行安装”,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随时修改”条款的存在。
二、有关“软件许可”和“软件许可协议”的法理分析
要明晰上述条款的效力首先必须对这些条款的出处——“软件许可协议”有所了解。
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将计算机软件保护办法的制定权委托给了国务院,而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三章提出了“软件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这一概念,因此,在我国法律当中,与一般大众的“所有权”思维习惯不同,装在电脑当中的软件并不是用户的所有物,而是软件著作权人对用户的一种“使用许可”。软件服务商们对这一规定也是定心领神会,微软公司的“软件许可条款”中文版第二条就特别规定:“该软件只授予使用许可,而非出售。”1. 参见《MICROSOFT软件许可条款》中文版,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5/6/F/56F3FE47-73CC-4042-B718-84846A622009/SQL_Server_JDBC_Driver_20_EULA_CHS.htm.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软件使用许可”的规定只有一条(第十八条),仅规定了“许可他人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应当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中软件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被许可人不得行使。”至于“许可”和“许可使用合同”究竟应该如何来订立,“条例”里并未规定;类似合同是否应适用《著作权法》当中有关“许可使用合同”的规定,“条例”里也未言明。
“许可”(License)本是一个普通法财产法(property law)当中的概念,后来进入到知识产权法领域,同时也被移植到了我国的“版权法”或者“著作权法”当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法律门类——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w,简称IT法),而“许可”又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这个法律领域当中。
“软件使用许可”这一概念就来源于美国IT法当中的“Software License”( 软件许可)。而美国IT法学者H. Ward Classen认为,要弄懂IT法上的“许可”概念必须首先弄懂英美法上的“权利组”(bundle of right)理论2. 参见H. Ward Classen,A practical guide to software licensing for licensees and licensors,second editon,P11, ABA publication,2005.。早年的美国法律教育者们认为,财产所有权(property ownership)不是一个单独的权利,而是非常复杂的一组权利。其中每一个权利都是相对独立的,都可以从“财产所有权”这个“权利组”当中拆除出来。这样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既bundle of sticks(直译为“一捆树枝”,暂且意译为“权利束”),每一种权利都被比作为一根树枝(stick),可以从这个“权利束”当中取出来单独使用3. 参见Thomas C. Shevory,Body politics: studies in reproduction,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117,praeger publishers,2000.。久而久之,“树枝”(stick)一词开始被单独地用来指称“权利组”当中的一项权利。
不知道是否是巧合,早期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在建立自己的语言体系时,也使用了stick一词,用来指称数据单位,中国的计算机学界将其译为“根”,我们常用的U盘,其英文名字就叫“USB memorysticks”(汉译为:通用串行总线记忆根)。如此一来,在谈到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某些问题时,“stick”一词就有了两重含义,既可以用来指称某些数据,又可以用来指称这些数据上所附着的财产权利,法律语言与技术语言在此出现了重合,我们模仿已经大量使用的技术语言,将这种可以从“权利束”当中单独拆分出来的stick,在IT法的语境下暂译为“根权利”。
Classen认为,所谓“许可”就是“财产所有者对使用其财产的一种承诺……财产所有者占有全部的根权利,其中也包括有一些可以被他人所利用(nonexclusive)的根权利。财产所有者授予了一项许可,就意味财产所有权人从自己的权利束当中取出了一些根权利放进了这项许可里”4. 同注释2。。注意:“许可”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合同(contract),而是一种“可以被他人所利用的”“根权利”。这种权利可以通过合同去转让,而转让这种许可的合同被美国IT法称为license agreement,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对“对许可的同意”,意译为“许可协议”——“协议”是双方“同意”的,而“许可”则是单方制作的。我国的《著作权法》显然受到了这种思想的深刻影响。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合同法的语境当中都不可能容纳单方意思的存在,因此,“许可”进入到合同领域,就与“协议”合在一起成为了“许可协议”(license agreement)。相应的,作为许可内容的那些“根权利”也就转化成为了我国合同法意思上“授权范围”(“授权范围”也是腾讯QQ2007Ⅱ软件“协议”第二条的题目)。“授权”依旧是一种单方行为——但即使是在“协议”当中,“许可”单方意思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为了平衡“许可”的单方性,合同势必要规定著作权人的合同义务,但确定著作权人的义务又必须仰赖合同双方的“意思交换”或者“协商”(negotiation)。一旦“意思交换”受阻,“协议”的特征就会退化,整个“许可协议”就会蜕变为一个单方性色彩浓厚的“许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量的“软件许可协议”都是通过点击对话框下部的“同意”按钮来签订的,这种方式很早就被美国的IT法学家们界定为“非协商性点击式许可”(nonnegotiable “click-wrap license”)5. 同注释2,p1.,顾名思义,这种许可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点击式”,既该许可用点击计算机按钮的方式确认;其二是“非协商性”,换句话说,由此形成的所谓“协议”,其内容根本不是“协商”或者“意思交换”的结果。这样的一种所谓“协议”直到1998年,才通过Hotmail Corporation v. Van Money案6. 参见Hotmail Corporation v. Van Money Pie Inc., et al. C98-20064, 1998 WL 388389 ( N.D. Ca., April 20, 1998).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得到支持。而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腾讯QQ软件开发成功,同年7月,《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The 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Act 简称UCITA)在美国制定完成,尽管这部法律“冗长、混乱、而且毫无必要的复杂”7. 参见Gary M. Lawrence, Carl Baranowski:Representing high-tech companies,P6-5,Law Journal Press ,1999.,但是其209条还是正式承认了“点击式许可”的法律效力。直到今天,在美国的IT法学界当中,围绕着“点击”(click)是否能造就出一个“协议”的话题,争论还在持续8. 参见Nathan J. Davis:Presumed Assent: The Judicial Acceptance of Clickwrap,Berkeley Technology Law,Journal,22 Berkeley Tech. L.J. 577.。
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点击式”(click-wrap)的“非协商性”特点毫无疑问对合同上的“意思交换”造成了严重干扰,而如前文所述,“意思交换”受阻使“协议”的合同性退化,而“许可”性加强。“协议”具有了浓厚的单方意思特征。
这种具有“单方意思”特点的所谓合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合同法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格式合同”,而早在2006年,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这种“协议”由软件服务商单方拟定,就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格式合同”【2】。
我国法律对“点击式许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可协议”都无专门规定,是否对这些概念加以承认,目前也还是一个悬置的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英特尔诉东进案于2007年以庭外和解告终,最终没能产生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软件许可判例【3】。无论如何,软件产业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趋势难以阻挡,其基本交易形式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美国的IT法理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许可”当中的规定都是软件服务商的单方“授权”,但是随着法律秩序的完善和相关诉讼的增加,“许可”当中开始出现了有关软件服务商义务的众多规定,“许可”的各种条款与合同条款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有的软件服务商提供了多种“许可”给用户选择;或者将“许可”模块化,交由用户自行组合;有的甚至于提供通道,让用户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直接与服务商讨论“许可”内容9. 例如微软公司。参见微软公司客户服务许可页面:http://www.microsoft.com/licensing/default.aspx.——新式的“许可”已经逐渐开始具备了“双方意思”的特征。因此,也有美国权威学者倾向将“软件许可”纳入“合同”的范畴10. 参见Michael Dennis Scott,Scot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w, Volume 1,3rd editon,p12-3,Aspen publisher.。可是,如果“许可”(license)和“协议”(agreement)都是“合同”(contract),那么“许可协议”(license agreement)究竟是一个合同还是两个合同呢?如果是一个合同,那么“许可”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关系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呢?
普通法意义上的“财产法”与“合同法”都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因此,上述问题在美国法律的语境下可能并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如果我们沿着腾讯的道路,将美国原始的“许可”理念移植到中国的合同法体系当中,那么上述问题就可能引发严重的概念混乱,而这种混乱的结果必然是“许可”在IT法中的逐渐消亡。
三、“许可”在IT法中的消亡
近代的知识产权法是在“纸质书籍”这一技术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纸质书本一旦售出就脱离了著作权人的控制,而一个人的法律义务又不可能建立在他无法控制的领域里。“许可”正是这样一种法律环境的产物,他强调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而著作权人的义务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根本无从谈起。
谁也不会想到“软件”这一“著作”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出了一整套的互动能力。软件售出之后并没有脱离著作权人的控制:作为360式的病毒防护软件,他需要从“著作权人”那里获得升级和更新程序;作为腾讯QQ式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需要在“著作权人”那里获得基本的通讯信息。像腾讯这样的“著作权人”甚至可以让售出的“著作”暂时失效甚至彻底被屏蔽。
传统知识产权所规定的是一种单方授权性的法律关系,而新式网络服务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平等的服务贸易关系。“软件的知识产权”与“软件的互联网服务”这两个概念已经在实践中分化开来,“软件著作权人”与“软件服务商”的分化也必然会展开。事实上,在1998年10月出台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Digital Millenium Copyright Act 简 称DMCA)中,软件作者(author)和服务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两个概念的分化就已经出现11. 参见Christopher Wolf,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text, history, and caselaw, P 995,Pike/Ficher,inc 2005.。
“许可”是“知识产权”→“著作权人”这一法律关系的产物,而在“互联网服务”→“服务商”这一新的法律关系中,他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位了。
人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法律也是一样,再新的法律关系也必须通过旧的法律语言来表达。这一点对于“崇尚先例”的英美法系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在他们的法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数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词汇,如“令状”(writ)、“侵入领地之诉”(trespass)等等,这些词汇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其外貌依然被保留了下来。IT法的语言大多从传统知识产权法中继受而来,“许可”正是这种继受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这一词汇所指称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和历史上的类似情况一样,仅仅作为一个词汇,它肯定还是会在美国的IT法律体系当中被继续沿用下去。
我国毕竟是一个法典制的国家,法典中的用语对法律关系的构建有着极大的影响。词汇的混淆会带来概念的混淆,而概念的混淆又会在法律关系的层面上制造混乱。因此,我们应当将“软件的互联网服务”从旧式的“许可”概念中剥离出来,去建立一个新式的“互联网软件服务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软件服务商不再进行单方的“许可”,他与软件用户都是合同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普通的服务。只有在这一法律关系之下,前述的“随时变更条款”、“随时中断和修改条款”才可能得到准确的定位,类似的讨论才可能获得一个合理的概念平台。
诚然,国外对IT法上各种法律关系的描述都是在“许可”这一语境下完成的。因此,在“互联网软件服务”这一全新的法律关系当中,我们只能将美国语境下“许可”话语转换为中国语境下的“合同”话语,去实现“许可”的合同化。在这一点上,以腾讯为代表的一批软件企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虽然不能说“许可”这一概念已经彻底“死亡”了,在传统知识产权法领域,它还会继续健康地存在下去,但在“互联网软件服务领域”,它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而“许可”的消亡或许正是IT法律体系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对“随时变更条款”的分析及立法、司法对策
如前文所述,在“互联网软件服务”这一法律关系当中,“许可”并非是一个合理的理论,即便美国式的“许可”是一个合理的理论,这也并不能说明腾讯拟定的“随时变更条款”就是一个合理的条款。
QQ2007Ⅱ软件“协议”中的“随时变更条款”前文已述,不再重复。需要注意的是, 2009年新上市的QQ2009将相应的文字改为“本《协议》可由腾讯随时更新,更新后的协议条款一旦公布即代替原来的协议条款,恕不再另行通知。用户可重新下载安装本软件或网站查阅最新版协议条款。在腾讯修改《协议》条款后,如果用户不接受修改后的条款,请立即停止使用腾讯提供的软件和服务,用户继续使用腾讯提供的软件和服务将被视为已接受了修改后的协议。”与QQ2007Ⅱ的条款相比,QQ2009进一步阐明了腾讯所设想的,迫使用户“接受修改后协议”的法律机理:在变更“协议”这一合同行为当中,腾讯公司拥有“随时更新”的权利,而腾讯公司的义务只是将更新内容公布;用户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用户除了要承担更新后的合同义务外,实际上还背负了一个必须随时“重新下载安装本软件”或查阅腾讯网站的义务。至于履行这个义务的时间和频率,完全由腾讯公司掌握。
面对这样一个条款,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十一条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定,或者适用五十三条有关“显失公平”的规定都并无不妥。略显尴尬的是,我国的合同法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原则和法理基础。而“随时更新条款”实际上已经让合同一方的意思完全置于另一方的随意支配之下。这样的“协议”究竟能否算作是“合同”也成了一个问题。该条款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可能更为妥当,该法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腾讯的“随时更新条款”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其协议内容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应当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正是在“随时更新条款”的掩护之下,腾讯于2009年将“协议”第二条第一款更新为:“用户……不可以对该软件或者该软件运行过程中释放到任何计算机终端内存中的数据及该软件运行过程中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数据进行复制、更改、修改、挂接运行或创作任何衍生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插件、外挂或非经授权的第三方工具/服务接入本‘软件’和相关系统。”其中,“第三方工具/服务接入本软件和相关系统”的描述与引发此次事件的360“扣扣保镖”软件基本符合。这一条款的掩护之下,腾讯或许作出了如下的判断:在所有的QQ用户当中,如果谁安装了360“扣扣保镖”软件,谁就违反了与腾讯公司通过“点击式许可”方式签订的“协议”。腾讯公司究竟是在2009年的具体什么时间将上述条款更新到了安装程序附带的“协议”当中?凭借笔者的技术能力还无法查实这个问题。如前文所述,由于“随时更新条款”的效力本来就存在瑕疵,因此在“协议”更新前下载QQ软件的用户不可能受该条款约束。但是,在“协议”更新后下载QQ软件的用户,由于安装软件附带的原始“协议”当中已经包括了上述条款,而用户又点击了“同意”按钮,腾讯公司至少在理论上就已经拥有了追究上述用户违约责任的权利。当然,这一切都要以我国法律承认“软件许可协议”和“点击许可”作为前提。
诚然,软件服务是一种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的服务,目前市面上的大量软件都存在在线升级的问题,离开这种升级服务,软件的性能无法得到提高;在网络和软硬件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升级的软件甚至会丧失其基本功能。而软件的不断升级换代则很有可能超出原有协议的约定范围。因此,一定程度的协议变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变更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腾讯式的“随时变更条款”来进行,因为即使是在美国的IT法语境下,软件许可的交易也是通过一个“协议”或“同意”(agreement)来进行的12. 参见Richard Raysman,Peter Brown,Jerry D.neuburger,William E.BandonⅢ,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law: forms and analysis: Volume 1-Page8-6,Law Journal Press , 2002.。而“随时变更”然后推定用户同意,这样的操作方式无论在中国式的“合同”层面上还是在美国式的“协议”(agreement)层面上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可是,离开“随时变更条款”,软件许可协议的变更如何来进行呢?由于用户数量庞大,距离遥远,软件所有者很难与每个用户进行传统意义上“意思交换”,整个“协议”的变更还是只能依照“服务器提出,用户同意或不同意”的方式来进行。
在美国的IT法理论当中,在“根权利”的语境下,由于“许可”(license)与“许可协议”(license agreement)两个概念相互分开,因此变更“协议”很难说就等同于变更“许可”。“许可”本质上是一项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因此“变更许可”其实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新的“许可”。而在我国,由于“许可”内容被看作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如果要让“合同变更”达到重新授予“许可”的效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新签署一份“许可协议”或者“许可合同”,换言之,就是让整个变更程序按照原始“协议”签署时的程序来进行,明确地来说,就是以类似安装软件时那种“点击式许可”的方式来进行。
综上,笔者建议,应在协议变更请求提出之后,给予用户一定时间的考虑宽限期,以便用户形成自身的“意思”;宽限期内,“协议”双方可以按照“点击式许可”的方式重新签订协议。类似法律行为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用户同意的“协议”版本,应该以用户下载时的版本为准。
第二,如果软件服务商确须更新“协议”版本,必须以明确可见的方式(比如弹窗、服务界面上的明显文字等)通知用户,并给予用户一定的宽限期(不同类型的软件宽限期可以不同,但最低宽限期应当法定),在宽限期内,“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然以旧版本的“协议”为准。
第三,宽限期届满后,软件服务商应在用户电脑上停止相关软件的运行,并以明确可见的方式向用户说明原因。如果软件服务商没有停止相关软件的运行,则视为“协议”更新失败,“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仍以旧版本的“协议”为准。
第四,宽限期内,如果用户启动相关软件,则软件服务商应以明确可见的方式通知用户,通知内容至少应包括:协议变更的请求,协议变更理由,新协议的内容,宽限期的长度,宽限期届满后的法律后果。并可以“点击许可”的方式要求用户对“同意”或“不同意”按钮进行选择。为了给用户以一定的考虑时间,宽限期内,用户即使点击“不同意”按钮,软件服务商也不应停止用户电脑上相关软件的运行。“同意”按钮必须设置两次以上,以免用户误击。如果用户点击最后一次“同意”按钮,则视为“协议”更新成功,“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从最后一次点击“同意”按钮时起以新版本的“协议”为准。
第五,如果软件属于付费软件,宽限期满后,当软件服务商在用户电脑上停止相关软件的运行时,应向用户支付相应补偿:如果原“协议”对付费软件的服务时间有一定限制,那么补偿应按照剩余服务时间在约定总服务时间中的比例支付;如果原“协议”对付费软件的服务时间没有限制(一次付费,终身使用),则软件服务商则应退还用户支付的全部价款。如果软件属于免费软件,宽限期满后,当软件服务商在用户电脑上停止相关软件的运行时,不用向用户支付补偿。相应的,在宽限期的规定上,免费软件的宽限期应长于付费软件的宽限期。
第六,以下信息应保留在服务器和用户电脑的相关软件当中,软件所有者与用户不得对其进行更改:1、软件的版本信息;2、协议更新通知的时间、形式和内容;3、点击相应按钮的时间;4、按钮上的文字。国家可法定第三方权威机构,对上述信息进行备份。
五、对“随时中断和随时修改条款”的分析及立法、司法对策
“腾讯特别提请用户注意:腾讯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和调整的自主权,腾讯拥有随时自行修改或中断软件授权而不需通知用户的权利,如有必要,修改或中断会以通告形式公布于腾讯网站重要页面上”——这个“随时中断和随时修改条款”在QQ2007以后的安装包附属的“协议”当中均未发生改变。这个条款是“协议”的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条的题目叫“法律责任与免责”,对照条款前后文可以发现,这个条款所规定的并不是用户违约之后腾讯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而是无论用户违约与否,腾讯都予以保留的一项权利。而这一“权利”就是腾讯公司对用户软件实行“不兼容”处理的法律依据之一。舆论习惯用“霸王条款”来形容类似的合同条款。但笔者以为,“霸王”的不仅是这一条款的内容,更是这一条款的所属位置。如果大众普遍知道,一个软件在装入自己的电脑后可以随时被软件服务商“自行修改或中断软件授权而不需通知”,那么这个软件的销路肯定会受到影响。腾讯QQ既可以打开销路又可以在“协议”中加入类似条款,其利用的,一方面是我国网民淡薄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则是这个条款的隐秘位置。
还是以QQ2007所属“协议”为例,据笔者统计,第四条第二款(也就是“随时中断、随时修改条款”)前至少还有59个条款,共7633字。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虽然“协议”第四条第二款中中使用了“特别提请用户注意”的措辞,但是,在一个大小不足20厘米见方的对话框里,反复下拉,看上近七千多字的法律语言,然后发现这个“特别注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对于缺乏法律素养的大众而言恐怕更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提起对方注意”的方式很难说符合《合同法》三十九条的“合理”要求。
在国外的相关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2002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Specht v. Netscape13. 参见Specht v. Netscape, 306 F.3d 17 (2d Cir. 2002).一案的判决。在该案当中,被告Netscape公司在提供软件下载服务时,将软件许可条款的链接放在了网页的最底端,必须将页面下拉很长一段距离才能看到,然后擅自推定,如果用户下载了软件就是同意了这些条款。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被告Netscape对其许可内容“缺乏准确表达”(regardless of apparent manifestation),造成“合同意愿表达不明”(contractual nature is not obvious),因此判决原告Specht不受该许可协议约束。可以说,腾讯的行为与Netscape在该案中的行为高度相似。
条款内容的“霸王”是由条款位置的“霸王”所引起的。如果腾讯将类似条款置于其网站、软件安装界面或运行界面的醒目位置,估计很少有人会下载QQ软件,而要打开销路,腾讯就不得不取消类似条款。因此,笔者建议,在软件上市之前,相关主管部门应审查其“许可协议”,并按《合同法》三十九条的要求,责令软件服务商将类似条款移动至醒目位置,以期“合理”地“提请对方注意”,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纠纷。
六、结语
2014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腾讯诉奇虎360不正当竞争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奇虎360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这场沸沸扬扬的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腾讯与360之争是目前为止我国信息技术史上最严重的法律纠纷,整个案件的基调从一开始就被定格在“反不正当竞争”,而作为这场争端最大受害者的广大软件用户则被排除在了这个法律关系之外。
腾讯的“不兼容”行为曾经深刻地刺激了网民的“权利是非感”,不用任何的解释,网民们就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并将其诉诸于法律话语,尽管这些法律话语很难符合“软件许可”这一全新的法律关系。面对舆论的沸腾,腾讯公司也不得不保持谨慎的态度,称自己也是在承受“难以承受之痛”【4】。因此腾讯公司也绝不会向大众搬出“协议”中的上述两个条款,那样做只能是火上浇油。
这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典型的法律现象,在法律的半真空状态当中,企业一方面痛陈虚情以应付舆论,一方面构筑法律壁垒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虚情是阳性的、多变的、可见的;法律壁垒是阴性的、稳固的、难以察觉的,只有到了诉讼中才会浮现出来。如果对其法律壁垒不加以研究和宣传,“不兼容”或者“强行安装”的事件就会一次次重演,而对公众的所谓“交代”也不过是一次次的安抚或者“危机公关”。QQ医生所绑定的只是聊天软件,而“软件许可协议”所绑定的则是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机关。
我们必须开始关注,所谓“软件许可协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法律行为,他的性质和效力究竟如何,他的移植在中国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而目前我国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立法还非常薄弱,以至于腾讯公司将部分“协议”的管辖权定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市”14. 参见腾讯QQ2007Ⅱ软件安装包附带“软件许可协议”附件一:“高通授权协议”第九段:“本授权协议适用加利福尼亚洲的法律进行解释,不适用冲突法则。对本授权协议的解释或强制执行,应提交至加利福尼亚洲的圣地亚哥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解释或执行。”,而早在2008年,就已经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类似的规定可能已经触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5】。所谓“随时变更、随时中断和随时修改条款”绝不仅仅在腾讯QQ的“软件许可协议”中才会出现,如今,类似的条款已经越来越快地在国产软件的安装包中蔓延,在各网站和各种网络游戏的“网络服务协议”【6】中蔓延。
信息技术的大潮无论在公法还是私法领域都对中国的法律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加快信息技术的研究和立法,结束互联网的“丛林状态”,这一切都刻不容缓。

【1】至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EB/OL】【2013-11-10】. http://im.qq.com/qq.shtml.
【2】陈明. 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协议法律效力分析【D】. 厦门:厦门大学, 2006.
【3】安雪梅. 朱雪忠. 论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的法律障碍——以英特尔诉东进公司案为主要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8):547.
【4】难以承受之痛的背后——致QQ用户的第二封信【EB/OL】【2013-11-10】. http://im.qq.com/index.shtml.
【5】童正伟. 请求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建议申请书(反垄断执法的举报信)【EB/OL】【2013-03-30】.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7a1cb070100b4h4.html.
【6】屠世超. 林国华. 网络服务用户协议的效力探析【J】. 电子商务, 2008(4):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