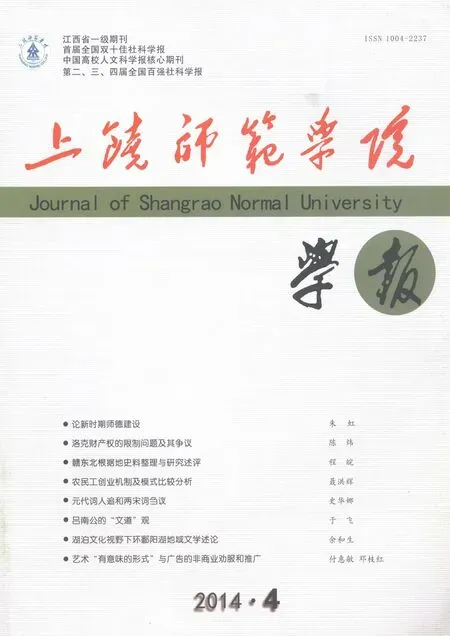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张爱玲的研究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既是一个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存在,又是一个饱含争议的人物。让笔者难以着手的原因还在于张爱玲身上所潜在的复杂性,一方面她博采众长,研究她需要调动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20世纪出现的各种文学思潮,在张爱玲身上几乎都有所呈现。一直以来,张爱玲都被视作40年代后期海派的代表人物。她的小说既包含了世俗的情与爱,同时又兼具现代主义色彩,尤其是《金锁记》与《倾城之恋》等以乱世的爱情故事和残酷的人性著称的作品,得到了文学界的大力赞扬。但张爱玲骨子里对现实的关注和对整个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洞察,并因此而呈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然而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倾注,使得她的小说在浪漫之余,显示出理性思考的深度。
一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于本世纪初。梁启超最先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1](P20)而真正从文学思潮上来谈论现实主义的是陈独秀。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写实文学”[2](P94),率先提出了建设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20年代,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盛,国外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尤其是俄国和东、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期,在借鉴外国作品的同时,现实主义也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创作热潮。乡土小说和世态讽刺小说的兴起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水平的提高。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兴盛,使得现实主义出现新的变化,“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 大多数作家, 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 都‘转变’了。”[3](P803)不仅如此,随着1931年左翼联盟的成立,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是逐渐成为法定的文学创作方法,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现实主义越发呈现出一种开放的色彩,作家们纷纷将他们犀利的现实主义解剖刀伸进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层,切合民族解放的时代命脉,对现实生活的黑暗进行暴露,同时在另一个方面,又开始向传统回归。而到了50至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是凭借超文学的力量,获得了独霸天下的地位。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政权的高度统一,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不断中心化,现实主义发生了畸变,成为极“左”路线统治人民的工具。进入8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的情况有所好转,学者们逐渐意识到“19世纪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成为今天必须固守的惟一模式,现实主义与其他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碰撞与融合中,必须创造出新的形态,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对文学的要求。”[4](P39)于是大量非现实主义的因素进入现实主义的维度,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再局限于写社会重大事件,不再仅仅关注人的阶级属性,而是在保持传统现实主义描写方式的基础上,注重人的直觉描写、意识流心理的刻画,以此来探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终极意义等永恒性的课题。
承接这条梳理的脉络,有学者就对现实主义进行了一个宏观的概括,以期全面地掌握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真正内涵。王嘉良就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中将现实主义分为了以下几类:一是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型现实主义,他们以18世纪欧洲启蒙思潮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为基础,强调文学创作的启蒙意义。二是以茅盾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其紧密联系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强调创作要“倾其全力于社会问题”。三是周作人领军的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着重关注人及人性的问题。此外,还有关照人生、描写风俗文化、重视“心理体验”,强调“政治阐释”等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王嘉良的这种具有总结的意义的研究,充分说明,现实主义的宽泛性,它不再仅仅只是对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机械反映,它也可以触及人的心灵,对个体的生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从现实主义的百年蜕变之中,我们可以断定,现实主义到了后期,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大量地采用非现实主义文学技巧,将自然主义的精致写实、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流的描写技巧和传统的象征、梦幻、寓意等表达方式兼容并包,在叙述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和情结的安排上也进行努力地探索。这就昭示了如果我们以整体的观点去关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很多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作家也同样可以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行列。将这一点反映在张爱玲文学创作的研究上,我们将会发现,作为后期海派领军人物的张爱玲其实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二
张爱玲开始文学创作之时,正是中日混战的4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新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肩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不管是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还是国统区文学,都呈现出同一趋势:即将文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尤其是沦陷区文学,将笔触伸向普通人的生活,在艺术上呈现雅俗交融的局势。应该说30年代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本时期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时代的诟病仍然是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张爱玲的创作虽说不关乎政治,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她的影响还是颇深的。1943年,张爱玲写了大量的国文作品。尽管张爱玲不像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热衷,然而随着涉猎的增多和对古代传统小说写作技巧的吸收,张爱玲的这些国文创作也因之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张爱玲开始创作之时,年龄甚小,但文学作品的质量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从文章的细节之中,我们可以窥视出其对于当时盛行的文学思潮的选择和吸收。突出社会矛盾,反映平常人的真实生活是此时期张爱玲作品主要的思想取向。她以对现实的真切关照,相继创作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封锁》《琉璃瓦》《金锁记》等小说。从这些早期的文学作品来看,张爱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文本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的笔法, 表现出对人性和现实的不满。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年轻女子葛薇龙为躲避战乱来到香港,投奔姑姑梁太太。梁太太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将侄女作为交际的砝码。薇龙在交际生活中自甘堕落,最终沦为司徒协、乔琪乔等人的玩偶的故事,将此时期社会的世态炎凉展现的淋漓尽致。小说《倾城之恋》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于中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张爱玲独辟蹊径截取了战争的一个侧面——战争中的爱情,借由白流苏和范柳原若即若离,勾心斗角的爱情战争,描摹出战争的另一种真实。乱世中 生活百态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封锁》则通过一对男女在公车封锁中的爱恋以及下车后爱情的变质,将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劣根性暴露出来。此外,《白玫瑰与红玫瑰》描写“正人君子”佟振保的道貌岸然,《琉璃瓦》道出了普通百姓婚姻变化的无常,《金锁记》诉说金钱社会的悲哀。这些小说将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一解剖,准确地把握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内涵。张爱玲用朴素的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出中国平凡百姓家常生活的困境,并对他们的遭遇寄予广泛的人道主义同情的文学创作范式,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呼应。
而在创作方法上,张爱玲同样采取了写实的手法。张爱玲本人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的写实功夫,她说道:“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5](P233)传统小说《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同样反映在张爱玲的创作之中。小说《花凋》取自真实的生活。小说主人公郑川娥一家是张爱玲的某个舅舅一家的真实写照。小说通过叙写郑四小姐的悲惨一生,告诉人们金钱社会亲情的冷漠。言辞之间,充满了对主人公的同情。在整篇文章的建构中,张爱玲刻画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她笔下的郑川娥处在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中,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排行老四的她受尽屈辱。张爱玲通过郑川娥谈恋爱,生病过程中家人态度的转变,真实地再现出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薄。综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整个《传奇》时期的小说创作,张爱玲都立志于展现腐朽的旧上海,描摹乱世中形态各异的人生本相,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40年代中期,张爱玲受到胡兰成的牵连,被贬为“文化汉奸”,小说创作一度停顿。颇具玩味的是,此时期的张爱玲居然开始了她并不擅长的诗歌创作。其中有一首诗歌《中国的日夜》,一反张爱玲以前创作的风格,颇有政治抒情诗的意味。诗歌基调昂扬向上,反映出扫除日寇后,中国大地的生机勃勃。这在某个层面上宣告了张爱玲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与诗歌一样,张爱玲中期的小说创作在世俗人情外多了一份政治领悟。一向与政治绝缘的张爱玲,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起政治来。在小说《十八春》《小艾》中,张爱玲穿插了不少与革命有关的片段,虽然稍显生硬,但也看出张爱玲对此类创作的热忱。《十八春》总体上来讲是顾曼祯和沈世钧的爱情故事,但字里行间,作者流露出的是对造成二人爱情悲剧的旧社会的批判,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十八春》可以算是一部具有批判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刻画了旧社会中的各类人物,非常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祝鸿才为代表的商贾,贪婪、自私、残忍,在霸占了曼璐之后,淫性不改的他又看上了曼祯,并将其侮辱;曼璐代表了下层人民不幸、悲惨、自私。曼璐敢于承担家庭重任,不惜出卖肉体来养活家中老小,可谓可叹可敬。但亲情最终却抵不过一己之私,曼璐选择牺牲妹妹,直接导致了曼祯的人生悲剧;叔惠代表的有志青年,自尊、自爱、自强。叔惠看穿了造成自己不能与翠芝结合的真正原因在于旧制度,因此他决定投奔解放区。《十八春》虽然没有正面提及革命,但我们从文本行进之中,还是能看到张爱玲对革命态度的转变。不管出于应时还是其他何种理由,张爱玲在这一时期已经无法完全对政治视而不见。尤其是在叔惠等人的处理上,我们可以见出张爱玲试图融入政治的努力。尽管有刻意为之的嫌疑,其对现实主义的运用也不太成功,但叔惠、世钧、曼祯三人探讨革命的场景,曼祯与叔惠关于革命的对话,及其翠芝、叔惠、世钧、曼祯等投身工业建设的结局(在修订本中张爱玲将革命删去,改成了美国),都体现出张爱玲现实主义的文学追求。
张爱玲曾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中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5](P279)张爱玲确实将真实贯穿于她文学创作的始终。虽说在政治上,张爱玲有不少应景之作,包括后来备受人们苛责的《赤地之恋》《秧歌》,但实际上自始至终张爱玲就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在她的文章中,张爱玲多次提及自己的创作,“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5](P278)张爱玲显然是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但在小说创作上,张爱玲又分明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她的文学创作虽然运用了很多西方小说的技巧和创作方法,颇为重视感觉和心理的描写,但是,细细比对,又发现与施蛰存、刘呐欧等人的气质不同。她的小说有着很明显的哲学、心理学痕迹,然而却不乏现实主义的力度。
小说《小艾》发表于50年代初的《亦报》上,被看作《十八春》风格的延续。小说通过描写小艾在解放前后身份的变化——从被席氏夫妇侵压到翻身做主人,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以及国统区的腐败。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张爱玲继续发挥她卓越的天资,将心理描写运用的炉火纯青。尤其在对人物进行剖析时,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压抑得到了很好地挖掘。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后一部分通过记叙冯金槐奔赴后方,小艾继续坚守在上海,经过一番苦难,上海解放,二人团聚,过上崭新的生活,光明的尾巴暗示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张爱玲对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刻意涉及,尽管在艺术上并不成功,但毋庸置疑其现实主义倾向还是非常鲜明的。
整个40年代直至50年代初的作品,当我们把时代的维度从社会历史范畴降落到个人身上时,不难发现,这个阶段,张爱玲的创作尽管不属于“抗战文学”,但她的“情”和“爱”并非完全超然于时代之外。在对待现实的关系上,不但没有拒绝与生活的关联,反而以她自己的方式描摹着现实社会的点点滴滴。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写作方式的坚持,使得张爱玲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外,能够深入人的内心,描写出人心理和精神上的现实。在坚守文学本质的同时,张爱玲试图将心灵的絮语和绝望的现实统一,不管是人物书写还是残酷事实的揭露,都立足于呈现人物最真实的情感。应该说,张爱玲是一个不完全的海派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具有现实关怀的海派作家。张爱玲前期和中期大量具有海派色彩又不失现实感的作品,既是社会的,又是生命的。她在探寻生命存在奥秘,追求人类整体的形而上的关怀的时候,一直坚持以现实为蓝本。
1955年,张爱玲奔赴美国。从香港到美国,身份的飘零,环境的改变,离乡背井的孤独感久久地萦绕着张爱玲。从而使得张爱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作为异国的作家,她甚至一度陷入名气的衰微和经济的困窘之中。在这一时期,张爱玲的创作也同样陷入瓶颈。从她对《金锁记》和《十八春》的修改,就可以看出,张爱玲恢复了早期对政治的漠视,但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她仍然十分关注。《怨女》《半生缘》两部作品虽然整体上看来是失败的,但无可否认文本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揭示依然很出彩。
张爱玲在海外的四十来年,除了将50年代创作但并未发表的小说《五四遗事》《相见欢》《浮花浪蕊》发表外,她也创作了一些小说。这些小说大多都执着于反映移民漂泊的悲苦命运,在戏剧化的创作场景之中,真实地再现时代的巨变和人生的苦难,同时寄寓作者自身的历史感遇。《浮花浪蕊》写的是女作家洛贞辗转于香港和日本之间,只身闯荡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张爱玲个人的人生遭遇吻合。小说对生活细节的描写非常逼真,充分展现了写实主义的特点。相较而言,《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在写实的基础上,更具深度。小说从反面来描写了五四运动,尤其是对五四所谓的反封建反包办婚姻的主张进行了反思。通过主人公罗文涛追求婚姻自由的失败,说明了现实生活中五四精神的变质。这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辉。《色·戒》是一部革命题材的文章,小说讲述了王佳芝打入汉奸头子易先生团伙内部,结果却爱上易先生,反被易先生所害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显然因不了解革命的实际,而仅仅依据胡兰成的转述,造成了小说主题思想的混乱。但在艺术上,张爱玲那种把握人物内心真实的本领仍然颇见功力。70年代,随着纪实小说的盛行,张爱玲也开始着手写自己的传记小说《小团圆》。《小团圆》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者现实生活艺术化的反映。很多片段都与张爱玲的亲身经历相关。《小团圆》达到了真实与虚构的完美结合。不仅叙写严格遵循历史事实,甚至在细节上张爱玲也做到了从生活实际出发。邵之雍、九莉以及旧家族的衰落都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她冷静地用第三只眼睛来审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描绘历史主体在历史转折时期复杂的心灵历程,有力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书写形式。
虽然,诚如于青所说,“张爱玲确实喜欢临水照花,但并不自怜自爱,于其说她在临水照她自身,不如说她在静静地映照着她周围的所有世界。仅仅是她周围的,与她有关的。”[6](P69)张爱玲或许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走上现实主义之路,她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她抒发个体生命体验,追寻生命超越意义的创作过程之中,40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百相,50年代移民生活的艰苦,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展现。张爱玲是真正做到了现实和现代兼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此消彼长,始终贯穿。
三
作为公认的后期海派的代表人物,张爱玲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倾向,耐人寻味。尤其是她早期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借鉴和晚期对纪实文学的热衷尤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初的思想启蒙、变换的成长环境、读者的接受及其作家所秉持的文艺观对其创作风格影响都是巨大的。张爱玲的父亲是清朝遗少,喜读诗书,母亲接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在父母的影响下,张爱玲从小就爱读《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又涉猎了西方一些现实主义大家的作品。张爱玲自己就曾说:“是的,我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呢。”[7](P129)在东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下,张爱玲的创作自然大多立足于反映现实人生。40年代,国内社会现实十分严峻,中日交战,苦不堪言。严酷的社会环境,悲惨的人民生活,促使她自然而然地要去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而当战争结束后,她因政治、经济的各种原因,移居美国。美国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生活带给她全新的生命体验。环境的格格不入很容易使她将自己的个人体验与50年代流落海外的内地移民飘零落魄的悲苦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创作出颇具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事实证明,在这段时期,她不仅创作了直接反映社会现状的小说,即便是在自叙传作品中,也流露出了对现实的关怀。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深谙接受美学。她知道,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在潜意识里早已形成了对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和创作方法的接受心理,对描写现实,贴近生活的文学体裁有着一种天然的偏好。或许正是由于读者的喜好,影响了张爱玲对创作方法的追求和选择。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提到:“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7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8](P5)作为一名视读者为生命的作家,张爱玲是做到了时刻将作品、作家及其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恒久不变地叙写着小人物的真实。
因此,可以说,张爱玲虽然崇尚自由,有着海派作家的气质,但她在本质上仍然怀着一颗关怀现实之心。虽然,政治上的软弱,曾使得她一度动摇,逃避现实,转而跑到爱情的世界去疗伤,但骨子里的精神追求,让她并没有一味消沉,而是将精神的希冀与现实的追求统一于心理体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书写风格。从张爱玲的创作看来,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现代主义忠实于个人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主义忠实于生活本身在内核上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张爱玲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缘由的,若以机械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张爱玲的创作,显然会抹杀张爱玲的多元性。笔者认为,张爱玲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时代存在着深层关联的偏向于精神和心理上的现实主义(当然她也有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她与时代始终保持着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虽然她的写作不像一般现实主义作家反映时代那么明确彻底,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生命的维度上,张爱玲是以个人的感受对现实生活进行回应的。虽然张爱玲的故事总是披着爱情与现代的外衣,但毋庸置疑,张爱玲对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表现出了一种深远的关怀。从她的创作个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应当明白,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学思潮就能概括的。在一定条件下,作家可以对创作方法进行改造,剔除陈旧的,引进新鲜的,使旧方法焕发出新生机。张爱玲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存在, 而是与各种创作方法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20世纪中国文论经典[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3]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宁秀丽.文艺探索书系与当代文艺思潮[D].上海师范大学,2007.
[5]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6] 于青.奇才逸女——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
[7] 胡辛.最后的贵族—张爱玲[M].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5.
[8] 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