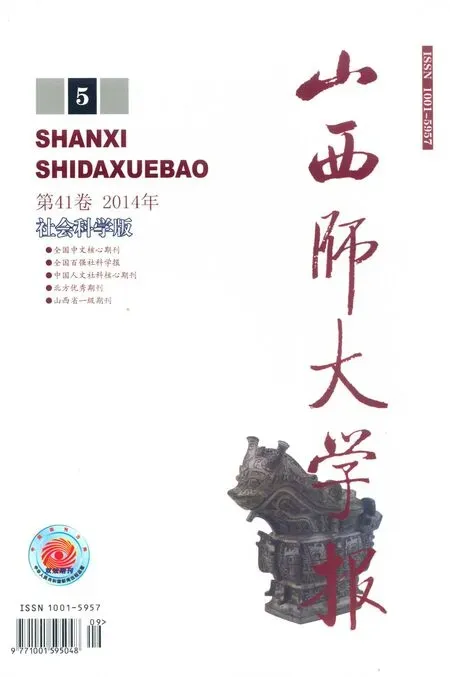汉代楚辞之“游”的新变及其成因探析
姚 圣 良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在战国屈、宋等人之外,王逸《楚辞章句》还收录了汉人的七篇楚辞作品,分别是贾谊(或无名氏)《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和王逸《九思》。汉人这些楚辞作品皆是屈原《离骚》、《九章》的模拟之作,后世亦称之为汉人拟骚作品,对其评价也不高。汉人这些楚辞作品,多有游仙描写。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楚辞的“游仙”在模仿屈原“神游”的同时,又发生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变。
一、从神游到游仙
汉代楚辞的模仿对象主要是屈原的《离骚》和《九章》。王逸《楚辞章句·九思序》云:“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1]314屈原所处的时代,仙话已经产生,而屈原本人也确实接触到了仙话,如《天问》就问到了一些早期的仙话传说:“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又曰:“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所问分别为“嫦娥奔月”与“彭祖长寿”的仙话故事。然而,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却无一处涉及仙话传说。《离骚》与《九章》中的“游”,主要还是以楚地流传的昆仑神话为背景,游历过程中所遇到的也都是神话世界里的神灵,属于神游而非游仙。
从屈原的《离骚》、《九章》到汉人的拟骚作品,楚辞之“游”发生了由神游向游仙的转变。汉代楚辞中已经出现了有名的仙人。如《惜誓》云:“临中国之众人兮,讬回飚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乔皆在旁。”赤松和王乔都是著名的仙人。赤松即仙人赤松子,《列仙传》云:“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2]1王乔即仙人王子乔,《列仙传》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2]9又如《七谏·自悲》云:“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借浮云以送予兮,载雌霓而为旌。”王逸注曰:“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1]250再如《九思·伤时》云:“蹠飞杭兮越海,从安期兮蓬莱。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台。”安期即仙人安期生,《列仙传》云:“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度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双为报,曰:‘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逢风波而还。”[2]10汉代楚辞中还出现了神仙方术,如《惜誓》云:“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王逸注曰:“众气,谓朝霞、正阳、沦阴、沆瀣之气也。”[1]229《七谏·自悲》亦云:“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九思·守志》又云:“随真人兮翱翔,食元气兮长存。”“食气”就是一种神仙方术,神仙家鼓吹通过“弃五谷”而“餐六气”,人最终就能够达到成仙不死之目的。汉代楚辞之“游”,正是因为仙人与神仙方术的出现,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仙。
汉代社会神仙信仰盛极一时,确实与汉代帝王追求神仙长生有直接关系。据《史记·孝武本纪》载,方士栾大被汉武帝宠信时,“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后汉武帝东巡海上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3]464—474在这一万民造仙的背景下,神仙信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作家提供了大量的仙话传说,汉代楚辞之“游”也因此实现了从神游到游仙的转变。
二、由神圣到世俗
从屈原的神游到汉人的游仙,楚辞之“游”亦发生了由神圣向世俗的转变。屈原之“游”的神圣感,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神灵自身的神圣性。屈原神游过程中所遇到的神灵,都来自于早期的神话传说。这一时期的“神话”,既没有经过秦汉“仙话”的改造,也没有被魏晋“鬼话”所浸染,是“神圣性”尚未减退的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神话。二是屈原对神灵的企求与依恋。屈原的神游,是现实社会“美政”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追求。屈原虔诚地向神灵陈诉,努力寻求与神灵的沟通,渴望得到神灵的理解和肯定,是因为神灵世界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黑白颠倒、贤愚不分,那里有屈原向往的正义与公平。屈原的神游,带有执著于理想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精神追寻。
汉代楚辞之“游”,则有着鲜明的世俗化特点:一是游仙路径开始从天界转向人间。屈原的神游,基本上是在遥远的天界巡游;而汉人楚辞作品中的游仙,游历的踪迹竟出现了不少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地点。如《七谏·自悲》云:“苦众人之皆然兮,乘回风而远游。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娱以忘忧。……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诗人的游仙,已经不完全是在虚无缥缈的天界;而是“凌恒山”、“至会稽”,往来于亦真亦幻的现实世界之中。在会稽山上,诗人不仅拜见了仙人韩众,而且还在他那里留宿,并向他请教神仙长生之道。李泽厚先生说过,汉人心目中的神仙世界,“不是与现实苦难相对峙的难及的彼岸,而是好像就存在于现实人间相距不远的此岸之中”[4]121。汉代楚辞作家将神仙世界移入到现实世界之中,其所反映的正是汉人神仙观念的这一特点。汉人楚辞作品中游仙描写由天界向人间的转变,拓展了游仙诗的艺术想象空间,对后世游仙诗创作影响甚大。如曹植的《飞龙篇》,就将游仙遇仙的地点设置在东岳泰山:“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5]421二是世俗生活气息。如《惜誓》云:“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王逸注曰:“言赤松、王乔见己欢喜,持瑟调弦而歌。我因称清商之曲最为善也。”[1]229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见到诗人非常高兴,他们奏乐、歌唱以欢迎诗人的到来,还与诗人一起探讨清商曲的美妙。再如《九怀·昭世》云:“闻素女兮微歌,听王后兮吹竽。”《九思·伤时》亦云:“使素女兮鼓簧,乘戈龢兮讴谣。声噭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婬。”汉代楚辞有关仙人奏乐、歌唱的这些描写,颇具世俗生活情趣。三是世俗享乐意识。如《惜誓》云:“苍龙蚴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后车。”王逸注曰:“载玉女于后车,以侍栖宿也。”[1]228再如《九思·守志》云:“历九宫兮遍观,睹秘藏兮宝珍。就傅说兮骑龙,与织女兮合婚。”汉代楚辞的这种游仙描写,带有明显的追求世俗享乐的色彩。
汉代楚辞游仙描写的世俗化,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汉人渴望成仙不死,主要是为了享受快乐的神仙生活,并非仅仅因为神仙可以长生不死。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说道:“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6]2596在司马相如看来,像西王母那样的长生不死就不足以让人羡慕。于是汉人就按照世俗的幸福生活标准,对西王母的形象进行改造。汉人先让西王母变成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女仙,然后又给她配个丈夫叫东王公,夫妻二人分别做男仙与女仙之主。这样汉人才算满意了。西王母的形象在汉代的演变,正是汉人神仙信仰追求世俗享乐的结果。《大人赋》亦有与汉代楚辞相似的游仙描写:“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7]2596可见,汉代楚辞游仙描写的世俗化,乃是汉人神仙信仰追求世俗享乐特点的反映。
三、从悯宗国到哀时命
楚辞之“游”从神游向游仙、由神圣向世俗转变的同时,抒情主体的思想境界与情感诉求也发生了从悯宗国到哀时命的转变。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以对宗国故土深挚的爱恋为基础的。刘熙载曾称屈原是“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7]8。屈原本应该“有路可走”,不管是放弃理想、随波逐流,还是远走他乡、另投明主,现实困窘皆可迎刃而解。然而,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宗国故土的无限眷恋,决定了屈原最终会“无路可走”。在《离骚》的结尾处,当诗人对楚国的黑暗现实深感绝望,决定远走他乡、另寻明主的时候,诗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震撼人心的戏剧性场景:“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的神游过程,至此戛然而止。幻想中的神游之乐与现实中的矛盾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巨大的反差。朱熹《楚辞集注》云:“屈原托为此行,而终无所诣,周流上下,而卒反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之尽也。”[8]26通过这一戏剧性的场景描写,诗人的爱国情感得到了艺术升华。
汉人模仿屈原创作楚辞,对屈原的情感认同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1]182与宋玉一样,汉代楚辞作家也是因为悲悯屈原,才拟骚以代屈原立言的。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及作家个体人生体验的不同,汉代楚辞虽是代屈原立言,但抒情主体的思想境界与情感诉求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从悯宗国到哀时命的转变。《惜誓》开篇即云:“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这里的“余”无疑是指屈原。紧接着便是“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开始了游仙描写。但在游仙之后,诗人却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麒麟如果不得“时”而出,其命运将会与犬羊有什么两样呢?“时命”之叹,已初现端倪。到了东方朔的《七谏·哀命》,诗人以意名篇,汉代楚辞的“时命观”得以凸显。其诗云:“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内怀情之洁白兮,遭乱世而离尤。”诗人将屈原的人生悲剧,归因于“时命之不合”。严忌的《哀时命》,更是题旨明确,且单独成篇。诗人开篇点题:“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接下来,诗人以“道壅塞而不通”、“江河广而无梁”、“无羽翼而高翔”来突出“进”之难,游仙幻想也由此而引发。游仙描写之后,诗人则又萌生了“退”而避害、远祸保身的想法:“鸾凤翔于苍云兮,故矰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在诗篇的结尾处,诗人最终发出了“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恐不终乎永年”的人生哀叹。严忌的《哀时命》,可视为汉代楚辞“时命观”的典型代表。之后,王褒《九怀·通路》有“启匮兮探策,悲命兮相当”,刘向《九叹·愍命》亦有“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王逸《九思·伤时》又有“时混混兮浇饡,哀当世之莫知”。自《惜誓》至《九思》,汉代楚辞之“哀时命”,可以说是贯穿始终。
屈原也有生不逢时的哀怨,如“哀朕时之不当”(《离骚》)、“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九章·涉江》)等,但这些只不过是诗人“美政”理想受阻时的几句牢骚语而已。到了汉代,“哀时命”却成了拟骚作品的重要主题。汉人代屈原立言而伤时哀命,实际上抒发的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感慨。汉代楚辞的“哀时命”主题,是汉代“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汉代“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形成,使士人失去了战国时期游说诸侯、直取卿相的客观条件,只能做汉家天子忠顺的奴仆。士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完全掌控在君主手中。士人与君主的关系,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的那样,“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6]2865。汉武帝时期可谓太平盛世,竟然会同时出现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和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原因就在于此。汉代楚辞之“哀时命”,正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
四、由殉国到退隐
在《离骚》的结尾处,屈原明确表达了将要以身殉国的决心:“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登天神游、上下求索之后做出的人生抉择。
汉代文人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但对于屈原的以身殉国却并不赞同。《汉书·扬雄传》云:“(扬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6]3515扬雄认为君子如果遇到好的时机就应该大行于世,若时机不好就要像龙蛇那样隐藏自身,遇与不遇都是命中注定的,何必自杀殒身呢!与扬雄一样,汉代楚辞作家也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在《惜誓》的结尾处,诗人云:“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认为屈原应该“远浊世而自藏”,以此来保全自己,这样才合乎“圣人之神德”。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惜誓者,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谊意以为原之忠贞既竭,君不能用,即当高举远引,洁处山林,从松、乔之游。而依恋昏主,迭遭谗毁,致为顷襄所窜徙,乃愤不可惩,自沉泪罗,非君子远害全身之道,故为致惜焉。”[9]159东方朔《七谏·谬谏》又云:“列子隐身而穷处兮,世莫可以寄托。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托。”认为“经浊世而不得志”,就应该“侧身岩穴而自托”。严忌《哀时命》亦有“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孰魁摧之可久兮,愿退身而穷处”、“时猒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可见,汉代楚辞作家是用道家的退隐保身来否定屈原的以身殉国。
汉代楚辞作家还把游仙与退隐相结合,开始出现了游仙隐逸化的倾向。如东方朔《七谏·自悲》云:“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居不乐以时思兮,食草木之秋实。饮菌若之朝露兮,构桂木而为室。杂橘柚以为囿兮,列新夷与椒桢。鹍鹤孤而夜号兮,哀居者之诚贞。”诗人“构桂木而为室”、“杂橘柚以为囿”,将隐居环境描写引入游仙过程之中,有“善鸟香草,以配忠贞”之用意,而游仙隐逸化倾向也由此而发端。到了严忌的《哀时命》,游仙隐逸化倾向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哀时命》在游仙过程中还具体描写了隐者居处的环境之美:“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雾露蒙蒙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九章·涉江》云:“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严忌的这段隐居环境描写,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但它又与屈原的描写有所不同。它退去了流放者眼中的凄清与蛮荒,变成了隐居者喜爱的空旷与幽静。于是在这一清静、幽美的环境中,诗人过上了与仙结友的隐居生活:“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在这里,游仙与退隐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汉代楚辞游仙与退隐的这一结合,开启了后世游仙隐逸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在游仙诗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代楚辞游仙与退隐的结合,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的人生观受道家思想影响所致。汉代社会虽然是儒学独尊,但道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汉代文人在仕途受阻时,总是转向道家的退隐保身以求解脱。汉代文人的人生观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导,相对来说,受神仙思想的影响还很有限。这是因为,汉人的神仙信仰毕竟还不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尚无法从根本上对文人的人生观产生影响。因此,汉代文人仕途受阻后,不可能在游仙中得到真正解脱,更不会将游仙作为最终归宿,于是道家的退隐便成为一种必然性选择。汉代楚辞的游仙隐逸化,正是文人对儒、道、仙诸家思想理性思考后人生追求的真实反映。
文学史上模拟之作一般都难以超越原作,汉人的楚辞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其价值和影响根本无法与屈原的作品相比。然而,由于时代及作家人生体验的差异,汉代楚辞之“游”在屈原神游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一些新变,正是这些新变使得汉人的楚辞作品成为了游仙诗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刘向.列仙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Z].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王夫之.楚辞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关于文学游仙的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