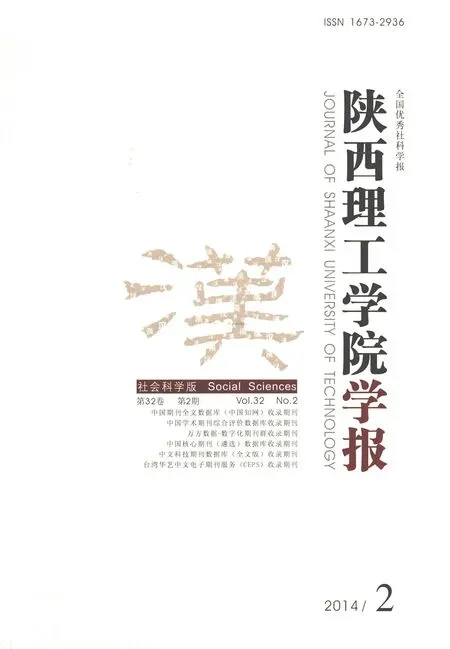元稹入蜀纪行诗及“百牢关”位置考辨
付兴林,马玉霞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百牢关是唐代由长安入蜀路途金牛道上的重要关隘,在唐代很长时期内因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常设关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百牢关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金牛道段线路亦不断迁移,百牢关渐被废弃以致湮没无闻。现存文献资料对百牢关的记载又较为粗略且多有抵牾,遂使后人对唐代百牢关的具体方位难以确认,这对研究唐代长安、陕南、蜀地间的交通、政治、军事乃至文学都造成一定障蔽。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在元和四年(809)到元和十二年(817)间,曾五次往返途经百牢关,留下20多首入蜀纪行诗。这些诗歌或记述旅途见闻,如入蜀路线、沿途风光、驿站格局及建制、历史典故、民风民俗,或抒写旅途对亲朋的思念,或表露对仕宦的复杂情感。因其记录行踪较密,且诗歌多有诗序或自注,故能借此补叙创作背景及地理状貌。正因如此,元稹的入蜀纪行诗为研究入蜀驿路特别是百牢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另,武元衡、于邺等人也存有偶涉百牢关地理位置的诗歌。是故通过元稹、武元衡、于邺等人的诗歌及相关史料记载,即可印证、考定唐代百牢关之确切方位。
一、元稹入蜀纪行诗
元稹的入蜀纪行诗主要创作于三个阶段:一是元和四年(809)三月到五月,元稹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返途中;二是元和十年(815)三月出为通州司马途中;三是元和十年(815)夏和元和十二年(817)夏秋因在通州任上患疟疾前往兴元(按:今汉中)养病的往返途中。
元稹两次由长安入蜀的线路相同,皆出长安、经骆谷、至褒城、抵汉中,再经西县,然后西南沿金牛道入蜀。这一线路可由其诗歌提供的线索推究按察。元和四年(809)使东川时纪行诗有:《骆口驿二首》、《南秦雪》、《邮亭月》、《黄明府诗》、《褒城驿》、《亚枝红》(自注“于褒城驿池岸竹间见之”)、《清明日》(“今日清明汉江上,一身骑马县官迎”)、《梁州梦》(自注“是夜宿汉川驿”)、《江上行》、《夜深行》(“夜深犹自绕江行,震地江声似鼓声。渐见戍楼疑近驿,百牢关吏火前迎”)、《百牢关》、《江楼月》(自注“嘉川驿望月”);元和十年(815)司马通州途中有《紫踯躅》、《山枇杷》(“往年乘传过青山”,青山驿在骆谷中[1])、《褒城驿二首》、《西县驿》、《题漫天岭智藏师兰若僧云住此二十八年》。由以上这些诗可清晰地勾勒出元稹入蜀的路线,其中由骆谷至西县段的线路甚明,而由西县至利州嘉川驿间金牛路的线路却因所常见的对百牢关位置错讹注释而存疑较多(其实这段路元稹走得更频繁,由通州至兴元养病时往返亦沿此路线)。元稹是唐代有诗为证途经百牢关最多的诗人,正如他自己所云:“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2]743也是以诗描述百牢关最多的诗人,现存入蜀纪行诗中有5首诗提到百牢关。
二、关于百牢关位置的诸多说法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2《山南道三·兴元府·西县》云:“百牢关,在县西南三十步。隋置白马关,后以黎阳有白马关,改名百牢关。自京师趣剑南,达淮左,皆由此也。”[3]560-561《两唐书地理志汇释·新唐书地理志汇释》地理四《兴元府·西(县)》云“西南有百牢关”[4]148,并以《元和郡县图志》上条补释。《陕西通志》卷3《汉中府·沔县》云“百牢关在县西七十里”、“白马关在县东一里”[5]108,不过这里的沔县是指东迁后现今的勉县城。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对白马驿的注解中也承《元和郡县图志》,注百牢关即西县白马关之改名[2]151。史念海的《河山集》“唐代前期关内道及其邻近地区军事形势图”、“唐代后期关内道及其邻近地区军事形势图”以及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山南东道山南西道”中,关于百牢关的位置也皆标于西县西南。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二三《金牛成都驿道》有“关于百牢关之位置,定其在(西)县西三十里,非三十步”,“宝历元年,(金牛)县省入西县,仍置金牛驿。后又移百牢关于此,盖唐末五代事矣,盖蜀人为缩短防线而内徙耳”[6]866-867之论述。严氏认为百牢关的位置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唐代前期在西县三十里,唐末五代时移至西南金牛驿。与严耕望观点相近者有周相录,他在2004年博士后论文《元稹年谱新编》中关于百牢关位置有以下论述:“此百牢关在嘉陵江岸,绝不可能为西出西县第一驿之‘百牢关’,张述栋、邓元煊、王珏繁《剑门关志》第一编《蜀道·金牛新道》云:‘上下七盘岭共二十里’,自注云:‘岭为秦蜀分界处,亦称百牢关。’七盘岭在嘉陵江岸,元稹赴东川又行经此处,故其所称当指此川、陕交接处之百牢关。”[1]周相录认为元稹诗中的百牢关位于现宁强县西南川陕交界处嘉陵江岸的七盘岭处,而非现宁强西南之七盘岭。
三、元稹等诗人诗中的百牢关方位考索
观元稹有关百牢关的诗歌,可以断定此百牢关必在嘉陵江畔,而非西县西南之白马关,亦非在金牛驿(此两驿附近之水皆为汉水而非嘉陵江)。
1.元稹等人诗中的白马关与百牢关
在元稹的诗中汉江与嘉陵江、白马关与百牢关是分得很清楚的。如《清明日》诗云:“常年寒食好风轻,触处相随取次行。今日清明汉江上,一身骑马县官迎。”[2]143《江上行》诗云:“闷见汉江流不息,悠悠漫漫竟何成。江流不语意相问,何事远来江上行。”[2]150《汉江上笛》诗云:“小年为写游梁赋,最说汉江闻笛愁。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自注曰:“二月十五日夜,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怅然忆得小年曾与从兄长楚写汉江闻笛赋,因而有怆耳。”[2]151这些诗中明确点明所历江水为汉江。而《百牢关》一诗写道:“嘉陵江上万重山,何事临江一破颜。自笑只缘任敬仲,等闲身度百牢关。”[2]154明确指出百牢关紧临嘉陵江。《夜深行》一诗写道:“夜深犹自绕江行,震地江声似鼓声。渐见戍楼疑近驿,百牢关吏火前迎。”[2]158写出百牢关在嘉陵江沿岸,且水势浩大,江声如鼓。又《江楼月》一诗写道:“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诚知远近皆三五,但恐阴晴有异同。万一帝乡还洁白,几人潜傍杏园东。”[2]148诗中描写江水时也点明所临之江为嘉陵江。所以元诗在提及江河时多明确指出江名——是汉水还是嘉陵江,且描写的嘉陵江水势明显大于梁州(按:今汉中)、西县之汉水水势。由对上引诗歌的解读可知,白马驿和百牢关显而易见是两处,白马驿在西县,百牢关在嘉陵江畔,且后者临近西南行的下一个驿站,其位置在驿站之北。
而白马驿,不仅元稹的诗中明确指出在西县,而且其他诗人的诗作也印证了这一点。如薛逢《题白马驿》诗云:“晚麦芒乾风似秋,旅人方作蜀门游。家林渐隔梁山远,客路长依汉水流。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7]6330诗中“家林渐隔梁山远,客路长依汉水流”(按:汉中到西县沿汉江)、“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按:西县有武侯墓),都指明是在西县境内之景、之事。且现所见唐代咏白马驿的诗中没有一首言及白马关即百牢关。由此我们更可断定,白马关与百牢关至少在中唐以来就是两处不同的地方。
2.从有关史料及元稹行进时间推测百牢关之位置
那么百牢关具体在哪里呢?“历史地理研究表明,古代自关中经陇右或汉中入蜀之‘蜀道’,在不同时期经由地和路线不同。蜀道汉中以西以南至成都段称金牛道,而金牛道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即先秦、秦汉时经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北白龙江右岸),唐宋时自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镇之西)以西以南循嘉陵江至利州,明清以后自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县北烈金坝)折南越五丁关经宁羌州(今陕西宁强)至广元。”[8]《唐代交通图考》有云:“《寰宇记》一三三《三泉县》‘后魏正始中置……唐天宝元年,自今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故县移理嘉陵江东一里关城仓陌沙少西置,即今县理也。’当置驿……地势峻险,又为水路交通冲要……宋世三泉以南江流亦有舟楫之利,想唐当无大异……自三泉南通利州之陆路,大抵亦沿嘉陵水东岸而行。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东岸行约六十里,至九井滩,最为险恶,为舟楫之阻,宋元祐中始整治稍平。又十里至五盘岭,杜甫、岑参皆有诗,盖置驿……又《蜀中广记》二四《保宁府·广元县》曰‘九井驿……其上为七盘岭,乃秦蜀分界处。’”[6]870-873由上关于三泉县、七盘岭山水地势驿路的介绍描述,我们可看出三泉县(驿)至七盘岭之间,且靠近七盘岭处极有可能就是百牢关所在之地。
再从元稹行进的时间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从武元衡《元和癸巳余领蜀之七年奉召征还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经百牢关因题石门洞》可知,其到达百牢关的时间为元和八年(813)二月二十八日。《旧唐书》载:“(武元衡)八年,征还。至骆谷,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9]4160《新唐书·宰相表》“元和八年”条则云:“三月甲子,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己巳,至自西川。”[10]1711今人研究认为:“则三月甲子(十一日)至骆谷当属可能,其时方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己巳为十六日,是日元衡方至京师。”[11]按此推算,武元衡从百牢关到骆谷的用时十二天,由骆谷到京师的时间为五天。而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七日使东川,行至褒城驿为三月十六日,用时十天,除去骆谷南口至褒城的两日路程(元稹出骆谷后西行,曾夜宿梁州汉川驿,到褒城已必为第二日),可知其由京师至骆谷南口用时为八日,比元衡略慢两三日。以武元衡从百牢关到骆谷用时十二天的行速比照,元稹由骆谷趋至百牢关当为三月二十八日前后。其《望驿台》一诗所提供的信息可与此推断恰成印证,诗曰:“可怜三月三旬足,怅望江边望驿台。料得孟光今日語,不曾春尽不归來。”[2]158《读史方舆纪要》卷68《广元县》云:“县(广元)北四十里有望喜驿,唐名也。今曰沙河马驿。”[12]3213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中注此望驿台在望喜驿左近。可知三月底元稹已达广元北四十里处的望喜驿附近,而此距七盘岭也就一两日的路程。除去这一两日的时间,正是我们推算元稹到达七盘岭附近的时间,这也正好证明了我们对百牢关位置的推断。郑馀庆《和黄门相公诏还题石门洞(黄门,武元衡也)》云:“紫氛随马处,黄阁驻车情。嵌壑惊山势,周滩恋水声。地分三蜀限,关志百牢名。琬琰攀酬郢,微言鼎饪情。”[7]3582有此诗所描述也可见出百牢关山势险峻、傍临江水、为秦蜀分界等特点。于邺《过百牢关贻舟中者》一诗曰:“蜀国少平地,方思京洛间。远为千里客,来度百牢关。帆影清江水,铃声碧草山。不因名与利,尔我各应闲。”[7]8316从此诗所提供的方域信息,也可印证百牢关当在入蜀路上,且江可舟楫。
3.对《元和郡县图志》关于百牢关位置误断的思考
百牢关,唐前未见此关名,初唐诗人诗中也未见提及,至安史之乱后方有吟咏,如杜甫、元稹、李商隐、于邺等人诗中渐见之,但数量并不多。《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作者李吉甫与武元衡、元稹乃同时代人,且曾同朝为官,武元衡更与李吉甫同日(元和二年)拜相,两人逝年只相差一年(李元和九年卒,武元和十年六月遇刺身亡)。武元衡元和二年(807)、八年(813)分别经百牢关,元稹元和四年(809)、元和十年(815)、元和十二年(817)皆经百牢关(按:元稹《百牢关》有句云“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由此可知,元稹所经之百牢关当与武元衡所经之百牢关必相同而无二。据此笔者推断,至少在盛唐安史之乱前后已见百牢关的关名,其位置已是在嘉陵江畔,而非西县,且百牢关在嘉陵江畔的时间最晚不会迟于中唐,晚唐五代诗中的百牢关也只能是嘉陵江畔的百牢关,李吉甫关于百牢关的注解明显与当时实际方位相左不符。
至于百牢关的位置是否如严耕望所说初在西县、晚唐五代始移至嘉陵江畔,笔者认为“迁移说”可能为解决疑难提供了另一思路,但是否真有这一变迁过程尚需有力的文献资料加以证明。事实上,随着时代变迁,百牢关战略地位的消失,金牛道的东移,人们渐渐模糊了百牢关的真正位置,而只是以讹传讹地注解下去。
综上,笔者认为百牢关至少在中晚唐时期位于三泉县西南约七十里处嘉陵江东岸、七盘岭北侧附近。
[1] 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D].成都:四川大学文学院,2004.
[2] 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 赵廷瑞.陕西通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孙启祥.杜甫、岑参诗中五盘岭地望考辩[J].杜甫研究学刊,2010(2).
[9]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鞠岩.武元衡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1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