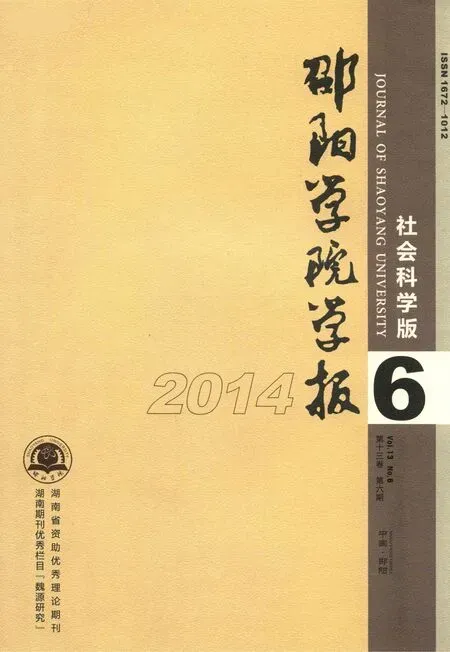无法言说的“言说”——试论福尔《特别响,非常近》
刘 霞
(1.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系,天津 300387;2.宁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宁夏 756000)
一、引言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文坛上出现了大量以9·11事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1977—)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以下简称《特》)以9·11事件为背景,是“后 9·11”小说的典范之作。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谈论9·11事件时,面对“九月的亡灵”,她“不知说什么好”;[1](P1-2)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9·11事件后不久接受美国哲学家博拉多莉采访时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发生了一件事,但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和事件本身的意义让人不可言说,难以形容……这件事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2](P92)“无法言说”成为“后 9·11”小说的一大特征。
《特》就是一部以独特的方式探讨灾难、创伤、失语与言说之间关系的小说。福尔采用多声部叙述的独特结构方式,将三个叙述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为表达主题服务。这三个叙述主人公分别是奥斯卡·谢尔、奥斯卡的祖父、祖母。9岁男孩奥斯卡在9·11事件中失去了父亲。他的祖父、祖母在二战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家人、又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儿子。三个叙述主人公都经历了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承受着无法言说的伤痛,却都在努力尝试、寻找述说的方式,寻求解脱的途径。
奥斯卡通过寻找与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钥匙匹配的锁,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目的是为了了解他的生死之谜。虽然奥斯卡最终发现寻找已久的答案只是源自一个误会,但在追寻的过程中,他克服自闭,勇敢地和陌生人交流,大声向每个人说出:“我父亲死了,我想……”从而使悲伤情绪得到宣泄,他逐渐走出忧伤、走向成熟、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与奥斯卡勇敢言说、自我疗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祖父自我毁灭式的失语和艰难的言说,这一言说具有更加突出也更为典型的意义。因此,本文以祖父为研究对象,从分析祖父的创伤、失语以及他独特的“言说”方式入手,探讨“后9·11”小说独特的表达方式。
二、无法言说的痛
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被视为“世界建筑宝库”,素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之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1945年2月13日,英美联军对德累斯顿发动了连续三天的大规模空袭。6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被看成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从极左翼到极右翼之间,各个政派都发表了意见。德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耶纳宣称:“看吧,德累斯顿大轰炸,真正针对平民的袭击。”小说《特》中,奥斯卡的祖父老托马斯·谢尔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了家人和怀有身孕的未婚妻。突如其来的遭遇使他猝不及防,无辜的亲人丧生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屠杀,他喜欢的人,他向往的生活在瞬间化为乌有。面对这样不可理喻的灾难,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他们要轰炸德累斯顿?”当祖父带着孤独、悲伤、迷惘来到繁华的纽约,他发现自己用于表达的词汇开始慢慢地消失,语言能力在逐渐萎缩。祖父曾这样写到:
“我以前并不沉默。我曾经说啊说啊说啊说啊,我不能闭上我的嘴。但有一天沉默像癌症一样征服了我:那是我在美国吃的头几顿饭的一顿……我从没想到过我是个安静的人,更不会沉默,我从来没想到过任何事情。一切都改变了,锲入我和我的幸福之间的不是世界,不是炸弹和燃烧的建筑物,而是我自己,我的思考,这种无法舍弃的癌症。无知是福吗?我不知道,但思考是这么痛苦。告诉我,思考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思考把我带到了什么伟大的地方?我想啊想啊想啊,我把自己从幸福中想出来了一百万次,却一次也没有把自己想进幸福中去。”[3](P17)
是什么让曾经诉说不停的祖父突然变得沉默?
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交流的工具,语言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的主要形式。语言学家格雷斯(Grice)指出:“交际过程中的会话含义,依靠的是对各种语境因素的综合考虑和推理能力的合理应用。”[4](P2)韩礼德(M.A.K.Halliday)进一步阐明:“语境因素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语言发生的具体环境和话题,即话语范围;第二,表明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的话语基调;第三,语言交际所采用的媒介和渠道,即话语方式。三者之间互相制约、互为补充、共同作用,决定交际的成败。”[4](P46)炸弹和燃烧物固然让祖父触目惊心,失去爱人更使他痛苦绝望,但当他离开被炸弹摧毁的故土,来到美国,从一个伤心的主人变成被人漠视的过客,主体身份的转换、生活环境以及语言环境的改变,造成祖父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在新的语境中,祖父失去了发表个人意见和观点的权利,被边缘化,成为美国文化语境中的“他者”,他遭受的巨大创伤显得微不足道,成了被压抑的、无法言说的痛。
第一个不能说的词便是“安娜”(Anna)——未婚妻的名字,第二个不能说出的词是“和”(and)——因为它听起来像“Anna”,接着,“要”、“羞愧”、“谢谢”、“是”等词汇从他的语言里无声地消失,直到最后,当他不能说出“我”这个词时,他的沉默就彻底完整了。“安娜”“和”“我”作为一个个能指符号,在祖父语言世界里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尘世生活中的祖父,一个价值和意义成为空壳的祖父,一个不被美国理解、被淹没在美国生活中的祖父。他的痛苦经历、他要表达的思想和听话者的期待格格不入,从而屡次导致祖父和周围人交流的失败,慢慢地,祖父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产生一种疏离感,这种无法融入的疏离感,加上灾难导致的创伤使绝望的祖父最终丧失了语言能力,患上了失语症。
祖父的失语具有寓言般的暗示作用,隐喻祖父非同寻常的沉默和绝望部分是由于快乐幸福的美国不允许他讲自己悲惨的故事,在高科技高效率的美国语境中,他无法回忆德累斯顿的燃烧弹。战机轰炸的可怕场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变得遥远。面对快节奏的美国,祖父实在无法诉说自己可怕的经历。在新的语境中,面对他人的话语,祖父只能将自己内心的话语不断挤压收缩到边缘位置,结果,他隐忍的创伤成了无法言说的伤痛,象征他在新的语境中话语权力的丧失和言语能力的衰退。
心理学家维姆·伍德(Wilhelm Wundt,1832—1920)认为:“语言的产生是把思想转化为按照一定次序组织起来的语言单位的过程,而语言的理解则把这些语言单位转化为思想。”[4](P2)小说中,祖父被凌乱破碎的创伤记忆困扰,无法摆脱遭受无妄的灾难带给他的愤怒、悲伤和内疚,无助的他,置身于忙碌的美国这样的语境中,他无法将自己的创伤记忆重构整理,无法按照逻辑把自己的思想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地表达,甚至无法找到可以听他倾诉的人。语言表述的愿望与表述语境的极端不适应、祖父想要表述的话题与听话人身份兴趣的不适应导致了交际的失败,环境的压力,使得祖父遭受的创伤成为无处言说、无法言说的痛。
三、难言的“言说”
然而,创伤必须被言说,正如贝塞尔凡·德考克(Bessel Vander Kolk)曾说:“创伤记忆源于难以忘怀的经历留下的伤痕,它必须与现在的精神状态相融合,必须被转换为叙述语言”。[5](P44)小说中,祖父的语言能力丧失了,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下去。失语的祖父,不得不使用非情景化的文字、书信、序列图片、数字符号等“辅助语”作为媒介和渠道进行艰难的“言说”。小说中,这些“言说”用图片的方式呈献给了读者。
非情景化文字。失语后的祖父为了努力保持与世界的联系,开始随身携带空白笔记本,以便可以写下他不能说出的话:“我不能说话,对不起”,“我想要两只面包卷”,[5](P19)“一点甜东西也不错”,[5](P20)“请给我老花样”,[5](P23)“我不确定,不过天晚 了”,[5](P25)“请帮助我”。[5](P26)这些写下的文字最初被用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可是后来发现,他写下的话远远不能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无法对别人在特定情境中的问话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如果有人问他:“你感觉如何?”他最好的回答可能是“请给我老花样。”或者可能是:“一点甜东西也不错。”这样答非所问的非情景性“对话”,一方面表明有限的文字和无限的愿望之间明显的悖逆,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他人的话语与祖父自身经验之间巨大的断裂。
书信。当祖父得知祖母私自违反他俩的约定而怀孕后,他仓皇逃离祖母,重新回到了德累斯顿。因为他“太害怕失去所爱的东西,所以拒绝爱任何东西”(福尔)。德累斯顿大轰炸中,祖父失去了怀孕的未婚妻,他恨他没有能力照顾好所爱的人,而自己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罪恶感和负疚感深深埋在祖父的心底,让他陷入对自己的极端否定认识中不可自拔。当他得知要再次面对一个新生命,遭受创伤后的无力感迫使他退却,他逃离了需要保护却无力保护的祖母和正在孕育中的新生命。然而,懦弱的逃离并没有让祖父有些许轻松,相反却又一次加重了他内心的罪责和负疚。为了摆脱负疚感和言语的困境,他不停地给自己从未谋面的儿子写信,每封信的标题都以“为何我不在你身边”为题,向他诉说自己的困惑、矛盾和内疚,却没有勇气将信寄出。祖父的言说成了没有听众的独语。对祖父而言,困境非但没有解除,反而使他深陷其中。“9·11”事件之后,祖父得知儿子死于袭击,他急切地重新回到美国。当见到自己的孙子奥斯卡时,他想要“一本无限厚的空白笔记本和尚未消逝的所有时间”。[5](P288-291)祖父有太多的话要说。因此,在给死去的儿子写的信中,最初几行字还能依稀看清,由于“担心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表白,逐渐地,词与词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挤,以至于整页变得无法认读,最后成了一块全黑的画布。祖父隐忍的创伤隐藏在了无法认读的密集文字中,他无尽的话语似乎永远在言说之外。
数字符号。9·11事件之后,祖父急忙从德累斯顿赶回纽约,一改之前消极的沉默。在机场,他给祖母打电话,急切地想要告诉她:他为什么离开,他去了哪里,他为什么回来等一连串不被理解的行为。但令人痛心的是,失语的他只能通过不停按压电话按键的方式“言说”,因为他想要“用手指摧毁我和我生命之间的墙。”[5](P279)想要把自己无尽的话语用有限的数字表达出来,于是,小说文本中留下了长达5页的阿拉伯数字,这些祖父用来“言说”的杂乱无序“语言符码”,无人能破解。祖父想要说的话,成了永远的谜。
序列图形。为了帮助祖父“言说”,小说中插入大量图片,成了创伤患者永恒的记忆和无言的“讲述”。这些图片包括:珠宝——暗示与谢尔家族祖孙三代艺术理想背道而驰却不得不经营的家族生意;紧锁的大门——象征祖父遭受创伤后日渐封闭的内心世界;反复出现的门把手——预示祖父在面对外界时渴望交流又无法交流的艰难处境;一张骷髅手的照片——暗示谢尔一家(Schell与shell谐音,原意为空壳、炮弹)空洞的人生;最值得一提的是,两张手心分别写着“Yes”和“No”的图片,是祖父为了保持交流,使生活可以继续,在自己手上纹上去的,这样,他可以通过举起任何一只手表明自己对某件事情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手势语,不可避免地将他置于是与否、对与错、黑与白、邪恶与正义等二元对立的简单选择中,从而拒绝了对世界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言说。失去的话语能力和有限的词汇将他局限于自己语言的笼子里,使他无法表达是与否之外更广阔的区域存在的可能性,使他面对世界,无法做出周全的判断。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说过:“一张照片就是一块碎片——一次瞥视。我们累积瞥视、碎片。我们脑中都贮存着数以百计的摄影影像,它们随时供我们回忆。所有照片都向往被记忆的状况——即是说,难忘的状况……它们向我们展示真正恐怖的东西,并成为我们有胆量看什么和有能力接受什么的一种测试。”[6](P131)《特》中,这些被用来言说的碎片般的图片不仅为作品中深受创伤之痛却无法言说的主人公提供了言说的内容,言说的方式以及言说的语境,也为读者展示了恐怖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
四、结语
历史的伤痛导致现实的失语,现实的创伤隐藏着历史的原因。灾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对于灾难事件中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而言,噩梦才刚刚拉开了序幕。他们需要世人更多的关心,以帮助他们走出心灵的阴影。凯西·卡鲁斯认为,“文学作品为创伤经历打开了一扇言说之窗,教会读者怎样倾听那些只能通过非直接的、非常规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经历。”[7](P34)在“无法言说”和“不得不说”的矛盾纠结中,福尔成功塑造了祖父的形象,通过描写祖父因创伤导致失语,由于失语主人公不得不使用非情境化的文字、图片、数字符号等“言说”方式,将历史与现实进行解码之后重新编码。这些独特的“言说”强化了小说“创伤的不可言说性”主题,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单一的语言叙述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特》中,福尔开创了“视觉写作”(visual writing)模式,在后现代的读图时代,这种将文字和图像结合起来兼收并蓄的越界方法,为“后9·11”小说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本文独特的写作风格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意蕴,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历史灾难事件的严肃思考。
[1]Judith Greenberg.Trauma at Home:After 9/11.[M].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Press,2003.
[2]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M].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M].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7.
[6]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Marylan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