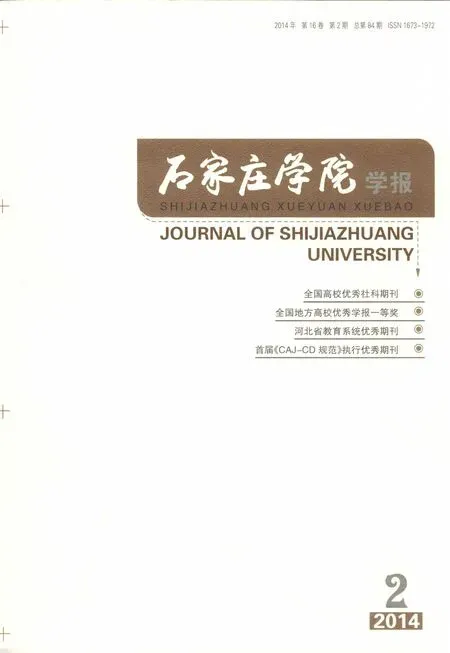唐代刑法之首恶及其认定的影响因素
冯红
(石家庄学院 政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唐代刑法之首恶及其认定的影响因素
冯红
(石家庄学院 政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中国古代刑法之共同犯罪到唐代规定已相当具体,不仅将首恶与“随从”或“协同”者、“被逼”或“被驱率者”、教令者相区别,而且还依据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区别量刑。但是,法律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法律也被刻上了等级与宗法的标签。在唐代刑法中,影响首恶的认定因素不仅是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的严重程度,还包括血缘关系和职务身份以及犯罪性质。
唐代;刑法;共同犯罪;首恶
唐代刑法之首恶类似现代刑法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中国古代律典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最早见于战国时魏文侯师李悝所著《法经》:“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1]366到秦朝,秦律已有对群盗的处罚规定。日本学者掘毅先生对此曾提出,“群指五人以上”,并进一步说明“因为当时实行由五名壮丁组成的‘伍邻’保制,以便互相戒备,大概以防御方面的‘伍’为基准,有关‘五人盗’的规定便应运而生”[2]236。经过历史的发展,到唐代颁布《唐律疏议》时,已经将共同犯罪的规定分为总则性规范和分则性规范。在总则性规范中,《唐律疏议·名例律》用了6条律文的篇幅,分别规定了共同犯罪的界定、处罚、捕首以及首恶认定等内容;在《唐律疏议·名例律》以外的分则性规范中,对某些个罪的共犯作出了特殊规定,起到了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在《唐律疏议》中,共同犯罪人分为首恶、“随从”或“协同”者、“被逼”或“被驱率者”、教令者,对应现代刑法中的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各自承担不同的责任,刑罚也不同。
一、首恶之定罪
首恶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类似现代刑法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早在汉代时,已有对首恶的规定,而且对共犯人规定了首恶从重处罚的原则。《汉书·主父偃传》载,西汉的主父偃犯罪,汉武帝本无意将其处死,但张汤说“(主父)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3]卷64上。《汉书》载:“后事发觉,被诣吏自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美,欲勿诛。张汤进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遂诛被。”[3]卷45又见“鸿嘉中,广汉群盗起,选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扈商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姊子,软弱不任职。宝到部,亲入山谷,谕告群盗,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过自出,遣归田里。自劾矫制,奏商为乱首,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3]卷77。《魏书》载,北朝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太保、高阳王雍议冀州阜城民费羊皮卖女给张回一案言:“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4]卷111可见,在唐代之前,大多也以造意、发意者为首恶。
到唐代,首恶主要包括造意者、最初引起事端的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
(1)《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2条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5]卷5造意者指最初提出实行犯罪动议的人。西晋初期,张斐言:“唱首先言谓之造意。”[6]卷30唱是倡的借字;唱首即为首倡,有率先之意;先言即为首先或最初提出者。
(2)《唐律疏议·斗讼律》总第308条规定:“若乱殴者,不知先后轻重者,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5]卷21即在斗殴中,不能分清行为的先后与轻重时,若是同谋共殴者,以初始的造意人为首恶;若是不同谋的斗殴者,以最先进行斗殴的人为首恶。
(3)《唐律疏议》将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称为“所由”“专进止者”,这类人有时也作为首恶处罚。《唐律疏议·斗讼律》总308条规定:“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5]卷21又见《唐律疏议·职制律》总第109条规定泄密罪,以初传者(初漏泄者)为首,传至者(传至罪人及蕃使者)为从。这里以对犯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主犯。《唐律疏议·贼盗律》第285条规定恐吓人财物罪,若造意人不实施恐吓行为,又不分赃,“以行人专进止者为首,造意为从”[5]卷19。《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97条规定,对共同盗窃罪中,若“造意者不行,又不受分,即以行人专进止者为首,造意者为从”[5]卷20。这里强调造意者未实行犯罪且不参与分赃,才可以“专进止者”为首恶,若造意者实行犯罪或虽未实行但参与分赃,造意者仍是首恶。“若本不同谋,相遇共盗,以临时专进止者为首,余为从坐。”[5]卷20这里立法者注意到共同犯罪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表现为主观上有联络。若“本不同谋”缺乏犯意的联络,只是“相遇共盗”,即以“专进止者”为首恶。可见,早在唐律就已经提出了临时共犯的处罚问题。
与唐律中首恶相对应的是“随从”或“协同”者、“被逼”或“被驱率者”、教令者,他们共同构成了唐律共同犯罪人。对“随从”“协同”者,《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51条谋叛罪中,注文言 “谓协同谋计乃坐”,疏文进一步解释:“协者和也,谓本情和同,共作谋计。”[5]卷9从律文可以看出,“随从”“协同”者与首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首倡者,处于“协同”地位。对“被逼”“被驱率者”,《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51条疏议解释:“被驱率者非”指“元本不共同情,临时而被驱率者”,对胁从犯“不坐”,对“‘谋叛、谋大逆’或‘亡命山泽,不从追唤’,‘既肆凶悖,堪擅杀人’,并‘刼囚’之类,被驱率之人,不合得罪”[5]卷17。《唐律疏议·户婚律》总第195条规定嫁娶违律罪,疏文规定:对男女“被逼”者,“主婚以威若力,男女理不自由,虽是长男及寡女,亦不合得罪”[5]卷14。对教令者是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的决意,进而使其基于此决意实行犯罪的情况,类似现代刑法中的教唆犯。关于教令者,早在秦律中已有规定,如《法律答问》载:“甲谋遣乙盗……皆赎黥。”[7]152《晋书·刑法志》载:“殴人教令者与同罪。”[6]卷30到唐代,对教令者的处罚更是具体。《唐律疏议·斗讼律》总第357条规定:“诸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者为首,教令为从。即教令人告缌麻以上亲,及部曲、奴婢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被教者,论如律。若教人告子孙者,各减所告罪一等。”[5]卷24《唐律疏议·断狱律》总第471条规定:“雇倩(请)人杀之及杀之者,各依本杀罪减二等。”[5]卷29《唐律疏议·诈伪律》总第378条规定:“诸诈教诱人使犯法,及和令人犯法,即捕若告,或令人捕、告,欲求购赏;及有憎嫌,欲令入罪:皆与犯法者同坐。”[5]卷25可见,对教令者与实行犯同罪同罚。但《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30条规定,凡是“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九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如果有人教令犯罪,只“坐其教令者”[5]卷4。 《唐律疏议·户婚律》总第195条规定:嫁娶违律“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5]卷14。这里只独坐教令者概因《唐律疏议》恤刑原则规定这些人犯罪可减免刑罚。其实,早在秦律中已有对教唆未成年人须加重处罚的规定,如《法律答问》载:“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磔。 ”[7]180《法律答问》甲教唆未成年人乙犯盗窃罪,对甲处以磔刑;对未成年人乙是否处刑,判例中没有说明。但据 《法律答问》载,“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马因受惊,吃了他人的庄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7]218。从此推断,也许此时未成年人乙不处罚,只处罚甲。
二、首恶之量刑
首恶与其他犯罪人量刑的区别可分为三种情况:前者重于后者、前者轻于后者、前后二者处罚相等。
(1)在量刑中,首恶重于其他犯罪人是一般原则。《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2条规定:“随从者减一等。”[5]卷5《唐律疏议·捕亡律》总第465条规定:“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杀人者斩,从者绞。”[5]卷28
(2)由于不同的身份等级导致不同的量刑,有时其他犯罪人重于首恶。《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3条规定:“诸共犯罪而本罪别者,虽相因为首从,其罪各依本律首从论。”[5]卷5例如,卑幼甲与外人乙盗窃自己家的财物十匹,甲是首恶,乙是协同者。依《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88条规定“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5]卷20,比照《唐律疏议·户婚律》总第162条规定“同居卑幼私辄用财”罪“加二等”处罚,甲只处笞三十,“他人,减常盗罪一等”[5]卷12。由此外人乙按《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82条规定的普通盗窃罪减一等,徒一年。又因为外人乙是随从,《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2条规定:“随从者减一等。”[5]卷5最终,对外人乙处杖一百。与首犯甲只处笞三十相比,随从乙的处刑重于首恶甲。这一方面表现了《唐律疏议》在法条竞合中贯彻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律疏议》中的同罪异罚原则。
(3)首恶与其他犯罪人同等量刑。它通常涉及侵犯皇权、国家统治以及侵犯一般社会秩序中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犯罪。《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3条指明:“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即强盗及奸,略人为奴婢,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5]卷5《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48条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 ”[5]卷17《唐律疏议·贼盗律》第297条规定,诸共盗者若“造意者不行(实行),又不受分(不分赃物),即以行人专进止者为首,造意者为从坐”,但此时作为协同者的造意者并不减轻处罚,只是“至死者减一等”流三千里。[5]卷20
但实际判例也有例外,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载:
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杻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寃而不为伸邪!万一闇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 ”无一人异辞者。[8]6042
本案按照《唐律疏议·贼盗律》总第248条“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5]卷17的规定,应全部处死刑,但基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为体现治狱平恕的原则,崔仁师对共犯人区分首从,只追究魁首十余人,其余释放。
三、结语
中国古代刑法之共同犯罪已规定得相当具体,不仅将首恶与“随从”或“协同”者、“被逼”或“被驱率者”、教令者相区别,而且还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区别量刑。但是,法律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法律也被刻上了等级与宗法的标签。对犯罪起重要作用、罪行严重的首恶的认定影响因素中不单单只考虑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的严重程度,还包括血缘关系和职务身份以及犯罪性质。唐代影响首恶的认定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客观因素、血缘关系和职务身份。首先是主观因素,因为造意者最先提出犯罪动议,主观恶性重于其他共同犯罪人。其次是客观因素,即在唐代的某些共犯中,以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人为主犯,体现了重罚“行”者的刑事政策。如对危害结果负主要责任的犯罪人为首恶;或者在共同强盗罪、共同盗窃罪、恐吓取人财物罪中,造意者既不实行犯罪又不参与分赃,以对犯罪起主要作用的人为首恶;又如在泄密罪中,最初漏泄者为首恶。再次,血缘关系也是认定首恶的影响因素。《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42条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家长。”疏议解释:“谓祖、父、伯、叔、子、孙、弟、侄共犯,唯同居尊长独坐,卑幼无罪。”[5]卷5家长身份成为认定首恶的影响因素。最后,职务身份也影响首恶的认定,主管官员因具有职务身份,被认定为首恶。立法者注意到有职务身份的共犯人利用其身份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使犯罪更易得逞,应当重罚,同时也加强了对其履行职责的监督与管理。
由于以上影响认定首恶因素的存在,使得首恶与其他从犯的量刑区别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首恶重于其他从犯。第二,其他从犯重于首恶,这主要由于不同的身份等级导致不同的量刑,这一方面表现了《唐律疏议》在法条竞合中贯彻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律疏议》中的同罪异罚原则。第三,首恶与其他从犯处罚相等。它通常涉及侵犯皇权、国家统治以及侵犯一般社会秩序中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犯罪。由上可见,由于影响首恶的认定因素不同,有时因为不同身份等级下的不同量刑标准的影响导致首恶量刑轻于犯罪较轻的其他犯罪人,而对侵犯皇权、国家统治以及侵犯一般社会秩序中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犯罪,唐律则不因犯罪行为轻重而区别对待,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犯罪性质导致罪不分首恶与其他从犯,同等处罚。
[1]董说.七国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日]掘毅.秦汉法制史论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 程铁标)
The Affirmation and Its Restraining Factors of the Chief Criminal of Penal law in Tang Dynasty
FENG Hong
(School of Politics&Law,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The joint offence in Chinese ancient criminal law was specifically defin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hief criminal was distinguished from attendants or cooperative persons or persons being forced or instigators,but also made sentenc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osition and role in crime.However,the law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social soil,thus laws were also engraved with the hierarchy and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in the autocratic society.So,in criminal law of the Tang Dynasty,factors affec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ster-slave relations included the sever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ehaviors as well as blood relations,social ident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the Tang Dynasty;criminal law;joint offence;chief criminal
K207
:A
:1673-1972(2014)02-0038-03
2014-01-08
冯红(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制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