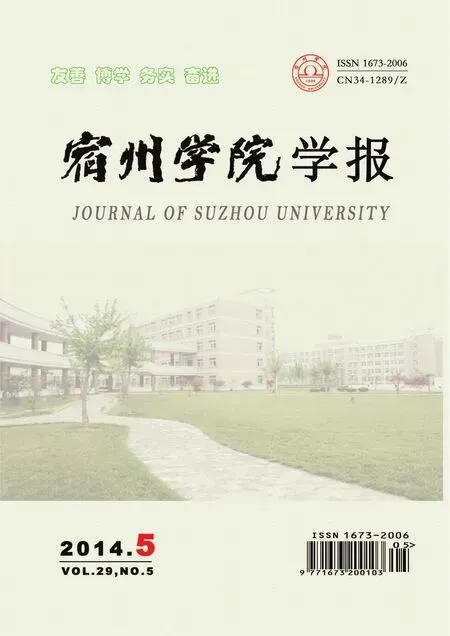解读刘禾《重返〈生死场〉》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冯晓曦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8
解读刘禾《重返〈生死场〉》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冯晓曦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8
《重返〈生死场〉》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作者刘禾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将作品主题置于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使得萧红的《生死场》再一次陷入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其创新和偏颇之处相当具有典型性。从对男性批评家的否定、女性身体状态的描述、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写作模式的不同、男性特点的削弱、男性与女性归属的对比等方面对文章进行个人性评论,以此解读刘禾的女性主义思想。
萧红;刘禾;《生死场》;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欧美文化界,是指在文学批评中以“女性主义”为主要立场与角度的批评。体现在用女性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历史及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中的各种传统。女权运动的爆发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重要背景,正因女权运动的高涨以致深入到文化领域,因而它从产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它以妇女为中心,将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及女性阅读等作为批评对象。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还广泛地吸取了在当代欧洲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解构主义等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有英美派(提倡从女性角度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法国派(提倡建立两性在文学创作及评论中的平等地位,通过解构男性来创立女性文学体系)。《重返〈生死场〉》的作者刘禾长期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精通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可谓是可以做到“踏东西文化,做宇宙文章”[1]。她推翻了以往国内批评家对萧红《生死场》的解读,转而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场上,观点新颖,意味深长。在文中,作者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目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的关系问题。”[2]192作者以小见大,借用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从接受层和生产层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和民族国家文学的关系问题,旨在说明评论家在分析小说时往往只看重“民族问题”而忽略作品本身更重要的主题问题,即文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
2 接受层
刘禾首先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即一些男性批评家作为读者在阅读了萧红的作品后所得出来的含有自我局限性的主题意义。文中详细地介绍了男性批评家的盲区,所谓盲区也就是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或是一味只关注某一问题而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传统意义上,对《生死场》的批评焦点一直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大多数评论者都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这种解释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3]刘禾指出,由于男性批评家在性别认识上的局限性,即对国家民族的关心使得民族主义成为萧红小说《生死场》的唯一解读。一方面,作者列举了20世纪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的观点并给予否定。一是说明了鲁迅、胡风等人对萧红作品的接受问题在于完全偏重于民族问题,也就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刘禾对这种看法显然不赞成且持反对态度。刘禾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之一便有《生死场》,在其1935年作的《生死场·序》中说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4]序中强调的是北方人民面临日本侵略者时表现的坚强和勇敢,胡风亦如此,两者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对作品作出评价。二是茅盾虽然发现了萧红并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如前两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的民族主义热情,但也没有找到萧红为何如此的原因。于是,刘禾提出萧红作为女性作家,面对的不仅是国家民族矛盾,同时也面临着封建父权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死场》的作者——萧红,人生经历曲折坎坷,抗婚离家,赴京求学,被迫就范,受骗怀孕,直至陷于旅馆面临被卖。她经历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少女时代,这样一种生活体验给一个心理上并未成熟却在身体上备受折磨的少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给萧红带来痛苦的根源便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控制和迫害。“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女子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可能已经被否定大半了,然而,在当时萧红生活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传统还依然主宰着中国社会。萧红作为女性,为反抗旧社会,追求自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1岁时,萧红遇见了萧军,她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来临了,可是却没曾想,在这样一段婚姻生活中又要面临女性、女权与男性、男权的冲突。萧红需要的丈夫不仅仅是生活的依靠、终身的伴侣,更是在性别上能够充分尊重她的良师益友,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在生活中一直存在。萧红经常为萧军抄稿。两人吵架,萧红出走,两人共同的朋友却因为萧军不敢收留她。萧红再次感到娜拉式的孤独,萧军代表的是社会主导意识,萧红则饱含女性自我意识,这两种矛盾再次发生冲突,于是这段婚姻意料以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告一段落了。后来遇到的端木也没有把她从男人的附属品中解救出来,反而又踏上了老路。此时的萧红像一个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木偶,再也无力挣扎。身体虽已破败不堪,思想却风起云涌,读者可以在萧红的小说中感受其坚强的灵魂。另一方面,作者列举1930年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因生活的环境与时代的传统,也同样与国家民族主义及父权传统之间产生矛盾,她在小说《三枚金币》中表达了明确的女性主义态度,从女性立场出发,控诉英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夺和不尊重,并以女人的名义将第三枚金币捐给了反战团体。刘禾列举鲁迅等男性批评家对《生死场》的评论,旨在揭露《生死场》中的女性话语被民族话语所掩盖的现象;列举与萧红处在相同立场的伍尔夫,旨在表明本人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为下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作品文本分析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3 生产层
立足文本,分析在小说中女性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如何同民族国家及男性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的?这一部分集中体现了作者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解读、分析文本,下面讨论的是笔者对刘禾话语的解读。
3.1 《生死场》封面解读
萧红本人为1935年版《生死场》所设计的封面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萧红设计了半黑与半红的图案。在男性批评家看来,红色的鲜血正是浴血奋战中的人民的鲜血;而在女性批评家看来,那是女人生育时流下的鲜血。这当中刘禾提出刘福臣的解读,刘福臣在文章中暗示从性别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封面。刘禾之所以强调刘福臣的解读,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文本中处处可见的、对女性扭曲身体的描写。
3.2 对孟、戴关于《生死场》中女性主义的发展
作者列举了孟悦和戴锦华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作出的评价。其中有一章《女性的眼睛》,孟、戴俩人指出:“女性处境的敏感来自同一个角度、同一种立场——主导意识形态阵营的边缘,甚至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盲点。这种边缘化的角度并不就是女性角度,但在当时情况下,它包含了女性角度。”[5]由此可见,孟、戴虽也想到了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观照《生死场》,但并没有将女性意识同当时的主导意识即民族主义置于对立的位置。作者将孟、戴的解读深化,形成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体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涵,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其次,在小说的后七章,萧红笔锋一转,从女性世界转向了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家民族主义进入村民意识的过程;这些描述不仅把‘男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最后,我认为《生死场》的写作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即作者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场所同民族国家空间之间有着激烈的交叉和冲突。”[2]196
《重返〈生死场〉》的后大半部分,作者结合小说本身,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揭露小说主题。笔者认为,刘禾运用了以下几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
(1)从女性身体出发,塑造扭曲的女性形象。月英和王婆的例子最为典型,月英本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可是因为病痛,被丈夫嫌弃,身体变成小虫的栖息地,最后惨死。“她的腿像两双白色的竹竿……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6]44王婆接受不了儿子的死讯,服毒自杀未果。“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胀,像是鱼泡似地。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直喷,射了赵三的满单杉。”[6]64旨在说明毁灭的女性躯体。
(2)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分析女性低下的地位。性,怀孕之于女性。金枝的例子最为典型,笔者认为萧红塑造的金枝的形象绝非偶然,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女性贞节的意义是由父权决定的,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这是由中国的传统观念决定的,女人只有依附男人才能得到合理的社会地位,即为男人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否则,连女人与女人之间也会产生矛盾。正如小说中的金枝在没嫁人前怀孕,被同村的妇女瞧不起。另一方面,在金枝的身上,或多或少地能看到萧红的影子。
(3)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出发,研究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模式。萧红的作品《生死场》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的作品相比较,一方面是人民反抗内容是相当薄弱的,这种薄弱不仅体现在叙述内容之少,还体现在人民反抗内容的描写上。其中老赵三的例子比较典型,老赵三最开始是不知所以然地、盲目地投身到斗争中,却失手打死了小偷,后因地主帮忙求情被救出大牢而又对地主深感忏悔,认为自己做错了。就连他的老婆也觉得他懦弱无能:“我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6]49将萧红与萧军的作品相比较,分析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作品偏重点的不同,也就是男性作家更加偏重于男性的特性,民族、国家、大义,女性作家则更加偏重于女性躯体以及用女性的视角来看待男性。另一方面,萧红是为了说明民族国家其实都是男性的,女性始终只是依附品。在李青山号召同村的人去参加革命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弟兄们!……是不是……弟兄们……”[6]84最先回应的却是寡妇们“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6]84。
(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论:伍尔夫曾在自己的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道:“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7]这种理论在文中表现为二里半的例子。萧红之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是因为他的残缺使他沦为与女性一样卑微的地位。二里半在小说中始终处于屈辱的地位,为了找羊被打,去金枝家提亲遭拒,又因为舍不得拿羊做仪式被同村人笑话。“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词,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8]二里半是最典型的代表,其人生始终和他的羊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二里半的地方,就有二里半的羊。二里半性别虽为男性,但其因残缺而女性化甚至动物化。
(5)从男性与女性命运的对比出发,男性与女性归属的对比,最为典型的就是二里半和金枝的例子。二里半作为男性,最后投身革命。而金枝为求生存,躲避日本人而逃到城里,却没想到在城里还有比日本人可怕的中国男人。“‘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都不恨。’”[6]96最后想出家却无处去。可见,在中国社会中,女性除了忍受屈辱是无路可走的。刘禾选取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男性批评家的角度,即完全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生死场》进行分析解读。通过描述毁灭的女性身体、揭露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分析女性作家的创作模式、运用“双性同体”论以及分析男女性归属问题五种方法的运用,将文本中蕴含的女性思想一一揭示,使得文章充满新意,让读者眼前一亮。然而,刘禾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解读《生死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将其主题意义置于与民族大义相对立的位置,这种解读是否片面?值得深思。
3.3 与丁玲相比较
如果将萧红的作品与其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进行比较,还是会看出萧红作品中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如丁玲,他们同为左翼作家,同样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丁玲的着重点则在于写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坚强、勇敢的一面,萧红侧重写北方农村女性的苦难生活。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特有的,以对中国贫苦女性了解为前提的,表现女性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挣扎,揭露男性对女性的冷漠与迫害。萧红是一位饱含女性主义思想的女作家,她着眼于女性的日常生活,描写北方女性的血泪生活,用文字诉诸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
4 结束语
刘禾完全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分析、解读《生死场》,这种解读是否合理?对男性批评家的否定是否有失偏颇?笔者很赞同刘禾的观点,否则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小说的前十章中未提民族大义的问题以及在后七章中对斗争描写的薄弱性,萧红始终把着重点放在对女性身体的描写上。但对于男性批评家的否定,也确实有失偏颇。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正是受到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使中国的男男女女始终以男主女副的位置自处着。想要冲破这种束缚和传统,就必然需要付出代价。那么萧红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因女性与男性、女权与男权的冲突与中国传统作斗争,身体的代价是惨痛的,但精神却是发光且永存的。萧红的小说在文学史中被纳入了1930年代小说的典型。1930年代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是被这样评价的:“30年代小说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它们堪称中国社会的历史教科书。”[9]148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为“《生死场》描写了沦陷前后的故乡东北人民的生活,愚昧的思想与异族的侵略,双重的挤兑使人们几乎窒息”[9]149。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似乎都被提升到了民族国家的高度上。而作者从女性角度来分析,充满新意。但文中作者对男性评论家的否定也略有不当之处,萧红的作品之所以会被男性作家套上“民族寓言”的帽子,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主观方面,萧红作品本身也的确有关于民族战争及人民反抗的描写,又因为萧红所处的时代背景很容易将其作品纳入到民族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客观方面,男性作家身处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萧红是在鲁迅的培养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鲁迅作为时代先锋、民族英雄,他站在民族的高度上来看待这部作品是可以理解的。
[1]陈树萍.再返生死场:评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J].河北大学学报,2009,29(2):100-102
[2]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重返生死场[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5
[4]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08-409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46-247
[6]萧红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7]张丽丽.双性同体视野下的伊莉莎[J].赤峰学院学报,2013,34(6):166-168
[8]冷东.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J].广州大学学报,2001,15(6):1-8
[9]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力)
10.3969/j.issn.1673-2006.2014.05.014
2014-03-18
冯晓曦(1990-),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I206
A
1673-2006(2014)05-0044-04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