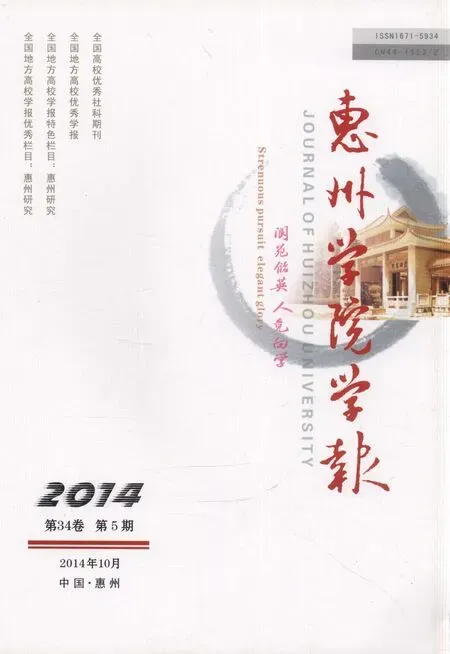劳伦斯诗歌与小说的互文性探析
马若飞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一、引言
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的盛名虽然是因其小说创作而成,但他最初却是通过诗歌创作而步入文坛的。他在1905年就完成了自己最早的诗作《致绣球花》(To Guelder Roses)、《致石竹》(To Compions)等,而后一生中创作出了近1000 首诗歌。劳伦斯在构制那些经典小说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诗歌创作,甚至在临终前还完成了最后一部诗集《最后的诗》。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并驾齐驱,势必使得劳伦斯的诗歌和小说之间有着或隐或显的彼此渗透,体现出互释互补的内在关联,在诸多方面具有互文性特征。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共同作用下而诞生的一种文学理论,最初由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启发下而提出的,后来经过巴尔特的阐释而得到迅速发展,这种互文性被后来的一些学者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1]95-97在克里斯蒂瓦看来,任何文本的构成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仿佛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其诗性语言至少是当作双重语言来阅读的。互文性强调的是一种性质或动态过程,用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发生关系的一种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隐射、重写等等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和文本对比分析来建立。[2]19-30透过互文性这一独特的视角,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劳伦斯诗歌与小说之间的相互指涉与意义关联。这种互文性主要是通过重写、隐射等方式而得以呈现,使得其诗歌主题的丰富性、意象的独特性和情感的悲伤化十分突显。
二、劳伦斯诗歌与小说主题的互文性
劳伦斯的一生都在进行着诗歌创作,共出版了十余部诗集,如《爱情诗及其他》、《我们走过来了》、《鸟兽花》等。他的诗歌创作是其文学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歌忠实地记录了劳伦斯情感历程和思想变化,蕴含着丰富的主题。这些诗歌与他的小说创作密不可分,两者在主题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互文性。
劳伦斯的诗歌主题涉及自然、爱情和死亡。对于大自然的书写,劳伦斯在其处女作诗中就单笔直入,《致绣球花》(To Guelder Roses)、《致石竹》(To Compions)等即是他对自然植物的直接抒情。在诗歌《黄昏的牝鹿》中,劳伦斯写道:“当我穿过湿地//一只牝鹿从玉米地跳出//忽地一闪跃上山坡//留下她的小鹿。//在那天际线//她转身而四顾,//她戳出一个漂亮的黑影//在那天边。//我看着她//感觉到她也在看我;//我成了局外人。//但我有权和她在那相视。//……是啊,作为男性,我的头并不坚硬,也无鹿角?//是我的腰腿并不轻盈?//难道她飞奔时凭借的风与我不同?//难道我的惊恐不如她的惊恐?[3]169-170”牝鹿是劳伦斯赞美的对象,是大自然中具有原始生命活力和野性本能的动物,她活泼轻盈,且颇有灵性,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一种强烈眷恋和呵护之情。尤其是在他的诗集《鸟兽花》中,劳伦斯更是将笔力聚焦于自然世界里的万物生灵,《无花果》、《杏花》、《蜂鸟》等诗融入了诗人渴望回归自然的深情。他在《枇杷与山梨》一诗中写道:
我爱你,腐烂的,
可口的腐烂。
我喜欢将你吮吸出皮外
如此的褐色和柔滑,
又如此病态,如意大利人所言。
多么罕见、强大和让人追忆的味道
在你坠落腐烂的过程中流溢而出:
溪水中的溪水。
……
枇杷,山梨,
更加甜蜜的秋的流动
从你的空皮中吮吸而出。[3]220-221
诗人通过对山梨和枇杷的描绘,将秋天的甜蜜滋味浓浓地体现出来,尽管有一丝淡淡的伤感,却又是一种蜜甜的忧愁。这种对自然的诗意书写,在劳伦斯小说的许多章节里颇为常见。譬如他的《白孔雀》,小说一开始就是一幅自然的风景,内塞梅尔谷地的优美恬静的风光让人们在这块迷人的土地上生活得十分惬意:“下午暖气洋洋,金光灿灿。麦捆变得更轻了:它们随随便便地相依而靠,像是彼此在低声细语。麦草发出缕缕香甜的气味。当把一捆捆可怜巴巴、晒得发白的麦捆举过树篱时,就会露出一片晃动的野山梅。迟熟的的野山梅随时都可能掉下地;在潮湿的草中还可以发现水灵灵的黑梅。这是人们还会看见,指项花乱蓬蓬的茎株上还挂着几朵钟形的花朵。……太阳落尽金光灿灿的西天,金色随之变成红色,红色越来越深,好像快要燃尽的一团火。太阳消失在一层乳白色的雾幕之中,像梅子树上白色的花儿一样泛着紫色。[4]84”
优美的自然,迷人的田园,人们在此生活得欢乐无比,畅快无穷。在劳伦斯的笔下,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的字里行间,诗人对自然的向往和回归之情显得一览无遗。
劳伦斯在对自然进行纵情抒怀之际,对爱情的感喟却又让人唏嘘。劳伦斯认为爱情的和谐源于合乎自然本能的性爱,男女唯有在结合中才能让爱保持完整,男女在情感的交流和性爱的结合中,才能美妙地融洽在一起[5]43:
绿色的夜里火焰在喘息,路旁
石榴花正在怒放,
小火堆红得耀眼在叶丛的夜里。
正午忽然黑暗、闪亮、无声,黑暗中
两人隐没,在遮阳的帽下;
唯有,从神秘腰部的叶丛间
红色的火焰隐约地映现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那。[3]499
劳伦斯在诗中强烈地突出了红的颜色,火焰的颜色,隐射出男女间的激情。因为他认为,“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如果你爱上了有生命的美,你就是在尊重性。[6]106”爱情与婚姻中的性爱主题在他的小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描摹。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就是以主人公对“性”的追求为主要内容展开的。此小说的女主人公嫁给了克里福德成了查泰来夫人,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克里福德参战并身受重伤,从此下身失去知觉,丧失了生育能力,使得女主人公生活在绝望与空虚中。但她与守林人梅勒士的相遇和结合点燃了她全身的激情:“现在,她觉得她来到了自己天性的真正的基岩上,而且原本就是无所羞惧的。她就是她本来的肉感的自我,赤裸裸的,毫无羞惧。她感到一种胜利,几乎是一种自负。原来如此!事情本来就是如此!生命原本就是如此!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掩饰或者害羞的。她和一个男人,另一个生命,共享着她的终极的赤裸。[7]191”这无比的激情和深刻的感触让她勇敢地和梅勒士私奔,走上新的生活之路。
劳伦斯在对自然、对爱情进行诗意的抒怀和小说绵延的叙事之际,对死亡的探寻成了他创作阶段的最后主题。《灵船》一诗被看作是劳伦斯诗歌中有关死亡主题的巅峰之作[8]215。
秋季,水果坠落
漫长的旅程通向湮没。
苹果坠落如大颗露珠
坠裂自己以求得出口。
是时候了,向自我道别,
找到一个出口
从坠裂的自我。
你造好了自己的灵船,是吗?
唉,造你的灵船吧,你用得上它。
冷酷的霜冻距离不远,当苹果密集坠落,
如雷声般落在坚硬的大地。
……”[3]603
诗人借“灵船”来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感怀,死亡既是终点,却又是新的起点,死亡能够让旧的自我走向新的自我,从而构建一个生命的轮回。在另一首诗歌《死亡不是罪恶,机械才是罪恶》中,诗人痛斥了机械文明给人类所带来的邪恶,而高歌死亡的再生性。这种死亡意识在其小说的某些人物身上,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意义彰显。小说《恋爱中的妇女》里的杰拉尔德虽然有着健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力,然而死亡的阴影如影相随,使其自身也显示出一种死亡之征兆。杰拉尔德作为工业主义和机械文明的代表,是腐朽和死亡的载体,他的死亡之途是从杀死弟弟开始的,而以自身死于阿尔卑斯山而告终,充分体现了小说的死亡主题。《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则更是对克利福德似的濒于死亡的现代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在此死亡的前提下,对灵肉融合的再生之路进行了构想,憧憬着重建人类失落的“伊甸园”。
三、劳伦斯诗歌与小说意象的互文性
劳伦斯诗歌与小说在主题上的互文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意象的互文性。意象的运用,使得劳伦斯诗歌和小说主题得以彰显的同时,又让它们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
所谓意象,是指一刹那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9]152意象至少包含着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性与个体情感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可观的呈现,两者复合现意,缺一不可。[10]21劳伦斯曾一度被划为意象派诗人,他的一些诗歌也被选入了意象派诗选,而且他的意象诗颇受好评。理查德·奥尔丁顿认为,如果把劳伦斯的诗歌放在意象派集子中则是天然浑成。[9]21劳伦斯小说也正是通过特定的意象来渲染主题,有时与诗歌中的意象相互指涉,从而产生意义的关联。
劳伦斯在诗歌和小说中使用了不少的相同的意象,如“树林”、“月亮”、“樱桃”、“马”等等,这些意象在各自的文体中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的同时,也让读者透过互文性视野获得更广更深的主题内涵。诗歌《虹》中有以下几行:
虹出现时,
我看到的是
一脚在女人怀里,
一脚在男人腰际。
支撑穹隆的双脚
上帝靠你撑起世界。
……
一只脚是男人心,
一只脚是女人心。
你知道男女的心,
从来结合不紧。
只有当他们向高处
一跃——
心啊,向高处跃吧!
——他们才横空相触,如同杂技,
建造一座虹桥。[3]579-580
劳伦斯通过“虹”这一特定意象,表达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破坏,致使男女关系陷入难以弥合的窘境,“一脚在女人怀里,一脚在男人腰际”,男女的心“从来结合不紧”。而要打破这种僵局,只有男女冲出世俗的偏执,唤醒内心世界的本能,才能够建立起男女关系的和谐世界,才能建造起一座新的虹桥。而这一特定意象“虹”,与劳伦斯的长篇小说《虹》这一标题不期而同。小说《虹》是《恋爱中的女人》的姊妹篇,但主题和基调却截然不同。后者是纯粹性的毁灭情怀,前者则是在毁灭性的基础上涂抹上了一层完美的理想色彩。《虹》记叙了布兰文一家三代的相关生活,其中第三代厄秀拉的精神成长的描绘在小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小说在主题方面是重点探寻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当厄秀拉病愈醒来之际,感到一切都是新的,眼前幻化出一道淡淡的彩虹:“她看见在飘动的云中有一条淡淡的彩虹,恬淡的色彩犹如山麓的一部分。她情不自禁地站立起来,寻找这飞舞的色彩和正在形成的彩虹。这虹在一处发出强烈的光芒。她怀着痛苦的希望寻找彩虹的阴影,因为在那儿应该能找到飞拱而起的彩虹。于是天上架起了一道淡淡的巨大的彩虹。这是集光线、色彩和苍穹于一身的伟大建筑艺术,其顶端连着天堂。……她知道彩虹就植根于他们的血液之中,并在他们的精神颤抖中获得生命;这新生命会长大,沐浴着光、风和雨露生长起来。她在彩虹中看到了大地上的新建筑,而陈旧腐朽的房屋和工厂被荡涤一尽,建立在真理那生气勃勃的结构上的世界,与飞拱在我们头上的苍穹遥相呼应,浑然一体。[11]200-201”小说结尾中这一道淡淡的彩虹与诗歌中那一座横空而立的双脚惊人的相似,在不同的文本中遥相呼应。透过互文性这一视角,可以感知到:这两道看似不同时空的彩虹一方面体现出现实批判性和社会分析性,另一方面还具有寓言式的高度概括性和流溢出浓郁的诗性激情,它表明对新生命的渴望与追求是不可遏制的,对彩虹般绚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11]174-175劳伦斯诗歌和小说中的“花”的意象在互文性的视角下也显得颇有意味。诗歌《一朵白花》共有四行:
月儿娇小皎洁犹如孤零的茉莉花
寂寥地靠着我的窗,在冬夜栖息,
晶莹似菩提之花,柔和似清泉细雨
她闪耀着,我纯洁的青春初恋,但缺乏激情也是枉然。[3]34
此诗中的意象“白花”当指纯洁之爱情,然而这花的色彩“白”却暗示着这种爱情缺乏激情,是纯属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白花又是如月般遥远不可及,又似寒冬的孤零零的茉莉花一般冰冷地靠着窗,给人以寒气之感,不可亲近。这种白花的意象在劳伦斯小说中不胜枚举,譬如在《儿子与情人》中,爱花的米丽安与保罗外出采花,欣喜地发现了玫瑰花:一簇簇白玫瑰宛如凸起的象牙,那么圣洁……她感情冲动地向花朵举起手,然后向前崇敬地触摸它们。洁白的玫瑰花,暗示了米丽安对保罗的爱是滤去了人性本能的欲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抑或修女式的爱,她心灵中荡起的那一股激情也是幻化了的。花儿的气味、色彩透过嗅觉、视觉弥漫在人物的意识中。[12]76-80小说中白花的意象是诗歌中白花意象在社会生活里恋人心灵世界的情感投射和放大,是对诗歌主题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不过,在劳伦斯的眼里,这白的花和彩色的虹其实一样,在相互指涉的意义生成过程中,都是在现实世界的表层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色彩。
四、结语
劳伦斯作为小说家,他的诗歌自然蕴含着小说的因子;作为诗人,他的小说又势必少不了诗性的成分。他的诗歌和小说所存在的较为明显的互文性,体现出互释互补的意义指涉和内在关联。这种互文性所带来的意义指涉和内在关联可以拓展读者艺术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对于理解作品的主题、探究意象的内涵以及洞悉作者的情感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Allen,G.Intertextuality[M].New York:Routledge,2000:95-97.
[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3]Lawrence,D.H.The Complete Poems of D.H.Lawrence[M].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2002.
[4]劳伦斯.白孔雀[M].谢显宁,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84.
[5]马若飞.基于血性意识的终极关怀:劳伦斯诗歌中的伦理诉求[J].外国语文,2013,29(5):42-46.
[6]劳伦斯.性与可爱[M].姚暨荣,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106.
[7]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M].饶述一,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3:191.
[8]Marshall,T.The Psychic Mariner[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0:215.
[9]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
[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1.
[11]伍厚恺.寻找彩虹的人:劳伦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2]刘维荣.浅析劳伦斯小说中的若干意象[J].上海大学学报,1999,6(6):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