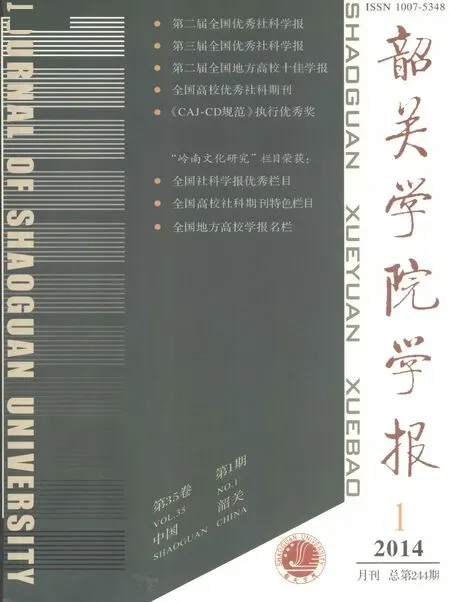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南经济生活的影响
李彩霞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宋代北方战乱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往南迁移。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替代陆上丝绸之路,并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南四周环海,港口遍布,地处海上贸易通道,经水路与内地、海外的贸易往来十分便利。在宋元时期,中外海上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一、宋元时期海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
宋元时期海南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较快,大量的商人、流放官吏及汉人移居海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海南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宋代海南港口林立,海口神应港(白沙津)与广口、泉州等贸易中心港都有密切联系,澄迈石躩港也是往来海舶停留的良好港湾。众多商船从海南出发,经崖山、新会至广州,“如无西南风,无由渡海,却回船本州石躩水口驻泊,候次年中夏西南风至方可行船”[1]。泉州港兴起后,闽浙商船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海南,“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2]57。
从宋代开始,海南与大陆经济共同进步,相互需求,双边贸易活跃。宋代海南虽然引进优良品种占城稻,稻谷产量大为增加,但因地瘠民贫、人口激增等原因,依然需要从对岸的雷州、廉州等地输入粮食。“海南所产粳稔不足于食,乃以薯芋为粮,杂菜作粥。”[3]“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4]“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可见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性。雷州到海南顺风只须半天,民间商人频繁往来其间,输入海南紧缺的米、耕牛、生产工具和日用品。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记载,海南深受大陆喜爱的特产有椰子、小马、翠羽、黄腊、吉贝、丁香、花黎木、高良姜等。当然,最受大陆欢迎的还是各类香料、槟榔和吉贝。宋代皇宫内廷和权贵阶层流行用香,檀香、乳香、沉香、丁香等域外进口香料十分昂贵,海南盛产名贵沉香,而且质量更好。从海南买香获利更高。海南沉香价本不贵,原始价仅一百三十文每两,一头牛可以换一担香,但因统治者升抬,使之一度与“白金等价”,运到大陆更可获利十倍。在厚利的驱使下,不少本地官员因贩香被革职查办。由于大量香药流入大陆,琼州知州朱初平在奏章中建议在广州设市,以便“和买”各类香药,虽未被采纳,但反映出海南香料舶卖之盛行。
槟榔和棉纺织品也是海南输往大陆的重要商品,“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海南、福建、广东人普遍嗜食槟榔,“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岛内外对槟榔的极大需求,刺激了海南槟榔的广泛种植。宋人王象之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非槟榔之利,不能为一州也”。槟榔税在海南“海商贩之,琼管以其征,岁计居十之伍”,是海南主要的经济支柱和重要财源。海南的棉纺织品享誉中原,在内地市场供不应求。宋真宗时提高麻布的收购价格,刺激了海南麻的种植,琼州四州军“岁四番收采,闽广专用之,常得倍利”。
元代海南与大陆的贸易往来紧承宋代而发展,从《云氏族谱》中的云从龙家书可看出当时的贸易情况。云从龙是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入元后任海北海南宣慰使。至元三十一年 (1294年)八月,云从龙从广州写信给时任万安知军的次子云铉说道:“今欲遣小舟过海南,可办藤席一万片,听侯船来装发前住,要在十月初间,不可过期失误。船到崖山,汝可一应付之。可将剑筇竹杖、花梨木货品寄来。”[5]138云从龙命儿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置办藤席一万片,及竹杖、花梨木等货品,可见这些货物在广东销路顺畅。
二、宋元时期海南的对外贸易
宋朝继承隋唐对外开放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海外贸易,进一步扩大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的外交商贸关系,使以南方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发展起来。据《宋史》、《元史》可知,宋代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婆(柬埔寨)、占城(越南)、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58个国家。元朝海南军事性质的屯田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人口、土地增长较快,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地区扩展到二百多个。商人汪大渊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对南海西南、印度洋航线及与其他国家通商的情况都有详述记载。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置琼管安抚司,统辖海南、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为鼓励、招引舶舟来华,北宋还设置巡海水师营垒,巡察南海海面,保证货船在中转、补给、避风时的安全。“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从屯门山用东南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6]即今西沙群岛附近。元朝在海口港外设置白沙水军,负责海上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水域的管辖。宋元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南海海洋的有效管辖,有力地保障了海上丝路的顺利发展。
海南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在古代贸易路线中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海南四州黎峒地与南蕃相望”,“自廉东南渡海,曰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中有黎母山,环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7]。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料、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8]14089。当时的贸易商船多以民间小船为主,商人经常在海南岛补充淡水和食物,中转货物。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出产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手工艺商品,多经海南向国外输出。近年来在海商汇集的陵水、三亚,陆续发现的北宋铜钱和瓷器,极有可能是从内地贩来,又从海南转口海外的。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迄通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七洲洋指海南文昌七洲列岛附近海面,亦可证明宋代已有航船在海南中转货物。楼钥 《送万耕道帅琼管》诗云:“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往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写船舶航行至海口休整补给再返回番禺(广州),反映了两地休戚相关的互补关系。海南本地物产中小马颇受海外欢迎。乾道年(1165-1173年)中占城人曾到吉阳军买马,“得数十匹”,第二年再来却没买到,淳熙二年又派六百人,驾船三十艘到海南买马,可见求购心切。
随着海南与内陆及东南亚贸易往来的日渐兴盛,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七月,琼州设市舶司,检查从南洋返回海南的船舶,向进出口商船征收船舶税。此外,“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舶舟分三等,中等日包头,下等称蛋船,由津务吏申告州军之差官,打量舟之丈尺,依据经册征收格纳钱,而本州之官吏兵卒,以之为支瞻”[2]58。可见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都有市舶抽税,也是海商集散之处。宋代船舶税附于商税之中,海南商税数额相当可观。据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统计,宋神宗熙宁元年到熙宁十年(1068-1077年),海南各税场税额增长近4倍,总计38 922 998贯。在同属广南西路的20多个州中高居首位,比首府桂州的18 903 580 贯高出两倍[9]。
元代总体上鼓励海外贸易,但自世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期间实行过四次海禁和长达三十余年的官本船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在海口设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管理海南的对外贸易事宜,海口港成为海货集散地。当时海南的交通分为东、西、外三路,其中东、西路指以海南北端的琼州为起点,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通往海南南部的岛内交通。外路指海南与内地和海外的往来。“外路:徐闻可半日。若达广州,由里海行者,顺风五六日;大海放洋者,三四日;福建则七八日;浙江则十三日。西自廉州二日。自儋州西行二日可达交趾;万宁县三日可抵断山云屯县;崖州南行二日接占城外番。”[5]137随着福建商船和移民的增多,在海口和白沙津都建立了天后(妈祖)庙,成为海南对外开放、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
三、疍民、番民、海盗及海外物种的传入
海南的经济兴衰、官方统治和民间生活离不开“以海为商”这一强大经济基础。宋元时期的海南,在参与海上丝路的过程中,疍民、番民、海盗这几大不同的群体得以出现并不断扩大规模,海外物种也传入中国,对海南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疍民。“疍民”最早见称于宋。《桂海虞衡志》称:“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为家。”疍民以渔为主,亦营运输,最早为百越一支的水居民族,以精于操舟著名。海南疍民散布在环岛的南北两大水域,尤以崖州、儋州、文昌、澄迈最为集中。唐朝实行“记丁输课”制,海南因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薄弱,使两广疍民大量移入。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下令海南富商可养疍民,“诏滨海富户得养疍民,毋致这外夷所诱”,两广疍民闻风南来。海南疍艇多采用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棹桨摇橹,小屋状圆拱篷顶,艇内空间宽敞,可容一家人居住生活,与黎族独木舟和汉族打鱼船皆不同。他们也不讲海南话或黎话,却讲广州话,皆可证明与两广疍族的关联性。海南疍民对海南岛开发贡献巨大,尤其在北粮南运中的运输作用。宋代因为北方移民越来越多,而本岛的土地开发地力十分有限,粮食短缺现象严重。为解决北米南运问题,宋太宗至道年间,朝廷“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其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官员遂令士兵送米到海峡北岸,再由疍民渡海来取,“海北岸有递角场,正与琼对,伺风便一日可达,与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第令琼州遣疍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8]9584-9585。
宋代在海南设“澄海军”戍海,其中“疍兵以疍民为之”,疍民被正式列入军籍。不过疍兵的职责主要是运粮,部分戍海,带有临时性质。元朝建立后,招募南宋末年的败兵及占城番人建立“白沙水军”,疍兵正式成为朝廷的经制之师。“收宋末祥兴败兵,置镇设官,管领海防。又籍占城降人为兵,立其首领麻林为总管,降四品印信,世袭。后俱为蛋人。”[10]
其二,番民。番民早在唐代就出现在海南。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海盗冯若芳、陈武振等劫取波斯船数艘,掠人为奴婢,很多穆斯林“蕃客”落籍海南。宋元对外贸易带动了海外移民的发展,因避难、投诚、躲避风暴及经商等原因而迁入海南的番客不少,琼州安抚司将他们安置在海口浦一带。《宋史》记载,“雍熙三年(986年)……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8]14080。“蒲”是阿拉伯语,音“阿卜”,蒲罗遏大概是居留在占城的阿拉伯后裔。海南最早的海外移民也始于宋代,《正德琼台志》记载,宋乾道八年(1172年),占城人来海南买马,掳走一批海南人,这应是最早的琼侨。宋元时期移居海南的蕃客主要是从大食迁到占城的占族,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迁居海南岛后不与当地黎汉人杂居,而是自发形成固定的聚居区,后来迁入的蕃客亦聚居在这些居住点内,将伊斯兰文化扎根在海南岛。如崖州“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亚里番村”[11];万州“至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番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安置”[12]。
元朝与暹罗的素可泰皇朝建有外交关系,元朝人可以到素可泰京都经商、做工以至侨居,两地贸易极盛。海南每年约有10至15艘船到暹罗湾初贝岛上收购棉花和燕窝,岛上聚居了不少海南人。“海南岛航行与暹罗贸易之船,皆泊于昆仑岛,以资樵没。”“暹罗有仁之棉花,每担约值暹币8株至12株,多输往海南岛。”[13]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也记述了中国商船载着海南槟榔航行至暹罗进行贸易,“货用青器、花印布、金、锡、海南槟榔、口蚆子”。
其三,海盗。海南扼南海航线之要冲,港口棋布,地势显要,“与安南、占城诸夷接境”,自古就是海盗逃避官兵追剿,逃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大海盗冯若芳、陈武振等人“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之住所也”。这些盘踞岛东南沿海的大海盗,因掠取粮食、波斯商船而富有。宋代海盗仍很猖獗,“海贼冲犯,如蹈无人之境”。为此朝廷特置“澄海军”,招收疍民充任疍兵,负责巡海任务,保护海上贸易安全。“庆历中,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澄海,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8]4642这些军队的主要作用就是打击海盗。
宋元海寇具有亦官亦商、亦侠亦盗的特点。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海盗陈明甫和陈公发组织一支几十艘海船组成的船队,占据崖州临川镇鹿回头(今三亚境内)要塞及重要商贸港口,向附近五十余村征收赋税,贩卖人口,号称“三巴大王”。又与海南陆地的黎族起义军联合起来,“倚强黎为党援,萃逋逃为渊薮”,官府不敢过问。咸淳十年(1274年)三月,琼管帅马成旺派大军出剿,二陈被俘,官府使用了罕见的酷刑处死他们,“悬髻、窒吭、穿足、钉手、炮烙其肤,脍缕其肉,运刀纷纭。”二陈抗击官府,自建武装,保护民间自由贸易,抢劫官商货船、外船。这种隐形的贸易战,令朝廷设市舶司垄断海上贸易的目的落空,故严加围剿。
元代虽有大军驻扎海南,仍有海盗出没,元朝特置白沙水军以“巡防海上”。至正九年(1349年)二月,一支海盗船队从交耻乘风攻合浦,进逼琼山,双方在澄迈石躩港交战,“海寇犯合浦,攻珠崖。宣慰使檄化州通判游宏道进兵会剿,宏道知友明为义士,命率师追贼于澄迈之石躩港,……俄而海南番兵先遁,寇乘胜四合……琼山县巡检周仁者,亦战殁”[14]。
其四,海外物种。宋元海南与占城、安南等东南亚地区物资交流密切,一些海外物种、特产被引入海南。占城稻是占城人培养出的一种高产良种稻,早晚二熟,“穗长而无芒,料差小,不择地而生”。岭南皆有种植,但其良种来自海南,“冬种夏熟曰小熟,夏种冬熟曰大熟。自宋播占城稻种,夏种秋收,今有三熟者”。那一次育种,被誉为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上的第一次革命。花生作为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也在宋元时从海外传入海南,“宋、元间与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贾)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原)”[15]。又菠萝蜜原产于热带亚洲。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中就有记载,南宋诗人范成大寓官广西时,也在《桂海虞衡志》中形容为“大如冬瓜,削其皮食之,味极甘”。明代诗人王佐《琼台外纪》认为波罗蜜树传入海南 “当在元中叶也。大抵琼居绝岛,或者气候类西海,故极繁盛。宣德季年,内使岁取充贡,临高甚若之”。并作《菠萝蜜》诗云:“硕果何年海外传,香分龙脑落琼筵。”清代学者屈大均亦认为,菠萝蜜于一千多年前自印度传入,大约在元朝中叶传入海南。
[1]叶显恩.广东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1986:61.
[2]赵汝适.诸蕃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19种[M].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3]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6.
[4]彭元藻.民国儋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729.
[5]黎雄峰.海南经济史[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
[6]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1055.
[7]周去非.岭外代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5.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小叶田淳.海南岛史[M].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50.
[10]明谊.道光琼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391.
[11]张嶲.崖州志[M].海口:海南书局,1914:34.
[12骨胄.正德琼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465.
[13]高虹.念郑和下西洋600年:海上丝路打开海南人视野[N].海南日报,2005-07-14(7).
[14]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开明书店,1935:315.
[15]檀萃.滇海虞衡志:卷 10 [M].长洲:小停云馆,18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