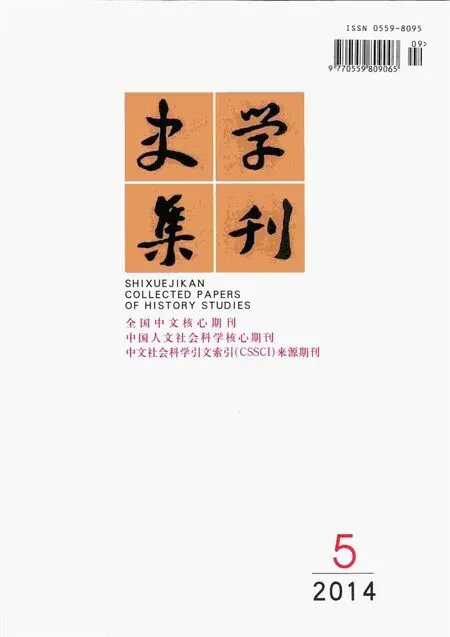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孙丽萍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①[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②[英]赫德利·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和理论的双重支撑。欧洲国际体系扩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动因:第一,国际体系主导单位的变化,部落、城邦、帝国、主权国家等人类组织形态的演进是推动国际关系嬗变的核心动力;第二,交往方式是衡量国际关系变革的另一标准,互动规模扩大、互动模式多样化及互动能力的提升是国际关系变革的先声。如果依据这两个标准,发端于欧洲的主权国家的全球扩张和互动能力的提升是推动欧洲国际体系发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的核心动力。
主权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欧洲现象,但在其早期形式绝对主义君主国出现后的几个世纪当中,它与中东、亚洲的古老帝国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酋长制、部落制、王国等人类组织形态共存于同一时空。直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主权国家形态从主权在君的绝对主义逐步转变为主权在民的国家形式,人民由臣民转变为公民后,主权国家实力大增并迅速崛起为欧洲人创造的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单位类型。1500年,欧洲人控制了全球陆地面积的7%。到1800年,他们控制了35%的陆地面积。到1914年,他们实质上已改变了三大洲的人口分布(南北美洲和澳洲),并控制了84% 的世界陆地。③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1990,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p.183.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是促成早期绝对主义国家转变为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要素。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行动,民族主义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时间上与工业化的兴起紧密相关。民族主义带来了国家形态的一场革命,“通过统一市场、行政管理体系、税收与教育,民族主义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方言、习俗与宗族,有利于创建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①Anthony D.Smith,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8,p.1.
民族主义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共同提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实力,为欧洲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关键性的物质权力。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普遍义务兵役制应运而生,人口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19世纪末欧洲各个大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成为衡量其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变革,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造、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主要内容。它产生的结果之一,是欧洲国家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保罗·肯尼迪指出,截至1900年,欧洲的工业资本与1750年相比增加了18倍之多,而当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军事用途时,实力差距即被进一步拉大,使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数十甚至百倍于落后地区。②Kenneth 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XVIII,No.4(1988),pp.149-150.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单位更有效率的新单位,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③[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在欧洲国际体系向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变中,互动能力的进步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互动能力是指围绕体系投送人员、物资、信息、货币和军事力量的能力。由马力和帆船等农业技术所主导的体系与以铁路、轮船、电讯和飞机为内容的工业技术所主导的体系相比,互动能力要差很多”。④[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颜震译:《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19世纪的轮船、铁路、运河和电报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互动能力的增长,使得距离和地理因素不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推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和强度全球传播与深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在地理空间上囊括全球、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为主导、欧洲外交惯例为规则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初步形成。与欧洲国际体系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欧洲不再是现代国际关系权力的唯一中心,美洲体系和东亚太平洋体系开始兴起。全球性国际体系形成之初,并不仅仅是一个扩大了的以欧洲为唯一中心的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和较为复杂的东亚体系对欧洲国际体系事态的发展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美日两国均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非欧洲国家,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时崛起为太平洋海上强国。如果说美国是欧洲的“衍生物”,日本则是欧洲的“仿制品”。美日的崛起表明这两大体系不再被动地接受欧洲权势大国的权力政治和秩序安排,它们不仅对各自的区域秩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美欧亚三大体系的互动还直接促成了整个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这是自1648年欧洲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作为新大陆的美洲和古老文明之一的东亚的事态对欧洲体系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当欧洲权势大国将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展到全球之际,其自身的多极均势格局却日益走向衰落。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内部的权力平衡,欧洲已经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全球性国际体系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杂糅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英、法政治家传统现实主义的产物。作为第一个全球性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形态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危机问题、大国权力失衡问题等,特别是德、日、意这三个“修正主义国家”,它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要求改变现状,重新确立其国家在战后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诸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并最终演变为德日意法西斯主义、英美新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矛盾与冲突,新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联合起来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美苏对抗的两极时代来临。
其次,国际关系主导单位——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日益多元化,多种意识形态和大国权力冲突剧烈。1870年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崛起,西北欧国家和美国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渐进式发展。但是,英美式新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唯一可能的形态,20世纪30—40年代,英美式新自由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和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较量。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演变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在二战后凸显并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全球性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
第三,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治理规则开始从欧洲无政府状态下的多极均势转变为大国合作下的集体安全,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都是集体安全的产物。同时,国际关系也开始悄然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叙事,开始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出现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从1865年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电信联盟成立,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这一趋势在二战后进一步增强。
最后,非西方世界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以主权平等的身份加入现代国际体系中,这是全球性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内容。日本是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其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人民也学习西方的政治革命、科学与技术革命,一战特别是二战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它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进行了选择或者尝试建立新的国家发展模式。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在部分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规则和惯例的同时,也尝试反抗或改造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机制。
综上,全球性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它上承多元并存的前现代国际关系,下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转型与裂变,是一座需要深度挖掘的学术知识矿藏。唯有借助多重视角和多种理论工具,研究者才能探寻到其中的智慧资源,思考历史,体察现实,预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