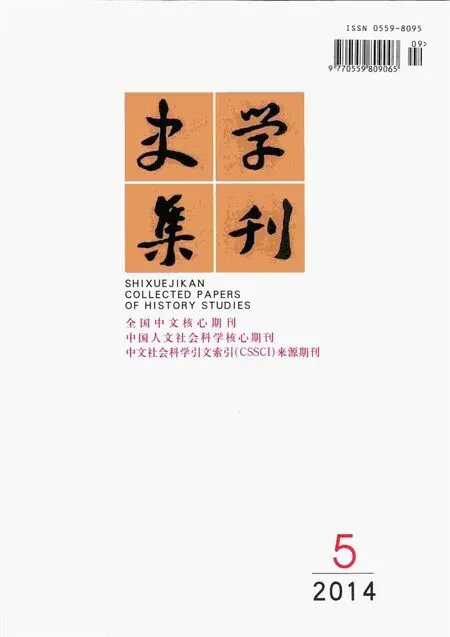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老人及其赡养
俞金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现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完备,有的国家被人们称为福利国家,那里的人们生老病死似乎无后顾之忧。但是,在福利国家形成之前,特别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西方人如何养老,我们所知不多。社会学家们根据传统农业社会的一般特征认为,那个时代的老人们生活幸福、安度晚年,他们的体能下降了,但他们因为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而获得了社会的尊敬。他们享有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的生活在家庭中得到保证。①见Durkheim,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p.23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p.950。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罗曼蒂克。
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上欧洲人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独特性的研究,使得社会学家对于近代以前西方人老年生活的描述,变得不是那么可信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方人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由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是欧洲社会中存在较为普遍的一种家庭生活模式,世代同堂的家庭在所有家庭户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②英国家庭史学家拉斯莱特宣称,工业化以前的很长时期里,英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75人。“在英国……,从已知的数字记录所包含的时间来看,大型的联合或扩大式家庭作为家庭群体的一种普遍形式,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存在过”。见P.Laslett and R.Wall(eds.),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126。此外,根据1622-1854年间对英国64个村社家庭结构的统计数据,由一代人、两代人和三代人所组成的家庭,分别占25.1%、69.2%和5.7%。欧洲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统计结果。见P.Laslett,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22,23,table 1.2。此外,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年轻人做佣工 (servant)的习惯,不少人早早就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他们结婚后就自立门户,大多不与父母住在一起。③J.Hajnal,“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D.V.Glass and D.E.C.Eversley(eds.),Population in History,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65;J.Hajnal,“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in R.Wall,J.Robin,and P.Laslett(eds.),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专门的研究可见 Ann S.Kussmaul,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这样的家庭形态与我们通常所了解到的农业社会中一般的家庭体系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使得我们特别希望了解欧洲农业社会老人的生活境况,如果老人们得以享受有保障的生活的大家庭环境这一情形,在社会中不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那么,老人们如何养老以及靠什么来养老,就不是社会学关于传统社会老人赡养的一般理论可以解释的了。本文试图在欧洲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老人及其赡养问题。
一、老人的概念
老人如何赡养的问题,与人们对老人的认识有关。在近代以前的欧洲社会里,谁是老人?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人到60岁或65岁就要退休,在现代的老人概念中,60岁或65岁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是进入老年期的起点。①例如,在二战以前的法国,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在60岁。自1954年以后,年满65岁或超过65岁的人为老年人,也是退休的标准年龄。[法]保罗·帕伊亚著,杨爱芬译:《老龄化与老年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但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以前是不大相同的。那时,人的生命质量十分低下。有研究者根据对1250—1500年意大利157名男子和63名女子的统计,男子的平均寿命仅为37.2岁,女子则只有33.14岁。②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83-85.对1276—1500年以每隔25年为一个时间单位,对每25年内出生者和死亡者的平均寿命进行复合统计,得出如下综合性的平均寿命数据:

1276—1500年佛罗伦萨人的平均寿命
从表中数据可知,14世纪初,佛罗伦萨人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左右。但是在100年以后,由于瘟疫的肆虐,平均寿命几乎减半。到15世纪时,尤其是1450年以后,平均寿命又大大增加,恢复到40岁左右的水平。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人口形势大体上代表了那个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状况。
但到近代早期,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人口历史学家对英国和欧洲贵族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的研究表明,在16—18世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贵族,平均寿命都仅有30多岁或40多岁。③T.H.Hollingsworth,The Demography of the British Peerage,Supplement to Population Studies,Vol.ⅩⅧ,No.2,1965,pp.52-69;T.H.Hollingsworth,“A Demography Study of the British Ducal Family,”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eds.),Population in History,p.362;S.Peller,“Births and Deaths Among Europe's Ruling Families since1500,”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eds.),Population in History,p.98.在英国,人口历史学家计算出1550—1599年英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2.5岁,1600—1649年为41.9岁,1650—1699年及1700—1749年这两个时段里,这一数字一直都停留在39.5岁的水平上。直到1750—1799年,英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才上升到45岁。④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81,p.252.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口发展趋势总的估计是:在12世纪时,欧洲人口增加了,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14世纪的前几十年,人们的预期寿命逐渐下降,而在该世纪中后期,由于黑死病及随后的几次瘟疫,人口数量及人的平均寿命均大幅下降。从15世纪至16世纪又逐渐恢复。在某些地区,这些数字的增长在15世纪的前25年里就已开始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可能要到15世纪晚期,甚至到15世纪末才开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是恢复性的增长,在人的预期寿命方面,18世纪中叶以前,始终停留在40岁左右的水平上。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40岁左右的预期寿命实在不长。所以,也难怪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欧洲说成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世界。①一位历史学家说,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社会。见Henry Kamen,European Society 1500-1700,London:Hutchinson&Co.Ltd.,1984,p.26。马克·布洛赫在讲到中世纪时也提到,老年早早来到,那个世界自以为很老,但实际上都由年轻人统治着。Marc Bloch,Feudal Society,I,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Kegan Paul Ltd.,pp.72-73.不过,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数字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好像社会中到处都是青壮年人群,已经没有老年人了。或者误以为某个年龄达到30岁的人,按平均寿命40岁计,只能再活10年;25岁的人,还可再活15年,如此等等。②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New York:Charles Scibnier's Sons,1984,p.109.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如此,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总体的生命质量。就每个个体而言,寿命的长短大不一样。有的人寿命很长,有的人则过早夭亡。实际上,正是这些过早夭折的人 (他们的数量比较多),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处在较低的水平。在近代早期的三个世纪里,欧洲的婴儿死亡率大约在150‰~250‰的水平。在有些国家,约有1/4的婴儿在一周岁之前就夭折,这就是广泛存在于近代早期欧洲人口体系中的一个特征。活过了一岁的孩子,命运依然不可预测。据估计,在欧洲范围来说,几乎有一半的孩子在10岁以前夭折。③Michael W.Flinn,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 1500-1820,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16-18.
但是,一旦躲过了婴幼儿和儿童高死亡率的危险期,人的长寿机会就会明显增加,活到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期和地点,尤其是排除黑死病时期的特殊情况,可以说,在中世纪中晚期,年龄在20~25岁的年轻人,有望再活30年,无论是贵族、教士、市民,还是农民,各社会阶层的年轻人都有这种可能。这就意味着,已经是20多岁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是50多岁。④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p.250;E.A.Wrigley,et al.,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80-293,Appendix 6,pp.581-600;Barbara Harvey,Living and Dying in England 1100-15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27-129;Richard T.Vann and David Eversley,Friends in Life and Death:The British and Irish Quakers i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165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Table5.11 and 5.12,pp.229-230.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活到60~70岁,甚至更长。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427年的托斯坎尼人中,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4.6%,而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占了9.5%。在1425年的维罗那,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占被统计人口的15.2%,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8.8%。⑤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pp.183-187.这种比率可以说明15世纪意大利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相当高了。在英国,“倒推法”统计出来的从1541年到18世纪末60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始终在7%~10%之间。其中,多数时段的老人比率在8%~9%。⑥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pp.215 -218,Table A3.1,pp.528 -529;P.Laslett,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Table 5.3,p.188.丹麦、冰岛和瑞士的多数地区,这一比率也在7%以上。老年人口低于7%的地区主要在比利时、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等国家。⑦P.Laslett,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Table 5.2,pp.186 -187.
如前所述,把60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划入老年行列是一个现代的老人概念。有关研究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公共生活中,60岁作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晰。⑧在英格兰,13世纪以后,担任陪审员的最高年龄一直是70岁,但60岁以上的老人担任地方行政官或验尸官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在14世纪中叶以后,劳工法规定60岁的男子可免于提供强制性劳动;不再因流浪而遭告发。他也不用强制性地参加法庭诉讼或服兵役。18世纪后期,海关职员享受养老金的最低年限定为60岁。1810年,60岁成为公务员退休的年龄。参见Keith Thomas,“Age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LⅫ,1976,p.237。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40岁的情况下,60岁的人自然就是老人了。然而,在数个世纪以前,人们的老人概念中的年龄标准可能比60岁还低很多。有人主张50岁为老人的标准,①Gransden,Antonia,“Childhood and Youth in Medieval England”,in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16(1972),pp.3 -19.如果以这个年龄为起点,那么,欧洲农业社会中老年人的数量会更多。
不过,不论是以60岁,还是以50岁作为衡量进入老年期的标准,都具有现代人的思维特征。实际上,在欧洲农业社会里,老人概念未必是以确切的岁数来表达的。那时,成为成人的年龄,因为与财产继承和有关法律的权利、责任相关,而显得比较重要以外,在其他场合,年龄要求可能并不十分严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自己的年龄只记得一个大概。②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pp.159-164.一直要到16、17世纪,随着教区登记在欧洲各地陆续推行以及一些君主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人的准确年龄才开始得到重视。③Georges Minois,History of Old Age: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p.289 -291.
所以,在那个时代,在日常的生活情景中,真正的老年是由人的身体状况来表示的,身体的衰老便是老年人的全部证明。因此,老年与其说是某个年龄,不如说是某个过程,是一个人的劳动能力逐渐衰退,身体健康状况逐渐衰弱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那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在这里,每个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就像孩子也可以成为家庭劳动力的一部分一样,年纪较大的人也可以继续在家里从事生产活动,只不过是孩子参与生产过程的程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进一步扩大,而老人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退出生产活动。所以,在农业社会,老人的概念是与那个社会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人生状态,从主要是一名生产者转变为主要是一个消费者,没有一个断然的年龄界线。但50~60岁是人生转向老年人的过渡期,在欧洲历史上,很多农民往往在50~60岁就逐渐地把财产的经营管理和持家的责任移交给继承人,这可能就是老年过程的具体体现。
二、有儿有女不成为养老的依据
人一旦脱离生产活动,就面临着养老的问题。从伦理上讲,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儿女的基本责任。在中国,这个观念始终是清楚、确定的。一个“孝”字便概括了一切。在基督教文化中,也强调子女要孝敬父母。④《摩西十诫》,《旧约·出埃及记》20∶12;《申命记》5:16。《新约·以弗所书》6∶1-3。在中世纪,孝敬父母的责任包括在父母生病时提供关怀照料;父母年迈时,提供生活需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就是孝敬父母的基本思想。孝敬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包括在父母死后,子女应当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做弥撒。因此,孝敬老人、赡养父母在中西方的文化中都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
不过,在确认这一点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基督教学说中还存在着一种离心的因素,那就是夫妻关系重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⑤《旧约·创世纪》2∶24。
西方人早就意识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的爱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父母因为爱儿女而做出的奉献,超过了子女为孝敬父母而给予的回报。父母的爱被认为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们是这样来解释父母与子女相互之间的爱的差别:胚胎由父母的本体所组成,子女吸收了父母的某些本体,但反过来,父母并没有从子女的身上得到什么。所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树根与树木的关系,树木从树根部汲取营养。树木虽然也以雨露滋润根系,为其遮阳,但它从树根所得仍然多于给树根的回报。⑥而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西方人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的差别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如此下传,一代一代地接力,故称为“接力模式”。而在中国,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形成了“反馈模式”。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第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中国家庭研究》第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该文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首发。这样,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自然就超过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圣经》上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①《新约·哥林多前书》12:14。
只是根据道德上的要求,指望子女为自己养老是靠不住的。中世纪的西方人对于养老的态度,一是告诫人们要为老年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各种各样的劝告书不断地敦促人们要积累充分的财物,以便为自己年迈体弱,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时所需。人们应当从中年时就开始做这种准备,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老来陷入贫穷更痛苦、更艰难;二是敦促人们不要在生前将财产转让给子女,以免落入依附于子女、受他们摆布的结局。15世纪的一位意大利人说,只要父亲还是一家之主,他的儿子就会服从他。一旦儿子掌握了家产和家中的权威,他就开始憎恨父亲,威胁他,等着他早死。这样一来,信任儿子的父亲就等于把儿子从朋友变成了敌人。②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7,p.93.在英国,14、15世纪的一些资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上下代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因为年轻人想取得家庭资源的控制权,而老年人则希望老有所靠,晚年生活能得到保障。③Barbara A.Hanawalt,The Ties That Bound:Peasant Families in Medieval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28.直到17世纪,英国做父母的人对于子女如何善待他们都没有抱什么幻想,“在子女的屋檐下生活,比坐牢还难受”。④Lawrence 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235.这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老年父母与儿女关系的一种认识。
在欧洲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各种故事、寓言,反映了人们对养儿防老的幻想的破灭以及由自己来掌握财产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
有一个在欧洲很多国家家喻户晓的故事,这是15世纪传教士布道时常用的一个事例。很久以前,有一名富人,他曾拥有大量的财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逐渐衰老。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许配给了一名年轻人。老人将自己的女儿,连同全部财产、房屋和土地交给了这个年轻人,以换取安度晚年。头一年,年轻人善待老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老人也有同样的享受。第二年,他把老人吃饭时坐的位子挪到了餐桌的另一端。老人的饭菜当然要比年轻人自己所吃的东西差一些。第三年,他把老人挤到厨房一角的地板上,让老人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年轻人还告诉他,他必须从房间里搬出,因为妻子 (老人的女儿)要在这间屋子里生小孩。于是,女婿以此为借口将老人逐出房间,老人只好在靠后门的一间小屋里安身。老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叹息。他决心设法来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天,老人向他们借来一个篮子,然后关上门,用几个旧硬币在篮子里倒腾,发出很大的响声,让人觉得他在数钞票。这家有个孩子,他站在老人的门外,以为听到的是老人在篮子里在装金币银币的声音。他回去后,便将所闻告诉其父。年轻人听说了这一情况,便来到老人面前,对老人说:“父亲,您老了。如果您有什么金银财宝,您可以交托给哪个靠得住的人去保管,免得您操心,这样做比较妥当。”老人随后答道:“我的钱箱里还有一点钱。有一部分我留着,以备生后安魂之用。我想,等我死后,这笔钱就由你来处置。”老人把篮子还给他们,并在篮子的缝里故意夹着一个银便士。他们了解到这一切以后,便把老人领回他的房间,像从前那样善待老人。老人死后,他们就翻箱倒柜,搜寻老人的宝藏。结果,除了一把小木槌,他们一无所获。棒槌的背面写着一句话: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子女,结果使自己沦为乞丐的蠢人,要受此棒的惩罚。⑤这个故事在欧洲很多国家流传,内容大体相同,而细节稍有出入。可参见Frances&Joseph Gies,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Harper& Row,1987,pp.249 -250;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p.94;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 Richard Wall,Jean Robin and Peter Laslett(eds.),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60。
据说在现代德国的一些城市里,还悬挂着这样的一根大棒,上面刻着这样的话:“谁使自己依赖子女为生而陷于贫困,谁将被此棒击死!”⑥参见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Richard Wall,Jean Robin and Peter Laslett(eds.),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pp.259 -260。
上述这类寓言和告诫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不是个别地区、个别国家的现象,它流行于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内的西欧、北欧和中欧地区,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不可根据这些故事和警言把西方历史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做片面的理解,误以为上下代人的关系十分糟糕。事实上,很多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将财产让渡给自己的儿女。而年轻的一代也不都像寓言中的人物那样虐待、唾弃老人。任何时候和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父不慈、子不孝的事情。但是,充满温情的家庭关系在社会中总是到处都存在着。上面的阐述意在说明:在养老方面,中西方人的态度和倾向性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道德和法律都捍卫孝道,人们的养老之道集中地体现在“养儿”这个人人沿用、代代相传的策略上,通过养儿以达到养老的目的。西方的情形则大为不同,社会告诫人们,仅仅依赖儿女来养老是靠不住的。老人所能依靠的不在于生养了多少子女,而是自己积累和控制了多少财产。有了自己的财产,儿女们就会喜笑颜开,他的意见就会受到尊重,说话就有分量。如果没有财产,或者放弃了对财产的控制权,那么,老人就有可能失去养老的依靠,受人冷落。一旦年迈体弱,财富往往就成为受人敬重的唯一资源。①Keith Thomas,“Age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LⅫ,1976,pp.247 -248.
这样,以财产换养老就成为农业时代的欧洲人广泛采用的养老策略,老人通过“退休”这个行为,将财产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给自己的继承人,并以签订养老协议的形式,确保继承人承担赡养的义务。
三、退休和退休协议
在西方,“退休”的概念和行为早已有之。
公元6世纪时,一些富人出于救赎的目的,不再从事尘世的活动,他们退休到修道院,为永生做准备。但在当时,退休只是少数富人的事。到公元8、9世纪,退休成风。一些地方的大型修道院激增,以便为老人提供寄居之所。而教士们因为从富有的退休者那里获益不少,也鼓励人们退休。退休有两种形式,一是与教士一起住在修道院里,并参与修道团体的活动;二是住在修道院外,接受供养金。退休要签协议,具体规定供养的各种条件。当然,退休者的待遇因人而异,这要取决于退休老人给修道院捐赠了多少财产。②Georges Minois,History of Old Age,pp.137,13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一些经济状况差一些的老人,退休的待遇就会较差。有的人若体力允许,还得为修道院干活。
后来,世俗社会也开始采用了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方式。在富有的社会阶层中,一些人为忠心耿耿的老年骑士建起退休之家。尽管这只涉及少数人,但它有象征意义,达官贵人们已经接受了为他们的老年仆从养老的观念,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有的地方的商人和工匠也开始学着过退休生活,他们将自己的财产抵押给养老机构,以换取在年老时有基本的生活待遇,有人能照顾他们。而慈善机构则为他们提供养老之家。③Georges Minois,History of Old Age,pp.245 -247.
所以,在欧洲社会中,“退休”算不上新生事物。当然,对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贫如洗,与“退休”根本无关。但是,退休的观念在社会中算是扎下了根。
大约从12世纪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对于退休和养老就做了规定。那个时代,拥有土地的老人如果想退休,就要去司法机构或当地的法庭,提出退休的要求。那些希望能得到老人的财产,并有意赡养老人的亲属也必须到法庭表明自己的意愿。老人的退休事宜安排妥当后,他就在这些亲属中间,每隔一定的日子轮流在各家生活。他在某个亲属那里居住时间的长短,直接与该亲属所继承的财产数量挂钩。这样一种制度在13世纪时所有早期的丹麦人的法律中都可以发现。④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p.251.以这种方式退休的人,被称为fledf ring,意为他是一个从自己家里走进另一个人家里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性法律对于退休之人没有专门的称呼,但都提到某人将财产交托给他人,以换取为自己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这一行为。14世纪20年代中叶以后制订的H lsinge法,通行于瑞典北部和芬兰的北部地区,其中使用了Sytning一词,来指称上述那种关系。Sytning源于动词syta,它是一个方言,指“看护”或“关照”某人。①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p.252.
在德意志的法典中,最早提到农民退休的是14世纪早期的一个地方法庭,它应用的一个条款规定:将要退休的农民,应当有权利从以前的住处得到“最好的床、水壶、锅、犁、马、推车等等”。还有一个条款进一步规定,继承人应当承担起将要搬到Leibzucht去的退休者的债务。Leibzucht是一块建有住所的小土地。这小块特定的土地是从现有的农场中划分出来的,老人死后要直接归还给继承人。②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p.254.在中欧,退休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及宗族法中。在中世纪的中后期,那里出现了养老财产。到近代早期,转让财产和养老的契约性规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③[奥]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著,赵世玲等译:《欧洲家庭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奥]赖因哈德·西德尔著,王志乐等译:《家庭的社会演变》,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51页。Thomas Held,“Rur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in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Austria:A Cross Community Analysis,”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3(Fall 1982),pp.227-254.
在英国,很多世纪以来,退休一直成为英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而且在各社会阶层中都得到实施。④David Thomson,“Welfare and the Historians”,in Lloyd Bonfield,Richard M.Smith and Keith Wrightson(eds.),The World We Have Gained:Histories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361.在农业社会,退休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有关。据研究,13世纪的一些英国庄园上出现了实行退休并将财产转让给儿子的养老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普遍。13世纪是一个人口压力严重、土地短缺的时代,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并不急于离开老家,他们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在父母年迈时仍有儿女留在身边。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在英格兰东部地区,获得土地比较困难,到13世纪时,退休的安排已比较流行了,当作为继承人的儿子结婚时,父亲就退休,并将财产传给继承人。另外,寡妇 (并不一定是年老的寡妇)在不能亲自耕种土地和为领主履行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相应的义务时,她们就将农场让渡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是让渡给女儿和女婿。她们宣布退休时,有时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特别在自己无力经营农场时,自己提出退休。有时则是出于某种压力 (比如来自领主的压力或继承人到了法定的年龄)而不得不退休。1348年的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损失,引起劳动力短缺,加上人口流动的频繁,一些有儿有女的农民急于将自己的子女安置在本村,以确保有继承人来耕种土地,并为自己养老。所以,退休协议到处激增。⑤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p.153.在这方面,伊莱恩·克拉克对中世纪英国养老协议的研究,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那个时期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她所研究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于英格兰东部的159个案例,其中3/4的案例属于黑死病以后的历史时期。⑥这159个案例的分布,从地区上看,有114份退休协议书来自于诺福克的21个庄园;22份来自于埃塞克斯的6个庄园。从时间上看,12个案例属于1258—1299年;33个是1300—1349年订立的。1350—1399年签订的有42个。1400—1449年的协议有64个。属于1450—1457年的共有8个。见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p.307-320。可见14世纪中叶的那场瘟疫对于退休这一在此前业已存在于西方社会的保障方式的进一步推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莱恩·克拉克说,黑死病以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不仅影响到老人的处境,而且也影响到领主和其他土地承租人对退休问题的态度”。⑦以上退休协议可参见伊莱恩·克拉克上引文,第310页。
退休协议是退休者和赡养人之间订立的养老合同。退休者将财产让渡给继承人,作为回报,后者同意承担赡养义务。通过退休协议,双方建立起互惠的交换关系。由于退休合同直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特别是退休的一方今后的生活直接取决于养老合同中的各项规定,因此,这种协议往往规定得十分具体、详尽。为了对这种协议有一个明确的印象,我们在这里选取伊莱恩·克拉克所提供的几则协议以做参考。
第一则协议。约翰·鲍威尔和妻子爱玛将一所宅院、一间茅舍、10英亩的土地和半竿⑧英文为rod,长度单位,等于16.5英尺。分散于别处的习惯占有地转让给约翰·爱斯特怀思及其妻塞西利亚。作为交换的条件,后者要为老人提供正屋北首和东首的房子各一间,在北首提供一间谷仓、一头母牛,夏季允许放牛。每年给四便士、一头猪、一只公鸡、八只母鸡,宅院内的半数水果,2.5英亩足以应付生活需要的土地。新的土地承租人要支付六马克①英国以前的货币名称。三先令四便士,以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付三先令四便士的形式分期付完。
第二则协议。莱斯特的儿子亨利将一所宅院和17英亩土地交给爱玛·阿特·斯蒂勒的儿子亨利。条件是后者要“真诚、适当地”照顾好前者。如果双方不和,致使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后者必须每年向前者提供八蒲式耳的小麦、八蒲式耳裸麦、32蒲式耳啤酒。如果老人先于新的土地承租人去世,那么,后者必须提供20先令以料理后事。支付手续费28先令。
第三则协议。陪审团介绍,死者亨利·佩科曾拥有一所宅院,10英亩土地,半竿习惯占有地。他的孙子也叫亨利·佩科,作为死者的继承人,小佩科也已成年,他请求继承上述土地。但老佩科的遗孀琼·莱切要求把其中的一半土地作为遗孀财产,她的要求得到同意。这样,双方各得老佩科的一半土地。小佩科可以在寡妇莱切死后得到另一半土地。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老妇保留地下、地面各一间房,一小块土地,她本人和她的朋友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条件还有:她在每年的11月30日得到价值12便士的柴草。每年得到八先令,并分四次支付,支付的日期分别是11月30日、复活节、6月24日和9月29日。小佩科要为她翻修两间她所住的房子,给她提供与自己所享用的一样的伙食待遇。如果她对伙食不满,她可因此而每年得到12便士补偿。她可以随便进出正屋。②以上退休协议可参见伊莱恩·克拉克上引文附录,第317-319页。
从上述几则来自于中世纪英国的退休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双方的交换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来进行的,金钱货币因素在其中比重不大,这种情况可能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直接相关。到近代早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种退休协议中的金钱因素明显加大,一则订于1785年的丹麦的退休协议这样写道:
女婿佩特为取得该农场要一次性付给我们100 rigsdaler。我们保留使用原有的大房子。佩特自己的房子另行建造。
此外,他每年要给我们交付养老金20 rigsdaler,3桶上好的裸麦粉,3桶可用于酿造优质啤酒的麦芽。1桶未经加工的裸麦,1桶大麦,1桶燕麦。大鹅、小鹅4只,要喂养得好好的。4只在冬夏季喂养的绵羊及小羔羊。每年2头活猪,1桶上好的黄油。在奶牛产奶时节,每天2壶牛奶。8担泥炭。以干净的羊毛、麻制衣服饲候好老人。③David Gaun,t“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p.279.
养老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住、吃、穿、用等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从上述几则协议的情况看,有的协议的条款比较简单。有的养老条件显然比较高,像丹麦的这则养老协议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显然已超过了维持两位老人的一般生活水准的要求。因为这种退休协议从根本上说就是协议双方的交换关系,所以,退休者所拥有财产的多少成为他换取养老条件时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和财产的人就可以提出较高的养老条件,他不仅可以提出足以让自己过上富裕的晚年生活的要求,而且还提出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比如在生病时,要允许朋友来探访;规定好丧葬及做弥撒安魂事宜。有的人还要求继承人替自己清偿债务,定期洗衣服,得到一间可供取暖的房间、裁衣用的剪刀、酿酒的大桶等等。还有的人要求得到自由出入厨房、花园的权利。这种种要求和权利无不反映了退休者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关心,更是反映了他的谈判实力。
相比之下,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拟订退休协议时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④据统计,维持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土地大约二、三英亩。因此,只有拥有比这更多的土地和财产的人,才有可能提出适当的养老条件。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令人同情。为了保证能得到别人关照自己,有的人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在诺福克的弗蒙特汉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一对退休夫妇为了取得赡养,不仅向新的承租人交出了一英亩耕地、一间住所及其附属的财产,而且还交出了床单、毛毯、被褥、头巾、衣物以及除了两只锅、两只碗和两只木箱以外的所有家用器具。在欣多尔伐斯顿,还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对老年夫妇将他们的住所和五英亩耕地交给当地的一对年轻夫妇以换取养老,并同意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要帮后者干活。老人们可以寄居在原先自己的房子里,吃、喝待遇与佣人一样。①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312.
做出退休安排总是有某种原因的。在通常情况下,年龄和身体状况促使老人考虑自己的养老退休事宜,大多数老人与自己的子女达成退休协议。英国诺福克郡的威廉·德·托诺维尔来到庄园法庭,说自己年迈体弱,生活贫困,如果没有“朋友”(儿子)的帮助,他已不能种地。法官和领主的管家听了他的这番诉说后便与领主作了商量,同意老人将房产、土地,连同老人的地租、劳役义务和对老人的另一个女儿的抚养责任,都交给了老人的儿子。儿子同意“诚实赡养”自己的两位亲人,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②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311.
诺丁汉郡的理查德·洛伍德的退休可能与继承人的婚姻有关。他将他的茅舍及其附属物的权利交给领主,洛伍德的继承人爱玛及其未婚夫向领主支付了5先令的费用后就占有老人的土地。小伙子答应要与爱玛结婚,并为老人提供衣、食等生活需要。③参见 Eleanor Searle,“Seigneurial Control of Women's Marriage:The Antecedents and Function of Merchet in England,”Past and Present,82(1979),p.32.
有时,户主在临终之前,以遗嘱的方式安排财产让渡。虽然这看上去不像是拟订退休协议,但遗嘱人往往要为遗属,尤其是配偶将来的生活做出安排。1407年,约翰·怀汀就是用这种方式安排财产让渡和遗属的生活的。他将宅院和土地交给西蒙·惠林,条件是:惠林将来要为他的遗孀提供生活需要,包括吃、喝和每年16蒲式耳的啤酒。此外,惠林还要给她6只母鸡、1只鹅、1头母牛。每年的农耕时节要为她耕种一英亩的土地。每年的复活节要给她提供1双鞋子和3先令用以做衣服的费用。最后,要允许她在家里继续生活,保证她有出入灶间、房间的自由。④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311.
领主的干预也不可忽视。由于农民从领主那里租种土地,所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限的,⑤参见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61页。他所占土地以对领主履行封建义务、交纳封建地租为条件。因此,农民耕种土地或转让财产,直接关系到领主的利益。这样,农民的所谓退休安排也可能是领主干预的结果。在土地的现有承租人无力胜任耕作和偿付租金的情况下,领主和村社共同体的有关人员就会上庄园法庭,安排新的土地承租人接管老人的土地,并安排新的佃农为老人养老。1382年,诺福克郡欣多尔伐斯顿地方法庭的陪审员说,该村住着一位贫穷可怜的寡妇,她拥有18英亩耕地。但她身体虚弱,头脑简单,无法照顾自己,也无法履行她对领主的义务。因此,他决定将她的土地转让给她最亲近的继承人,让该继承人为这位可怜的妇人养老,为她提供相应的生活需要。这种退休养老的安排其实并不坏,它使三方面都得到妥善的处置:对老人来说,他 (她)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法律保障。养老协议在法庭上是作了详细的规定的,并由领主和法庭来监督执行;对领主来说,他是鼓励这种安排的,他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替代老人,从而保证自己能得到地租和土地让渡的费用;而新的土地承租人则因此而获得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土地财产。⑥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310.Thomas Held,“Rur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in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Austria,”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3(Fall 1982),pp.230-231.
我们已经指出,仅仅指望儿女来养老是靠不住的。但是,大多数养老协议仍然是在父母与子女或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签订的。根据雷齐对英国伯明翰郡西部的黑尔斯欧文教区法庭的档案的统计,在1270年到1348年间签订的老年农民与他们的土地继承人之间的61份养老协议中,有34份是父母与子女所签,6份是祖孙间的协议,还有20份是一般的亲族成员之间订立的协议。与近亲以外的人签订的养老协议只有1份。从1350-1400年间43份养老协议中,与儿女和孙子女所签协议20份 (占46.5%),与一般的亲族成员所签协议19份 (占44.2%),与外人所订协议只有4份 (占9.3%)。这表明,老年农民明显倾向于在家内或是在亲族成员之中寻求养老。不过,从1430年代起,该教区所签养老协议中,老人与亲属成员之间订立的协议比例开始大大下降,36名退休的农民中,有27位(占75%)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显然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以换取养老。①Zvi Raz,i“The Myth of the Immutable English Family,”Past and Present,No.140(August 1993),pp.12-13,27,32.伊莱恩·克拉克也发现类似的情形,在14世纪中叶以前,与子女签订养老协议的比例较高,而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这类协议的比例大大下降。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显然就是黑死病造成的高死亡率,使得很多老人失去了儿女、亲人。也因为黑死病以后,人口流动增加。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No.4(Winter 1982),pp.314 -315.
上述数据 (特别是退休老人与亲属成员之间的协议占较高比例)看上去与我们所主张的仅仅指望儿女为自己养老靠不住的观点相矛盾,其实,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父母与子女及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的天然亲情决定了老人首选亲人作继承人,并由他们来承担养老的责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亲情并不决定赡养关系,决定赡养和被赡养关系的因素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正像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农场的拥有者和他 (她)的继承人之间达成书面或非书面的退休安排,通过这一安排,财产所有权或农场的世袭承租权得到转让,以换取退休户主的生活需要。从法律上讲,退休协议不是子女对父母的个人义务,与报答养育之恩的关系不大。尽管继承人往往是儿子或女婿,但退休安排并不必然意味着亲族关系。②参见 Thomas Held,“Rur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in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Austria,”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No.3(1982),p.228。
因为退休协议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关系。所以,从协议的条款中,我们看不出订立协议的双方显示出多么深厚亲情。不仅如此,协议的订立、执行、变更或解体都经历了一定的法律程序,这就使得协议的双方即使是最亲密的父子关系也都成了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方面,庄园法庭的介入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退休者担心今后会受到其继承人的虐待,那么,他就可以去庄园法庭订一份正式的养老协议。③Zvi Razi,“Family,Land and 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No.93(November 1981),p.7.如果老人的权益的确受到侵犯,他就可以去法庭提出申诉,法庭不仅出面干预,甚至还对违约者罚款。④Frances Gie and Joseph Gies,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Harper& Row:1987,p.172.对于诸如拖欠老人的钱物,阻止老人根据协议的规定自由出入某些地方及遭受虐待等申诉,法庭会进行调查。如果情况确凿,陪审员就会对违约者提出警告,乃至中止退休协议,将财产退还给退休者。⑤在英国的诺福克郡,有的协议规定,如果土地的继承人没有履行对老人应尽的义务,唾弃老人,有12位邻居作证,老人可以收回财产。
有时,退休成为一个公开的事情,赡养老人的责任处在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退休者的权益通过保证人得到保护,儿子要在法庭上当着证人的面,发誓赡养父母。在有些情况下,继承人要向当地法庭提交保证书,登记为赡养老人而抵押的物品名称,如果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法官可以扣押他的财物,直至他履行义务为止。在某种意义上,儿子在法庭上立下的保证书如同法庭的判决书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在儿子违约的情况下,老人不必提起要求赡养的法律诉讼,法庭有权根据保证书来执行协议。当财产让渡发生在法庭以外,如土地拥有者在临终前让渡财产,庄园法庭会派人作证,并在下次开庭时报告、登记。⑥Jane W hittle,“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 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0-1580,”Past and Present,No.160(August 1998),p.34.这种情况类似于户主的临终遗言,目的是为配偶今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养老协议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是有条件的养老,谁接受了土地和财产,谁就承担赡养的义务,像债务一样,赡养的义务有时是可以转让的。1415年,在英格塔斯通,有一位小土地所有者在临终之前将一间茅舍和一英亩土地交给妻子使用,条件是她要照顾好他体弱的姐姐,为她送终。从交换关系来看,赡养的负担比较重,但其妻还是同意了这个条件。由于她很穷,她要求法庭减免了通常在让渡财产时应交纳的费用。法庭同意了她的请求。两个女人随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6个月。后来,她从茅舍中退了出来,安排当地的一名男子接管了土地,并让他承担起赡养老妇人的责任。这名男子与老妇人共享了这间茅舍达一年,然后又把它连同那一英亩耕地卖给了另一位村民。1418年时,该村民又以24先令的价格出卖了房子和土地。①Elaine Clark,“Som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in Medieval England,”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No.4(1982),p.313.
由于养老不是根据上下代之间的亲缘关系来确定双方的义务与权利,所以,养老的契约是开放的。即一方面,儿女可以不参加签订养老协议;另一方面,老人也可以将养老的希望寄托在他人或机构身上。
四、机构养老
事实上,正如在前所述,与养老有关的“退休”一事就首先发生在社会机构中。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机构养老主要是宗教机构所承担的赡养责任。宗教机构所承担的赡养对象有两类,一类是机构本身的人员。在宗教团体中,老年人的数量不少,至少,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由老年人把持的。有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从职位上退下来。有的则至死都占据这些职位。对于这样有身份的老人,修道院会提供适当的生活待遇。此外,有些修道院也为长期在修道院里供职的老年俗人和低级教士做出养老规定,这些人包括牧师、侍从、面包师、洗衣女工、男女仆佣等。对这些人,修道院有时提供养老金,或者是雇员用积蓄购买养老待遇。养老的待遇通常包括住所和与个人的地位和资财相适应的衣、食。不过,这种为在修道院中工作多年的人在年老时提供生活保障只是一个道德责任,而不是一个法律义务。
修道院要负责赡养的另一类人不是修道院中的教士或工作人员,而是以财产或金钱换取养老生活的普通人。在中世纪中晚期,有很多中老年妇女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尤其是一些寡妇,她们喜欢选择修道生活。还有一些女子,一心想做修女,但在年轻时为父母所逼,只好结婚,到了中老年以后,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修女,她们放弃了家庭生活和个人财产,由修道院负责她们的晚年生活。到中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子也开始进入修道院,这些进修道院的男子不是做教士或修士,而是成为领取养老金的人,他们以自己的财产来换取养老生活。这样,修道院逐渐成了人们选择养老的一个场所。
当修道院开始更多地承担社会养老的责任时,这种责任完全就是交换关系的产物。有很多老人并不住进修道院,他们宁愿喜欢待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从修道院里购买到一种被称为corrody的养老金(赡养必需品的津贴)。这种corrody起先是给穷人、麻风病人和其他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提供的一种救助金,后来就扩大为养老津贴,典型的corrody明确地规定多少磅面包、多少加仑啤酒、每年的油脂、食盐、燕麦粉的数量,加上由修道院的食堂日常供应的鱼肉。还规定一间带炉子或有柴火取暖的房子。退休者与修道院之间所建立的赡养关系又一次显示了退休者个人财产的多少对于老年生活状况的决定性作用。1317年,一位妇女以140马克的高价买了一份奢侈的corrody。而同一年,一位佣人只花了10马克就签订了一个养老协议。头一个协议保证每天向该妇女提供3磅面包,2加仑啤酒。每年提供6头猪、2头牛、12份乳酪、100条雪鱼干、1000条鲱鱼以及价值24先令的衣服。用10马克买来的corrody,其待遇只包括每周4磅适合佣人吃的面包和6加仑啤酒,外加由修道院的食堂所供应的日常菜肴。②Frances and Joseph Gies,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p.172.13世纪时,在慈善院中购买养老金的做法已十分普遍。13世纪晚期,法国里尔的城市法规对于那些退休后要去修道院或慈善院养老,将大部分 (或全部)财产捐献出去以换取养老的人实行征税。在14世纪晚期的英国,在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中购买养老金的大部分人是工匠和生意人,他们属于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领养老金的人或者居进修道院,或者住在修道院附近,以便于接受修道院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的继续住在自己家里,接受修道院提供的未经加工的定额食物。从14世纪晚期起,养老金往往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在奥地利的城市中,购得的养老保障逐渐从原来的在有关机构中居住的形式转变为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养老的货币化程度逐渐扩大,购买养老金也从宗教团体扩大到其他世俗机构。①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pp.142 -143.这就有利于新型的养老方式的发展。
教会中的一些高级职位也都是由老人把持的,大主教、主教、富有的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在退休时不会发生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在放弃圣职俸禄后,可以得到可观的养老金。教会承认,年迈体弱而必须退休的牧师都有权得到退休金。但是,那些从低级教职上退下来的牧师,只能得到小笔的养老金。所以,在退下来的各种教职人员中,有的人可以过舒适的晚年生活,有的则勉强可以生活。而另一些人所得养老金很少,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上半期英国退休的神职人员中,年金多的人有20镑,少的只有1镑,收入相差20倍,而当时合理的生活费用至少要有5镑的收入。②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p.109.养老金的数目主要是由退休牧师的圣职收入来决定的,这笔俸禄既要为他提供养老金,又要为他的继任者提供薪水。因为退休和现任的神职人员共享有限的薪俸,所以,下级退休人员的生活就显得较为艰难。教会当局意识到这些老年神职人员生活上的困难,但一直也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保障制度。倒是一些慈善家愿意为低级牧师购买退休金。有些慈善院是专门为那些被逼放弃俸禄的退休牧师以及年龄虽不大,但身患疾病的牧师开办的。在13—15世纪,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法国的图尔奈和英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慈善机构。
社区对老年穷人的救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将养老的责任交给了老人的亲属。但实际上,17世纪以后,有关济贫法的账册资料表明,老人是从教区救助中得益最多的人之一,随着他们的劳动能力的下降,他们越来越依赖教区。③Richard M.Smith,“Fertility,Economy,and Household Formation in England over Three Centur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7,No.4(December 1981),p.607;Jill S.Quadagno,Aging in Early Industrial Society,p.122.其中,寡妇数量不少。在赫特福德郡的有些教区,17世纪中叶,有40%以上的寡妇每周领取养老金。很多贫穷的老人即使在本地有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也依赖教区的救济为生。有一些老人是由邻居照顾的,他们在乡村的住户中被列为“寄居者”,这些人也往往是教区支付了养老金而由邻居来照顾的穷人。从16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上半期,这种依赖教区救济的模式一直持续了下来,④Richard M.Smith,“Fertility,Economy,and Household Formation in England over Three Centur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7,No.4(December 1981),p.608.以至在1834年议会举行济贫法的听证会时,有人反对由教区负责老人赡养,理由是:这样做会进一步削弱家庭关系。有趣的是,听证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用教区赡养替代家庭赡养,因为英国的劳动阶级已经完全缺乏天然的孝心。⑤Shulamith Shahar,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p.122.
对于机构和社区在前现代社会的养老事务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似乎难以做出确实的评估。但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欧洲人的养老从很早起就不受家庭关系的限制。
结束语
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尤其在西欧和西北欧地区,以核心家庭为主导,主干家庭或世代同堂的大家庭比率较低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形态,意味着人类学、社会学关于老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受人尊敬,在大家庭里安度晚年的一般图景,在这里并不能完全适用。
的确,研究显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们的养老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老人虽然也倾向于在自己的子女或近亲族中选择为自己养老的人,但子女为年老的父母养老送终似乎不是天经地义和具有强制性的。“继承人”这一概念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但这一概念与退休、养老有关,仍值得我们注意。老人首选子女,同时,也选择无亲族关系的人,甚至选择社会机构为自己养老,并签订退休、养老协议,是以出让自己的财产控制权为前提的。这样,“继承”、“退休”、“养老”就成了同一个过程中前后相关的三个节点。“继承人”承担赡养的责任,乃是因为他 (她)们获得了前者的财产。可见,正是老人先前积累起来的资财,才换取养老的条件。从欧洲的历史传统来看,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主要不是取决于年轻时生养了多少子女,而是取决于积累了多少财产。老人越是富有,他的赡养的条件就越是优厚。而贫穷之人,老来便越发贫困。
这两种极为不同的生活结局,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历史上年轻欧洲人对人生和对自己未来的态度、影响到他们积累财富的愿望、影响他们的生育观和家庭观以及如何影响到社会养老制度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欧洲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我们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我们仍可推测到它们之间的高度关联。从这种关联来思考,欧洲历史上的老人及老人赡养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顺便指出,以财产出让为条件的养老习惯,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欧洲社会中的家庭关系冷漠无情。欧洲家庭史研究表明,近代早期的欧洲父母尽力帮助子女在社会中取得独立,正是现代西方家庭情感高涨的一个重要表征。①Stone,L.,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 -1800,New York,1979;Aries,Philippe,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New York,1962.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如何,不是根据我们传统的家庭关系准则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的,正如我们发现18世纪的英国人用“朋友”一词来指称自己的父母一样,②Tadmor,Naomi,Family and Fri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Household,Kinship,and Patron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