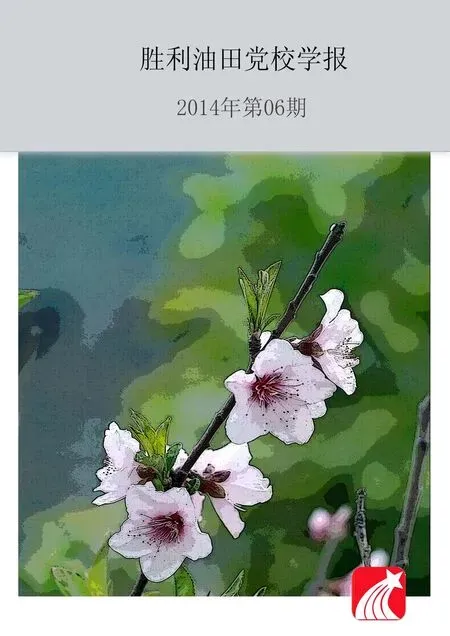人的本质:自由的劳动实践
——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陈仕伟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所有哲学家都没有对“人的本质”做出科学的界定,因为他们都“形而上”地片面追问或者片面地“形而下”地界定“人的本质”,最终将人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走向了抽象的“人的本质”论。要么抽象地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上帝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么就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物质。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明确定义为“自由的劳动实践”。这一界定是一个重要而又科学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
“人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直到现在也仍然没有一个共同而完整的论述。要将人的本质厘清,首先就需要与其两个相近的概念——人的属性和人性——区别开来。所谓人的属性,是指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性质和特性。只要可以在人身上找到的属性都可将其归入人的属性中。人的属性是最表层的东西,不仅包括了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也包括了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人的属性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可以分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所以说,单单从人的属性来看是无法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所谓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所有属性。由以上定义可见人性与人的属性的关系:人性包含于人的属性,但人的属性不能归结为人性。如果将人的本质仅仅是看作与动物相区别的性质,那么人性就等于人的本质。但是“这样来区别人与一般动物,是不科学的”[1]251。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是很多的,如:意识、理性、价值、语言、交往、自由等等。是否可以将这些属性都划归到人的本质范畴中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认为:“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就是根据。”[2]259对根据与本质的思考应该采用反思的方式,需要抽象的思维,而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人的本质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之质,是最一般的且又是相对稳定的内在根据,只有经过理论的抽象才能把握住。如意识、理性、价值、语言、交往、自由等种种性质,都是直接地在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是经验层次的,没有经过理论的抽象,只不过是对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的简单列举。以上经验层次的概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也达不到对人的根本之质的深层次认识。可见,不能简单地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人性。
因此,人的本质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性质,而且还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之质,是与人的诞生过程相联系的。应该认识到,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与人性一样是解决人区别于动物的问题,但是人性的解决方式是在设定一个既定的前提下来进行的,那就是当下的人与当下的动物做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显然是属于经验的、表层的东西,没有解决人的本质中“人之为人”的问题,即人的发生学问题。因此,人的本质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源性性质,人的本质应该是动态的;而人性其实是在静态中做比较的结果,所以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质。要找到人的本质就需要追溯人类的产生史。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上帝的杰作;人类源于动物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促使人脱离动物界或者说超越动物界,并不是什么神的作用,而是人自身作用的结果,即劳动的结果,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374。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3]378;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3]373。所以,人的本质应该是劳动。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的产生,就无所谓“人的本质”的问题。人类社会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性是在人类的长期劳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性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表露。人性与人的本质相比:人的本质是本质,人性是现象。所以说,将人性等同于人的本质是缺乏根据的。但是,要认识人的本质又需要认真分析人性,因为“劳动的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只有借助于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和他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和协作中,劳动才能进行”[4]35,人性才会在劳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认真地分析人性就可以更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
二、人的本质就是自由的劳动实践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是在批判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得出来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也就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5]205所以,“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5]205。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205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外化产生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矛盾运动又最终返回到绝对精神;它是一个封闭的循环运动,运动的动力就是人的劳动,在精神领域中的活动。这就是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5]207黑格尔之所以将人的本质定义为人的“自我意识”,原因就在于“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5]205。劳动不能仅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因此,劳动的对象化或异化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劳动的对象化不是精神外化为物质,而是人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发生符合人的需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对象化或者外化仅仅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劳动是有人的意识参与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将劳动归结为精神的活动。因此,马克思讲的劳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162依此分析,人的劳动本质就决定了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以区别于其他的动植物。或者说,自由的劳动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人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而动物是与自然界同一的,即动物不能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别开来。
马克思在《手稿》中仍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类本质”。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定义为人的本质,只不过是借用而已。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仅仅是指人的自然本质,即将人的自然属性归结为人的本质,认为人与动物同类,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属性就是人的本质。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男女之间的情爱,无差别无等级的爱,动物式的情欲。这是极端错误的:这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反而将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所以,马克思《手稿》中的“类本质”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并非同一概念。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5]161“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162因此,自由的劳动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就直接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不是人的本质;并且人的自然属性只有在人类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真正人的属性,否则就与动物的属性没有本质的区别。换句话说,自由的劳动实践决定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
正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类社会才会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并且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重要展现。因此,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192。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特有的社会就不是困难了。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劳动实践也就将人定义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这也就从根本上将人与动物本质地区别开来了;同时也就将人的本质规定在现实的基础上,不只是“抽象的精神的活动”了。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指出,动物之所以不能建立起像人一样的社会来,原因在于动物的活动不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是对象性的劳动,因为它的活动与对象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能将自己的活动与对象区别开来,通过自身的劳动把对象改造为属人的对象,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生存就是社会性的生存。
劳动的诞生就意味着人类的诞生,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的诞生与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先有劳动而后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最初是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是人类最初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对象。自然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和先在性,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所以,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5]162“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现实。”[5]163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劳动实践”是科学的,也就将人的本质与人性区别开来了。
三、《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的劳动实践,不仅克服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而且也指出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性。这也就指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此时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就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避免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5]188所以,个体的生活是特殊性生活与普遍性生活的统一。个体不能脱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进行普遍性的生存。以往的哲学家为什么不能对人的本质做出科学的界定,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也就是抽象的了:唯心主义者将人的本质定义为抽象的意识之类的东西;而旧唯物主义者则将人的某一方面的自然属性夸大为人的本质。因此,他们都不能面对历史,也不敢面对历史;他们未能指出为什么人类社会会不断向前发展,面对了也只能求助于上帝之类的第一推动者或者意识之类的东西。这对于人类的解放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至多只能起到意识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质的必然后果。
其次,《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指出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类的劳动实践并不是指单单个体的活动,是无数个体相互交往相互协作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实践也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这样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劳动实践也就指出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生存。人的社会性的生存是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共同进行劳动实践,“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5]189。任何个体都是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感到他是社会的存在物,感到“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5]187。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体从事的任何活动都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动物的机能,“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5]188这就意味着,人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再次,《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与“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矛盾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据此,往往有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思认为的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就简单认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自由的劳动实践。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在其现实性上”这个修饰语。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而劳动实践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另外,劳动实践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实践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确证的历史。因此,人的本质总要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一切社会关系是随着自由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人”的界定:“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525这样就可以得出,马克思前后两个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都是科学的。
最后,《手稿》中的人的本质论指出了人类解放的完整目标。这就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89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劳动实践,并且完全占有自己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产品为劳动者之外的他人所有,从而人的劳动实践也就不是自由的了,也就不是人的活动,而是动物的机能。这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后果:人的本质被异化,人就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人,被沦为“自然的奴隶”和受剥削者。因此,人类的解放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人类对自己的本质进行全面的占有和享有,进入“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即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探讨的最终目的和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综上分析,通观《手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科学的,并且克服了以往哲学家的抽象弊端,真正将人定格在社会的存在物,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动力;指出了人类解放的最终归宿。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相对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是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发展的根本以及发展最终的归宿。因此,此时的马克思思想已经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
[1]王锐生,景天魁.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张奎良.时代呼唤的哲学回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