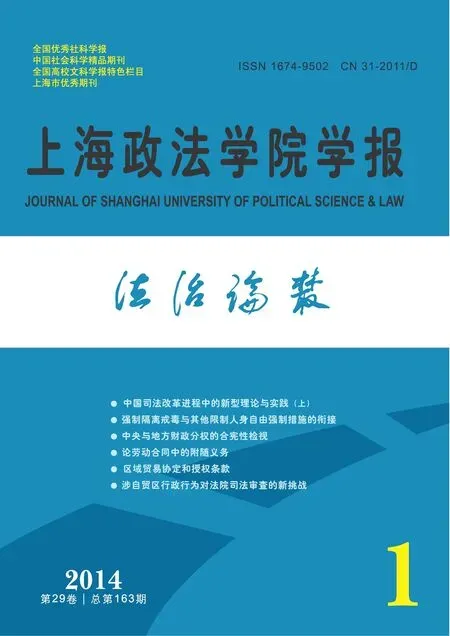转型期司法过程中民意功能的迷思
——兼评《民粹主义司法》
张 建
转型期司法过程中民意功能的迷思
——兼评《民粹主义司法》
张 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三千年未有之大格局”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司法的体制、机制等的转变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为此中国的司法应该向何处去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如对审判模式的讨论、对司法职业化的讨论等,这些讨论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套用方乐的话就是“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公共讨论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的问题,一个理论话语的市场竞争与社会大生产的问题,更是一个实时性的问题,一个极具实践取向和生活意义的问题。”①方乐:《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当下中国司法理论研究立场的转换》,《法律科学》2012年第12期。有关司法的讨论和方乐对讨论意义的揭示,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就是,今天在看待和分析司法运行和变革过程中出现的诸问题时,不能仅仅就司法谈司法,也不能仅仅看到司法本身的问题,而应该要将其嵌至于整个结构和观念的关系性视角中。
关于司法有着太多需要也值得讨论的议题,如司法管理模式问题、司法去行政化问题、法院纠纷解决模式问题、审判与调解等,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都容易使我们陷入就事论事的进路之中,而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讨论则会促使我们开放视野,为此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当下颇为重要的话题之一。通览既有的关于司法与民意的研究,发现都是在一种二元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或赞同司法吸纳民意、或反对民意干涉司法、或认为需要折中考虑,②下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不限于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探讨,但它们共享一种可进行立场调整的二元关系分析路径:李清伟:《网络媒体与司法裁判》,《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英霞:《“媒体审判”的防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戴承欢、蔡永彤:《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调和——刑事司法审判中的民意渗透及限制略论》,《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张善根、郑辉:《网络民意须重视更需甄别》,《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但由于大多数论者仅限于通过立场调整的方式在展开论述,进而也就不会有细腻的分析,更遑论深刻的思考!看到刘练军教授的《民粹主义司法》一文,则使得笔者眼前一亮,吸引笔者的不仅文章标题所有的思想味道,更在于详细的数据和严密的思路,同时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也促使笔者感觉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也产生诸多的疑惑和不解。
一、刘文的话语脉络重述
对文章进行分析和评判,在笔者看来有两种基本的讨论,一种是一边勾勒文章中呈现出来的观念,一边进行分析、讨论和展现自己的观点;③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十分欣赏的文章则是魏敦友教授对范忠信教授的一次演讲进行的点评。魏敦友:《范忠信迷津:从中国社会秩序构成原理角度看——解读范忠信教授”厦门讲演”》,《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另一种进路则是,首先将文章的话语脉络加以重述,而后提出自己的观念并在讨论自身观点的同时注重与文章中的判断进行互动。两种基本的讨论各有各自的优劣,而我个人则较为偏好第二种思路,所以有必要先对刘练军的文章大致结构进行重述。
在文章的开始,作者就以一种极为严峻和严肃的语气向我们指出,“民粹主义正在席卷我国司法领域并形成了史上罕见的民粹主义司法现象”。①刘练军:《民粹主义司法》,《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对何为民粹主义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活跃在政治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民粹主义就不会染指其它领域,就中国的现实来说民粹主义目前正在大规模地侵扰司法领域。文章同时指出,司法领域之所以会受到民粹主义的干扰,原因有二: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司法腐败现象;二是,与我国维稳至上的理念下所形成的压制性社会有关,因为在此机制下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纠纷由于在政治领域不能得到充分地释放和缓解,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怒火”烧向上层构造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司法领域。文章行文至此的大多数观点我都是极为赞同的,如维稳至上司法理念、压制性社会、经济发展与司法腐败等判断。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对民粹主义舆论的传播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三种基本路径:一是,运用传统媒体进行的舆论审判、借助现代网络进行的舆论审判和利用自媒体微博进行的舆论审判,对民意的传播路径的分析笔者也是赞同的。接着,作者分析了舆论审判/民意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认为“舆论审判是民粹司法的基本存在形态,而民粹司法导致专业性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程序被普通大众实时性的非理性与盲目性稀释和遮蔽,法官难以继续在案件裁判过程中扮演主导者和决断者角色,大众化的舆论审判取代了职业化的法官审判,决定案件判决结果的不再是法律和证据,而是双方在舆论民意上的优劣与胜负。”②同注①。这一判断实质上也是对民意的性质进行的界定,但对此一判断笔者则是万万不敢苟同,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不同判断:一是,如何认识民意对司法实践所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整体地并且不应价值先行地看待这一判断;二是,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型结构中,司法机构对民意的响应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刺激——反映”模式,笔者认为不宜做简单的分析。
如果文章行文至此的话,必然也会陷入前述的二元框架下的立场选择的套路上,文章出彩和紧要之处还在于,作者从社会精英与民粹司法的关系性视角对民粹司法形成的内在机理和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形成,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精英引导普通大众对司法案件制造社会舆论审判态势,由此形成民粹司法;二是,社会精英尤其是他们中的法律人群体性地质疑司法案件。旋即,作者发现民粹主义实质上不过是政府进行治理的一种策略,并且也是精英群体试图在实现自身目标过程中的一种话语策略。为此,在作者看来,民粹主义司法必然会导致诸多问题,如:强化了实质公平这种非理性司法观,导致程序公正的应然司法观在我国落地生根变得更加艰难;对司法案件形成舆论审判,刺激民众不信任司法,阻碍司法权威的建立与巩固、对同类案件缺乏同样的关注、逼得同案不同判,在社会上造成看得见的司法不公正现象,结果是继续削弱司法的民众信任基础。为了能建立理性司法观、树立司法权威,作者认为可以通过法院“不听杂音”、社会精英司法观纠偏、传媒权力中立化以及司法与政治相剥离等方案来实现使司法远离民粹声音的目标。
本文主要从两个大的视角来对刘文进行反思性分析:一是,如何认识当下民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功能问题;二是,对作者之所以作出误判的原因进行讨论和分析。
二、民意的监督功能
民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或者态度,无论是通过传统媒体、现代网络,还是自媒体微博,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一种民意,都是社会民众(包括作者所认为的社会精英在内)对司法、政府等公共权力机构进行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在政治、规范和事实上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也“成为现实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和法治的一股重要力量。”①邵晖:《中国当下网络公共舆论与民主、法治进程的矛盾与张力》,《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从规范的角度看,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条规定应该是公民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诸机构进行监督的法律/法理基础,但或许提出这一观点会遭之如此批评,认为民意会过度地侵蚀了司法的自治并会影响司法实践中法律逻辑的展开,但须指出的就是,这实质上是在刺激—反映简单模式上的认知,同时也将司法机构所具有干扰因素阻缺机制予以轻视了,这在后面会分析。
从社会事实的角度看,公民对某一特定案件进行监督也有自身的合理性,这导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带来的大规模的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二是,更是由于司法本身在运行过程中的不透明、不公开所导致。民粹主义(暂且使用这一词)的存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与整个司法环境、法治环境、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的,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看待,因为“意义和确定性都是语境的构建”。②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代序。在此,我们同样可以作者列举的江平教授的例子加以重新分析和说明,江平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就杨佳案件指出,“尽管上海市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我坚持认为,杨佳杀了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我完全同意上海高院的判决结果。”据说此时一位听众指出,“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若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③转自刘练军:《民粹主义司法》,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82~483页。就是这一例子,作者认为该听众代表的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表现,但这一意见是不是有失偏颇我觉得有待商量。对此也可从规范的角度理解,《宪法》第125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同时,杨佳案件也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83条和274条规定的4种情形,④詹建红:《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0页。为此应该是予以公开的。所以说,“司法的归司法”固然是一种值得期待和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是没有前提的,那应该是建立在司法机关本身遵行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基础之上。就杨佳个案来说,上海高院的证据不公开、审判程序不公开,导致公民对其的质疑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影响司法权威的建立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了。所以说,简单地将社会中公民对司法实践形成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归结为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表现或套用民粹主义思想,既是不恰当的,也是较为武断的,更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
需要继续加以指出的是,在对民意与司法关系予以讨论之时,刘练军简单地将司法认为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的假定也是不恰当的,这一假设忽略了司法/官僚体系在日常的、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惯性以及司法/官僚体系对外在结构的适应性改造能力。史景迁对雍正王朝发生的曾静案的研究时发现,虽然雍正认为曾静难逃一死,但他还是决定网开一面,而群臣则是认为应依照法律,绝不容稍加宽待,从而凸显了皇帝与官僚机构在对待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路;⑤[美]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58页。无独有偶,孔飞力在对乾隆年间的妖术大恐慌加以研究时,也发现乾隆与官僚之间就如何处置相关人员的问题上造成了内在紧张的问题。⑥[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3~250页。透过史景迁和孔飞力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洞见到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官僚机构(请允许笔者从当下视角将司法机构归类为官僚机构的一种)在运行的过程中,都是有着自身的运行依据、规律和惯性的,并不会轻易地由于外界干扰而改变方向。具体到司法与民意关系问题上,可以10年前四川泸州中院在审理完有名的“二奶继承案”后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接受采访时所指,“执法机关、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法律,而应该充分领会立法的本意。如果我们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某的诉讼主张,那么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的公平、公正精神。”①王甘霖:《“第三者”为何不能继承遗产》,《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日。所以说,对于社会公民对司法机关、司法过程进行的监督,没有理由恐慌,也没有必要急忙地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当下的民意远远地缺乏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所以其也仅仅只能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而已!
三、民意的减压阀功能
要是从政治、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性和结构性角度出发,来批判民意所具有的功能的话,笔者认为民意对当下整个社会来说还具有减压阀的功能。对于这一判断,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和分析:一是,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来分析政治、司法与民意相互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司法过程中对民意加以吸纳的行为;三是,在上述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应该如何界定民意的性质。
对于政治、司法与民意相互关系问题的识别,有必要从思想和社会分工的视角出发加以认识。基于思想文化传统看,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体,在如何看待事物的问题上,它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来看待诸问题,这与西方一分为二而将世界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思想是不同的。②魏敦友:《新道统论为中国法学奠基》,检察日报2011年1月6日。在整体性思维的导引下,并不会单纯地存在一个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它们相互之间是紧密而内在地勾连在一起的并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经常被法学界批评的法官“送法下乡”、“主动上门服务”的活动,将其置于整个场域中时,会发现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中国思想还主张主体至善的文化观,要求做到“内生”和“外王”的统一,故而要求在讨论问题之时不应该将动机与客观行为割裂开分别加以讨论,而是需要不断地往返于外部和内在,可以这样说“中国思想的整全性不仅表现在外部,同时还表现为内在与外部的整全”。③张建:《从理学到法学的现代历程》,《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当下的中国思想和思维实践仍然是处于这一传统的延长线上。
基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分工理论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当中国在实质性地接触、学习和模仿西方之时,乃是一个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从而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权力分制、权责清晰等具有现代味道的上层结构,更遑论设立专门而独立运行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西方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挑战,迫使中国必须在一个时空挤压的环境中建立起一个现代的上层构造。但由于舶来的思想理念、上层构架与中国现实社会需要并不完全吻合,套用苏力的话就是“制度供给的不适用,产品的不对路”,④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实质的根源更在于上层构架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社会变迁、社会分工、社会职能分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导致上层构架、思想观念与社会相互之间的胶着、折冲和激荡的态势出现与存在。恰恰是由于“近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笔者加)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它与重道德,轻视技术,主张集权和专制,反对分权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⑤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而是中国通过不断地试错而形成当下所讲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或“政法传统”,这一传统的要领在于“要遵循群众路线,遵循党的路线方针。”①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勾连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之所以鹦鹉学舌般地重述法律制度、思想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紧张,不是为了增加文字或为了论述而论述,其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在对当下中国问题进行分析之时,不能简单地从单一性视角出发来分析某一问题,比如从法治视角(西方法治视角?)出发来分析司法问题或其它,而是需要不断地往返于制度、观念和社会之间整体地来分析诸问题。将这一观点投射到具体需要考虑的政治、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上时,就在于启发我们,它们三者应该是相互而内在地勾连在一起并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整体性思维和“政法传统”逻辑出发,再次对中国当下包括司法在内的诸多问题予以重新分析时,可能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见解。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对应当如何看到司法过程吸纳民意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思想—结构”、“知识—社会”的关系性视角中加以把握。基于思想—结构视角,会发现无论是从政治视角对法制进行的定位,还是司法对自身的定位,中国的司法从来没有独立于政治过。胡锦涛在2008年阐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时,对政法的定位又给予了新的强调,认为“政法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发展;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②胡锦涛:《立足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的新局面》,《人民检察》2008年第1期。胡锦涛对政法工作的定位实质与“社会主义法律新传统”或“政法传统”一脉相传的,都在于指出服务大局是政法工作的重要使命。司法在对自身予以定位之时,无论是宏观的认识,还是微观的实践;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自我阐述,还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定位,从来也都是将自身嵌进党中央、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并且也是从党中央、同级党委和政府的话语结构中寻找自身的定位。所以说,在讨论司法问题之时,不能仅仅就司法而言司法,否则仅能看到司法问题的皮相,使研究陷进片面之中而看不到司法的实质和繁复性的面向。
在外部的政治结构限定和司法对自身主观认识的支配下,在结构中运行的司法必须要在自身所嵌入的结构中寻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必须要通过在结构中发挥适应、目标获取、整合和模式维持的功能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③[美]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5页。在司法过程中对民意加以吸纳就是司法在结构中发挥功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司法吸纳民意的过程实质上降低了民意对政治带来的冲击。一如我们所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是建立在政治威权体制和社会公众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参与国家各种正式决策活动的前提之上的,此外,也由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是以锦标赛式的政治机制作为发展动力的,④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故而诸多如环境问题、社会两级分化问题、公民参与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但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如经济发展的放缓、公民法治意识、公民参与意识等的普遍提高,包含上述诸问题在内的“问题束”都不断地呈现和释放出来,这些从理论上说都是需要政治加以响应和吸纳的。由于凝固的、稳定的和静态的社会秩序观预设、⑤张建:《社会冲突与法律控制机制》,《党政论坛》,2009年第9期(上)。维稳型体制的路径依赖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前景的担忧,⑥[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7页。都是令政治与民意关系陷入僵局,使政治响应和吸纳民意的问题成为两难问题,最终导致民意涌向上层构造中较为薄弱的司法环节。
条分缕析地分析政治—司法—民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便于展现内在的逻辑,这句话也意味着,这一逻辑可能与现实逻辑不一致,实际情形却是如此。由于上层构造是以一种整体性的形象呈现在社会、公民面前的,所以民意对司法的“反叛”实质就是对政治的“反叛”、司法在实践过程中对民意的吸纳实质就代表了政治对民意的吸纳。恰如上文所指,司法对民意的吸纳也是有选择性的,通过有选择性的吸纳,既可以缓解民意给政治所带来的压力和冲击、又可以迂回地将民意导向政治层面,①张友连:《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161页。还可以增强司法在整个上层构造中的重要性位置。
所以,从整体和总体的层面看,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和司法对民意的响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对政治来说实质发挥了减压阀的功能,通过司法缓慢地、有序的吸纳,从而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不满和贸然进行政治改革而带来的风险,但对于这些问题,法学界并没有加以重视和认真对待,更为糟糕的是,众多论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具体到刘练军的文章来说,作者之所以对民意产生如此不良的印象甚或是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原因之一或许还在于陷进思维方式和西方范式中心观的迷津之中。
四、民意促进法治进步的功能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民意的监督功能和减压阀功能,实际上是在“司法—民意”以及“政治—司法—民意”的关系性视角中予以讨论的,置于这一推理策略,也有必要从“社会—民意”的关系视角出发来讨论民意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对此,本文认为在此关系结构中民意总体发挥的是促进法治进步的功能,为此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民意具有促进个案公平、公正解决的功能;二是,民意具有促进整个社会法治进步的功能。
刘练军在文章中对司法实践中认为受到民意过多干涉的个案——如黄静案、邓玉娇案、张金柱案、吴英案——予以分析后,认为这些案件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最终结果,原因就在于民意的过分干涉,比如张金柱本来不该死但实际是舆论将他“处死了”,比如吴英案中出现的景象“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广大网民俨然各个是法官、人人是专家,对吴英案的两审判决结果极尽谴责之能事,形成全民微博批判吴英案判决之态势。”②刘练军:《民粹主义司法》,《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这里暂且不对这种观点做过多的分析,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比如吴英案要不是民意的监督,吴英可能早就领到最高法的死刑复核通知书了,这根本上应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同样要指出的是,刘练军实质上忽略了上文所分析到的,司法对民意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仅仅进行选择性吸纳,而司法的选择性吸纳所针对的案件恰恰是争议较大的案件,尤其是在司法审判不公开、司法腐败广泛存在的制约下,更是司法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加剧,所以说,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实质上是有助于促进个案公平正义地加以解决的。
刘练军在文章中指出,由于舆论监督的乏力,导致舆论没有监督到的地方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或许是由于逻辑混乱而导致的严重误判。以其文章中所举的黄静案为例,该案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网络上呈现的民意实质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表征,根源应该还在于黄静案中内含的被害人家庭与被告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平等性。以此维度进一步拓展开来看的话,无论是邓玉娇案,还是吴英案背后所隐藏的都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博弈,更为紧要的则是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由于不同场域是相互敞开的,导致这种不平等能转化为在司法领域的行动能力并进而影响案件的审理,所以与其说民意是对个案本身的关注,还不如说民意是对这种不等结构及系统相互敞开的博弈过程的关注。要想使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够公平而公正地加以解决,有两种可能:一是,司法按照公开原则将所涉及到的程序、证据及案件情况等都加以公开,主动地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博弈中的弱势者借助于外在力量来加强博弈能力,以保证博弈的公平。从当下司法实践及上文的分析中可看到,第一种方案被有意无意地堵住了,如上文提到的上海高院对杨佳案的处理情况表明的就是这种态度,这种情形的存在,迫使弱势者必然要借助于外界力量,而这种借力行为在以刘练军为代表的一大批学人看来,就是干涉司法的行为、就是民粹主义司法,恰恰被他们忘记的是理论逻辑的分析不应该取代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
应当说,刘练军没有能够看到民意形成的内在机理,同时在逻辑不够严谨的情况下导致对“同案不同判”的错误理解和判断,误认为是民意导致案件的不同解决,而忽略其中两种不同的解释向度。一种解释思路是,司法机构本身严格遵循实体法和程序法,由于民意的干涉导致被关注的案件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出现畸轻畸重的结果,从而违背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另一解释思路是,由于司法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会游离于法律之外,恰恰是由于民意的广泛关注,才使一个个的个案得到了合乎法律和合乎正义的结果,比如云南李昌奎案件。采用哪种解释进路并无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符不符合现实、符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刘练军是以第一种思路作为研究假设的,但被其忽略的是,这一假设应该具有相应的前提要件,如司法应该具有独立性而不应该被嵌入进各种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之中,显然现实的司法实践不能满足这一要件,故而可以说刘练军的判断存在严重错误。个别的判断失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在于这一判断失误所表现出的笼统地、单一地依据某种法学理论或法条而不是现实地、有价值地对问题进行分析的思维方式才是紧要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可能诱使我们走向片面的结论中,所以或许如侯猛所言,“审慎细致地分析当代司法的实际要比大胆的构想更有意义。”①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刘文又指出,社会精英在利用民粹主义对司法予以干涉之时,是夹杂着私心的,如:对现行法律体制的愤懑以及对改造的期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由此激发对权贵阶层的愤恨、对官员的不信任及逢管必反的非理性情绪、对社会民生问题的高度敏感借机表达民生诉求以及对社会道德伦理滑坡的焦虑,期望重建社会道德诚信。②刘练军:《民粹主义司法》,《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这一判断有着“诛心之论”的味道,之所以这样讲,因为任何评判都是夹带着自身的观点和期望的,凸现出的是以感性的认识取代理性的分析后所带来的后果。这一观点实质是在“民意—司法—政治”的结构框架下展开的,刘练军的判断是以司法独立以及政治与司法相互分开作为前置假设的,但这一假设的正当性以及是不是符合现实逻辑却没有经过反思和质问。
通过对刘练军文章中的几个观点进行反思性分析,意在指出通过民意监督司法来使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得到公平而正义的解决,总体上来说能够有助于整个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和法治建设的进步。恰如上文的分析所表明,通过司法吸纳民意并将民意折射到政治层面,能够有效地推进政治、法治和法律机制的变革,进而可以避免激烈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的风险。同时,通过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博弈、激荡和折冲,所形成的判决一方面使其限制于法治的框架内,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社会加以接受,进而可以缓解由于移植西方法律而造成的法律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紧张,也可以缓解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与社会公民的参与期待的紧张,同时也有助于为后来的类似案件树起标杆。
五、反思刘文误判的原因
笔者在上文对民意在当下中国所具有的功能的认识与刘练军教授之间形成了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并不是在同意、反对和协调的二元框架下经由简单的立场调整而形成的。民意对于司法乃至整个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笔者看到的是民意所具有的监督功能、减压阀功能和促进法治进步功能,而刘教授看到的则是“强化了实证公正这种非理性司法观”、“对司法案件形成舆论审判,刺激民众不信任任何司法,阻碍司法权威的建立与巩固”等,③同注②。虽然这里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辨析,但对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差异的讨论可能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刘教授之所以会给民意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斩钉截铁的对民意加以否定,在笔者有限的判断能力看来,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将西方司法独立的法治观预设为前置条件而没有对其正当性加以反思;二是,也与刘教授所采用的具体分析理路和外在视角有关。
坦率地说,之所以被刘教授的文章吸引,就在于“民粹主义司法”这一题目,笔者想这样一个有思想的题目应该是有些内容和深刻见解的。需要一提的是,文章开始也谈到了民粹主义的知识,但遗憾的就是民粹主义的思想并没有能够贯彻于整篇文章的分析过程中,当然这是题外的话。当笔者读到文章的第三部分“社会精英与司法民粹”之时,就暗暗感觉到大事不妙,不妙的原因就在于感觉到刘教授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对什么是民粹主义通透的加以说明,更多的可能就是司法—民意关系与民粹主义是两张不同的皮,有着这一隐约的判断后,继续往下读时,果不其言的得到了印证,文章写作的目的还在于将自己的预设结论化,如司法“不听杂音”、司法与政府相剥离等。就刘教授的思路来看,如果去掉民粹主义的大旗,将结论作为前提,然后采用演绎而非归纳的方法,同样是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只不过那样就会稍微显得没有思想、没有高深学问了,也会将自身的逻辑彻底地暴露了。
刘教授的结论实质上在当今的法学界都是常见的判断,采用的逻辑也是惯常逻辑,那就是以西方司法独立法治观作为分析和评判中国司法实践的标杆。在西方司法独立法治观的扫描之下,中国的司法实践就成为一个病态的、问题丛生的样本,是一个需要西方给予救治的病人,这种情形恰如斯科特对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场计划批判到的那样,“专家只要有地图和很少几个关于规模和机械化的假设就可以制作出计划,无需参考地方知识和条件。”①[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但被他们忽略的是,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和成长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展开的,西方的思想、制度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强行地安置于异域中必然会导致不适应,这方面已有太多的例子和教训了,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南美、非洲开展的法律现代化运动、南美诸多模仿美国政治体制的行动,无不是以失败告终,西方的法律思想强行安置于中国社会之上同样会导致一样的结果。刘教授虽然以民粹主义思想作为开路先锋,但不能掩饰的就是实质上是以西方司法独立观作为知识背景的事实,所以有必要反省这种至果为因的逻辑思维方式,一如邓正来所批判的那样“如果我们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进行检讨和反思,我们便能够发现一种基本且持续的取向:中国论者依凭各自的认识向西方寻找经验和知识的支持,用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价中国的现状、建构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②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而刘练军对民意和民粹主义司法的反思以及建议,不过是体现这一思路的一个版本而已。
之所以与刘练军在看待同一问题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我们所采用的思维框架也是有关系的,刘教授可能采用的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单一线性框架,而笔者采用的是整体性的分析理路;刘教授可能采用的是外在视角的分析方法,而笔者采用的是内在视角的分析进路。就第一个区别来说,在上文的第三部分“民意的减压阀功能”中已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这里主要对第二个区别简要地加以分析。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本身是不存在高下之分的,问题的紧要处在于方法使用是否恰当以及对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是否能保持必要的警醒。从内在视角可以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发现事物运行的逻辑,从外在视角出发可以使我们发现事物的不足,基于内在视角而不能走出来,则会导致封闭心态的产生,基于外在视角不能发现反思前提的正当性,则会导致观察对象无一是处,所以恰如曹锦清所言,“中国应该如何的判断要以中国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而要研究中国是什么,就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③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刘教授在采用外在视角之时,虽然研究了民意传播的途径以及民意传播的背后因素,但根本上还是在西方司法独立法治观的价值支配下进行的,所以其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能够真正地把握研究的对象,更不要说分析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了,这是让人扼腕的。为此,基于整体性和内在视角,会发现当下的民意形成以及所发挥的功能实质是与民意所处的历史情境相容而共生的,反过来说,当约束性条件发生变化之时,民意的形成机理及其功能也会发生变迁的。
六、结 语
经由借助于《民粹主义司法》一文中的诸多观点而加以展开的讨论,目的并不在于向刘教授发难,讨论的目的在于希冀借助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加以发挥,从而展现民意对于当下的司法实践、法治建设乃至是整个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也在于指出,如果总是以外在视角作为研究中国的进路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不会触摸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要是总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①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更不可能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