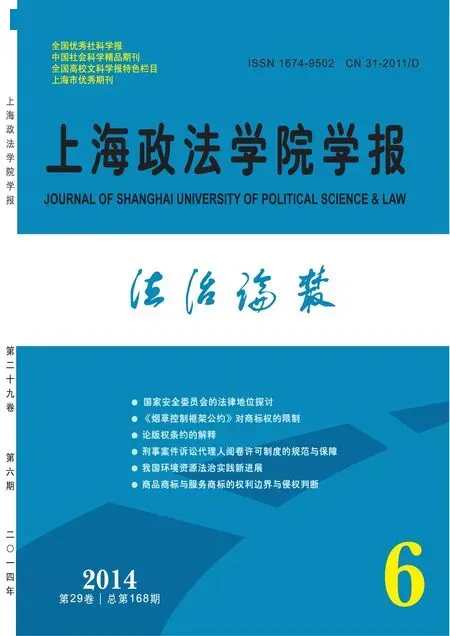论版权条约的解释
——以版权限制和例外条款之解释为例
马松涛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 300300)
论版权条约的解释
——以版权限制和例外条款之解释为例
马松涛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 300300)
版权条约的解释,在具有传统条约解释共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特殊问题。为了保证一体化与多样性有效统一的版权利益平衡保护体系的构建,版权条约解释的渊源,不应只局限于自足性条约本身的资料,还应包括其他更为广泛的解释渊源。同时,版权条约的解释,也需要注意相关版权公约中的联系条款,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解释,并注重对成员解释权的适当尊重。
版权;条约解释;限制和例外;三步检验法
一、版权条约解释的渊源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中解释条约的“上下文”、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因素,以及“条约用语的特殊意义”第32条中条约解释的“补充资料”,成为确立条约解释的重要渊源。而由于版权公约交叉性的特点,在版权条约解释中,确定这些解释的渊源往往比较复杂。
(一)自足性公约本身的资料作为其自身解释的渊源
首先,每个自足性版权公约本身的“上下文”以及“补充资料”等,无疑构成解释本条约自身的重要渊源,典型的如WCT/WPPT中相关的议定声明,是解释这两个条约的重要渊源。
而这一点对TRIPS协定中版权条款的解释的影响,则值得引起注意。TRIPS协定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全体成员期望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与阻力……保证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与程序不至于变成合法贸易的障碍。”这意味着,与传统的只单独调整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不同,TRIPS协定下的知识产权被融入了贸易的因素,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工具。而TRIPS协定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与减少贸易壁垒的GATT协定和促进市场准入的GATS协定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TRIPS协定中版权条款的解释,就可能会受到WTO追求经济利益,实现贸易自由化理念的影响。①Neil W. Netanel, The Next Round: The Impact of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on TRIPS Dispute Settlemen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pp.456-462.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GATT协定和GATS协定严格解释限制和例外的方法,就可能会类比适用于TRIPS协定版权限制和例外条款的解释。如GATT1994第20条准许各成员处于特定目的或原因,采取偏离GATT1994的措施,这包括环境保护与卫生检疫、社会道德、文化等各种措施。①参见GATT1994第20条。而在这些措施是否被准许的解释上,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以往报告中,有时采取的是一种限制性解释的方法,即贸易优先于这些相关的例外措施。②See e.g.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pp.55-75.
而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方法,成员方基于公共政策确立的版权限制和例外制度,就可能会被否定,这种机械性类比适用的方法的合理性是值得疑问的。首先,与减少贸易壁垒的GATT协定和促进市场准入的GATS协定不同,TRIPS协定的版权保护只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方面,如果将保护的强度推向极端,这可能也会形成贸易的壁垒,扭曲和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从而也违反了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其次,对于版权法而言,其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公共政策,其自来就是在作者激励和公共接近之间的一种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的理念,也恰恰明确规定在TRIPS协定的序言、目的和原则中,构成解释版权条款的重要渊源。
所以,对于TRIPS协定中版权条款的解释,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是,GATT协定和GATS协定中追求贸易自由的方法(如严格解释例外条款的做法),不应机械性地适用于TRIPS协定中版权条款的解释。而对此,一方面可以在TRIPS协定本身之外寻找更为广泛的解释渊源,另一方面,则可以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解释。
(二)“提及”和“复述”条款在相关公约解释中的作用
《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的某些条款是通过“提及”的方式被纳入到之后的TRIPS协定和互联网公约中的。③TRIPS协定和WCT提及了《伯尔尼公约》的全部实质性条款,参见TRIPS协定第9.1条,WCT第1.4条;而TRIPS协定和WPPT则只提及《罗马公约》的部分实质性条款,参见TRIPS协定第1.3条,第14.6条,WPPT第3.2条以及第3. 3条。这里的问题是,这些条款在新的公约中应如何解释并加以适用?如果严格按照版权条约自足性的保护体制标准,同时考虑到不同条约成员之间的不完全重合性,那么将《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解释的渊源,作为解释TRIPS协定或WCT/WPPT的渊源是值得疑问的。但从这些条约的规定来看, 缔结TRIPS协定和互联网公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纳入《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的约文,而否认前《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解释渊源的作用。Frederick M. Abbott教授对此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直接在TRIPS协定(互联网公约)中重述这些条约的约文,而没有必要要求WTO(互联网公约)成员遵守《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④See Frederick M. Abbott,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Editied By Ernst-Ulrich Pertersmann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421.因此,一种理解是,对于这些通过“提及”方式纳入到TRIPS协定或WCT/WPPT条款的解释,应该将《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相关条款解释的渊源都考虑进去了。⑤See Mih á 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a2.24-2.25.
而WTO争端解决实践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在美国版权法案中,专家组在肯定“小例外”原则是《伯尔尼公约》第11条和11条之二的“上下文”一部分后,认为在TRIPS协定没有作出任何明示排除性规定的情况下,被纳入TRIPS协定的《伯尔尼公约》第11条和第11条之二的内容包括这些条款的全部资料,也应当包括对专有权规定的“小例外”的可能性。⑥See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Section 110(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 WT/DS160/R,para6.62-6.63.该案中,专家组似乎走得更远,为了解释TRIPS协定第13条,专家组还援引了在他们看来十分具有价值的《伯尔尼公约》第9.2条的历史资料。而TRIPS协定第13条与通过“提及”纳入的方式不同,其是属于通过“复述”的方式被纳入到TRIPS协定中的。Mih á ly Ficsor博士认为,该案表明,上述原则不仅可以适用于通过提及的方式被纳入的《伯尔尼公约》条款,也适用于只完全原文地“复述”的《伯尔尼公约》条款。①See Mih á 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a2.24.所以,在他看来,某些“引入的”(imported)文本与通过提及的方式而包含的文本的性质非常相似,某些情况下,在穷尽了相关协定的信息,仍无法确定某些术语的含义时,从某些原先的公约中寻找解释的渊源似乎是合理的。
TRIPS协定和互联网公约是建立在以往《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完全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版权保护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按照Mih á ly Ficsor博士的观点,解释这些新协定时,考虑以往版权公约的解释渊源就似乎说得过去。但是,这个观点却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本身的渊源,并不仅仅限于美国版权法案中专家组所引用的《伯尔尼公约》的历史资料,还有可能包括《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或《罗马公约》1961年文本)之后新发展的嗣后协定、嗣后实践等,比较典型的如WCT/WPPT,因为这两个公约与《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相互联系,完全有可能构成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本身的嗣后协定、嗣后实践或补充资料。②同样的结论可以适用于TRIPS协定,因为《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也是TRIPS协定实体条款产生的基础。这里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仅以互联网公约为例来做说明。而按照上述结论,那么当WCT/WPPT构成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条款的渊源,而这些条款又被以“提及”或“复述”方式纳入到TRIPS协定时,WCT/WPPT中的相关条款也将因此可能成为解释TRIPS协定的渊源,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TRIPS协定时予以考虑。这样TRIPS协定所纳入的《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的条款,可能就成为了TRIPS协定和WCT/WPPT之间联系的桥梁。
但这一推论是否合理,本文接下来从两个步骤入手,首先分析WCT/WPPT是否可以构成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本身的嗣后协定、嗣后实践或补充资料?其次,如果可以构成,是否可就此认定WCT/WPPT可以成为TRIPS协定的解释渊源?
(三)WCT/WPPT作为《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解释的渊源
1.嗣后实践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b)项规定了条约解释,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因素的“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方(the parties)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这里使用的措辞是“当事方”(the parties),这与第31.2条(a)项中的“全体当事方”(all the parties)的表述不同。国际法委员会曾对此做过评论,③1964年约文草案是“全体当事方”,但是后来的正式约文省去了“全体”一词,国际法委员会解释说这并不是要改变规则,只是考虑到“各当事方理解”这种提法必然指“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事方”。它省去“全体”,只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误解,即每个当事方都必须参加这个实践,才满足其同意这种实践的条件。See Sir Arthur Watt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49-1998,Volume Two:The Treaties Part Ⅱ,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89.这个评论表明,第31.3条(b)项中的“当事方”虽还是指全体当事方,但排除了全体当事方都逐一参加这一实践的严格要求。即可以说,成员同意这一实践,并不仅仅限于明示的方式,暗示或默示接受规则的方式也可以。④See Joost Pauwelyn ,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261, Footnote 70.同时,嗣后实践可能既包括国际层面上的,也包括表明了成员对于条约义务共同理解的国内的立法和其他事实、作为或不作为。①See Ian Sinclai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84, pp. 136-138.
对《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成员而言,会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一种是《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和WCT/WPPT的成员重合,另一种则是成员仅参加了《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对于第一种情形,《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这些成员缔结“特别协定”——WCT/ WPPT的事实,应理解为是这些成员采取明示的方式同意这一实践,即这一实践体现了这些成员关于《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规则含义的共同理解。而对于第二种情形而言,这些成员虽没有加入WCT/WPPT,但是他们可能对于上述其他成员缔结WCT/WPPT的事实,或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或者在其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同样实施着与WCT/WPPT相同的规定。而根据上文所述,这种暗示或默示同意的方式,也可以证明这一实践体现了成员对公约义务的共同理解。由此,在这两种情形(主要是第二种)下,就可能证明这一实践——不管成员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上的同意,能够体现《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各成员对于这些公约义务的共同理解,此时,WCT/ WPPT也就相应地可以构成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嗣后实践。
但另一方面,这里各当事方对条约义务的共同理解,应被认为是一个“协调、共同一致的”连续行为,或者是足以确立一个暗示当事方就条约解释达成协定的可辨别模式的声明,一个孤立的行为通常不足以确立一个嗣后实践。②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p.13.而由于《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成员方众多,所以,即使构成嗣后实践并不需要全体成员方采取明示的方式,在如此众多的成员中,认定这些成员都“协调、共同一致的”同意后来的WCT/WPPT的实践,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而一旦当事方之间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也就很难认定这一实践是各当事方对《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义务的共同理解。而在WTO的争端解决实践中,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构成嗣后实践的解释也显得比较谨慎。在加拿大药品专利案中,加拿大主张某些成员政府的嗣后实践支持了将TRIPS协定第30条理解为准许管制审查例外的观点,但是专家组拒绝了这个理由。专家组认为,单个国家的嗣后行为并不能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b)项含义范围内的嗣后实践。专家组的这个理由与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类税案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美国版权法案中,为了论证“小例外”在《伯尔尼公约》中的法律地位,专家组主动提及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解释条约一并考虑的因素,并同时列举了来自不同成员国内法中基于“小例外”原则规定的例外的一些实例,但是专家组只是认为这些实践佐证了“小例外”原则所得出的结论,其并不在于表达这些实践是否可能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嗣后实践的观点。
因此,认定WCT/WPPT中的某些条款构成《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解释的嗣后实践,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但是,即使《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条(b)项不能适用,某些《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成员方关于WCT/WPPT的嗣后实践也有一些证明价值。③[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0页。而且,当对《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条款的解释出现意义仍不明确或难解、所得结果荒谬或不合理时,借助于WCT/WPPT中的条款进行解释,可能会有助于澄清这些条款的含义。所以,此时WCT/WPPT仍可能成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2条项下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补充资料。④《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仅给出了主要的补充性解释方法的例子,人们也可以查找一些在存有疑问的前后通过的有关相同事项上使用相同或类似用语的其他条约。[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194页。
2. 嗣后协定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a)和(c)项,分别规定了条约解释,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当事方(the parties)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以及“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其中对于(c)项中的“当事方”(the parties)这一措辞,学术上有各种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a)项和(c)项所使用的措辞是相同的,有关(c)项不同的论述应同样适用于(a)项。①如GATT专家组关于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案的裁决是有关第31.3条(a)项的,但David Palmeter 和 Petros C. Mavroidis认为,这个裁决同样也应符合第31.3条(c)项。See David Palmeter, Petros C. 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 Sources of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8,p.411. 本文认为这个结论反之亦然。同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a)、(b)、(c)项中所使用的措辞均是“当事方”(the parties),如果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地解释”,那么上述(b)项的分析结论应该同样适用于(a)项和(c)项。这样,上述有关WCT/WPPT成为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嗣后实践的分析结论,也应该同样可以类比适用于此。
也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当事方”应理解为特定争端的当事方。②See David Palmeter, Petros C. 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 Sources of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8,p.411. 在美国海虾案中,专家组的报告遵循了这一做法,其认为上诉机构参照的国际法法律文件,马来西亚和美国双方都同意或接受了。See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Recourse to Article 21.5 by Malaysia,WT/DS58/RW,para5.57.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在有关《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争端中,如果争端双方又是WCT/WPPT的成员,那么WCT/WPPT就成为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嗣后协定。而如果争端当事方,只要有一方没有加入WCT/WPPT,WCT/WPPT就难以被认定为是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嗣后协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WCT/WPPT仍可能成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项下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补充资料。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WCT/WPPT完全可能成为《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解释中,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嗣后协定、嗣后实践或补充资料。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条(c)项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这一结论。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达成一种与当事方意图相一致的解释可能不但要求考虑条约缔结时的国际法,而且也要考虑当代国际法。③[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这意味着,对于《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解释,不能完全局限在这些条约缔结时的情况,很多规则在新的数字环境下不得不作出演变性地解释。如《伯尔尼公约》第9.2条关于复制权限制和例外的规定,影印技术时代所界定的“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正当利益”的含义,已经很难适应新的数字时代的挑战。而WCT作为数字时代产物的国际公约,其关于复制权及其限制和例外的规定,进一步阐明和解释了《伯尔尼公约》第9.2条。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理由在解释《伯尔尼公约》第9. 2条时,拒绝考虑作为“特别协定”的WCT。
但是适用上述结论,并再用《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作为桥梁,建立TRIPS协定和WCT/ WPPT之间的联系,而将WCT/WPPT当然地确立为TRIPS协定解释的渊源的推论,则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TRIPS协定所纳入的仅限于1971年《伯尔尼公约》和1961年《罗马公约》的文本。对此,有学者指出,对TRIPS协定中术语的解释,应理解为是根据这些术语在WTO协定缔结时的国际法上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将《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上述文本之后发展的WCT/WPPT,作为TRIPS协定解释的渊源,就可能是WTO成员在缔结TRIPS协定时没有预料到的,从而违反了条约解释的“当时法原则”。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时法原则”还存在着例外,有时需要对条约作出演进性的解释。对于TRIPS协定的条款而言,很多还是抽象和模糊的。而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TRIPS协定中条款的解释,可能还会面临与GATT协定和GATS协定不同的情况。因为对于GATT协定和GATS协定的义务来说,这可以通过成员的谈判或达成新的承诺来完成,但TRIPS协定仅仅是给成员创设一种最低的保护义务,成员很难再就这种新出现的情况达成新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对TRIPS协定中纳入的版权公约条款,采用一种演进性解释的方法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这里用“当时法原则”否定TRIPS协定和WCT/WPPT之间关系的理由不是太妥当,这个障碍因素应被排除。
第二,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要求WTO专家组将其他国际条约的解释渊源作为TRIPS协定解释根据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毕竟WTO成员遵守的只是实体义务的TRIPS协定规则,而不是《伯尔尼公约》或其他国际公约的谈判文件,以及这些公约之后发展的国际法规则。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就得要求WTO成员在关注TRIPS规则本身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国际组织谈判的文件和公约的发展资料。但TRIPS协定中只是提及了这些被纳入的公约,而没有提及相关的谈判文件等。
在美国版权法案中,专家组针对双方争议的公共政策目的是否与本案有关的问题,虽然在报告中提到了《伯尔尼公约》第9.2条中关于解释“特殊目的”的历史资料,但专家组还是认为对此应谨慎解释,并认为“某些特殊情况”不等于“特殊目的”,因此并没有按照《伯尔尼公约》中的历史资料进行解释。《伯尔尼公约》的这些历史资料应是WTO成员在缔结TRIPS协定时知晓的,而对于WTO成员知晓的这些历史资料,专家组亦没有完全考虑,就没有理由要求专家组去考虑《伯尔尼公约》之后新发展的国际版权法规则。
由此,使用《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作为桥梁,当然地建立TRIPS和WCT/WPPT之间解释关系的推论是很难成立的。但是,抛开《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的桥梁,考虑到WCT/ WPPT和TRIPS协定成员的重合等因素,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毕竟TRIPS协定和互联网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并非都源于《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如关于出租权以及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权较长保护期限的规定),这些条款虽难以对解释《伯尔尼公约》(或《罗马公约》)本身起到作用,但其仍然可能在TRIPS协定和WCT/WPPT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构成两者之间的“互为解释”现象。接下来,笔者将以WTO为视角,分析WCT/WPPT在TRIPS协定解释中的作用。
(四)WCT/WPPT在TRI PS协定解释中的作用
根据上述有关嗣后实践、嗣后协定等论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WCT/WPPT完全可能成为解释TRIPS协定相关条款的嗣后实践、嗣后协定或补充资料。但这个结论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
第一,根据WCT第1.1条的规定,WCT不得与除《伯尔尼公约》以外的条约有任何关联。这似乎从表面上否定了TRIPS协定和WCT之间的联系。对此,有学者认为,上述结论不适用于作为独立条约的协定声明,因此,即使WCT协定本身不能作为TRIPS协定解释的嗣后协定,WCT的议定声明也可以成为TRIPS协定解释的嗣后协定。但是这仍然面临第二个方面上的关键问题。
第二,将WCT/WPPT的规则作为TRIPS协定解释的渊源,会出现两种可能情况:一种是WCT/ WPPT中的规则仅是对TRIPS协定中某个特定术语的含义阐释清楚,另一种则是在TRIPS协定中适用WCT/WPPT中的规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前者是用一项规则对另一规则进行解释,属于条约解释的范畴,其根据可以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中找到;而后者则可能是两项规则一起被适用或是一项规则选择退出,属于条约适用的范畴,而在主张WTO争端解决机构应严格适用法律的学者们看来,这是不允许的。①代表人物如Joel P. Trachtman 教授,他认为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法律是非常清楚的,即只能是WTO涵盖协定,而适用其他非WTO法是荒谬的。See Joel P. Trachtman,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999, p.342. 反对观点的代表人物如 Joost Pauwelyn,有关详细论述See Joost Pauwelyn,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pp.535-578.也有观点认为前者和后者中两项规则同时适用的情况并不存在严格区分,②See Lorand Bartels, Applicable Law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01, p. 511.从而后者的情况有时也可以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中找到根据。实际上,这些不同观点的论述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并不是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能否考虑其他国际法规则,而是这些规则能否可以用来确定TRIPS协定中措辞的含义和成员在TRIPS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③这一点Joel Trachtman教授也承认。See Joel P. Trachtman, 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1999,p.343.
以复制权为例,虽然TRIPS协定所纳入的《伯尔尼公约》第9条中的复制指“任何方法或形式”,但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数字存储作品的形式;后续的WCT第1.4条的议定声明则规定:“《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下的复制。”在这种情况下,当TRIPS协定中“复制”这一术语模糊不清时,假设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将WCT第1.4条的议定声明作为TRIPS协定的解释渊源。这样,如果认为这时WCT规则仅仅是对TRIPS协定中“复制”的含义阐释清楚,不属于条约适用的范畴(或者按上述这时条约解释和适用不需要严格区分的观点),那么,自然可以从DSU第3.2条提及到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中找到根据。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这个解释可能改变了TRIPS协定缔结时WTO成员不急于涉及数字环境的本意,从而可能增加了WTO成员在TRIPS协定下承担的义务,因此与DSU第3.2条和19. 2条不符。而如果认为这时的WCT规则已经超出了条约解释的范畴,成为WCT和TRIPS规则的同时适用,那么,在主张WTO争端解决机构应严格适用法律的学者们看来,这应是不允许的。
再以版权的限制和例外为例,TRIPS协定第13条规定的三步检验法,其并没有像WCT第10条及其议定声明一样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在美国版权法中,美国和欧共体就该条的适用范围各执一词,其中,美国提到了WCT第10条及其议定声明,并认为WCT第10条的议定声明,表明了欧共体及其成员和美国在内的共同承认。欧共体则认为,WCT在当时仅为少数缔约方所批准,尚未达到该条约生效的要求。专家组并没有对双方的观点做出详细评述,只是认为,“小例外”原则后来的发展,既不构成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也不构成嗣后实践,这一后来的发展与本案并无多大关联。现在WCT已经生效,欧共体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但是,根据前文所述,即使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构成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标准,条约的生效也不应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此,我们假设专家组将WCT第10条的议定声明作为TRIPS协定第13条的解释渊源。如果按照上述条约解释和适用之间区分的观点,这应属于WCT第10条议定声明与TRIPS协定13条一起被适用,而不是DSU3.2条提及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准许的司法解释,那么这种做法,无疑会受到主张WTO争端解决机构应严格适用法律学者们的质疑。而如果按照上述条约解释和适用之间有时不作区分的观点,这还是属于被《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准许的解释。但是,我们注意到WCT第10条议定声明的规定,包括了“既不扩大”和“也不缩小”《伯尔尼公约》所允许的限制和例外可适用性范围的两层含义,前者与TRIPS协定第2.2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后者则是TRIPS协定所没有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为这仅仅是将WCT第10条的议定声明作为对TRIPS协定第13条所做的准许的解释,也可能使得TRIPS协定第13条同样确立了“不得缩小”《伯尔尼公约》限制和例外适用范围的含义,而这将可能减少成员在TRIPS协定项下承担的国际义务,从而与DSU第3.2条和19.2条的规定不符。
因此,将WCT/WPPT作为TRIPS协定解释的渊源,并不是非常容易。在美国版权法案中,专家组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专家组在认为“小例外”后来发展的WCT议定声明,既不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的后订立条约,也不是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之后,却又指出除非这些条约中包含不同义务,否则在对TRIPS协定解释时,为避免在整体框架内发生冲突,也可以在WCT的上下文中寻求相关指导(guidance)。
可以说“指导”(guidance)这一措辞,使得专家组在解释TRIPS协定时,不至受制于WCT及其议定声明的约束,为其解释TRIPS协定留下了自由裁量的余地。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宽泛性的质疑。但另一方面,“指导”一词,也同样不能避免其他国际法规则对TRIPS协定可能的影响,而在严格固守WTO自足性法律体制的学者来看,这可能还是不被允许。
但笔者认为,将WCT/WPPT作为解释TRIPS协定的渊源,无论最后是阐释TRIPS协定中的术语还是可能形成两种规则一起被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都应当是合理的。
第一,被DSU第3.2条所提及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从没有排除其他国际法规则在WTO解释中的作用。这一点,即使是严格固守WTO自足性法律体制的学者也无法否认。而这里的争论点,主要在于WTO涵盖协定之外的国际法规则是否可能会改变成员在WTO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对于仅确立最低保护义务的TRIPS协定而言,认定WTO涵盖协定外的知识产权规则是否增加或减少了WTO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时是很难的。如上述提到的解释TRIPS协定第13条,参照WCT议定声明解释的方法,虽然从措辞上看,这会和WCT议定声明一样,确立了“不得缩小”《伯尔尼公约》版权限制和例外适用范围的含义,从而可能违反DSU第3.2和19.2条。但是,由于《伯尔尼公约》中的版权限制和例外抽象和模糊的规定,其本身对于限制和例外的适用范围就是有分歧的。这样,当TRIPS协定中三步检验法的解释,否定成员实施《伯尔尼公约》中版权限制和例外的规定,也就很难认定这背离了WCT议定声明“不得缩小”《伯尔尼公约》版权限制和例外的要求。因此,可以说,此时对于TRIPS协定第13条的解释,并没有完全受制于WCT协定声明,从而影响到成员WTO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WTO法不应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自足性的独立法律体系,而应是国际法的一部分,WTO法不能与一般的国际法规则完全隔离开来,上诉机构在美国汽油标准案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①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 DS2/AB/R, p.17.对于TRIPS协定而言,其从来就和其他的知识产权公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知识产权公约对于解释TRIPS协定,确定成员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忽视这些国际法规则的作用,一味地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只机械地将TRIPS协定本身的条款作为解释渊源,则可能会造成版权公约规则之间的冲突。
(五)国际人权公约在TRIPS协定版权条款解释中的作用
但是,如果WCT/WPPT的规则可以成为TRIPS协定的解释根据,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还是可能会增加成员在TRIPS协定下的版权保护义务,破坏版权利益的平衡保护体制。如模拟技术时代,权利人不能控制某些专有权市场的情形,在数字时代,由于数字管理系统(DRM)的发展而得到改变,权利人的控制范围得到拓宽。同时权利人的这种控制,不仅仅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而且被落实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要求互联网的成员方遵守。这样,考虑到互联网公约中有关技术措施和DRM保护的国际义务规则,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TRIPS协定第13条—三步检验法的解释,就可能使得任何的版权限制和例外都会被认为是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从而认定违反TRIPS协定。而对于版权限制和例外与技术措施接口的这个棘手问题,很多成员国内的实践和理论,往往会从版权限制和例外体现的表达自由权的价值理念中寻找构建平衡体制的根据。
对此,笔者认为,既然解释TRIPS协定时,WTO专家组可以将WCT/WPPT中的规则作为指导,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与TRIPS协定密切联系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规则,WTO专家组也不应完全不予考虑。①TRIPS协定第7条和第8条为和人权条款的联系提供了可能。See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UNCTAD-CSTS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ara5.2.因为与互联网公约相比,后者既为广大的WTO成员参加,也更能反映成员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因此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的要求。
但这可能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会由此引出WTO与环境、劳工标准等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关系的敏感话题,有关讨论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认为,就版权条款的解释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考虑国际人权公约中的规则是合理的。
首先,除非之后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再遵循美国版权法案所阐明的“指导”一词,否则就没有理由不考虑国际人权条约中的规定。而如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只片面地将TRIPS本身的资料作为解释的根据,那么其解释将极有可能受到WTO以经济为中心的思路影响,可能因此增加成员在TRIPS协定项下的版权保护义务,削弱版权法促进公共利益价值追求的要求,从而破坏了版权的利益平衡体制,而这违反了TRIPS协定本身的目的和原则。
其次,如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全然不顾人权公约中的条款,而作出与人权公约相冲突的裁决,败诉的成员则将可能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是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定违反了TRIPS协定的版权保护义务,不执行该裁决将面临贸易制裁的可能;另一方面,却是执行这样的裁决,可能违反本国承担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或与本国宪法的规定不符。这时候,成员能否善意地执行DSB的裁决将是个问题。
(六)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版权条约的解释提供了根据。但是,版权条约的解释,能否超越自足性版权条约本身的资料,适用更为广泛的国际法规则,则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甚至否定性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些公约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公约成员之间的重合等因素影响,使得我们相信版权条约解释的渊源,不能仅仅局限于封闭的自足性条约体制本身的资料,解释版权条约时,适当地考虑其他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是可行和合理的。
WTO争端解决的实践证明了我们上述的结论。但是,我们注意到WTO专家组的报告还仅仅是从相互联系的版权公约中寻找根据,而从构建版权利益平衡体制构建的角度看,这种做法还需要适当地拓展。对于版权的限制和例外条款的解释而言,这意味着不应仅仅局限于相关版权公约的规定,还应适当的包括其他相关的国际人权法规则。如三步检验法的第三步——没有不合理的损害作者(权利人)正当利益的解释,由于融入了版权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使得在这一步解释时,适当考虑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则有了可能。因此,在判断是否不合理的损害到作者(权利人)的正当利益时,不仅仅应该考虑到作者(权利人)的利益,同时还应该适当考虑其他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关版权限制正当性理由的规则,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表达自由权的规定。②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2条。这就可以确保在这一步的解释中,恰当地平衡各个相关主体的利益,从而体现出版权法的利益平衡理念。
二、版权条约解释中需考虑的问题
在确立广泛的解释渊源的同时,版权条约的解释需要注意某些问题,这对于维护版权公约体制的统一性,保证版权公约在成员方国内的有效实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前约与后约之间的联系条款
《伯尔尼公约》第20条的规定,表明之后的国际公约不能降低它的保护水平。①参见《伯尔尼公约》第20条。Mihá ly Ficsor博士指出,WCT是《伯尔尼公约》第20条的“特别协定”,而这意味着必须采用一种解释方法尽量与《伯尔尼公约》第20条一致。②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作为“特别协定”的TRIPS协定和WPPT,即在解释这些版权公约时,也需考虑作为其产生基础的相关公约的条款。在这里,本文只选取TRIPS协定和WCT来作分析。但是,当该条作为冲突条款单独适用时,其上述作用则可能是有限的,其并不能当然保证未来条约不会减损之前《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水平(如这些公约成员之间的双边协定)。因为根据条约法的理论,除了《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这种特殊情形之外,规定本约优先于未来条约的条款不能限制国家的缔约自由,他们总能被当事方之间共同的协议所改变。③See Joost Pauwelyn,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355, Footnote 70.参见TRIPS协定第2.2条,WCT第1.2条。但对于WCT和TRIPS协定而言,则不存在这一缺陷,因为一方面,这些公约本身又规定了和《伯尔尼公约》第20条类似的保障条款。④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2条规定:“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视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该先订或后订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另一方面,《伯尔尼公约》第20条已经被通过提及的方式纳入到这些新的公约之中,成为新公约中的条款。而这也使得这些条款的效力可以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2条找到根据。⑤See Jo Rg Reinbothe& Silke Von Lewinski, The WIPO Treaties 1996 :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And The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 : Commentary and Legal Analysis, Butterworths,2002,p.35.由此,这些条款就成为了《伯尔尼公约》版权保护水平的重要保障。
在WCT和TRIPS协定下,这些条款的保障作用并不是否定成员制定版权限制和例外的权利,只是认为成员不得减损《伯尔尼公约》公约中的义务。⑥⑦See Mih á ly Ficsor, The Law of Copyright and the Internet: the 1996 WIPO Treaties,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ara5.76.WCT第10条的议定声明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虽然TRIPS协定第13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上述分析,TRIPS协定的第2.2条和9.1条提及的《伯尔尼公约》第20条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WIPO所出具的报告,似乎否定了TRIPS协定和《伯尔尼公约》报告之间冲突存在的可能,在有学者看来,这个报告表明:TRIPS协定第13条只是《伯尔尼公约》限制和例外的解释工具,并不会扩大《伯尔尼公约》这些条款的适用范围。这样,TRIPS协定第2.2条似乎就并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不是太妥当,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一种可能,即在TRIPS协定第13条的解释下,是一种可以被准许的版权限制和例外,但是在《伯尔尼公约》版权限制和例外的条款下,则是不被准许的,这样在TRIPS协定第13的解释下,则是成员可以授权性实施的行为,但在《伯尔尼公约》中的条款看来则是对成员的禁止性义务,这是一种典型的授权性规则和禁止性规则之间的冲突。这时,根据一般的条约解释方法,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冲突,其中的办法就是适用冲突规则。⑦See note 16 p.251.而此时,TRIPS协定第2.2条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保障作用。如Sam Ricketson教授提到的《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第(2)款的规定,在他看来,根据TRIPS协定第2.2条的保障条款,TRIPS第13条的解释,不能因准许实施播放权的免费使用,而减损成员依据第11条之二第(2)款获取合理报酬的权利。①See Sam Ricketson, WIPO Study on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2003, pp.52-53.在美国版权法案中,欧共体提出这个理由,却没有被专家组接受。但该案中,专家组只是将《伯尔尼公约》播放权规定的专有权限制和例外分成了“免费使用”和“强制许可”两个部分作分析,并认为美国版权法规定的例外应当是属于前者,从而与第11条之二第(2)款无关,其实际上仍没有否定上述冲突条款的效力。
另一方面,上述保障条款的效力有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如有关TRIPS协定中是否包含精神权利保护的问题。虽然TRIPS第9.1条将《伯尔尼公约》第1~21条纳入该协定,但却将《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或派生的精神权利排除在外。对此,Daniel Gervais 教授认为,按照TRIPS协定第2.2条的规定,《伯尔尼公约》成员仍然不应减损其所在《伯尔尼公约》下承担的精神权利保护义务。②See Daniel Gervais , The TRIPS Agreement: Drafting History & Analysis, 2nd Ed Sweet & Maxwell, 2003, para2.33.这个观点也出现在欧共体香蕉案的仲裁员报告中,See WT/DS27/ARB/ECU,para149.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既然TRIPS协定已经在纳入《伯尔尼公约》条款时,明确排除了精神权利的保护,那么,TRIPS协定中的条款就不可能要求成员做出与在《伯尔尼公约》中精神权利保护相反的义务。③See Sam Ricketson and Jane 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Beyond,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ra5.57. 同时,他们指出,虽然这时会可能与《伯尔尼公约》相抵触,但由于在TRIPS协定之前,并没有任何强制《伯尔尼公约》成员实施公约中精神权利的方案。因此,TRIPS协定并没有降低《伯尔尼公约》关于精神权利保护的水平。See para6.137.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解释TRIPS协定有关精神权利的问题上,TRIPS协定第2.2条和被纳入的《伯尔尼公约》第20条应该让位于TRIPS协定第9.1条的明示排除条款。对TRIPS协定第13条中“利益”(interests )一词的解释,在WTO框架下的含义就不应包含作者的非经济利益(non economic interests) 。
(二)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在规定了约文解释的同时,也要求条约的解释应考虑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有时候并不容易确定,此时,一个避免争议的方式,就是从条约本身的文本中确定条约解释的目的和宗旨。④美国代表团的观点表明了这一点。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353页。而某些版权公约也恰在文本中明确了其目的和宗旨,这其中某些公约所阐明的目的和宗旨与知识产权保护追求利益平衡的价值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如TRIPS协定,WCT/WPPT。⑤参见TRIPS协定序言和第7,8条,以及WCT和WPPT的序言。因此,对于这些公约中版权条款的解释,在适用具体约文规则的同时,结合这些条约中明确规定的“目的和原则”则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追求利益平衡的目的和宗旨,有时并不明确规定在版权公约中,如《伯尔尼公约》的文本中就没有像TRIPS协定和WCT一样明确版权利益平衡的规定。恰恰相反,《伯尔尼公约》序言的措辞规定,似乎更是偏向版权的严格保护。《伯尔尼公约》框架中的条款,结合条约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的结果,反而可能会更有利于版权人的权利保护,如果再考虑到上述前后版权公约之间的联系条款,《伯尔尼公约》的这个解释结果,也会影响到后来的TRIPS协定和WCT追求版权利益平衡的理念。这一点,就与上述WTO框架下强调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解释方法的影响,有些不谋而合。
对此有学者指出,确定《伯尔尼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能局限于《伯尔尼公约》的序言和标题,而审查《伯尔尼公约》整个文本的其他条款表明,《伯尔尼公约》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保护作者权利的目的,其他的利益同样被它的相关条款所承认。《伯尔尼公约》外交会议的一段历史记录,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当初在1884年的外交会议上,《伯尔尼公约》起草会议的瑞士主席Numa Droz就曾阐明,起草协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给予作者更广泛和一体化的保护,同时还应该考虑通过公共利益对版权的限制。
可以说,版权利益平衡的理念蕴藏在整个公约中,即使《伯尔尼公约》文本中没有作出“利益平衡”的明确规定,公约其他条款和缔约的历史记录也同样可以证明,公约成员追求利益平衡的共同意思。相应地,结合《伯尔尼公约》目的的解释方法,除了要考察公约中的具体条款之外,也需要考察公约中暗示的利益平衡理念。而这也使得TRIPS协定和WCT的解释,不至于受到《伯尔尼公约》严格解释版权保护的负面影响。
结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解释方法,对于上文提及的TRIPS协定摆脱单纯的以经济为中心的解释理念的影响,也显得比较重要。如对于三步检验法的解释,考虑利益平衡的因素主要还是集中在三步检验法的第三步。而在目前三步检验法严格递进式的解释方法下,只要三步检验法有一步通不过,成员国内的版权限制和例外制度就会被认定与公约不符。而三步检验法的第二步解释,从WTO专家组的报告来看,还是在强调以专有权为中心。这就可能使得成员基于公共利益制定版权限制和例外的主权自由受到严格制约,从而不利于版权利益平衡体制的构建。对此,有学者以版权条约的目的和历史资料为根据,提出可以在第二步的解释中,考虑非经济规范的方法,也就是“正常”一词包含的真实类型的规范考虑程度,即确定现在和将来潜在的市场,哪些应该由版权的所有人来控制。由于融入了对版权所有人控制市场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版权所有人控制市场的范围。同时,这种解释方法,还意味着需要对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利益进行平衡比较。因此,这种解释方法就克服了目前第二步的障碍。
当然,从三步检验法的缔约历史、实践和措辞来看,这种解释方法的可行性还有一定争议。①有关反对观点的详细评述,See Andre Lucas, For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Step Test,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2010, pp.279-281.而且,从条约解释的方法看,结合条约的目的解释方法往往是第二位或者从属的步骤。如在加拿大药品专利案中,专家组虽然指出,TRIPS协定第7条和8.1条规定的目的和限制二者都必须明确地牢记,但实际上,该案中专家组的解释,还是忽视了TRIPS协定第7条和8.1条,而仅使这些条款从属于TRIPS协定第30条。
不过,从克服目前三步检验法以专有权为中心、严格递进解释方法的障碍、构建版权利益平衡体制的价值理念追求出发,这种解释方法,相比效修改版权公约和由成员方作出解释性宣言的做法,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三)适当尊重成员的解释权
结合条约目的解释的方法固然重要,但如何在版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不同目的之间做出取舍,可能就变得比较困难。因为这些不同的目的都代表了协定成员方的不同观点。例如,如何界定“促进技术的创新、技术的转让与技术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争议的,而对此,公约成员方都有可能将其与本国的情况联系起来。在WTO框架下,这就意味着专家组可能需要对成员国内版权政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作出判断。但是,考虑到主权的因素,WTO的专家组的解释可能显得比较谨慎,因为一旦不慎,专家组的解释就可能有干预成员立法和司法主权之嫌。如在美国版权法案中,专家组虽然提及到了“特殊”一词的量的因素,但还是认为公共政策目标是次要的,为此,专家组还援引了以往在对GATT协定和GATS协定进行解释时,上诉机构拒绝适用国内立法目的和目标的做法。
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如果公约中没有统一的国际判断标准,那么在WTO框架下,负责审查的WTO专家组,就应该尊重成员自身的解释权。①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 Andreas F. Lowenfeld, Two Achievements of Uruguay Round: Putting TRIP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Together,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p.297.在加拿大药品专利案中,专家组在认定加拿大的专利法案第55.2(1)条是否违反了TRIPS协定第27.1条非歧视性规定的问题上,指出“由于缺少其他证据,法案的措辞,要求专家组接受加拿大关于这种例外法律适用于任何受市场审批需要的产品的保证。”专家组的这段表述,并没有融入自己在加拿大法律上的判断和解释,完全是建立在加拿大对自身法律解释的基础上,体现了对加拿大解释权的尊重。
但是,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一味地表示出对成员的尊重,否则协定所谋求的统一性就会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在印度药品专利案中,印度要求专家组尊重本国自身的法律解释权,对此,专家组虽然提到了TRIPS协定的第1.1条,并指出由印度决定如何具体实施其在TRIPS协定第70.8条下的义务。但是,专家组认为,为了客观评价印度目前的机制是否与TRIPS协定一致,必须分析印度的现行制度,是否可以确保达到其他WTO成员的专利申请依据协定第70.8条(a)项合法预期的法律安全和可预测性。专家组的报告,等于否定了印度自己提出的当总统法令失效时,其所实施的行政指令符合实施TIRPS协定条款的解释。专家组最终认定印度的制度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上诉机构也没有接受印度看似矛盾的主张,并维持了专家组的这个裁决。
因此,对于TRIPS协定的解释,尊重成员解释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只能依靠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个案的审查。对此,有学者提出TRIPS协定的解释,可以参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方法,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根据TRIPS协定争端的不同类型,对成员国内的决定尊重采用不同的度。对于专有权的限制和例外解释而言,当国家在寻求作者的权利和公共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未来作者获取版权作品之间的平衡时,国家应得到最大的尊重。在解释TRIPS协定的版权条款时,对于那些反映成员公共利益的国内版权政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应该尊重成员的解释权,无须作深入的审查,以免背上干预成员主权之嫌,而对于那些明显没有体现公共利益的国内版权政策,则并不需要尊重成员的解释权。
(责任编辑:王建民)
DF523.1
:A
:1674-9502(2014)06-057-13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
:2014-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