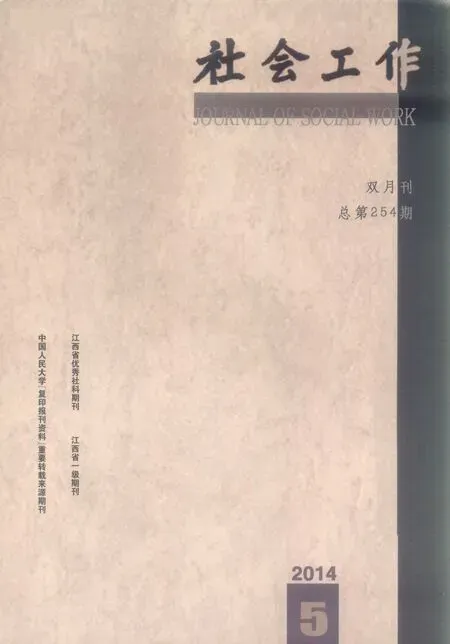“抗逆力”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乔倩倩 贾志科
“抗逆力”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乔倩倩 贾志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研究“抗逆力”。“抗逆力”也成为近期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在“抗逆力”研究是否有意义方面,仍有争论,即使是对“抗逆力”研究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也认为,现有“抗逆力”研究是有问题的:缺少共识的定义,进而在操作性和测量方法方面无法达成共识。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综述,认为“抗逆力”是一种调试的过程、能力和结果的综合;在“抗逆力”测量方面应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理论的运用;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注重本土化和生态整合,扩大研究领域和服务对象,重视认知的作用。
抗逆力 保护因素 危险因素 综述
乔倩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贾志科,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46;河北保定 071002)
“抗逆力”一词是由英语resilience翻译而来,国内有学者还将其译为“复原力”(朱森楠,2001),“心理弹性”(席居哲、桑标,2002),“压弹”(刘取芝、吴远,2005),或“韧性”(于肖楠、张建新,2005)。这一概念主要源于压力应对,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逆境会有适应或不适应的反应,随后有学者研究了危险因子及保护因子,而后提出了“抗逆力”的概念。近年来,“抗逆力”研究成为了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目前针对抗逆力概念的提出及抗逆力理论的意义尚存有争议,有学者持否定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要批判性地看待。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抗逆力研究与之前“积极调整”没什么区别,是无意义的研究;而持批判性审视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抗逆力确实与“积极调整”有相似的地方,但它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地发展,它以更专业的方式提出了其创新性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概念在定义、专业术语以及操作性和测量方面确实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不断地进行规范化和统一化。
那么,如何定义“抗逆力”,如何对“抗逆力”进行研究,在实践中如何培养抗逆力,在研究中如何进一步做好抗逆力研究?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与评述,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有关抗逆力定义的论述
(一)抗逆力的概念界定
对抗逆力的概念界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对于这一概念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特质论、结果论和过程论。
特质论把抗逆力定义为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潜能或特质。这些能力、潜能或特质均指个体的认知或情感的心理特质,包含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陶欢欢,2009)。刘玉兰认为抗逆力是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响的资源或者优势的出现,展示积极的适应结果,所以,抗逆力的本质是指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刘玉兰,2010)。
结果论认为,在环境和危险因素改变的情况下,抗逆力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抗逆力应该被视为适应良好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固定品质。
过程论者认为,抗逆力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在某一时点上相互影响博弈的过程(N.F.Watt,J.P.David,K.L.Ladd&S.Shamos,1995);关注抗逆力过程的研究主要强调的是个体战胜压力境遇,获得平衡的过程。这些研究力图发掘那些有助于个体获得复原的过程与机制(陈香君、罗观翠,2012)。
(二)抗逆力的内涵
由于抗逆力的概念比较复杂,提到抗逆力的概念一般会通过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来理解。
刘玉兰(2010)认为所谓的危险性因素,指个体所生活的环境中造成其在生存和发展上出现消极结果的因素。正是由于危险性因素的存在,个体才能展示出其抗逆能力。风险因素往往由个人的归因能力和信仰系统来决定,并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风险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发生保护性的作用(陈香君、罗观翠,2012)。风险性因素是指那些会增加不良适应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的生物的、遗传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保护性因素是指那些能够促使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事件、减少消极发展的个人或环境因素(李燕平,2005)。内在保护因素就是当事者具有一种积极的生理和心理潜质,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激发出来,并帮助个体在面临危机和逆境时,柔性应对,顽强生存(刘劲松,2013)。
大部分学者从内外两方面来了解保护性因素。其中对于内在保护性因素,大部分学者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来概括。如宋丽玉、施教裕(2010)在研究优势视角时指出Wolin(1993)提到七项协助个人发挥抗逆力:洞察力、独立性、关系、主动性、创造力、幽默感和道德感。
对于外在保护性因素,很多学者是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环境中进行分析的。在家庭的保护性因素方面。谭水桃、张曼莉等(2009)对中学生家庭因素的调查显示,高亲密感与情感表达的家庭会给孩子营造一种和谐的、相互信任和安全的氛围;讲求道德宗教观的家庭注重伦理道德、健康价值观的培养;而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独立的中学生更容易成为高自尊、高自信和高自主能力的学生;家庭成员间公开暴露愤怒和矛盾的程度较高,家庭成员间矛盾冲突多,子女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以及信任感就低。也有研究指出母亲采取的教养方式对于子女抗逆力的影响大于父亲,消极的教养方式对于子女抗逆力发展的影响大于积极性的父母教养方式(雷璇、闫瑞红、张澜,2010)。在学校、社区与周围环境的保护性因素方面,李燕平(2005)指出学校的良师益友、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良好的同伴关系及支持性的朋友是学生有利的保护因素;刘劲松指出有三项指标对形成保护性外在环境至关重要:一是充满关爱和互助的生活环境;二是寄予期望和支持的精神后方;三是参与实践的机会和锻炼的平台(孙积宏,2012)。
二、抗逆力研究的视角、范式与方法
(一)研究视角: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
目前对抗逆力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种,一是问题视角,二是优势视角。在早期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像其它助人专业一样,主要遵循医学治疗中以问题和疾病为本的思维模式,认为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瑕疵、有问题、有疾病、是病态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以专家的身份为其提供帮助和治疗,故早期的专业人士一般将社会工作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问题或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过程(闻英,2005);沈之菲也有对问题视角的理解,认为问题视角,也称为缺陷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以往的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疾患、行为问题看成是危机的结果,为了减少疾患或者问题,注意力往往专注于问题本身(沈之菲,2010);赵罗英(2010)分析比较了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其观点如下:问题视角以案主的问题为切入点,认为案主有已命名的问题和病态,认为问题是案主一个人作为人本身的问题,忽略了案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如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家庭、社区等因素对案主问题造成的影响,并且认为案主面对问题是“无能的”和“脆弱的”,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的身份,运用专业技术为这些病态或偏离常态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专业性的服务,以使其恢复到常态。在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和受助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专家和学生、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存在着控制和掌握、距离和权力的不平等。在面谈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直使用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语言,看不到潜藏在案主身上的力量,并且不断地强化案主的问题,形成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环境、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最终使案主形成消极的自我认同。
近年来问题视角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如在早期田秀国(2007)就认为传统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遵从的是一套病理学范式,采用陈述症状、专业诊断、关注病态、实施治疗、恢复健康的工作路经,这是一个荒谬的过程;杜立婕(2007)提到在其它一些传统的治疗模式中,社会工作者常常以拥有一套精深的专业技术而高高在上,以专家和权威自居,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权力关系悬殊,也有人提出“问题取向”看上去似乎只是满足了那些专业人员的需求,对案主的“问题”过度关注和过长时间的“诊断”、“治疗”,实际上满足了社会工作者的虚荣心,而没有真正满足他们所服务的案主的需求;沈之菲(2010)认为这种视角容易给青少年贴上标签,不利于发挥其内在想改变的动力和力量,也不利于青少年利用和发挥其改变的内外资源提升其抗逆力。
现在对抗逆力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基于优势视角。伴随着优势视角的兴起,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中采用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也逐步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的热点问题,它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田国秀、曾静,2007);杜立婕(2007)认为优势视角则提供了“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新模式”,那就是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常常用病理学的知识去分析每一位案主,尽管他们都是带着问题和病症而来,而是应该帮助他们去挖掘和发挥存在于身上的潜力和优势,帮助他们找到成就感,转移他们对问题的过度注意力,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会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逐渐消失,这样才会以更人性化的手段达到助人目的;沈之菲(2010)提到,抗逆力就是以优势视角看待青少年,认为个体是自己问题解决的专家,任何解决问题的资源都存在于人体身上,发现和利用个体现有的力量和资源,是个体抗逆力提升的关键;王君健、薛小勇、董凌芳(2010)认为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认为,压力与逆境是唤醒抗逆力的重要催化剂,逆境和危险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伴随有改变的机遇,也伴随有激发使生命的潜能,唤醒生命中沉睡的部分,促进生命向更高段发展;杨涛(2012)运用优势视角介入青少年成长困境中提到,案主最大优势在于其内在的“抗逆力”。
(二)研究范式:以被试为中心和以变量为中心
Masten(2001)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后认为,研究者对心理韧性的研究一般采用两种范式:变量为中心和被试为中心。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应用多元统计方法来考察个体内外各种因素与发展结果之间的联系。以被试为中心的研究按照一系列标准来比较不同被试组个体的特点,从而确定是什么因素将心理韧性个体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
李海垒、张文新(2006)、师彦洁(2011)等学者借鉴Masten(2001)研究的成果,总结了这两个研究范式的概念及不足,观点如下:以被试为中心即关注的是人,通过多元标准鉴别出在高危和低危生活环境中具有良好适应模式的人群和具有不良适应模式的人群,从而考察导致适应结果不同的因素;以变量为中心即考察个体内外各种因素与个体现在发展状况的关系。以被试为中心的一个缺陷是未考虑低危组人群,即生存环境良好,发展也良好的被试群体;相对于以被试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变量为中心的范式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出影响被试处于现在状态的因素,有利于针对实地情况进行有效的干预,但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分开的,丧失了对人的整体感。
自抗逆力提出以来,有关研究被试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集中在特殊群体,国内对抗逆力的研究也集中在特殊被试之间进行,如徐迎利(2007)对贫困大学生复原力进行考察;王君健(2010)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失依儿童抗逆力养成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研究从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入手来考察复原力的发展规律及状况,如,席居哲(2006)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滕沁、张宁(2009)研究了自尊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贫困大学生复原力的影响;谭水桃、张曼莉等(2009)对不同心理复原力中学生家庭环境因子进行了比较研究;郭雪萍(2011)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与复原力关系进行了研究等等。
(三)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对抗逆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采用定性研究的学者有孙瑞琛、刘文婧、贾晓明(2010)在研究汶川地震后个体抗逆力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个案研究,使用参与式观察、心理咨询的记录文本分析及生活随访;田国秀、侯童于(2012)于2008年9月~2010年7月,在北京某中学通过参与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焦点小组等方法,对学习困境中的学生的干预过程与效果进行研究;雷鸣、戴艳(2012)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着重从压力源、应对的内外资源方面进行访谈和录音,归纳出优秀贫困大学生心理复力内外在保护因子;姚进忠、郭云云(2014)项目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生活随访、入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
采用定量研究的学者主要借助于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量的方式来确定影响因素。师彦洁(2011)研究的第二部分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自尊、社会支持的特点进行考察,并探讨了自尊、社会支持与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之间的关系;沈之菲(2009)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上海市5个区的3662名中小学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中小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抗逆力的情况;韦海燕(2009)在对大学生复原力的干预的研究中,采用观察记录、量表施测、成员访谈、反馈等手段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郭雪萍(2011)运用复原力量表、情感指数量表和一般心理健康问卷,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对河北省664名大学生的复原力、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进行评估。
国内学者在借鉴外国量表的基础上开始编制适合研究对象的量表。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开发出适合我国青少年群体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共27个题目,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阳毅(2005)编制了大学生复原力量表,包括31个项目,共6个维度:自我效能、自我接纳、稳定性、问题解决、朋友支持和家人支持;徐浩兰(2008)对Effrey C和Wayman等人(2002)编制的教育复原力问卷进行翻译修订,设置了8个因子,即社会悦纳、自我效能、家庭支持、师生关系、自信心、乐观主义、学校认同感及同伴关系。
三、有关抗逆力培养的论述
研究抗逆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从而采取措施预防问题行为的出现或使问题行为减少或消失,使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一)理论研究
很多学者采用了某一种理论对如何培养抗逆力的方法步骤技巧进行探讨,如精神分析疗法在抗逆力恢复中的作用(孙瑞琛、刘文婧、贾晓明等,2010);叙事疗法的使用(田国秀、曾静,2007;迈克安戈尔,2006)及优势视角的使用(杜立婕,2007;沈之菲,2010;田国秀,2007)。
1.精神分析理论
陈香君、罗观翠(2012)在研究个体特质和环境特质的关系时提到了Fergusson和Horwood对个体在童年时期(0~16岁)所经历的各种逆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16~21岁)的精神健康状况,指出:如果个体在童年期面临的高危逆境越多,那么他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会面临更多的内隐问题与外显行为问题;孙瑞琛、刘文婧、贾晓明(2010)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抗逆力的内涵进行阐释,得出基于抗逆力恢复和养成的有效心理干预途径——以“足够好的治疗关系”修复早年养育的失败,努力营造一个能够让服务对象重新成长的“抱持性环境”,使得在早年中断了的复原力——“健康的自恋”的养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
2.叙事研究
后现代主义治疗以“叙事疗法”为总括,把治疗视作一个意义构建的过程,在一定的规范和文化框架中,通过治疗师与工作对象的对话而进行治疗(田国秀、朱笋、杨莉锋,2006);田国秀、曾静(2007)也提到叙事研究,又称“故事研究”,是一种研究人类体验方式的思维方法和研究范式,是一种典型的“描述——解释性”研究,叙事治疗把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现实因素引入治疗过程,它使很多不能言说或者被忽略的言说有了存在的空间,并将这些内容转化成故事。
田国秀、朱笋、杨莉锋和田国秀、曾静都提出了叙事治疗干预的三个阶段,即反思、挑战和定义。反思阶段重在解构问题。具体技术是:进入案主的生活情境,了解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权力关系,仔细聆听案主讲述重要的生活事件、他人、记忆深刻的场景,从中了解案主的“问题认同”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挑战阶段是解构与建构的交互使用过程。通过各种对话促进案主回顾并挑战反思阶段中解构的旧的叙事,深入到问题的背后提升案主的抗逆力;定义阶段侧重于建构意义(田国秀、朱笋、杨莉锋,2006;田国秀、曾静,2007)。
3.优势视角
有很多学者在优势视角下提出了提升抗逆力的步骤。沈之菲(2010)认为其工作模式可以归纳为:了解情况——理解个体——挖掘资源——重新解释——助人自助,整个过程基本是针对个体本身而不是个案的问题;田秀国(2007)提出了运用优势视角提升服务对象的抗逆力的步骤。第一,解构“问题”: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第二,建构意义:挖掘问题背后的抗逆力。第三,重构生活:用“常规途径”替代“非常规途径”;杜立婕(2007)认为实践中需要注意:第一,社会工作者通过询问一系列的问题来发现服务对象的优势,特别要激发起服务对象自己对抗逆性力量的讲述。特别是侧重于对个人品质和外界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进行挖掘。第二,还要准备一套关于优势的词汇(运用服务对象的语言),对服务对象的能力和成就给予积极的反馈,帮助服务对象去发现生活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特别是当服务对象极力否认自己的优势时;赵罗英(2010)认为实践路径分以下两个:第一,重新界定问题。优势视角要透过问题,挖掘新的意义,将服务对象问题背后的抗逆力和案主本身的优势挖掘出来。第二,将优势应用于行动中。挖掘出服务对象个人的优势后,就要鼓励服务对象按照自己的期望,挖掘周围环境中的积极性因素,去运用刚刚发现或学习到的能力,通过与社工一起行动,去寻找新的参与发展机会,以替代服务对象之前的应对压力或逆境的模式。
(二)实证研究
1.服务对象自身的干预
在提升服务对象抗逆力的实务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只需要服务对象单方面的干预,即通过课堂教育、班级辅导、小组辅导等形式,学习人际与沟通合作、问题与冲突解决、情绪与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沈之菲,2011),如席小华、王韶坡(2006)在对犯罪少年抗逆力恢复的研究中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来改变犯罪少年的态度和行为。先后在少年犯中开设了情绪管理小组、自我认识和探索小组、提升沟通能力小组、灌注希望小组等,尝试通过以上小组活动培养犯罪少年的内在和外在保护因素,以期实现犯罪预防的宏观目标。许静(2010)在对大一新生抗逆力团体辅导的实证研究中,运用相互认识、问题解决、情绪管理、冲突处理、目标设定、整装待发等小组活动主题来提升大一新生的抗逆力。
2.家校互动
有的学者从服务对象——学校——家庭三方面来提升服务对象的抗逆力的。颜苏勤(2009)在对中职生抗逆力现状与提升的实证研究中对中职生的总体干预方案就强调家校的互动,构建家庭与学校的良好环境。如对家长进行专题讲座、家长现身说法等;在学校组织专题讲座、开展各种主题活动、对学生活动进行点评、专题研讨会、“师生牵手”活动,而且通过“两会两信”、“坚强青少年、坚强家庭”演讲比赛、心理剧、亲子沟通沙龙等形式联系了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钟宇慧(2009)介绍了香港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具有预防性和治疗性的“成长的天空”计划。有识别出在未来时间里有可能出现行为偏差的学生的机制,还有以辅导课形式推行的发展课程和以小组形式推行的“辅助课程”,其中学校协同家长、教师共同协助服务对象提升抗逆力;熊远来、朱泮霏、张莉萍(2012)在对青少年抗逆力现状及其培养对策中提出,抗逆力还受到外保护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外保护性因素中,家庭、学校、社区保护性水平都相对较低,尤其存在“高期待比例高、有意义参与比例低”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将家长、教师也纳入到抗逆力学习的主体中来。
四、相关文献的评述
(一)对抗逆力定义的评述
学者分别从静态(特质和结果)和动态来定义抗逆力,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视角了解复原力,不过在生命周期中,人会面临各种问题,而且对问题的反应也存在时间上的差别,不能根据一时的反应就决定个体的抗逆力是怎样的,因此将其视为一种结果不妥;而过程视角的抗逆力研究强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里考察个体对持续压力的反应,虽然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复原力,但是对问题的应对方式也依赖于个体的能力,拥有良好的能力(如问题解决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等)才能成功的适应环境。而且有很多的学者也倾向于将抗逆力定义为能力,如萧文、田秀国等。
(二)对抗逆力内涵界定的评述
原题:Bayesian approach for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le events in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对于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的概念界定,虽然具体描述不一样,但是大体意思是一致的,危险性因素是那些不利于服务对象顺利适应环境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促成或加剧服务对象的问题,阻碍他们的良好成长和顺利社会化;保护性因素是指那些能够促使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事件、减少消极发展的个人或环境因素。对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的这些论述的说法也不一,但是存在很大的共同点,即都是从个体内在特质和环境(家庭、学校、社区)两方面来进行论述的,这就遵从了生理——心理——社会的分析模式,较全面地分析出了影响复原力的因素。但是这些学者忽视了一些特殊群体的特点,这样就忽视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一些保护或危险性因素,如青少年群体逐渐摆脱家庭的束缚,与同伴的关系愈加密切,受同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考虑影响他们的抗逆力的因素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同伴群体的哪些方面会对其产生影响。
(三)对抗逆力研究视角、范式和方法的评述
问题视角关注服务对象自身的问题,忽视了他们的能力,易强化对问题的关注,而近期受到关注的优势视角在承认服务对象问题的同时,强调看到他们的潜能,弥补了问题视角的不足。根据上文中学者提到的两个范式的不足,为弥补各自的不足,在研究中可以整合两个范式,以变量测量为主,在准确测量影响服务对象的因素后,采用以被试为中心的范式,将他们再分组进行对比试验。这样就可以较准确地测量出导致服务对象现在处境的因素了。同时,也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
(四)对理论研究的评述
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抗逆力的学者从病理视角分析服务对象的问题,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童年早期经历中发现造成现阶段抗逆力难以恢复的原因,实践证明精神分析的运用对提升服务对象的抗逆力有一定的效果,但忽视了服务对象现阶段的一些因素,有学者开始运用叙事方法和优势视角来培养服务对象的抗逆力。新阶段对抗逆力的理论研究比较多,而实证研究还比较少,不过实证研究已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
五、抗逆力研究的未来方向
由于概念是其他研究的基础,抗逆力概念界定的不统一给研究造成不便,因此,需要提升概念和专业术语的一致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或改进。
(一)扩大抗逆力研究的服务对象和领域
现在的研究服务对象大部分是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处境不利”或特殊群体,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Anthony(1974)就对24个父母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儿童进行了追踪研究,确定处在不利处境的儿童的复原力状况;田国秀的《从抗逆力视角对“问题青少年”实施干预》等,近来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抗逆力研究也在增多,如许静的《大一新生抗逆力团体辅导》;赵翔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抗逆力研究》等等。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除了个体,组织和社区也同样面临各种困境,把组织当作是一个整体,来考察组织的抗逆力水平成为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外国文献的翻译上。因此,后期在研究个体抗逆力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组织及社区抗逆力的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面了解抗逆力,促使个体、家庭和社区都可以很好地适应压力情景。
(二)加强认知研究
上一条说明了文化对服务对象抗逆力的重要性,同时Shek(2005)对199个香港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追踪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对逆境的信念或价值观是影响遭遇贫困境遇青少年获得良好心理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对逆境持积极文化信念的青少年,倾向于拥有更少的问题行为,心理社会发展更加健康;席居哲(2010)发现:在缺乏心理弹性组,发现社会认知具有显著的主效应,对压力(逆境)的负面影响起补偿作用;在心理弹性组,社会认知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其与压力/逆境显著的交互作用,可见不同水平社会认知的功能特点并不一样。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个体在逆境中,其认知图式的建立、改变、完善和情绪调节、行为改变的效果,从而逐步建立起正确认知在作用机制中的调节作用。
(三)注重本土化抗逆力的研究
Ungar(2006)运用国际抗逆力项目的研究数据去分析抗逆力的一般特征和具体文化特征,经分析表明文化和性别因素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抗逆力的重要变量。
由于文化差异性的影响,国外的研究难免会掩盖本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考虑到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里,人们对何谓健康的心理与行为、对抗逆力的信念以及在压力境遇下何谓积极健康发展的理解是有所差异的,因此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量表及干预策略;同时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也具有不同的信念和个性,还应该重视跨民族、跨地区的交叉比较研究,多角度来了解不同群体的抗逆力,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抗逆力理论与实务模式。
(四)编制有中国特色的量表及发展多元测量方法
不同群体的抗逆力是不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别。现在对群体的抗逆力测量大都是依据加州儿童健康调查而进行的,但它并不能够准确测量特定个体或群体抗逆力的影响因素。因此,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量表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要根据个体或群体的特点选择多元的测量方法和工具才能确保更加准确地确定服务对象抗逆力的影响因素,以便针对具体情况提供有效的干预计划。
(五)注重运用生态视角
传统上抗逆力的研究多是在心理社会水平上开展的,积累的实证资料大多也是从行为指标上获得的,对服务对象抗逆力的培养也多是以服务对象自身能力提升为重点,但是人是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外在保护因子对服务对象的抗逆力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在制订干预计划时,需要注重生理和心理的相互作用,应尽可能考虑可能对服务对象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运用系统的和生态的观点来审视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包括生物、心理、家庭、社会网络、机构等多个方面。
(六)注重抗逆力发展的整合研究
为了解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体或群体抗逆力的影响因素或作用机制,需要测量和分析的多元化。有学者呼吁要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复原力。虽然部分研究已经涉入到脑细胞、分子水平,但尚未厘清抗逆力的生理机制,除了要结合生物学的知识外,还应该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同时,保护因素存在于不同的层面,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时注重预防性和补救性的整合的干预方法。
[1]陈香君,罗观翠,2012,《西方青少年抗逆力研究述评及启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2]杜立婕,2007,《使用优势视角培养服务对象的抗逆力——种社会工作实务的新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3]高翔,郑日昌,2009,《中学生复原力测评的三视角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期。
[4]胡夏娟,2009,《大学生压力知觉、复原力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李海垒,张文新,2006,《心理韧性研究综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6]李燕平,2005,《青少年研究的新趋势---恢复力研究述评》,《青年研究》第5期。
[7]雷鸣,戴艳,2012,《优秀贫困大学生心理复原力内外保护因子的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6期。
[8]雷璇,闫瑞红,张澜,2010,《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复原力的相关关系》,《中国学校卫生》第6期。
[9]刘劲松,2013《论当代大学生“抗逆力”的激发与培养》,《江苏高教》第4期。
[10]刘取芝,吴远,2005,《压弹:关于个体逆境适应机制的新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2期。
[11]刘玉兰,2010,《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
[12]罗东霞,田雅琳,时勘,2011,《组织抗逆力研究——微观和宏观视角之启示》,《经济研究导刊》第36期。
[13]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心理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
[14]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2012,《社会工作实务(中级)》,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5]田秀国,2007,《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挖掘学生抗逆力的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模式浅析》,《中国教育学刊》第1期。
[16]田国秀,侯童,2012,《优势取向的学校社会工作辅导路径探析——对学习困境中学生实务介入的个案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17]田国秀,曾静,2007,《关注抗逆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领域的新走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18]陶欢欢,2009,《复原力(resilience)研究的回顾》,《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报》第5期。
[19]沈之菲,2011《抗逆力的学习模式》,《思想理论教育》第12期。
[20]沈之菲,2009,《上海市中小学生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抗逆力的实证研究》,《思想理论教育》第5期。
[21]师彦洁,2011,《高中生日常性学业复原力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2]宋丽玉,施教裕,2010,《优势观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3]孙瑞琛,刘文婧,贾晓明,2010,《“5.12”汶川地震后抗逆力的个案研究— —来自精神分析视角》,《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24]孙积宏,2012,《积极心理学视野下青少年学生抗逆力的培养现代》,《基础教育研究》第6期。
[25]谭水桃,张曼莉等,2009,《不同心理复原力中学生家庭环境因子比较》,《中国学校卫生》第2期。
[26]王韶坡,2006,《犯罪少年抗逆力的恢复》,《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27]席居哲,2006,《基于社会认知的儿童心理弹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第5期。
[28]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2,《心理弹性(Resilience)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健康心理学杂志》第6期。
[29]萧文,2000,《灾变事件前的前置因素与复原力在创伤后压力症候反应心理复健上的影响》,《九二一震灾心理复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彰化: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30]熊远来,朱泮霏,张莉萍,2012,《当前青少年抗逆力现状及其培养对策》,《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第5期。
[31]颜苏勤,2009,《中职生抗逆力现状与提升的实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32]杨彩霞,王伟,张丽芳,2010,《我国复原力研究现状》,《校园心理》第5期。
[33]杨涛,2012,《优势视角下青少年成长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以优势发展为核心的案例分析》,《青年工作与政策研究》第4期。
[34]于肖楠,张建新,2005,《韧性(resilience)——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35]赵罗英,2010,《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优势视角”模式》,《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2期。
[36]周碧凤,2004,《复原力研究的进展与方向》,《求索》第10期。
[37]钟宇慧,2009,《香港抗逆力辅导工作及其启示——以“成长的天空”计划为例》,《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第77期。
[38]朱森楠,2001,《从复原力观点谈国中中辍复学生的复原因素—以一个个案为例》,《新竹:九十年度教育研究集刊》,新竹县教育研究发展暨网络中心。
[39]A.S.Masten&D.Coast worth.,1998,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American Psychologist.(53):205
[40]N.F.Watt,J.P.David,K.L.Ladd&S.Shamos.,1995,The Life Cours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n Deflecting Life's Slings and Arrows.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15):209
编辑/杨恪鉴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SH046);河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项目。
C916
A
1672-4828(2014)05-0140-10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5.016
——认知行为治疗介入精神障碍康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