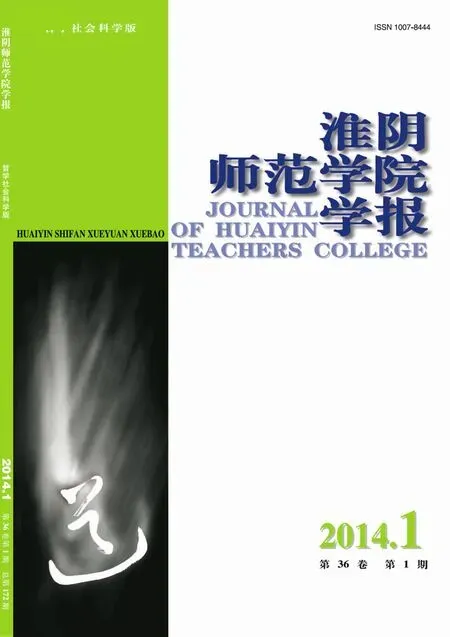明代苏松重赋的成因
周岐琛
(南京大学 商学院经济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苏松地区因其物产丰盈,宋元以来课税较重,而明代尤重。这成了明清以后学者们颇为关注的历史现象。当然,对于明代苏松地区是否重赋以及重赋的原因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故有对这一历史现象再作探讨的必要。
一
对于苏松重赋,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除去极少数地区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的问题”[1]。但自明清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重赋现象确实存在。明人谢肇淛有这样形象的记载:“三吴之地,赋役繁重,追呼不绝,祗益内顾之忧耳。彼但知福之从田,而不知累之亦从田也。”[2]73而明清的布衣学者对此论述尤为详尽。明代郑若曾专著《苏松浮赋议》,清代周梦颜撰辑成《苏松历代财赋考》一书,详论这一事实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于苏、松二府,究竟何者更重,《国榷》引述松江人陆深对于明初税粮的统计,说:“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3]586认为松江赋税之重更过于苏州。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重赋现象并非苏、松所独有,江西、赣西、宁州等地亦有重赋。但总体而言,明清以来,学者普遍认为苏、松赋重乃天下之最。但对苏、松重赋的原因认识并不一致。有从经济方面分析重赋乃明王朝统治者财政的需要,有从苏、松及江南经济状况来论证,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朱元璋恨吴人随张士诚坚守苏松,于是以重赋惩之,对此《明史·食货二·赋役》载: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4]1896
我们认为,苏、松重赋是明代突出的一个政治经济现象。有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经济、心理以及论述者的里籍等因素,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二
苏松重赋诸种原因中,太祖迁怒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当然,这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总体而言,明代学者讲得较为含蓄,如《菽园杂记》卷五载:“(苏州)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5]59与张士诚的因素有关的,仅是“张士诚义兵头目”,所受影响颇为有限。范濂的《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记载:“有因张(士诚)氏义兵而籍入者。”范围广及“兵”而不仅限于“兵头目”。以上多为文人笔记所载。在正式文书中也有谈到张氏与苏松重赋的关系,如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枕书》说:“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人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6]360既然出现在给巡抚的呈文之中,“籍没张氏义兵”,当为确有其事。而“一依租额起粮”则被推到“不体圣心”的有司头上,这当是明代作者因时代环境使其然。明代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论述这一现象时说:“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什之六,或谓沉没万三时,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或又谓张王不降之故,欲屠其民,后因加赋而止,皆不可晓。”[7]32其中的“沉万三”,吕景琳案:“沉没万三,当作没沈万三”,亦即籍没沈万三时将民田变成了官田。所谓的“张王不降”,当是指吴民附从张士诚,守城不降。究竟何者为是?王士性“皆不可晓”。但是,以性情疏放“恶礼法士”[4]7352著称的祝允明则毫不讳言,说:“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盖惩一时之弊,后且将平之也。”[8]直接指出苏赋之重,是因太祖之“愤”。
清代学者对苏、松及江南重赋的原因表述得更为直接。如,谈迁在《国榷》中说:“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3]585同样,顾公燮、沈德潜等人也有相似的结论。比较而言,顾炎武的学生潘耒的论述则与明人还有些许承祧的痕迹,说:“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9]即,是因籍没“张氏故臣”的土地而致重赋。综合明清学者的记载可以看出,苏、松重赋与张士诚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朱元璋是否如此器量狭小而重赋吴人呢?也有论者提出了反证。但是,我们以为朱元璋惩吴民附张,也许确实比较符合朱氏心理。事实上,除了苏、松重赋之外,还有一些记载可以附证,如,明人王錡云: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10]
不但如此,郑克晟在考察明初的赋税情况时发现,因为江西大部在元末属于陈友谅所据,同样也被征以重赋。陕西宁州,虽然土地贫瘠,但明代以来也是“科赋独重”,原因则在于李思齐抵抗明军。[11]随张士诚坚守城池,且物产丰盈的苏、松地区初课以重赋,则是符合朱元璋的性格及其心理特征的。范金民先生根据建文帝诏书:“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之顽民耳,岂可为定例?”指出:“怒民附寇一说很可能首先出自朱元璋的嫡孙建文帝朱允炆之口。”[12]堪称的论。嫡孙而言其祖“用惩一时”,几为铁证。因此,朱元璋惩吴人附寇,这是从政治心理角度分析苏、松重赋成因的可靠结论。
三
探讨苏、松重赋形成的原因,除了历代学者讨论最多的朱元璋惩吴民附寇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历史原因。明代大学士丘浚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经制之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2册,第336页。论浙东、浙西的赋税之重,从唐人韩愈的言论说起。可见,江南重赋,早在唐代即已形成。这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同,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即首先引丘浚《大学衍义补》为据。而清人陆世仪说:“苏州税额,比宋则七倍,比元犹四倍。”*陆世仪:《苏松浮粮考》,清光绪陆桴亭先生遗书本,第2页。但这并不能证明历史上苏、松赋税不重。元代是赋税较轻的朝代,据明初叶子奇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13]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比元犹四倍”,仍不能说明元代时苏州税额较轻了。由此亦可见,苏州以及江南赋税偏重,有历史的因素。但何以到明代特重?这与苏松两府的官田比重大有关。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又具有历史的原因。顾炎武《日知录》曰: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剡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6]365
根据顾炎武所说,官田的租额之重远高于民田,因此,苏、松重赋的背后与官、民田的比例失调有密切的关系。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又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自元代的王公大臣直到张士诚居吴时的各级官吏都有大量田地,这些土地在明初都被籍没而为官田。这无疑是苏、松重赋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原因。苏松及江南地区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谢肇淛说:“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2]79意思是说,北方土地的收入不及江南的十分之一。(乾隆)《江南通志》载:苏州“擅江湖之利,兼海陆之饶,繁华盛丽之名甲天下,至若万流所辏,分津导渠,组绣交错,田赋所出,常书上上”*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苏州府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7册,第154页。。松江“谷水昆山自昔传为名胜,以故钟灵毓秀,雄望埒于苏常,不独谷帛所资,推为财赋要区矣”*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松江府图说》,第507册,第154页。。清人王应奎在《浮粮变通议》一文中说:“湖广全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全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岂非极重难反之势哉?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14]苏松不但农业发达,棉纺织业同样如此,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将南方的纺织技术带回乡里,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元政府颁布了江南税制,将木棉、布、丝绵、绢列为夏税征收的实物,这从侧面显示了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将棉花列入征收赋税的一种,“桑麻科征之额,麻亩科八两,木棉亩四两”*《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洪武元年夏四月辛丑朔”条,钞本,第5页。。这也说明了江南经济的全面发展。王仲荦进而认为:“朱元璋因苏松嘉清四府的纺织业发达,才把四府的租额定得特别重,以变相进行他对纺织业的剥削。”[15]唐文基也认为:“明初江南重赋,是新王朝利用这一地区土地产量高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国有官田,同时又通过政治暴力扩大近额官田的结果。”[16]
苏松经济的发展也衍生出了较为侈靡的民风,这也成为苏松重赋的另一诱因。嘉靖时的苏州通判余永麟说:“王北川仁山云,予昔在科时,曾过湖查册,偶见苏、松旧册一本,前开重赋之由。盖太祖见苏、松俗尚侈靡,故重税以困之,亦一时之权宜也。后以东南财赋苏、松为最,遂以此为常法。云太祖见某氏租簿遂定以为税者,想传闻之误。”[17]这一现象从其他的文献中也得到了一些印证。如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5]156奢靡之习的基础在于经济,没有丰饶的财富,奢靡而不能。习俗正是经济状况的一个佐证。奢靡又是重赋的一个诱因。出于在苏州为官的余永麟的记载,这更不应为我们探讨苏、松重赋原因时所忽视。
最后,论者原因。古代学者以据实书史为荣,但作者的主观情感往往影响著述的内容。赋税政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不同里籍的作者,对苏、松重赋的感受往往影响着他们见诸书册的文字。不难发现,肯定并对苏松重赋记述翔实、分析透切的往往是苏、松地区的文人。冯桂芬修的同治《苏州府志》中的《艺文·田赋》中列入了众多苏州籍作者的著述。陆容在《菽园杂记》中特别强调苏州赋税重乃明代所独有,云:“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5]59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亦著有《苏松浮粮考》,说明了苏州税额明代独重。陆容和陆世仪都是江苏太仓人,太仓是明弘治十年(1497)苏州府将所属的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分出部分土地而成,亦即他们都是苏州府人。比较而言,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则对苏松赋重的态度明显超然:“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然吴人所受粮役之累竟亦不少,每每佥解粮头,富室破家,贵介为役,海宇均耳,东南民力良可悯也。”[7]32言吴中而结论则是“东南民力良可悯也”,其“东南”,自然延及作者之临海。将苏松重赋撰成专著,论述较为翔实的明代的郑若曾、清代的周梦颜等人,他们不但著书论述,周梦颜还在1699年康熙南巡江浙期间,偕同陆淳风等人到扬州行在跪奏,请求减免苏松浮粮。郑若曾与周梦颜都是苏州昆山人。晚清冯桂芬为李鸿章撰疏,请求为苏松减赋,并有《江苏减赋记》一文专门记之*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清光绪二年冯氏校邠庐刻本,第6页。,而冯桂芬也是苏州吴县人。作者的里籍,是我们分析苏、松重赋是否存在,程度究竟何等之重时需要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解开明代苏松重赋这一历史谜团。
[1] 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J].历史研究,1957(10).
[2]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4.
[7] 王士性.广志绎: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邓士龙.野记(一)[M]//国朝典故:卷三一.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17.
[9] 潘耒.又送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M]//钱仪吉.碑传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472.
[10] 王錡.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11] 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J].南开学报,2001(6).
[12] 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J].中国农史,1995,14(3).
[13]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47.
[14]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三十二户政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789.
[15] 王仲荦.明代苏松嘉清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J].文史哲,1951(2).
[16] 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J].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
[17] 余永麟.北窗琐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小说家类:第24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