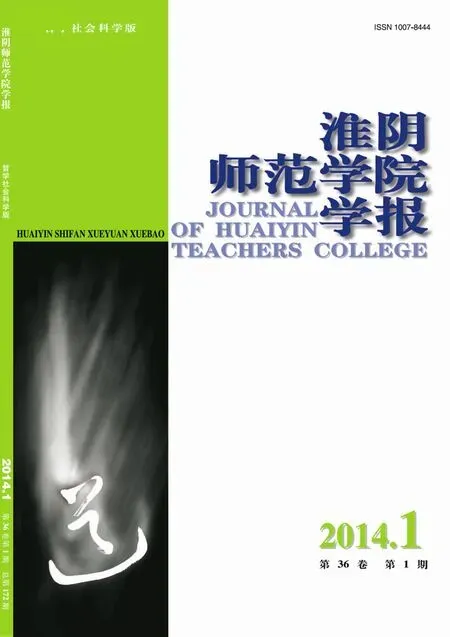学习弘扬侯仁之先生三大治学风范大力推动历史地理学深入发展
朱士光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建者之一,我的“文革”前研究生导师侯仁之院士,虽于2013年10月22日下午以102岁高龄在京辞世,然而他的学术成就与对国家的贡献,他的治学理念与风范必将长存于世,继续惠泽于学界和世间。他辞世三天后的10月26日的下午,我赴京在北京大学祭奠仁之师的灵堂上,应接待工作人员之请,在祭奠仁之师逝世纪念册上曾题词:
先生百岁仙逝,遗教万世长存。
学生当更发愤,努力传承创新!
这确是我作为一个由仁之师引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大门,又于“文革”后由他竭力帮助我专业归队,终于在1982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并自那以来不断勉励指导我在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科研岗位上矢志不渝坚持工作,不曾稍有懈怠的一个老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悼之情与出于专业职责的自觉心愿。
对于仁之师高尚的人品与卓越的智慧,以及他深邃的治学理念与崇高的学术风范,我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从1963年深秋一个下午在他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考察小组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布和沙漠考察归来后不久,我应命赴燕南园61号他住宅一楼客厅与他首次见面始,迄止今年3月17日,我由尹钧科学弟陪同至北京大学校医院住院部A26室见到他静躺在床上的最后一面,在50年里,通过我之亲身感受与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全面而又具体的认识。本文现仅就仁之师学术研究方面之治学理念与风范试作一些剖析,着重从他具有的开创的精神、开扩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三个方面加以阐释,以供学界朋友传承弘扬时思考。
首先是开创的精神。
仁之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开创精神在他毕生治学实践中时时处处都有体现,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上。这当中又以下述两篇论文作用最著。
其一是1950年7月发表于《新建设》杂志第二卷第11期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这是仁之师于1949年夏初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9月底回到北京不到一年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我国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在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倡导成立禹贡学会后所取得的多方面重大进展的实际情况,吸纳了西方英、美等国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他的导师达比教授有关这门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还结合他在利物浦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的心得体会,郑重地提出:“旧日大学里被称做‘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史地理’。”正是在此文的推动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带动下,我国一些高校纷纷将原开设的沿革地理课改为了历史地理课,或新开设历史地理课。自此,历史地理学也就在我国这一东方沃土上扎下根基,茁壮成长起来。
其二是1962年3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八卷第1期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该文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学科构成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特别强调要着重结合人类历史时期人为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这实际上已明确宣示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为“人地关系”理论。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仁之师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促成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建立;而《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则奠定了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基础,并由此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全面蓬勃的发展。所以这两篇论文在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作用。
当然在上述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之后,仁之师在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建设上还有不少新的建树。诸如1978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学分会上作的题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阐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之“历史时期”要扩展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日益显著影响时,就是地质史上的“中全新世”或考古学分期上的新石器时期中期;1993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倡导的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相互结合开展统一的综合的研究等,无不放射出仁之师开创性的思想火花。它们对历史地理学之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均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继之是开扩的视野。
仁之师于1932年秋参加北平燕京大学特别考试,因成绩优异获四年奖学金得以到历史系学习。后因参加了禹贡学会,本科毕业后留校做顾颉刚教授硕士研究生,并兼任顾颉刚先生所任历史系主任助理,协助顾先生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常到北平郊区进行现场调查,又曾赴坝上张家口与黄河河套地区进行考察,这就使他的专业领域超出史学范围。抗日战争胜利后仁之师赴英国留学,师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已跨入地理学领域。1949年9月回国后,先生曾应梁思成先生之邀至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城镇地理基础课,后至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出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先生领导该系所设的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貌学、古生物学、地质构造学、岩石矿物学等6个专业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自1960年夏起连续几年赴西北沙漠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后,为探寻沙漠中的遗迹与文物,借之研究一些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形成、演变之历程,仁之师又主动邀请考古学家参加工作,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效果。因而他在之后写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中(该文收入仁之师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曾深有感触地写道:“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我深切感觉到,在探讨现代地理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文物考古工作者参与协作,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就很难圆满解决。”同样,仁之师为了全面推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充分完成历史地理学肩负的研究任务,也十分强调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与地质学工作者,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纪地质学工作者协力合作。正是因为仁之师具有如此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地质学(二者可合称为“地学”)以及考古学(以前我国教育部颁行的学科目录将之归属到历史学,2011年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集纳于一体,所以方能在历史地理学之理论建设以及他具体进行的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地理等分支学科中取得创新的成果,他由此也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推进历史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他不仅自己具体践行,而且也将之传授给他的学生。例如我于1963年秋进入燕园后,他一方面亲自给我讲授历史地理学理论课与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专业基础课,另一方面安排我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地质学专业着重学习考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课程。我从中亦受益良多。所以“文革”后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后,在协助史念海先生培养研究生以及我后来独立培养研究生时,也遵奉这一理念。对大学本科学历史学的学生,让他们加学地理学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学本科学地理学的学生,则让他们加学历史学方面的课程,以促使青年学者充分适应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发展的需要,胜任有关科研工作,成为出色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
再者是开放的胸襟。
仁之师一贯将学术成果视为社会之公器,不将之当做个人争名逐利之私有财富。正因为他有着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就使他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既十分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又能虚心听取批评问难,以使其研究成果能为人类增添知识宝藏,为社会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所以他在学术论著问世后,都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学术界与社会的商榷、评论,并服膺真知灼见,择善而从。其中最令人敬仰的例子就是他在发表于《文物》1973年第1期上《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一文中,坦然承认他刊载于《地理》月刊1965年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一文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东南端城川镇的“城川古城”定名为唐代的旧宥州城“是错误的”,并采纳了我于1965年夏前往城川地区进行历史地理综合考察与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即前述“城川古城”当为“唐代元和十五年(820)以后的新宥州城”。应该予以特别说明的是,我的这一见解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也没有向仁之师正面提出。1965年暑假,我遵奉仁之师的安排只身一人在城川地区进行了近1个月的气候、地貌、河湖、植被、土壤与城川古城及其附近地区古代遗址、遗物(如古代钱币等)考察,工作已近尾声时,突接系里电报通知,命我立即结束工作返回学校;我回校后一位系领导告诉我,因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学校认为我不能继续研究生学习,要我参加当年本科毕业生分配,尽快离开学校。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只能服从。于是在赶写出考察报告《对城川地区湖泊古今变迁的初步探讨》后,将该报告连同在城川地区采集的一箱拟做孢粉分析的土样送呈仁之师,不久即匆匆离开燕园前往西安工作。之后在陕西省水利厅属下的水土保持局任职,远离了历史地理学学术领域,所以对上述情况从未对人道之及。不曾想到,过了将近八年,仁之师在1971年10月从江西鄱阳湖滨之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回到燕园,1972年在应约于“文革”爆发后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即将仅仅他知我知的城川古城定名事和盘托出,没有丝毫遮掩躲闪辩白解释,其真诚坦然之情跃然纸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令我肃然起敬!这在当时神州大地上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科学民主精神被横扫殆尽,野蛮愚昧言行充斥于世的时代氛围中是多么难能可贵!该期《文物》印出发行后不久,我即在1973年春夏之交收到仁之师邮寄的样刊。当我读到仁之师论文中那条详叙城川古城定名经过的注释时,内心所感受到的震撼真是难以名状!当然我从中也深深感悟到,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是多么的伟大!自那以后我也下定决心,一定以仁之师为楷模,终身学习笃行他这种精神;并在1982年1月专业归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后,给自己确立了在学术研究中“不怕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进行争鸣、不怕有人指出错误进行批评、不怕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三不怕”的准则。
当然,面对学界的辩难与批评,仁之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在认真听取后仍然坚持自己见解的同时,也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中确立新的突破口,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演变问题,面对有学者认为该沙地史前时期即已存在的不同观点,他毫不为之所动,只是更为坚定了朝着既定研究方向继续加强工作的信心。可惜的是这方面工作因“文革”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了十几年。
以上所述仁之师在学术研究中遵循的开创的精神、开扩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三大治学原则,是他自青年时代求学燕园起,直至耄耋之年时,始终坚持不渝的。这也就使他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一株永葆青春的不老松,始终充满激情与活力,每项成果都闪耀着创见与新知。现在仁之师虽已仙逝,但正如本文开头我在北京大学祭奠仁之师灵堂所题挽辞所说的,遗教必将长存。相信学术界同仁会铭记仁之师的遗教,遵奉他的治学理念,传承弘扬他的学术风范,推动我国学术研究事业,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科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