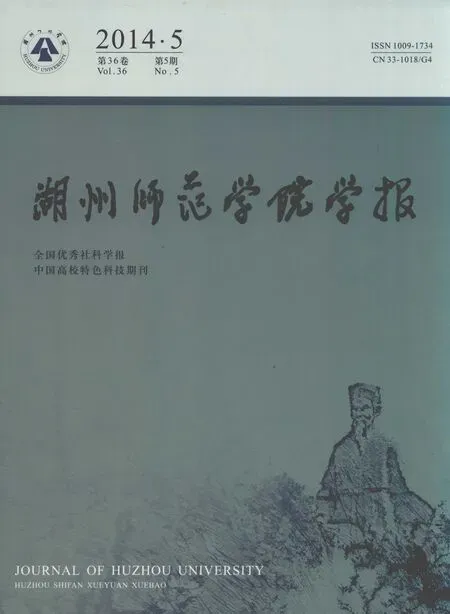同构与解构:奥斯丁小说对童话叙事的超越*
步雅芸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贸易分院,浙江湖州 313000)
同构与解构:奥斯丁小说对童话叙事的超越*
步雅芸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贸易分院,浙江湖州 313000)
简·奥斯丁小说不仅与童话叙事在故事原型、主题、创作思想等方面有着同源同构的关系,书写了边缘化的女性生活,而且奥斯丁以其女性独有的视角对童话叙事的人物、情节、结构等要素进行了修正与解构,体现出其对传统童话叙事的超越和对同时代女性地位的关注。
奥斯丁小说;童话叙事;同构;解构;超越
简·奥斯丁一生所写的六部小说都以描写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生活风貌为主,主题围绕三五户人家的居家度日和婚恋嫁娶,被认为是小题材大哲理的经典之作。两百年来,随着文学口味的不断翻新,她同时代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消逝在了浩瀚的历史长河,唯有她“经久不衰”,一直深受读者喜爱。[1](P36)奥斯丁小说出版的1811年至1817年间也是欧洲童话创作崛起与发展的阶段。作为女性的奥斯丁与童话的受体——儿童一样,同处于弱势及边缘地位,创作的小说也与童话一样,蕴含人类丰富的经验;奥斯丁的小说与童话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1939年,英国贝德福大学心理学教授D·W·哈丁就提出了奥斯丁“对灰姑娘主题的迷恋”。[1](P95)此后,童话中的“灰姑娘情结”成为奥斯丁小说原型批评的主流,较为有影响力的包括黄梅在美国出版的专著Transformin g the Cin derella Dream:From Frances Burney to Charlotte Bronte,该书从灰姑娘模式出发,解读了范妮·伯尼、奥斯丁及夏洛特·勃朗特这三位英国女性作家文本中灰姑娘故事的演变。[2]卢爱芝等发表《从〈爱玛〉看简·奥斯丁小说中的灰姑娘主题》一文,把奥斯丁的小说与经典童话模式挂钩。[3]戴岚专著《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也涉猎奥斯丁小说的童话模式。[4]但是,大部分评论作品的关注点都仅仅停留在奥斯丁小说与灰姑娘故事的联系上,没有从源头上分析产生联系的原因,也鲜有作品指出奥斯丁在童话模式和思想内涵上的创新点。实际上,奥斯丁创作的小说不仅与童话叙事在故事原型、主题、创作思想等方面进行着同源同构,奥斯丁还以其女性视角对人物、情节、结构等叙事要素进行了修正与超越,表达出她对女性成长和女性主体身份的积极思考。
一、与童话叙事的同源同构
妇女和儿童常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都曾处于边缘的从属地位,并在生理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固有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有着最亲密的联系,产生了许多共有特征。奥斯丁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六部小说,分别为《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爱玛》(1815)以及作者逝世以后出版的《诺桑觉修道院》(1818)和《劝导》(1818)。六部小说与童话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相似的故事原型
“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景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5](P44-45)爱情与婚姻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中不变的主题,是人们的深层意识之中普遍的精神追求,所以,“灰姑娘以自己的善良和美丽扭转悲惨的命运,最终与王子结婚”的童话故事已成为人类文学中最令人动容的原型之一。灰姑娘的故事有几个特征:一是女主人公处于相对低位的社会地位,但却拥有出众的品质;二是爱情经历巨大的波折与考验,王子千辛万苦才最后找到真爱;三是幸福圆满的结局,善恶总有报,男女主人公如愿以偿幸福地结合。“灰姑娘”故事的原型历经时代变迁,却经久不衰。奥斯丁的小说与童话故事套用了相似的原型。《曼斯菲尔德花园》被认为是奥斯丁小说中最典型的灰姑娘故事。小说女主人公范妮出生贫寒,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因此从小寄养在富有姨夫、姨母家里,过着寄人篱下、位卑言轻的生活。两个表姐看不起她,伯特伦姨母只把她当作解闷的陪伴,诺里斯姨母则将她视为女仆对待,常常支使她干这干那。只有二表哥埃德蒙关心爱护她,教他读书与思考,也使得范妮芳心暗许。但是埃德蒙却未察觉,在经历埃德蒙对克劳福德小姐的追求、克劳福德先生对范妮的求婚等一系列波折后,范妮以其始终保持的一颗善良并能感受到美好情怀的心灵赢得心中白马王子埃德蒙的真爱,两人从此幸福地生活在曼斯斐尔德花园。当然,类似灰姑娘故事的翻版也体现在《劝导》中的安妮、《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爱玛》中的简、《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诺桑觉寺》的凯瑟琳等角色身上。
(二)类同的成长主题
“成长”是童话故事的永恒主题之一,最耳熟能详的当属《丑小鸭》了。“丑小鸭”通过对美的向往和不懈的追求,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与“丑小鸭”童话一样,奥斯丁六部小说主题也是围绕成长展开,描写了各女主人公爱情观和价值观形成与完善过程中的困扰,被认为是18世纪少女成长的规范读本。奥斯丁小说中最典型的成长来自于《爱玛》的同名主人公。这是一个作者曾担心除了自己,没有人会非常喜欢的主人公。[1](P264)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爱玛如何在替别人乱点鸳鸯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不足与真爱,而最终嫁给一直心仪于她、不断提醒她、助她成长的贵族奈特利先生的故事。芮渝萍在评价奥斯丁的成长故事时,曾归纳出一重要论断:“奥斯丁的所有小说关注的并不是爱情故事本身的悲欢离合,而是注意表现女性爱情观念的形成和变化。”[6](P32)所以为配合女主人公“成长者”的功能定位,奥斯丁也安排了《傲慢与偏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克服偏见而个性更完善;安排《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和玛丽安自我完善后达到个性上“理智”与“情感”的融合;安排《诺桑觉寺》的凯瑟琳从哥特式的幻想中摆脱出来而与亨利牵手幸福;安排《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公范妮不再逆来顺受,拒绝了劝婚而收获幸福;也安排《劝导》中女主人公安妮经过八年的感情磨难而成熟、冷静、处事有道,最终赢得温特沃斯上校的感情回归。
(三)共同的创作追求
19世纪前后的英国社会虽然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但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与儿童身上被强加着各种限制。在男性霸权文化的影响下,童话的创作反映出成人对儿童行为规范的指向,女性的创作则必然要围绕淑女和绅士道德品行的规范。因此奥斯丁小说创作和童话一样关注的重点是主人公成长,体现出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强化的是作品的教育功能。
奥斯丁的创作与童话一样,都包括了主人公成长的背景、爱的困惑、遭遇考验、陷入困境、获得醒悟和拯救、幸福婚姻等相似的经历。这种类似的创作,在纷繁的表象下面反复出现,既是对童话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来源于对19世纪真实生活的反映,是对“至真”的表达。同时,奥斯丁的小说都以婚姻结尾,其叙述的重点都落在圆满结局到来之前男女主人公在社交过程中对自己认识和行为偏差的不断修正上,这是对“至善”的追求。这种因美德而收获幸福的创作思想不仅把婚姻与成长的主题水乳交融,而且把18世纪理性主义传统强调培育自我意识的思想完美融入,体现出两者创作对“至美”的心理需求。
奥斯丁的小说与童话在多方面进行同源同构,戴岚曾评价“奥斯丁的小说,是一部部纯情女子的童话读物,是她们踏入情感世界的教科书,是得体言行、交际处事的行为指南,也是自我警示、保持理性的生存手册。”[4](P101)
二、对童话叙事的修正与超越
奥斯丁的小说毕竟不是童话。童话的世界很美好,编织的是一个个超现实的浪漫故事。丑小鸭最终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森林里住着可爱的小矮人,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们历经苦难最终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奥斯丁的故事充满了理性的成分。无论是从人物、情节和结构等方面都表现出对童话模式的修正、解构与超越。
(一)女主人公性格角色的修正
童话故事里女主人公的塑造一般是粗笔勾勒的,“美丽”、“善良”是她们代名词。如果灰姑娘没有善待小动物,表现出其善良的一面,就不会得到仙女的帮助,使她从炉灶边的灰姑娘变成美丽的公主。而如果灰姑娘没有穿上华丽的礼服和水晶鞋参加舞会,就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美貌,从而吸引王子的注意。除此之外,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是模糊的。在男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背景下,童话故事里美丽和善良女主人公形象是男性对理想女性的审美期待和价值评判标准,所以其性格塑造是凝固化的,烘托的是合乎儿童的心理特征和期待的“美德有报”的主题。
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性格角色不再只是用“美丽”与“善良”两词作扁平化处理。她们也不再被动地等待“王子”来拯救。奥斯丁的女主人公同灰姑娘一样处于清贫的环境,但是她们的美貌却已经被淡化,相反女性的智慧被加以重视,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性格教养被加以细致刻画。《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是奥斯丁最喜爱的女主人公。在与达西相遇的第一次舞会中,伊丽莎白就遭遇达西的冷遇。达西冷冷地评价道:“她还可以,但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的心,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7](P12)这一情节安排是对《灰姑娘》故事中舞会情节的颠覆。但是伊丽莎白的言谈举止和聪明才智渐渐虏获了达西的心。她的语言妙趣横生、诙谐幽默,使她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冷场。斯蒂文森评价说:“每当伊丽莎白·班纳特开其金口,他就情不自禁想要跪下来崇拜她。”[8](P82)
其实,奥斯丁的女主人公一个个都拥有非凡的才智品貌,伊丽莎白睿智伶俐、爱玛独立自主、埃莉诺沉着理智、玛丽安活泼浪漫、凯瑟琳活泼单纯、范妮矜持自尊、安妮沉着冷静。她们的形象已经由童话故事里被动、温顺的传统女性形象转变为智慧而富有个性的新女性。
更重要的是,奥斯丁赋予了她的女主角更多的爱情自主权。爱玛的词典里可以有“终身不嫁“的言论:“女人通常都想结婚,我可没这种想法……没有爱情而去改变目前的处境,那才是傻瓜呢。”[9](P73)伊丽莎白对达西第一次傲慢的求婚可以拒绝得理直气壮:“遇到这一类事情,通常的方式是这样的:人家对你一片好心好意,你即使不能给以同样的报答,也得表示一番感激,照人情事理来说,感激之心是应该有的,要是我果真觉得感激,我现在就得向你表示谢意。可惜我没这种感觉。我从来不稀罕你的抬举,何况你抬举我也是十分勉强。我从来不愿意让任何人感到痛苦。纵使惹得别人痛苦,也是根本出于无心,而且我希望很快就会事过境迁。”[7](P216)就连最腼腆温顺的范妮也在拒绝看上去条件很优越的亨利·克劳福德的求婚时也会说出这样的理由:“即使一个男人人人夸奖,但至少会有一个人可能不答应他、不爱他。即使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可爱都集中在他身上,我想,也不应该就认为,他想爱谁谁都一定会答应。”[10](P317)女主人公这些精彩的一言一行对于经济不独立、没有工作机会、没有继承权的18世纪女性来说是一种突破。
奥斯丁这种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和举止的描述是对传统灰姑娘“谦卑、被动”形象的修正与超越,更预示着传统女性价值评判方式的转变,女子在婚姻问题上独立自主的意识亦表露无遗。如果说奥斯丁赋予女主人公的功能是中产阶级少女言行举止和道德的规范范本,那么到小说的尾声,女主人公无不是成长为一个集智慧、冷静、自尊、独立为一体的迷人形象。
(二)情节模式的解构
传统的童话故事一般隐藏着典型的“追寻”原型。在《灰姑娘》中,王子对灰姑娘一见钟情,拿着灰姑娘留下的一只水晶鞋,下令寻找鞋子主人,挨家挨户进行试鞋,最终如愿以偿,以圆满婚姻完成追寻。情节中关于爱情的波折主要体现在王子穷追不舍的坚定和艰辛。
奥斯丁遵循着同样的情节发展线索,却对这个模式进行了解构与重组。奥斯丁的小说亦采用对美满婚姻的“追寻”模式。但是,追寻的主体由男性变成了女性;追寻的目标主要围绕“女主人公的自我完善”;并在这“自我完善”的追寻过程中,不约而同出现了一位“第三者”,干扰着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成长,构成了女主人公寻找爱情道路上最大的波折。
《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没有延续传统童话中的“一见钟情”模式。相反,第三者韦翰的介入还给两人的交往带来危机。伊丽莎白对英俊潇洒、讨人欢心的韦翰第一印象甚好,甚至认为他是她曾经遇见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人了。要不是韦翰本性自私、贪图享乐、挥霍无度,恐怕连伊丽莎白都会被其迷惑。
《理智与情感》中的威洛比亦是通过英雄救美之举,先博得了玛丽安的好感,成为她眼中“能力强、反应快、性情开朗活泼、感情丰富、极富魅力”的形象。[11](P48)后来展现出的放荡不羁、始乱终弃的面貌才使玛丽安从这段热恋中摆脱出来。
《爱玛》中,弗兰克·邱吉尔被认为是海伯利唯一与爱玛般配的对象,也曾赢得了爱玛先入为主的好感,两人一度交往甚密。虽然最后谜底揭开为弗兰克早已订婚在前,这些举动只是把爱玛当做了掩盖真相的挡箭牌,但在爱玛、奈特利先生和读者心理都引起了不小的影响。
奥斯丁的这三部小说中,正是这些男二号成为引导女主人公认识自我的介体。通过“被男二号吸引——加强交往——逐渐认识——男二号本性暴露——女主人公摆脱迷惑”的情节过程,女主人公历经了爱情波折,转变了原本对世界的感性认识,弄清了自己的感情归属,体会到了男主人公的可贵品质,而最终收获到幸福。
在奥斯丁的另三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劝导》中,女主人公虽然对男主人公的感情始终如一,不曾为男二号所动,但是男二号却时时处处被拿出来与男主人公做比较,配合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波三折。《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当擅长辞令、见多识广的亨利·克劳福德向范妮展开追求时,连一家之主托马斯爵士都出面劝说范妮接受求婚,让人不禁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捏把汗,所幸范妮早就看清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性,继续坚持暗暗喜欢和自己有着一样道德追求和价值观的埃德蒙表哥。《诺桑觉寺》中约翰·索普在追求凯瑟琳时,在蒂尔尼将军面前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当追求凯瑟琳成为泡影后,又加油添醋地把凯瑟琳说得一名不文,他的言论使得凯瑟琳和亨利的交往像坐过山车一样被迫从云端掉到谷底。《劝导》中当表面上温文尔雅的男二号艾略特先生开始追求安妮时,马上引起了男主人公不自觉的关注,唤醒了他埋藏心底的爱恋;与此同时,这种对男二号的妒忌也起到了阻碍作用,使得男女主人公在不断迟疑中才逐渐弄明白彼此的心意,最后彼此靠拢。
可见,在奥斯丁的所有小说中,都会有一名男二号成为女主人公们追寻自我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构成了三角的恋爱关系,决定着情节错落起伏的幅度,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由被动等待转而积极选择。通过这种三角关系的引入,奥斯丁解构了童话故事中相对单一的“一见钟情”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追寻”模式。正是通过女主人公对两位男性复杂的认同变化过程,奥斯丁写出的是人性中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凸显出女主人公内心认知和成长的过程。这种对童话故事的改写与颠覆,既丰富了故事情节,又加强了故事叙事。
(三)二元对立模式的超越
在叙事结构上,童话故事总是采用一目了然的二元对立模式——爱和恨、美和丑、善和恶十分鲜明。童话的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被认为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结构概念,是童话最为基本的特征之一,它将抽象概念赋予具体形象,从“善良——丑恶”、“英雄——懦夫”、“仙女——巫婆”等两级对照中加深给读者的印象,升华两级的情感体验。[4](P103)
与童话一样,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也在二元对立的叙述中,反射和引导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中上层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以及对爱情与婚姻的态度。《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的两两对举可以顾名思义。《理智与情感》集中表现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赞赏的是女主人公埃莉诺的既重感情又有理智。《傲慢与偏见》中男主人公带着傲慢,女主人公则有偏见,小说提倡的是克服傲慢与偏见的相处。《曼斯菲尔德花园》对比的是克劳福德小姐的金钱爱情观和范妮所追求的德行相契。还有《爱玛》中爱玛的自负及清醒后的谦逊、《诺桑觉修道院》神秘与现实的世界、《劝导》中迷失与修正的故事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奥斯丁的小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她的人物既不是完美无缺的天使,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妖妇,而是有优点也有瑕疵的人;她的故事中不仅仅有虚荣与真诚、世俗与高雅、磊落与卑鄙、温情与冷漠的对比,更有男女主人公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与爱情的认真思考和道德的完善与成长,是在传统的童话主题上不断深化与超越。奥斯丁曾把自己的创作比作是“两寸象牙上的精心雕琢”,在她精致入微的叙述中,二元对立式的模式并不再停留于表层,而深入到故事的内核。
比较奥斯丁的小说与童话,可以看出奥斯丁借助灰姑娘的原型做跳板,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出“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12](P28)奥斯丁的创作和童话一样,在原型、主题、创作思想上都是传承十八世纪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奥斯丁在创作中通过女主人公们独立特行的爱恋表述和婚姻选择,通过突显第二男主人公在情节构成中的作用,也通过对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提出了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处处流露着其内在渐渐成长的女性意识。
[1]朱虹.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2]Huang Mei.Transforming the Cinderella Dream:From Frances Burney to Charlotte Bronte[M].New Brunswick: Rutgers UP,1990.
[3]卢爱芝,于复选.从《爱玛》看简·奥斯丁小说中的灰姑娘主题[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2(3).
[4]戴岚.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5]卡尔文·斯·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6]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玛甘妮塔·拉斯奇.简·奥斯丁[M].黄美智,陈雅婷,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
[9]简·奥斯丁.爱玛[M].祝庆英,祝文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0]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M].李业一,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7.
[11]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M].黄慧敏,译.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12]简·奥斯丁.诺桑觉寺[M].孙致礼,唐慧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Isomorphism and Deconstruction:On Jane Austen’s Transcendence Over the Narrative Modes of Fairy Tales
BU Ya-yun
(Faculty of Business&Trade,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Huzhou 313000,China)
Jane Austen’s novels and fairy tales have similar story archetypes,theme and creative intention,which reflects the emotions of people living on the margin of society.But different from the fairy tales,Austen’s novels lay more emphasis on the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s in her heroines,and her plots are designed innovatively to subvert the fairytale prototype of the princess chased by the only prince,a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modes are transcended as well.By such innovation in the novels,Austen tends to express her concern about the female identities and status in her time.
Jane Austen’s novels;fairy tales;isomorphism;deconstruction;transcendence
I106.4
:A
:1009-1734(2014)05-0043-05
[责任编辑陈义报]
2014-03-19
2013年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简·奥斯丁小说叙事的传承与创新研究”(FX2013235)成果之一。
步雅芸,副教授,从事英国文学研究。